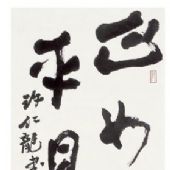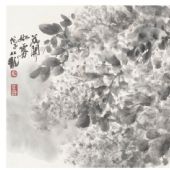感谢命运,使我不期而然地与书画家许公仁龙先生成了同一个村的村民。既同为一村之民,自不免偶有交往;而一经交往,即发现有不少意趣相投之处,可谓神契。近日,许公以其画论《上苑卮言》书稿过我。读后,觉其中许多见解皆深合余心。这里且举一二。
“中国画须靠中国文化入画”
古有绘画六法。许公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提炼出中国画之三法:一曰“神与物游”,二曰“以大观小”,三曰“书法用笔”。此三法者,愚意以为“神与物游”言酝酿,“以大观小”言构图,“书法用笔”言落纸,舍其一即不足为中国画。而此三法背后之根基,则是中国传统文化。
人是什么?古人云“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何为“天地之心”?古人又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朱熹《仁说》)因此,生而为人,即应以天地生育万物的精神为自己之心。如先贤所说:“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朱熹《中庸章句》)“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历无间隔。”(王阳明《与黄勉之第二书》)“古之人,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黄宗羲《黄孚先诗序》)这是中国古代的人生境界,道德境界,同时也正是中国古代的审美境界。郑板桥有言:“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题画》)试想:若无此种境界,岂能有他那些情趣盎然的竹石图?而这就是“神与物游”。
中国画之酝酿,就是酝酿物我一体的生命意象,使形之于心。离开“神与物游”,如何能酝酿出这样的生命意象?也正因为是自由而无意的“游”,所以在构图上是“以大观小”,而不是定点透视。至于“书法用笔”,就更是中国文化的专利了。
总之,“中国画须靠中国文化入画”,舍此即无门可入。
“对景创作,有景而无我,有形而无神”
看了许公的书稿,才知道画中国画还有“对景创作”一说。
按照西方正统观念,世界上只有人有“理性灵魂”,其余万物都没有。而人的“理性灵魂”的主要表现,就是认识与征服自然。所以自然万物只是人的认识与征服的对象,除此之外不可能与人有任何交往。而文艺也是认识,即所谓“求知”:“我们看见那些图像所以感到快感,就因为我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断定它是某一事物。”(亚里士多德《诗学》)于是有了根深蒂固的“模仿说”。显而易见,所谓“对景创作”,就是贯彻“模仿说”。许公云:“对景创作,有景而无我,有形而无神。”是的,“模仿”是为了“求知”,故以绝对客观为原则,何能有我?万物没有“理性”,没有“灵魂”,何得有“神”?而无我、无神,还是中国画吗?
中西文化是两种迥然有别的异质文化。它们之间,是此一特殊与彼一特殊的关系,而不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故尽可相互参取,却无法捏做一团,更不存在谁指导谁的问题。作为各自文化体系中的分支,中西绘画、中西文学等等,亦复如此。我从前的本行是中国文学理论史。当时有不少《文学概论》《文学原理》一类的著作,实际内容都是西方那一套,却自诩为文学的普遍规律。按照一般指导个别的原则,我自应接受它们的指导。这种指导的结果,无非是以西论中,以西绳中,诸如把中国的“感物说”纳入西方的“反映论”之类。面对这种情况,我只能宣布“拒绝指导”。近来见到一部2011年出版的《新编文学理论》,欣喜地发现,面貌大变:全书只略分为“文学与世界”、“文学与作者”等几个部分,而每个部分都分两章,一章讲中国传统文论,一章讲西方文论。值得庆幸,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终于走出了“西方文化中心论”。
许公说,这种“对景创作”的方法,“我花了数年时间才摆脱掉”。他所摆脱掉的,正是绘画领域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不摆脱这种方法,就不会有真正的中国画。
“退避时流,亲近自然,是吾愿也”
2002年,许公为人民大会堂接待大厅作巨幅中国画《万里长城》,受到朝野上下、大众专家一致好评,声名大振。在当今之世,对一个画家而言,此可谓功成名就,到了收获的季节了。从此,类似的作品可以轻而易举地批量出产,名利与荣誉自会源源不断地扑面而来。而许公却于此时毅然告别繁华,回归寂寞,转入了潜心读书、亲近自然的蛰伏生活。他说:“深知自己在文化底蕴和艺术修养等方面,还有很多欠缺,需要迅速补充营养”,故“退避时流,亲近自然,是吾愿也。”
人多以激流勇进为难,而不知激流勇退之尤难也。因为这意味着舍弃:既要舍弃许许多多为常人梦寐以求、而今自己已然到手的东西,安心处约;同时也要舍弃一些自己在艺术创作上得之不易、而今已然驾轻就熟的本领,从头再来。故王阳明尝云:“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非天下大勇者不能”。(《传习录》)许公即具有这样的大勇。
或问:这值得吗?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说来,没有什么值不值的问题,此乃必行之路。沉浸于热闹场中,久而久之,即不为“权力话语”所“规训”,亦难免为市场话语所腐蚀,那就是艺术生命的终结。
如今十多年过去,许公在传统文化方面学养大进,在书画艺术方面亦新境大开。对于他近来的书画作品,以我外行人的眼光自难作出专业性的评论;但我突出地感觉到:比以往更加自由洒脱,也更像、更是中国画了。
许公仁龙先生要我为他这部书画论著写序。我既不能书,也不会画,何敢妄序此书?然则惠我遇许公者,天也!我岂能负天?故不避谫陋,妄言数语,可谓不堪为序之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