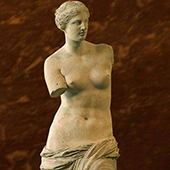对话人:隋建国、刘礼宾
时间:2010年9月14日
地点:隋建国工作室
重新写实
刘:这次的访谈是围绕“写实雕塑”专题展开的,写实风格和你的雕塑创作构成怎样的一种关系?
隋:我的当代艺术作品中只有一部分是属于写实风格的,就是从《中山装》(1997年)到《大提速》(2006年) 之间这段时间创作的作品,并且我的“写实”是解构传统意义上的“写实”概念的。如果不仔细区分,泛泛地说“写实雕塑“,那就什么都说不清了。
刘:不能回避的是,写实主义传统在中央美院雕塑系的教学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你个人的学习经历以及教学过程中,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隋:我的创作中有两类“写实“雕塑,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写实雕塑,比如肖像等;另一类是《中山装》这样的“重新写实”的雕塑。后者我自认为属于当代艺术。
大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批留学生从法国、日本带回西方写实雕塑。但在我看来,那个时候对雕塑的认识是很粗浅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我称之为“集体主义”雕塑阶段,因为这时的雕塑不讲个人艺术态度。民国时期的李金发、刘开渠等雕塑家是比较突出的了,大概就是能做肖像,或者创作主题性雕塑,都没有超出法国的系统。1949年后,社会主义文化把大家都推到一条宽阔的大道上,虽然宽,但是一条道,大家在上面齐步走,同样的目标,共同的审美。我也在这个系统里面创作过,当我还不是一个“当代艺术家”的时候,我就做这样的雕塑。
进入八十年代,我受新潮美术的感召,开始试着脱开社会主义的系统,学院的系统,寻找自己的艺术道路。我当时想借助中国上古传统的老庄和禅宗文化,找到一条能够超越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捷径。八十年代开始有很多人同时走上了这条道路,寻找自己个人的艺术,中国当代艺术由此展开。这里有一个艺术现代性的问题。所谓现代性的实现在个体的人身上,体现为相对于群体性的个体独立。要超越现代主义,现代性是绕不过去的,艺术上同样如此。在这样一种当代艺术的状态下,每一个艺术家必须或者不得不独自面对整个艺术史,不得不一次次地颠覆既有的艺术规则,从中建立起自己的艺术道路。这就是所谓“个人主义”雕塑的阶段,它建立在个人的艺术态度之上,从八十年代持续至今。
我做《中山装》始于1997年。是经过1989至1996年建立起自己的当代艺术坐标之后的进一步实验。通过中山装这类作品的实践,我发现写实雕塑的依据存在悖论:拷贝自然,本来是要拷贝得特别像,就像罗丹说:“要忠实于上帝,忠实于自然”。 但是因为你是用手做,用肉眼看,你不是用机械(比如平面的照相机发明后,可以忠实记录世界,人的肉眼彻底向照相机蛰伏了,认为照相机是最准确的东西),所以你做的不可能那么像。立体的东西复制起来更难,现在刚刚有了立体扫描和立体打印,但是还远远没有普及,立体照相式复制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由于不可能做得完全像,难免会有所背离,有的时候背离远点,有的时候背离得近点(超级写实主义离得就近一点,表现主义离得远一点)。因此人手工做的拷贝与真实自然对象之间的距离就变成了艺术个性的尺度:离得多远,就多有个性。不知不觉间,做不像本身就变成了艺术的根据。当然这是我的个人想法,别人不见得认可。
我把“个性”原则取消了之后,就尽量机械地去做,冷冰冰地去做,不表达个人感受,艺术家的个性、手法都消失不论。用这个方法,从1997年到2005年,七、八年的时间中我制做或者说“重做”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罗丹、非学院式的“重新写实”。
刘:老子曾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西方艺术理论中有些理论家也强调“零度书写”,反对创作中主体情感的介入,尊重语言本身的价值,这和你上面所说的“不介入性”有关。
隋:就像照相中的趣味。当你认真拍照的时候,脑子里不知不觉会有一个审美的要求,会模仿某种流行的照相趣味;而当你随便按下相机快门,或许是并不怎么好的取景,“照相机”本身却跳出来了。
刘:在这个阶段,你有两个原则:第一,你选的东西必须和“你”有关;第二,用一种完全客观化方式将其呈现出来。
隋:对,尽量客观地重做。有时不仅是再做一遍,有的时候放大,有的时候局部改变。像《熊猫垃圾箱》我改变了底座的高度,按照它的梯形不断地往下延展,就变成了新的作品。我还借过《打电话的人》;复制过故宫的镏金狮子;请过农民艺术家来合作。我的这些办法都是为了尽量借别人的手,避免自己的手会忍不住去表现自己。
借助客观性,艺术家的手变成了点金指,一指某物,某物就变成了金子。但点金指永远指向艺术家躲避不过,个人心理上纠缠不休的事物,此即所谓和我有关。而所谓客观化的方法也很重要。“中山装”很多人用过,很早就有几个做版画、画油画的画过,刘建华和展望也都先后用过,但他们用的时候,《中山装》并没有出来。
刘: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隋:他们是用“中山装”作为媒介说别的事情,要表达自己的情绪,表现艺术家自我的感受。正是这些东西把“中山装”给遮蔽了。我的作品则是想呈现“中山装”本身,它就是它,不附加别的东西。它甚至应该成为一面镜子,观者从中看到的只是自身,投入的是自身的经验。
我也是经过几次试验,不断去掉自己的痕迹,最后才找到一个合适的标准。
进入当代
刘:八十年代后期你在中央美术学院上学的时候也处于类似罗丹的表现主义状态。
隋:1986到1989年,我把它算作我艺术发展线索的一个阶段,其实还是“前当代阶段”。
在山东的时候,并没有进入当代艺术状态。我还是想找一个现代艺术的创作方法,于是就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材料实验。但是那时候我没有一个强烈的欲望的自我。现在每个艺术家都有强烈的自我,如果有个人没有那么强烈的自我,反而会比较显眼。我在山东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无我的态,后来我对这个状态不满意。
刘:没受到关注?
隋:不仅是没受到关注的问题,是没有进入当代的创作状态。
到了北京之后,觉得北京太风云激荡了,自己原先那个状态不行,觉得老庄哲学没用了。而且明白:在山东那个状态下做艺术,只是得到了现代主义的形式。虽然你可以追求东方的,中国的特色,但那还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在中国的翻版,或者分支。我不满意的原因主要在这里。
在北京的激荡之下,强烈的主体愿望就出来了。产生了焦虑,对自己有了要求。1986年到1989年这个阶段,焦虑是主要的生存状态。由于你的生存状态是特殊的,于是在这种生存体验下的艺术,一定是独特的。 那个时候生存体验确实不一般。一方面,你的追求跟整个体制不合拍;另一方面,单身来北京读书,举目无亲。再加上读的书也影响你的状态,比如萨特的存在主义。
刘:我觉得你1989年之前处于表现主义状态,把自己的真实状态表现出来就可以了。后来这种热情突然冷却下来,给了你一个回头看自己的机会。你在山艺的时候,去淄博做陶,就想把陶的特性呈现出来。现在你又把石头的特性呈现出来。
隋: 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让我突然间进入了一个特殊的状态。
那年秋天,在远离伤心之地北京的蓟县大山里,因为反省之前盲目的热情与喧嚣,无意之间对坚硬冷漠的石头有了感悟,而且这个“感悟”跟之前所有不痛不痒的感悟完全不同。因为这时候你的心是完全变成了极端状态的一颗心。这个时候你的“心”跟外物碰撞的时候,对物质是有要求的。这个时候给你一团棉花,你会觉得不够硬。只有石头,钢铁之类的才能承载得了你的心。它需要一个高强度高硬度的着力点。
我当时是宁愿把我自己当做一块石头。当然首先得通过劳动把石头转化为自己生命的承载者。这里面还潜藏着一个东西,就是自虐的快感。石头坚硬很难打得动;越打不动,我越要打,一抬头,太阳已经落山了。那个时候我就想避开北京这个烦心的地方,通过身体的劳累减轻精神上的痛苦,安静下来反省自己。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完成了我1989至1996年的第一个当代艺术的阶段。
刘:在当代艺术史的书写中,把你的《中山装》视为当代艺术创作。这个脉络里边,既有杜尚的成份(将现成品直接拿过来予以呈现),也有劳森伯格的成份(波普特征)。
隋:“香港回归”前后,兴起了讨论中国一百年近现代史的热潮,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发现《中山装》的。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真正反省我自己跟“社会主义”,跟“毛主席”的关系。这就和80年代的反思不一样了:以前是群体反思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现在反省的是我自己,以及我自己和社会制度、精神领袖的关系。选择什么表现对象来做作品,出自我的反省需要。
此波普与彼波普有所不同,中国艺术家的心理背景也不同,搞理论研究的人应该深入寻找这个东西背后的根源。
刘:中国的经验和西方还是不一样的。徐冰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他想把革命经验(很多人视其为局限)视为一种可以发掘的经验。
隋:中国艺术家和其他资本主义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家不同,他已经拥有了社会主义这个背景资源,甚至想摆脱都不可能。
刘:除了《中山装》,你后来的作品把毛泽东雕像的典型体征分解开来表现,比如《衣纹研究——右手》、《底座研究》,并且开始和具体空间相关联。
隋:《底座研究》是在左岸空间展出的。一般毛主席雕像高12米,基座是6米。正好左岸空间层高是6米,中间高出来一个天窗,所以还可以有一段腿部放在天窗下面的六米高的基座上,跟环境很协调。但是因为是租的空间,主办方死活不干,说影射太明显(当时正在进行美伊战争,电视上有萨达姆雕像被拉倒的图像,半截腿留在底座上。)。所以很可惜,最后底座上只放了一双鞋,没能与建筑空间达到最紧密的关系。
这件作品让我第一次意识到雕塑可以变成建筑空间的一部分。后来我又做了《祖先》,是一个18米长的草人。作品位于后现代城的一个大空间里面,空间长30多米,里边有三根柱子,柱子插在草人身体里边,与空间的关系就出来了。我开始意识到:和建筑空间发生关系,这里面有很多文章可以做。这就是又一个新的“线索”。
我觉得我1997至2005年那一阶段做艺术的好处是在不断地拓展“线头”。现在我准备收“线头”了。
刘:为什么?
隋:2006年之后,我发现时间不够用了,所以必须收着做,现在我就处于收束的过程中。我要看哪个“线头”最有价值,我才去牵动它,没价值的就不再管它了。
刘:其实是重新认识自我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你好像参加了不少展览。
隋:当时我是在尽量地拓展,所以我那个时候什么展览都参加。因为再小的展览,再差的展览都有具体的环境,而且都有具体的主题。我有那么多线索,总会有一个线索符合这个空间,这个主题。就像广告词说的“总有一款适合你!”(笑)。
1989至1996年是一个特别纯粹的阶段;后来彻底放开了,1997至2005年所谓“波普”时期,我自由地运用后现代的手法,当代艺术语言基本上熟练得差不多了。最终才有06年以后现在的状态。
有人觉得我在1989至1996,1997至2005这两个阶段像两个人。我也在想:为什么会这样?
刘:后来找到答案了吗?
隋:算是找到了。2003年我回青岛。一帮年轻艺术家约我聊天。里面有一个小伙子一直不吱声,后来突然说了一句(那个时候我刚做了《睡觉的毛主席》):“你做《中山装》、《睡觉的毛主席》,这些作品政治性都很强,你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我说:“我是找一个新的方法来做写实雕塑。”他说:“我不是问这个,我是问你的心理状态。”我说:“你觉得呢?”因为我真不清楚我是什么心理状态。他说:“我觉得你好像在证明你是勇敢的,证明自己敢挑战政治禁忌。我这样说你别不高兴,可能其实你胆子很小,你为了证明给别人看(首先证明给自己看),我胆子并不小,所以要这样去做,去挑战这个禁忌。”我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之前还真是没有想过这个动机是怎么来的,我总是从艺术语言的必要性上考虑我的创作动机。”我现在想起这个阶段的创作动机,有点像暗夜里的行路人,在惊恐的环境中,一旦发现任何可怕的东西,比如妖魔鬼怪,往往不是拔腿就逃,反而会本能地越想看清楚带来惊恐的对象。我小时候曾有过类似的经验,把铅笔刀磨快了之后,总是忍不住要去抚摸锋利的刀锋,直到手指被割破流血。也许这是一种共同的经验,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在摩天大厦的屋顶往下看的时候,总有一种想要往下跳的内心呼唤。
其实面对这些禁忌的时候,也并没有觉得需要多少勇气,更多是真情流露。包括我做的《睡觉的毛主席》,其实里边真是说不清到底有多少爱恨情仇。客观上知道可以批评毛泽东的错误,但实际上他的许多思想已经都在我的生活习惯之中。我对毛泽东的感情是最矛盾的。
刘:这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隋:因为从小的灌输,人格已经被毛泽东塑造出来了。虽然后来我是在不断地反省。我跟展望合作过《五大书记》,我们是想塑造一个真正的毛主席,而不是既定意识形态里的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我觉得毛除了公认的功绩,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有不少负面影响,特别是他本人人格上的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对于权力的贪婪;一方面又有自小长期熏陶形成的敬仰之情,虽然其中有很多是制造神话的宣传所致。
挑战了禁忌,所以你得准备好受伤害。我做石头和胶皮的时候,是向内的自我反省与焦虑,自我伤害。做后来这些重新写实作品的时候,倒真好像是要去面对禁忌寻找伤害、承受压力。
回过头来,我自己把1997至2005年这第二阶段的当代艺术实践,看作是与第一阶段相辅相成的一个对应体,一个内向,一个外向,是一种心理的两种表现,分裂的状态。
刘:这种自我反省在很多你的同代艺术家身上是没有的。
传统的系统
隋:我希望能够超越写实雕塑的概念,来理解中国传统。从技术上来说我是一个雕塑家,更大范围意义上我是一个艺术家。我希望把“艺术”变成一个世界观,变成一个人类得以生存于世界之中的,对于世界的看法、对于世界的态度的核心。希望把艺术乃至生活中所有的器物性存在,都视为“雕塑”的范畴。具体的油画、国画、雕塑,甚至建筑师盖的房子,园林师做的园艺和假山,桌子上摆的文房四宝,乃至交通工具,或者所有的工具,它们的器物性存在都可以被雕塑涵盖。
这样的话,艺术可以真正被视为人类实践的核心,其中既有形而上的成分,又有形而下的成分。形而上部分是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如何去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仅是自然界,也包括人类社会自身。一方面是人自己,从一个主体到另一个主体,另一方面就是再扩展到到自然世界。现在除了科学,只有艺术才能为人类担当起面对世界这个责任来。这就是我觉得艺术值得我去投入毕生精力的原因。
前面说的这个是世界观,形而上的部分。但是形而上的观念,一做成作品就进入形而下的存在,不断地做出作品,就不断地进入形而下;而每一个形而下存在都是形而上观念的一个证据,同时又在具体地拓展着形而上的范围。
因此,这世界上每一个东西都是人生存所需要的,比如说这支录音笔,这把茶壶,再到每一件艺术品,都是起这个作用,而且不断地拓展和改进。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巨型的反馈与负反馈的系统,并不断地演化,而且是开放的。我最近刚把这个问题想出一点苗头,这个事情是件大事。不只是去做艺术而已,它还是一件挺重要的关乎人类文化的事情。
刘:你是把雕塑创作视为一种塑造世界的活动。
隋:人要面对世界,没有一个系统是不行的,世界观这种形而上的东西是“系统”,所有器物化的存在也是一个大系统。这样来看,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超越具体形象雕塑的东西,拥有更为广阔范畴上的“雕塑”传统。
器物化的存在是各种各样的,即便是眼前这样一个盘子,或者一个陶瓷的茶壶,我们都把它当做一个文明的积淀来面对。你说它是一个现实形象,还是一个具体物品,还是一个什么工具?都可以。它就像这部手机一样,它是进化过来的,由于在人类的生存过程中需要它,它就得以不断地进化,它的器物化的存在就是在不停地变化。这个进化的过程,任何一个物体的进化过程都是可以像我们面对雕塑这样去面对它。
而且作为器物化的存在系统,雕塑可以成为一个核心。因为这个作用绘画是承担不起来的,这就是你看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说“装置跟雕塑有何不同”,我总是说它们都是“ 雕塑”而已 。我认为只有两种视觉艺术:绘画和雕塑,分别为平面和三维形式。可是平面承担不起这个过程——器物的进化过程,因为绘画是永远止于图像化的存在,作为器物化存在绘画不起作用。但是雕塑作为器物化的存在核心,它是无所不在的。
这样的话,雕塑以及你做的这个关于雕塑的展览就有了和古代中国传统文明联系起来的无数条线索,就不用必须跟外来文化比较了,当然,要比较也可以,没有什么绝对不能比较的。
刘:这一点说得蛮好的,如果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讲,一个艺术家创作状态的获得就是他获得一个看世界的方式。当然这个方式可能有大有小,有的成就很低,有人就比较宏观,比较强大。现在的中国艺术,中国艺术家应该提供怎样的一种东西?如果从小处来讲,是提供一种什么样的艺术语言?或者提供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形式;从大的一方面来讲,是提供一种新的文化价值。你如何看待你这次在《造型》展览上的作品?门口的脚手架也是件“器物”吗?
隋:我真没有把它当成我的作品。我是接受了造型学院的委托,为造型学院做一个精神象征。我原来想给造型学院一百多个老师做一个脚手架构成的长形的架构,把大家都视为建筑的元素,视为建筑工人,因为我们正在建设未来世界。我想把老师们的形象全放到架子上面。结果在艺术委员会上没有通过。我说如果不放照片,就只有把这个架构竖起来。
刘: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塔特林纪念碑,并且这件作品使美术馆处于“未完成”状态。你以往的“创作”好像很少为集体而做。你怎么看集体主义?
隋:不是说原来的集体主义意识及其艺术形式没有价值,它其实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很独特的一个文化状态。当然,其它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也有过类似的艺术,大家互相影响又有各自的背景和特色。放大一点说是人类自己进行的一次规模宏大的一次文化试验,人类历史上可能再也无法重复。但也可能在中国容易出现这个东西,即便是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这个东西也会出来。它跟中国儒家传统有关系。同样的一俩代人,比如说在东南亚,或者日本,韩国,同样是留法回来的这几代人,他们去的时候接受的就是个性表达类型的教育,回来的时候虽然还是进行个性表达,但这个“个性”跟西方文化意义上的“个性“还是有差别的。中国艺术家(包括我看你写的《民国时期雕塑研究》中的雕塑家),多是这个状态。现代性需要有一个消化过程,自我真要渗透进去,是需要历练的。从这一点上来说,社会主义甚至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帮助了中国艺术脱胎换骨,因为它把集体化推到了极端。推到极端后,才会有新的文化形态的出现,导致彻底改变。要不然也许这个东西还需要更漫长的过程。
集体和个人这两个线索搞清楚了。再把艺术的形而上、形而下的线索跟中国最早的“根”穿起来,就有意思了。
身体与空间
刘:上面的聊天其实潜藏了你一直以来对“心”的追问。
隋:王阳明所说的物与心,物就是世界,心就是面对这个世界的人。其实按照现在哲学的发展,“心”包含的东西太多了。心跟自然世界跟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也许在佛教里边早已经阐述过,只是我们不清楚而已。因为我感觉佛教的逻辑是非常严密的。我们今天要用什么概念套当年的什么概念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谈艺术,谈艺术理论,上升到美学层面,最终可能会介入到哲学层面,这里面藏着很多的不对应。
这些年西方的很多哲学家对艺术感兴趣,或许他们觉得只有通过艺术品才能阐释他的哲学概念,这可能跟宗教衰落,审美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日益重要有关系?问题在于:艺术能不能上升到哲学层面?我现在做艺术的时候,是越来越希望做到单纯。
要说起“心”的概念,如果不仔细厘清,把它等同于原来的所谓“意识”,就容易简单化。“心”可以包含很多意识的成分,但另外又可以作为“人格”的存在看待。“心”还可以落实到身体上,因为“身体”既包含了意识,也包含了无意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与“人格”相对,身体本身还可以被看做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想这个问题的人不是我一个人。
刘:还有谁呢?
隋:英国雕塑家安东尼高姆里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当人问他为什么一开始就用自己的身体做艺术时,他回答说:“作为一个雕塑家,你第一个要面对的材料就是你自己的身体。根本不用去再模仿另外一个身体,你的肉体已经是你要面对的第一个物质和空间。”他说的很有意思。五、六年前他来北京做“亚洲土地”的时候,在长征空间有一个专门的研讨会。邱志杰故意逗他说高姆里做的是写实雕塑,他死活不干,说:“我不是写实雕塑,写实雕塑是纳粹主义的,你们社会主义的雕塑才是写实雕塑。”他急了说:“我不明白,像隋建国这样的艺术家居然还在美院教写实雕塑!我做得不是写实雕塑!”
那个时候如果我有这个概念,就会帮他说话,一个雕塑家,首先运用的第一手材料就是自己的身体。还可以进行进一步地分析:因为人的身体虽然和人的意识、人的神经系统有关系,但是这中间还有好几个不同的层面——首先,作为“人格”存在的人,其实是不完全受身体限制的,比如你宁愿牺牲一条腿也要保全你的身体,因为人格虽然似乎是居住在身体里面的,但你的人格不会因为一条腿被砍掉了,就缺一块。但身体的完全死亡就会导致人格的彻底消失。然后还有“意识”,意识是处于人格、身体之间的东西,人格通过意识来指挥身体。身体接受了外界的刺激,又通过意识和无意识最终影响到人格。
尽管人格非常独立,但人格也会不知不觉地被身体里边的某些基本欲望控制着,这就是无意识和潜意识或者下意识,作为人格的人自己都不知道。
高姆里说身体是人的居所,还是挺有意思的见解。他说:“身体是人暂时居住的空间,就像身体要暂时居住在房子的空间里一样,而房屋空间之外还有城市这样的空间。”再往下推应该还有山川以及天地等可以系列推演的空间层面。如果这样来看人格、意识和身体与空间的关系,其实是达到了哲学层面。这可能跟他学过哲学,更与他在印度呆过有关。
刘: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触觉是不是一个充分理由?》,可能朦朦胧胧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时下中国,视觉好像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更近一些。但我一直没有做更深入的研究。这次的《雕塑》展,强调“塑”和“雕”的手工性以及纯粹性,也和你所说的身体有关系。
隋:找到一个线索往往会导致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经过弗洛伊德、拉康、海德格尔等人的深入挖掘之后,现在对人、社会、身体、艺术的看法其实比以前复杂得多,“身体”甚至成为了一个特别核心的东西。我在自己的实践中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后来做了卓越空间的《个人意志的“放大器”》那件作品。
刘:那个作品我专门去看了,很好的作品。
隋:那个作品做出来之后,大家说好,但谁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好。然后就问我,我也说不出来(笑)。开幕式之后吃饭,孙原说“老隋这个真棒!”顾振清故意挑衅说:“你这个不就是放大法吗!”我说:“你说这是放大法也行,但是我这个放大,放大的不是形象,我请孙原替我回答。”因为我也没法再说,当时我也说不清楚。记得博洛夫斯基正巧来北京,看了展览后也说好,问他好在哪里,他也说不清楚。
过后我自己想,其实这件作品里的放大,放大的是我身体运动的轨迹。我当时无意坚持泥塑的原作,就是要给观众一个现场塑造的感觉。《中山装》的写实方式使我躲开了罗丹的笼罩。而卓越空间这组作品,其实是通过一次纯粹的泥塑行为,把我的罗丹情节彻底克服了。罗丹晚年作品做得最精彩,他原本就近视,晚年视觉就更不行了,其实更多凭感觉去做雕塑,看不清就去摸模特,借助触觉。他的晚年泥塑的做法,强调了触觉,但没有被更多的人了解。
刘:中国的书法和身体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写书法的姿势有时候很像练习武功。
隋:是有关系。我是闭着眼做《个人意志的“放大器”》的小泥稿。闭着眼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排除意识的参与,靠得是下意识,或者是潜意识在起作用。我想把我以前对雕塑的认识,所有现代主义、古典现实主义的遗产全部抛开,剩下的只是原始的身体接触。
书法是贵在天天写,把有意识的控制累积在无意识之中去实现。有意识者,人的境界;无意识者,造化的境界。造化之力其实已包含了人为之力,但这造化之力竟然是借人的身手来实现的。
刘:最近写了一篇文章——《王迈对关键词的个人理解》。我觉得艺术家有很多工作,一段时期他在处理一个问题。
隋:一般是这样。只要找到一个关键词,解释透了,前后线索,艺术史关系一下子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