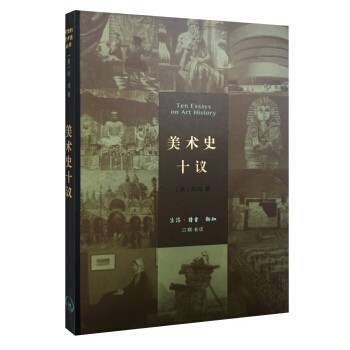
【图书信息】
作者:[美]巫鸿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2008
定价:26.00元
ISBN:9787108028723
【内容简介】
“美术史”是一个问题吗?随着现代社会的成形,美术史作为人文学科的一支新军,也得以在人类最近的历史时期当中萌芽并成熟。但是,在著名美术史学者巫鸿的眼光中,这一广受尊重、日益重要的学科本身仍然是一个年轻的问题,其相关讨论还远远没有充分展开。在《读书》杂志所开的专栏“美术纵横”,巫鸿发表了十篇文章,就美术史何以成为问题、如何拓展其思考的路径、这一问题所置身的波澜壮阔的当代人文场景等等,提纲挈领地阐述了个人的见解。本书为这些专栏文章的部分汇辑。
【作者介绍】
巫鸿,早年任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硕士。1980到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此后在哈佛大学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同年受聘主持芝加哥大学亚洲艺术的教学、研究项目,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2002年建立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同年兼任该校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
巫鸿的著作包括对中国古代、现代艺术及美术史理论和方法论的多项研究。其著作《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获该年全美亚洲学年会最佳著作奖。《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被《选择》杂志评为1996年杰出学术出版物,进而被《艺术论坛》列为20世纪90年代最有意义的艺术学著作之一。《重屏:中国绘画的媒介和表现》获全美最佳美术史著作提名。其参与编写的重要著作包括《中国绘画三千年》(1997)、《剑桥中国先秦史》(1999)等。巫鸿多次回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客座讲学,发起“汉唐之间”中国古代美术史、考古学研究系列国际讨论会,并主编三册论文集。
【目录】
一、代序:“美术”小议
二、图像的转译与美术的释读
三、美术史与美术馆
四、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五、重构中的美术史
六、“开”与“合”的驰骋
七、“墓葬”:美术史学科更新的一个案例
八、“经典作品”与美术史写作
九、美术史的形状
十、“纪念碑性”的回顾
【序言导读】
这本小册子所收的是我在2006到2007两年中为《读书》杂志“美术纵横”专栏所撰写的十篇文章。在应《读书》之邀开设那个专栏的时候,我感到首先有责任向读者说明它的内容。因此第一篇的目的便是开宗明义,正好借用作本书的小序。顾名思义,"纵横”是全方位的意思:经为纵,纬为横。此处又引申为时空两个轴线:纵指历史的发展,横指地域的延伸。但这个专栏的目的绝不在于对美术史进行时间和地域的系统整理,而更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纵横驰骋,惟意所之”的领域。每篇短文的主题或古或今,或近或远,或宏观或微观,从多种视角引出对美术史的反思和想象。
比较难于解释的倒是“美术”这个常见的字眼。实际上,我对选择这个词作为专栏的标题踌躇再三,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美术”一语是近代的舶来品,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和含义,是否能够用来概括中国传统艺术实在值得重新考虑。比如说古代汉语中的“美”可以形容食品、人物(主要是女性,但也可以是男性)、德行以至于政治,但却很少用于表彰艺术作品。宋元以后的主流文人画更是反对绘画的感官吸引力,其主旨与对视觉美的追求可说是背道而驰。但是当“美术”这个词从西方通过日本纳入中国语言之后,它马上给艺术创作规定了一套新的规则和目的。如画家胡佩衡就在20世纪初期写道:“而所谓美术者,则固以传美为事。”(《美术之势力》,载于《绘学杂志》)。鲁迅在1913年作《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文中第一句话就是:“美术为词,中国古所不道,此之所用,译自英之爱忒(Art)。”在说明了西方文化,特别是柏拉图美学中“爱忒"的含义之后,他指出美术足以辅翼道德、救援经济等种种用途,进而提出弘扬公共美术教育、保护美术遗址、促进美术研究等一系列主张。在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及其同志在近百年前对美术的鼓吹,包括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号召,都是他们所大力推倡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弘扬西学、改革陈规。陈独秀和吕徵在《新青年》杂志上以《美术革命》为题展开对话时,陈特别提出这场革命的对象是传统中国画风:“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指清代以降在画坛上占正统地位的四王画派)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因此当“美术”被引进的时候,这个概念有着非常明确的政治性和“现代性”。虽然时过境迁,这个词终于成为现代汉语中对古往今来所有艺术作品的泛称,但其意义变化的过程还没有被认真清理,而论者却已经把古代中国艺术的全发展描述成为一部“美的历程”。
我之犹豫使用“美术”的第二个原因关系到美术史的范围和内涵。实际上,这个学科即使在西方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固定的和“科学”的定义。欧洲传统美术史研究以绘画和雕塑为大宗,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主义学派深受进化论解释模式的影响,把艺术形式本身的发展演变,以及艺术家对美和完善的追求作为研究和说明的主要对象。但是这种学术取向在近二三十年来受到新代美术史家的不断批评,而最有力的挑战则是来自美术史学史,即对美术史自身发展过程的审视。一些学者相当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学科的不断变化着的内涵包括研究的对象和问题、对材料的分类和所采用的分析模式实际上都是不同时期与地区的特定历史现象,和该时期与地区的文化、政治、社会及意识形态密切联系。根据这种理解,甚至“美术”(fine arts)和“艺术家”(artist)这些基本概念也都必然是特定时期的发明,美术史学科的产生又是奠基于这些概念上的进一步发展。把这个理论拿到中国历史中检验一下,找们大致可以说,为观赏而创作的艺术品和创作这类作品的艺术家均出现于魏晋时期;在此之前的青铜、玉器和画像等作品首先是为礼仪和实用目的制作的,其作者则大多是无名工匠。虽然这些作品在晚近历史中获得了重要的商业和美术价值,但这些价值均为后代的附加和转化。
这种把美术史“历史化”的努力可以被看成是对传统美术史的解构,但其结果却并没有导致这门学科的消失或缩小,而是出乎意料地引起了它的迅速膨胀。换言之,新一代的学者们并没有退入被重新定义后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缩小范围,而是把更大量“非美术”的视觉材料纳入以往美术史的神圣场地,其结果是任何与形象(image)有关的现象甚至是日常服饰和商业广告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对象。以我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美术史系为例,目前的十几名教授中只有一两位仍继续专攻往日美术史中赫赫有名的大师和杰作,其他人的研究则是包罗万象,从教堂仪式和朝圣者的经验,到光学仪器的发明所引起的视觉行为的变化,从早期电影与游乐场中活动布景的关系,到美术馆陈列方式所引起的绘画风格的改变,从书籍、图片以至钞票的印刷,到文人、艺术家、商人、官僚组成的沙龙,从欧洲中世纪绘画中花草的医学价值,到现代法院建筑的权威形象。这些研究题目不再来源于传统的艺术分类;对它们的选择往往取决于研究者对更广泛的人文、社会及政治问题的兴趣。因此这些题目从本质上米说必然是“跨学科”的,其长处在于不断和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互动,对美术史以外的研究领域提供材料和施加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美术史在西方学术中地位迅速提高的原因)。但是对学科的跨越也必然造成美术史本身的危机。研究者的身份日益模糊:不但美术史家越来越像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宗教学家甚至自然科学家,而且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和自然科学史家也越来越多地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视觉形象,有的甚至改行成为美术史家。在这一系列动荡和变化之中,“美术史”这个名词变得越来越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含义。悲观者谈到学科的死亡,谈到“美术史”堕落成职业代号。但是从积极的方向想,也可能今日的美术史代表了一种新的学科概念:不再奠基于严格的材料划分和专业分析方法之上,它成为了一个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各种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的交汇之地和互动场所。
所以当我试图给这个专栏起名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找到一个新词,以概括这些虽然目前包括在美术史研究之内但又不能被“美术史”这个传统名称包含的内容。首先浮现的一种可能性是用“视觉文化”取而代之,这也是近年来美国美术史界的一个辩论焦点:一些学者认为视觉文化这个概念可以扩展美术史的范围和含义,更多学者则认为二者虽有重合之处但基本属于两个不同学术领域(此派学者认为文化研究和人类学关系密切,强调集合性人类行为.而美术史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同时重视潮流和艺术家个人及其作品)。我虽然不太同意第一种看法,但与第二种学者的论点也不尽相同。对我来说,正如“美术”的概念一样,当代西方美术史研究中对“视觉”的强烈兴趣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与架上绘画的产生、美术馆的普及以及心理分析在人文学科中的强烈影响息息相关。架上绘画(其在中国的对应物足独立的卷轴画)是为了观看而创造的艺术形式。在这种形式产生以前甚至以后,无数艺术品的首要目的并不是被实际观看和欣赏:欧洲的大教堂高耸入云,教堂内部天顶上的雕像和画像虽然极其美妙,但从地面上几不可见。我们今日可以在精致的画册中仔细欣赏敦煌石窟中的辉煌辟画,但是在千年以前的点点烛光之下,进香者能够看到的只是烛光所及的隐约一片。中国的墓葬艺术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虽然墓中的壁画、雕塑和器物可以在入葬礼仪过程中被人看到,但一旦墓门关闭,它们的观者就只能是想象中的死者灵魂。如果把所有这些作品都称作“视觉文化”的话,那就很可能会犯把三代礼器和秦汉画像都笼统看作是“精英美术"(finearts)的同样错误,用一种后起的概念”框架“早期的制作。实际上,足够的证据说明古人在创造佛教艺术和墓葬艺术时所遵循的恰恰不是“视觉”这个概念。检阅敦煌的功德记,造窟者所强调的是“制作”而非“观看”,因为只有通过制作他们才能积累功德。而墓室从先秦就被称为“藏”,而藏的意义是“欲人之弗得见也。”(《礼记棺分》)。
一旦排除了“视觉文化”,我也考虑了是否能够用“图像”一词代替专栏标题中的“美术”。这个词的好处是它出自中国传统语汇,至少从汉代起就具有了和英文词(image)类似的含义,指对人物形象的复制或再现。有关例证见于《论衡·雷虚》和《后汉书·叔先雄传》等文献,3世纪的卫操说得更明白简洁:“刊石纪功,图像存形。”(《桓帝功德颂碑》)把图像和文字当作两种记录现实的基本手段。但遗憾的是“图像”这个词也有两个重要局限,使得它既不能反映今日美术史研究的内涵,也无法囊括我所希望在这个专栏里讨论的内容。第一个局限是根据其原始定义,“图像”或image所指的主要是对现实的再现,因此适合于指涉具有写实风格的绘画和雕塑。但是当代美术史的研究对象远远不止艺术再现,而是包括了大量非再现类型的形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说传统美术史研究肖像画,那么今日的美术史家也会去研究肖像所再现的人物本身:他们的服饰、姿态和举止都构成了现实中的视觉表现。即使是研究肖像画,今日的美术史家也不再仅仅考虑画家的风格和流派,而会提出订画的意图、陈列的方式、与历史和记忆的关系等种种图像之外的问题。
“图像”一词的另一个局限是它对艺术作品物质性的拒绝。这种拒绝实际上是传统美术史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兴趣:欧洲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绘画发展常被表述为绘画形象对其承载物的征服,把一堵墙壁或一幅画布转化为一扇通向一个幻想世界的窗户。传统中国书画研究中对笔墨的强调具有同样的作用:鉴赏家越是把笔墨作为欣赏和分析的对象,绘画形象也就愈趋独立,脱离承载它的卷轴或册页。今日美术史中的一个重要发展可以说是反此道而行之:由于研究的范围即不断超越对风格和图像的分析,美术史家也越来越重视艺术品的物质性,包括媒材、尺寸、材料、地点等一系列特征。这种兴趣的原因很清楚:只有通过研究这些特征他们才能判定艺术品的使用、观赏和流通,进而决定它们的社会性以及精神、文化和经济的价值。
因此,我最后还是回到了“美术纵横”,但是希望这里所叙述的思考过程为我将要谈的“美术”做出了一个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