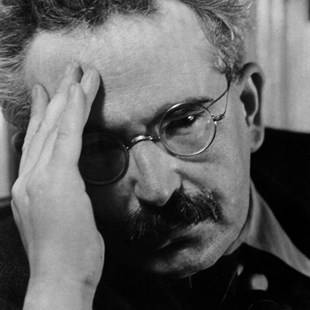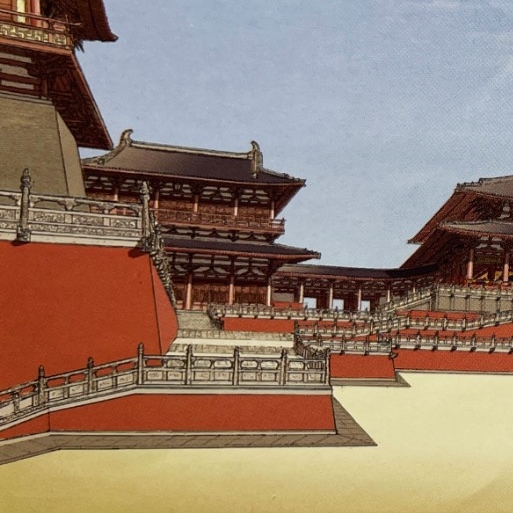试图逃避当前艺术批评的迷雾,跑出去呼吸清新的、确认的空气,是充满诱惑的事情。当然,每个人关于哪里能找到这样的气氛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参与《十月》(October)杂志圆桌会议的人想要更多地关注 严谨而又有理论性的成熟批评,以及“批评话语的复杂层次”。另一些人则希望艺术批评家们有规则、规范、理论,或者至少有一些共同的关注点。有人哀叹说, 21世纪没有引导性的声音——哪怕是一个可以引导我们走出日趋衰落的多元主义迷宫的声音。呼吁对艺术批评进行改革的那些报纸通常是抨击术语,提倡用简明的观念。保守派批评家想要提升艺术的道德目的。克雷默(Kramer)希望引入一些老派的学科和严格的标准从而进行“区分”。报纸批评家们有时也想通过取消批评与市场的联系来改革艺术批评。
我认为事情要复杂得多。在当前的批评状态中发现问题的想法是由历史本身决定的。为什么《十月》杂志 要在2001年秋举办一个批评的圆桌会议?这些会议文章大部分没有发表。为什么以“艺术批评发生了什么?”为标题的文章在2003年春天出现?理解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浮出水面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在驾驭历史思维的潮流,而我们只是断断续续地意识到这些潮流。对各种呼吁进行批评改革的原因的思考,有助于揭示那些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往往是来自于对过去特定时刻的怀念。让我试着用七个增加长度和难度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这些并不是对应艺术批评的七个头部,而是一旦你开始思考这七点,你就很难停下来。)
1.批评应该通过改革回归到那种非政治性的形式主义活力的黄金时代。在《罗杰·弗莱读本》( A Roger Fry Reader)一书中,美术史家克里斯多夫·里德 (Christopher Reed)指出,因为弗莱(Roger Fry)具有复杂性,“与权威的反传统关系”,以及“社会使命感”,弗莱可以被解读为是一位“后现代”的批评家。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写了一篇像往常一样不耐烦的批评文章,声称里德的观点是不可行和错误的;克莱默认为这是后现代“无视历史”的典型产物。替代里德(Christopher Reed)的版本,克莱默想要一个深思熟虑但又保守的弗莱,而不是一个像“前卫燃烧弹”的弗莱。克莱默不喜欢受到政治影响的艺术批评,这促使他强调弗莱有兴趣在“生活之外的领域”中找到艺术法则(里德用这一短语来提醒读者,弗莱所做的并非全部)。没有什么能阻止弗莱从每一代新人中重生:那是历史接受的本质。然而克莱默的弗莱是克莱默的“前卫”语言:一位杰出的形式主义者,他了解并尊重过去的艺术史,并且不害怕提出“生活之外的领域”。显然,克莱默的争论是出于怀旧。他想要的是他想象的事物曾经的样子,而这并不是当代艺术批评的合理模式。
2.批评缺乏一种强有力的声音。1973年,既是艺术家又是美术史家的昆汀·贝尔(Quentin Bell)用与我一开始说的同样的话,哀叹权威艺术批评家的衰落:“尽管用出版商的话来说,艺术文学正在蓬勃发展,但在某一方面遭受了损失。”贝尔思念的是那种批评家,他可以是一个“审查员”和为当代而辩护的批评家,就像狄德罗(Diderot)、波德莱尔(Baudelaire)、拉斯金 (Ruskin)或者罗杰·弗莱那样的人。为什么现在的艺术界没有这样的“大学者”?贝尔认为这就是“现代艺术的特征”,它很难被讨论,或许是高质量的插图的传播消除了描述的必要性。不幸的是,对于贝尔的论点而言, 批评的历史表明,在瓦萨里之后的几十年里,甚至可能 是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缺乏强有力的批评声音。在温克尔曼(Winckelman)之前,批评的声音很弱,而且很分散。正如托马斯·达科斯塔·考夫曼(Thomas DaCosta Kaufmann)所说的那样。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争论说,在狄德罗之后,批评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在波德莱尔之后,出现了许多有趣的批评家,其 中包括泰奥菲尔·托雷(Theophile Thoré)、欧内斯特·切斯瑙(Ernest Chesneau)、朱尔斯·卡斯塔纳里(Jules Castagnary)、爱德蒙·杜兰蒂(Edmond Duranty)、费利克斯·费内翁(Felix Feneon)或者阿尔伯特·奥里尔(Albert Aurier),但没有一个像波德莱尔(Baudelaire)那样对现代主义如此重要。在布鲁姆斯伯里派(Bloomsbury)和格林伯格(Greenberg)之前,批评的声音可以说是微弱的。我们目前没有先知,但这并没有对我们产生不良的影响。贝尔的抱怨是怀旧的另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主要是指布鲁姆斯伯里派的过去。
3.批评需要系统的概念和规则。在一些观察家看来,批评简直就是一团糟。在20世纪40年代,美学家赫尔穆特·亨格福德(Helmut Hungerford)想要把绘画按“类别”进行分类,并制定出和每个类别相关的标准,如组织、整合和技巧。在他固执的理性主义背后,我读到了他对形式分析命运的焦虑感。亨格福德的标准崩溃了,尽管他试图通过在类别和标准中提出“一致性”的附加标准来支撑这些标准。在我看来,亨格福德现在已经完全被遗忘了。也许艺术批评不能在逻辑上进行改革,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没有符合规则的结构。艺术批评长期以来在学术上都是一个混血儿,它从其他领域(崇高与美丽、判断与模仿、凝视与景观)借用所需的东西。它从未一以贯之地运用哲学的概念,而且,希望它 将来会做到这一点也是毫无意义的。
4.批评必须变得更加理论化。也许,可以稍微降低一下标准,艺术批评应当运用共享的理论兴趣,不管它们来自哪个领域。影评家安妮特·迈克尔逊(Annette Michelson)在一篇关于保琳·凯尔(Pauline Kael)的精彩文章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她把凯尔和安伯托·艾柯 (Umberto Eco)(他写了一篇关于《卡萨布兰卡》的文章)进行了比较,认为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她说, 艾柯确信“激励和支持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将有利于交流”。迈克尔逊认为,凯尔“对她毕生作品主题理论化的顽固抵抗,抑制了她用品位和厌恶之外的其他术语来解释电影的影响的能力。”随着岁月的流逝,凯尔 “不再更新她的知识资本,而是承认并从庞大的集体努力取得的成就中受益”。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表达观点的方式:与这一代的其他人一样,成为概念和理论工具宝库的一部分是至关重要的,即使他们只在未使用的资本形式中进入工作。我发现很难反驳这一点:它不是教条主义,也不是由对早期完美激情和雄辩状态的怀旧支撑起来的。我会在最后有更多的说明。
5.批评应当是严肃的、多层面的和严谨的。这一呼吁或多或少是2011年《十月》圆桌会议上的共识,它有一个特殊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与《艺术论坛》有关的批评家,主要是从1962年《艺术论坛》成立至 1967年左右(这一时期)。这些批评家包括卡特·雷特克里夫(Carter Ratcliff)、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约翰·卡普兰斯(John Coplans)、马克斯·科兹洛夫(Max Kozloff)、芭芭拉·罗斯(Barbara Rose)、 彼得·普拉根斯(Peter Plagens)、沃尔特·达比·班 那德(Walter Darby Bannard)、菲尔·莱德(Phil Leider)、安妮特·米歇尔松(Annette Michelson) 等。还有一些人属于一个松散的并且基本上分裂的群体,尽管如此,他们共享了一种艺术批评新的严肃目标。艾米·纽曼(Amy Newman)的访谈集《挑战艺术:艺术论坛(1962-1974)》( Challenging Art: Artforum 1962-1974)是理解该群体难以捉摸的批评意识的一个很好的来源。在《挑战艺术》一书中,约翰·科普兰斯 (John Coplans)认为,这股致力于分析批评的浪潮间接地来自侨居在外的德国学者,尤其是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尽管事实上,有几位艺术批 评家的职业生涯始于对像悉尼·弗里德伯格(Sydney Freedberg)等美术史家作品的批判。科普兰斯指出,美国早期唯一的严肃的艺术批评典范就是《艺术杂志》( The Magazine of Art),特别是当罗伯特·戈德沃特(Robert Goldwater)在1947年担任杂志主编时。他说,《艺术杂志》“完全反对法国的模式”,那种被认为诗人的传统模式。纽曼(Amy Newman)采访的一些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诗人和评论家卡特·拉特克利夫(Carter Ratcliff)回忆说,一些诗人-评论家仍然对“私人历史、个人历史”感兴趣,而另一些人,尤其是《艺术论坛》群体的批评家,他们“试图建立一些合理的方案,一份历史示意图”,从而将新艺术放入其中。“就这样,”他总结道,“他们就能在历史发生的时候正确地追踪历史。”在同一本书中,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区分了《艺术论坛》式的批评和典型的法国“美女语言”式的写作,“诗人会为艺术家撰写充满感情的目录序言”。她说,发表在 《艺术论坛》上的批评文章要归功于英美新批评,这种批评“涉及到一种文本分析,在这种分析中,你要对你面前的文本作出陈述,这些陈述必须是可证实的。你无需介绍关于艺术家的传记或者历史,它实际上仅限于页面上的内容,因此任何读者完全有能力查看你对该作品的评价”。克劳斯说,除了格林伯格,她对西德尼·詹尼斯(Sidney Janis)、托马斯·赫斯(Thomas Hess)、多尔·阿什顿(Dore Ashton)和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等用英语写作的艺术批评家的“观点的模糊性和不可实证性感到非常沮丧”,他们所写的任何内容都没有让她感到是“确凿的、可以证实的”。同样,弗里德也提到赫斯和其他人“所有那些夸张的写作”(Fustian,一个非常尖锐的词,通常用来形容羊毛织物,不仅意味着夸张和膨胀,而且因此也毫无价值)。科普兰斯说,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伦敦唯一有趣的批评家是“劳伦斯·阿莱塞(Lawrence Alloway)与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他们就超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罗伯特·罗森布鲁姆(Robert Rosenblum)在《艺术论坛》上总结了这一情况,他回顾了马克斯·科兹洛夫(Max Kozloff)撰写的一篇题为“威尼斯艺术与佛罗伦萨批评”(1967年12月)的文章。“我喜欢这个标题,”罗森布鲁姆回忆说,因为 “它指出了《艺术论坛》经典写作的一个问题,即它是佛罗伦萨风格的,它是知识分子那种干巴巴的,从来没有真正符合观看艺术的那种感官愉悦感”。撇开罗森布鲁姆的特殊观点不谈(他的写作在这些术语中是出了名的纯粹),他用佛罗伦萨风格和威尼斯风格的比喻是准确的:《艺术论坛》以及晚些时候的《十月》杂志,代表了艺术批评是严谨精确的写作,是对各种各样浮夸写作的反对。
所有这些都是“严肃的批评”将意味着所有的基础。自1976年以来,它还体现在《十月》杂志,以及托马斯·克劳(Thomas Crow)、托马斯·麦克维利 (Thomas McEvilley)以及许多其他作者在不同场合撰写的论文作为例证。要求回归到严肃的、多层面的和严谨的批评,要归功于《艺术论坛》及其后继者所提供的批评模式。反过来,这也意味着,我们有必要问一下:重新唤起那些特定的承诺感、可验证性和知性主义是否有意义?在我看来,唯一站得住脚的答案是,这样的价值观不再适合21世纪初的艺术。在《艺术论坛》的讨论中,智力劳动、困难和挑战的隐喻反复出现,从格林伯格开始:当作品是枯燥的、坚硬的、顽固的、不可分割的……时候,作品就是好的。很难想象这些价值观是如何被转换到当下的,即使它们是,也很难想象它们在现在还能如何使用。
6.批评应该成为对判断的反思,而不是对判断的炫耀。这就是罗莎琳·克劳斯在1971年提出的观点,并且在1985年又再次提出。主要是在学术写作中,批评在接受史和制度批判中付诸实践。如果你把艺术世界想象成一个由制度和权力关系构成的矩阵,那么像“质量” 或“价值”这样的词就没有直接的意义:它们是由艺术界的分工所决定的,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制作,这目的包括学术权力和市场价值。如果你对接受史感兴趣,那么艺术界的硬仗就成了历史趣味的对象。你会想知道产生对“质量”或“价值”这样的词感兴趣的历史上下文, 而你的兴趣将是纯粹的历史,甚至是语言学的——你对结果的投入不会比昆虫学家观察一个蚁族与另一个蚁族之间的斗争更多。即使是制度批评所提供的解释也会受到接受史的影响:制度批评的理念始于20世纪80年代, 并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它对“质量”或“价值”等词的解释将有分量,但在它之前、之后或之外,它们就没有分量了。
制度批评和接受史所面临的问题是当下。我们生活在其中并作出判断。当我们评判当代艺术时,我们会采用我们相信的概念,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评判。对于一个实践接受史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难题。这样的批评家会敏锐地意识到,当下还没有概念诞生。用来判断艺术的概念必须有它们自己的历史,一旦这些历史变得显而易见,就不可能像它们曾经所要求的那些批评家们全心全意地去相信这些概念。如果像格林伯格这样的人物已经远远退居过去,以至于他的论述成为历史分析的对象,那就意味着当代艺术中发挥作用的概念与他已经完全无关。如果它们不是——如果格林伯格对“扁平”“抽象”“庸俗”和“前卫”等词的感觉仍在当下回响——那么对当代艺术的评价就会变得非常成问题。 毕竟,怎么可能用那些不再可信的、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标准来评判一件当下的作品呢?当所有的概念都属于过去的批评家时,批评就变成了编年史,而判断变成了对过去判断的沉思。当下沉浸于历史之中,并最终被历史所淹没。
这些都是艺术批评的难点,我已经尽量阐明了它们。据我所知,像布洛赫(Buhloh)这样的批评家,他们进行制度批评和接受史的实践,并不认为对日常判断的交汇和中立的立场是有问题的:像每个人一样,布洛赫在遇到新作品时就作出评判,他把老作品理解为他们那个时代对话的产物。作为给艺术批评开的处方,转向对判断的反思一直是这个“病的解决(方案)”(ill resolved),尤其是当它的目标是取代艺术批评的时候。
7.评论家至少应该偶尔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听起来是有道理的,也是必然的:这是最起码的要求。然而,这恰恰是当代批评中最有争议的问题。让我用两位截然相反的批评家之间的对比来解释这个问题。第一位是杰瑞· 萨尔茨(Jerry Saltz),目前是报纸《乡村之声》( Village Voice)的艺术批评家;第二位是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他曾经是《艺术论坛》( Artforum)的领军人物。他们两位我都认识,我几乎想不出还有哪两个截然相反的人了。迈克尔·弗雷德,正如每个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能证明的那样,绝对且坚定不移地忠实于他在20 世纪60年代提出的某些理论。如他所描绘的现代主义的方案;一种不可或缺的,充分了解艺术史的必要性;艺术具有至关重要的历史意义和重要性,这对于某个特定时期和观众而言,是令人信服的。杰瑞·萨尔茨则与这些观点相反。这并不是说他不善于辩论——他和他们一样犀利、风趣和健谈——但以我的经验,至少他的论点是不固定的,他也希望这样。这与萨尔茨的艺术批评有关,正如弗雷德坚定的理论与他的艺术批评相关一样, 因为萨尔茨的写作充满了活力和口语化,好像他一直对自己感到惊讶。萨尔茨收藏了4万张幻灯片——这收藏如此之大,以至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在他退休时向他要这些幻灯片——每当他举办讲座时,他就会展示各种各样的实物的图片。如他从机场乘坐出租车离开、他所在的城市街道上的景象,以及他所参观的画廊的外观。这不仅仅是分散注意力,也是为接下来转向观察做热身准备。当我问萨尔茨,他的哪篇文章最能说明当代批评家立场的难题时,他给我看了一篇名为《在工作中学习》( Learning on the Job)的文章,这是他在2002年秋天写的。在文中,他说自己被芭芭拉·克鲁格 (Barbara Kruger)抓住谈话,后者对他明显缺乏批评方法的反应是:“我们真的需要谈谈,哥们!”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是萨尔茨的立场声明,或者说是关于缺乏立场的声明。他反对理论,他指的是在事实之前形成经验的普罗科斯特公式(Procrustean formulas)。“我唯一的立场,”他写道,
“是让读者了解我的感受;试着用直白、没有术语的语言写作;不要过分简化或通俗化我的回答;要在每句话中都清晰地表达一个想法、一个判断或一个描述; 不要太想当然;解释艺术家如何可能是原创的或衍生的,以及他们如何使用技术和材料;观察他们是在发展还是原地踏步;提供上下文;做出判断,希望能比我的观点更有意义。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立场或一个理论,它需要另一些东西。这另一些东西就是和艺术、批评有关的一切。”
这个长句子由9个部分组成,中间用分号隔开。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分句是关于语气和观众的问题, 它们目前并不直接相关。第四个分句——“要在每句话中都清晰地表达一个观点、一个判断或一个描述”—— 这是反对不合逻辑的立场,尽管这也不是支持一个不断发展的逻辑论证的立场。(我认为,如果一个语法句子不能表达一个观点、一个判断或一个描述,那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第五个分句,他不想“太想当然”,再次表示他不想用某个理论来指导经验。第六、第七和第八个分句(从“解释艺术家如何可能是原创的或衍生的”开始,还包括向艺术家解释“如何是原创或衍生”,并提供“上下文”)是百分之百的艺术史,而不是艺术批评,它们包含某种理论的暗示,因为它们意味着创新比重复更好——也就是说前卫的,或它的某种多元化的形式,仍然是批评不可或缺的指南。
第九个分句和最后一个句子,承诺“做出判断,希望能比我的观点更有意义”,在我看来,这是无立场或无理论的艺术批评悖论的关键所在。与艺术史信息、风格、逻辑或观众相对的是,这也是9个分句中唯一一个关于批评性判断的句子。考虑到人性,萨尔茨在《乡村之声》中做出的判断很可能会被其他人分享。从逻辑上讲,如果他的批评只有少数读者知道,那么他的批评就会非常不受欢迎;如果没有一个读者知道,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胡说八道。但是“做出判断,希望能比我的观点更有意义”这句话的意思远不止于此,因为关键不在于受欢迎程度或意义,而在于历史的联系。萨尔茨的判断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观点,他的判断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判断有着共同的基础。这就是矛盾的所在,因为在我的阅读中,萨尔茨说“我不想被理论束缚”“我的批评需要与之前的理论联系起来”。他需要建立联系,但又不太了解这种联系:不要为其担心,不要太严肃或太系统化。为了保持优势、保持敏捷,并能够做出敏锐的判断,这是不需要考虑别人的理论的,但是当工作完成时——在第九个分句中——对于那些选择观察的人来说,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也很重要。
像我在这里如此慢地、尽可能多地阅读报纸上的评论文章,这不是常见的做法。从萨尔茨的观点来看,我不怀疑我理解错了,但我也知道这句话是这么说的。需要明确的是:萨尔茨无立场的立场,使他获得了许多精彩的见解。他可能会说,一致性是小心眼的妖怪,就他写作的目的和与研究对象的接触而言,一致性显然具有有限的吸引力——事实上它倾向于以“理论”的形式出现。我并不反对这些:自发性或许是一种虚构,而对某个对象的纯粹开放或许是不可能的,但当涉及到这些假定状态对萨尔茨写作的实际影响时,这完全是不相干的。当把他的全部批评和其他人的批评进行比较时,困难就开始了——这并不是说萨尔茨曾经说他认为这样的 项目会有什么价值。但在我看来,历史的意义是无法保留的:一旦它开始渗透到文本中,就像9个分句中的一些那样,文本很快就会被渗透。一旦做出了某个判断,而这个判断的意义依赖于之前艺术史上的判断,不管这个判断如何间接,那么,每个判断迟早都会想要从历史中获得它的意义。这意味着,根据洪水的逻辑,没有任何一堵墙可以阻挡历史的意义:最终,我们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问一问,萨尔茨的批评写作与其他批评家的写作相比,其总体效果如何?这是在支持多元主义的争论中经常被忽略的关键点:如果文本的组成部分——个体的判断,因为它们与艺术史的联系而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整个语料库就必须在一个历史平衡中进行权衡。幸运的是,不是每天都这样,也不是当你遇到艺术或与芭芭拉·克鲁格争论时也要这样——但最终,如果任何事情都要有意义的话,那就要这么做。
格林伯格(Greenberg)在《一位艺术批评家的怨言》( Complaints of an Art Critic)中以其特有的简洁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就在他声称审美判断“是艺术的直接体验所给予和包含的”,而且完全是“不由自主的” 之后。即便如此,他写道:“在潜意识的运作中,定性原则或规范是存在的”,因为,“否则,审美判断将纯粹是主观的,而这些判断不会通过以下事实显示出来:即那些最关心艺术、最关注艺术的人的判断,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趋同,形成一种共识”。格林伯格并不认为揭示这种共识与他有任何联系,我也不认为这是每一篇艺术批评文章摘要的一部分:但当问题涉及到一位批评家的整个立场,或立场总和的意义和重要性时,它就变得有必要了。这就是萨尔茨的第九个分句闪烁其词的地方。“做出判断,希望能比我的观点更有意义”:它们不可避免地会比他的观点更有意义,所以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希望?为什么没有人能审视并搞清楚这些呢?
在弗雷德的艺术批评中,对此有哪些反对?1966 年,在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一场关于批评的小组讨论中,弗雷德信念的力量,以及这些信念通过合理的解释来调和的方式尤其明显,芭芭拉·罗斯 (Barbara Rose)、马克斯·科兹洛夫(Max Kozloff) 和西德尼·蒂利姆(Sidney Tillim)也参与了讨论。罗斯回忆到格林伯格曾经引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话,大意来说是批评家的任务是定义主流。但是,她说:“在任何特定时期,主流只是整个活动的一部分,在我们这个时代,它甚至可能是最小的一部分。因此,专注于主流会让人们的观点窄化,甚至连达达主义(Dada)、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波普艺术(Pop Art)等主流的支流都不值得考虑了。”弗雷德 回答说:
我很想说,如果有人喜欢那个东西——暂且不提在特定的情况下,去考虑那种东西到底是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所说的自己也被诺兰德(Noland)或奥列茨基(Olitski)或卡罗(Caro)的作品感动、说服或击倒。我的意思是,不是我拒绝相信,我真的不能相信, 我无法理解我被要求相信的内容。我所能做的最多的就是假设,无论谁提出这一主张,他都会欣赏诺兰德和奥列茨基的绘画或卡罗的雕塑,确切地说,不是因为错误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处于错误的经验中——一种错误的身份体验。
这和格林伯格的主张虽不同但类似,即他并不总是同意自己的判断,但他被迫做出这些判断。弗雷德暗示他处于一个有根据的立场,这是有道理的——正如对一 个相反的立场经过想象重构所证明的那样——同时也是充满激情的,以至于不可改变。格林伯格在一篇仍然题为《一位艺术批评家的怨言》的文章中,对自己在面对自己的判断时的无能为力进行了最有力的阐述,这篇文章是对《艺术论坛》关于批评状态的系列文章的贡献。关于反对批评家应该有立场这一观点,他的立场最简明扼要的表述如下:
你不能合法地从艺术中获得或希望得到任何东西, 除了品质。以及你不能为品质设定条件。无论它怎样和在哪里出现,你都必须接受它。你有你的偏见、你的倾向,但你有义务承认它们并防止它们干扰你。
弗雷德和格林伯格在信念问题上的立场都异乎寻常地坚定,我不知道有哪位批评家或史学家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严肃地对待这些观点。包括蒂埃里·德·杜夫(Thierry de Duve)在内的一些艺术史家都曾思考过这些理论的含义,但这似乎是来自外部,作为他人理论的历史观察者。我想,没有人把这些想法放在心上。我的意思是,考虑到拥有这种信念的可能性或可取性,完全把格林伯格或弗雷德捍卫的某种艺术排除在外(正如弗雷德所言,“在特定的情况下,先把那个东西是什么这个问题放在一边”) 。通常的态度是,把弗雷德或格林伯格基于信念的立场与他们所捍卫的艺术混为一谈,从而有可能因为后者而抛弃前者。正是这种误解,让人们在决定自己不像他那样喜欢奥列茨基后而撇掉弗雷德,或者一旦发现格林伯格不喜欢波普艺术后,就停止阅读格林伯格的文章。事情比那更复杂。
弗雷德在他早期文章中的立场是忠于现代主义绘画和雕塑,但这不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即一个人说:“他采取了那个立场。”这是弗雷德当时和现在都坚持的一个立场,但不是他从其他立场中挑选出来的立场。如果是那样的立场,读者将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阅读他的文章,从而揭示使他“采取”现代主义、反文学主义立场的先前立场。我们有可能遵循先前的立场,被它们说服,接受它们。格林伯格在《一 位艺术批评家的怨言》一文中会说,弗雷德的立场不是他必须同意的立场;他只是“接受”了这个立场,因为它迫使人们信服,从而推动了写作的前进。
萨尔茨的理论——他的理论是关于艺术批评家如何不应该有理论——更类似于一个人可以选择接受的立场,因为萨尔茨认为理论是一种源于与先前经验无关的 一些东西。如果你在去参加画廊开幕式之前,喝咖啡时就决定了你的一切理论,那你的评论就会很糟糕。那种理论或立场,破坏了思想开放地与研究对象接触的可能性。在他的文章中,萨尔茨的确抱持着不那么稳定的立场,但这些立场都是短暂的,敏感于不断变化的艺术、当前的情况,或者此刻的心情。这些不稳定的立场可能被称为“态度”(stances)更好。这个词在当代艺术批评中很常见,因为它有助于表明,在当前多元主义的环境下,成熟的立场过于笨拙。“态度”也暗示了弗雷德和格林伯格完全无法接受的观点:批评家是一个远离写作的代理人,会根据不同场合选择不同的立场。这就是“我对那件事的态度(stance)是……”措辞的修辞力量,而不是“我对那件事的立场是……”。“态度” 所恳求的问题是赋予批评家作为代理人选择“态度”的权威来源。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立场,能够允许并协调构成当代艺术批评的态度如闪电般地转变?萨尔茨就像一个风向标,在任何时候都能随着微风旋转;而弗雷德就像一个恒温器,无论开着还是关着,都没有中间设置。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令人好奇、尚未被探索的领域。显然,如果艺术批评要改革,就必须要求批评家有明确的立场,那就不可能是弗雷德所举的那种立场, 因为那些立场是不能被接受的;如果批评要没有立场地进行下去,就不可能像萨尔茨那样,不遇到没有立场的问题。
也许最好根本不要担心立场问题,而是通过使批评变得更诚实、更直接、更有吸引力来改革批评。萨尔茨精力充沛地写各种各样的东西,完全不担心他在缺乏“理论”的情况下写作会如何。弗雷德关于批评的声明,与提出对艺术的判断的文章相比是很少见的。然而,立场永远不会完全消失。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就是一个奇特的例子。在文艺复兴之后,他实际上对整个西方绘画进行了权衡——他的写作比所有人都要全面得多,只有少数艺术史家例外——在所有这些写作中,他几乎从未考虑过自己的立场。在一篇关于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的精彩文章中,他对这种“难以捉摸的”“奇特多态的”艺术表示叹息,这种艺术“总是显得很草率”,而且“通常很平庸”。他打趣道:当克莱门特“画面很明亮的时候, 他就画得非常非常轻”。他抱怨说:大多数时候,克莱门特“就像个笨蛋一样画画”。然后他坐下来只看了 一张图片,一张神秘的海滩场景,上面有五个红色轮子。它们可能来自一个婴儿的手推车吗?暗指以西结 (Ezekiel)的火轮,还是称作宝座的天使等级的象征? 通过最简单的方法,一个人被转移到一个不可能的平行世界。在最好的情况下……克莱门特的作品在色情和文化记忆的交点上,过着一种令人颤抖的、只能部分解读的生活。尽管它的智慧比塑料更具文学性,而且它的颓废总是能让收藏家想要拥抱它。但是它的稀有、智慧和颓废依然存在。
这是一篇精彩的文章:明智、慎重、即兴的。最后的“拥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休斯的名声很大程 度上是通过降低声誉来获得的。
阅读休斯的文章,我经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他说出他在寻找什么,或者他发现自己在回应什么,换句话说,如果他会把观察当作理论来陈述的话——那么我就不会感兴趣了。他说他重视清晰、平衡、技术技巧和坚实(德·库宁的早期绘画“都是表面上的细微差别和疑问,并且“底部像铁一样”)、空间感,一种救赎的 “文化综合”(波洛克),一个“明确无误的宏伟象征视觉”(基弗),抽象概念的具体化,以及与大众媒体相对立的“有自己的规模和密度”的艺术。这些理想都是虚无缥缈的,往往在作品面前化为乌有。正如他承认的那样,它们也主要是晚期浪漫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的概念[大部分可以在世纪之交的科蒂索斯(Cortissoz)的批评中找到]。休斯在美国和英国都很受欢迎,但以我的经验来看,他对学术界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除了包括学术精英主义在内的所有常见原因外,这种忽视是由作为他的积极标准的思想的轻率造成的。我想,读者喜欢他,是因为他们喜欢他对虚伪的不耐烦,喜欢他给出的理由的不成熟。这些吸引力可能会让他们忘记艺术成功的无趣原因。
这真的很重要:休斯能写出精彩的有味道的文章, 而且他的文章中有很多精彩的画面。就像格林伯格的一 个门徒在莫里斯·路易斯(Morris Louis’s)的画布上 “摇摆着、咕哝着最后一粒颜料”;就像学习《塔木德》( Talmud,犹太教典籍。——译者注)的学生在向 《艺术论坛》的读者发布艺术史必然进程的公报之前, 先对一个文本进行争论——或者,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在“梦游和正步之间” 的观点。但是,当这个主题涉及到整个20世纪的艺术批评时,就其与艺术史的关系和更广泛的学术争论而言, 那么当揭穿真相优先于思考历史的形状时,它就很重要了;还有重要的是休斯的立场,这些立场可以从字里行间收集,不会被拿来与之前的判断进行比较。休斯不太关心别人写了什么,所以他专注于揭穿已被接受的观点,并为自己的回答寻找合适的词语。
没有立场的艺术批评家,包括像休斯这样对立场不感兴趣的人,仍然很有吸引力。然而,像大卫·西尔维斯特(David Sylvester)这样的批评家和大卫·班克斯 (David Banks)这样的批评家是有区别的。前者对自己的 反应很谨慎,尽管他经常不知道自己的反应如何与他人的反应相合拍;后者最近称赞布里斯托艺术家索尼娅·汉尼(Sonya Hanney)和亚当·戴德(Adam Dade)的装置艺术,承认“在艺术批评的伟大传统中,我对此了解得并不多,但我知道我喜欢什么”。西尔维斯特说的话通常来自他自己的本能反应,“艺术影响一个人身体的不同部位”。他在2001年接受批评家家马丁·盖福德(Martin Gayford)采访时表示:“例如,有时通过腹腔神经丛或胃,有时通过肩胛骨……或者,你可能会有 一种漂浮感——一种让我特别联想到看马蒂斯作品时的体验。”西尔维斯特的狭隘关注是合理的,因为现象学建构了他的批评方法;班克斯的观点不能用同样的方式 来辩护,休斯的也不能。
在格林伯格所持有的那种不受欢迎的信念与萨尔茨所支持的无立场的立场——无理论的理论——之间, 存在着许多危险的地方。这两者之间是驱使着弗雷德艺术批评的强烈信念,它们同时被拥有或拥有别人,以及休斯文章中时而出现、时而又很快消失的标准。那些似乎没有立场的艺术批评家最终还是会有自己的立场。当许多判断的总和似乎指向一个方向时,就像一群小昆虫缓慢地上升或下降,尽管个体向各个不同的方向移动。 一个立场可以通过最协调一致的努力来实现,以避免前后一致。所有这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这就是写作的方式。然而,当写作本身暗示应该有一个立场时,无立场就有了它的局限性。一个对理论敬而远之的批评家可能会成为自我免疫反应的牺牲品,因为他自己的批评暗示他实际上是有立场的。另一方面,一个强势的立场或万物理论限制了他与其他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的对话, 而在格林伯格的例子中,它甚至似乎限制了他对自己偏好的起源的阐述。很明显,通过要求艺术批评家有自己的立场来改革艺术批评,往好了说也是值得怀疑的:它沿着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往回走,通向一种承诺,这种承诺是如此凶猛,甚至持有这种承诺的格林伯格都把它描述为一种超越自己的力量。这并不是说相反的情况更好——而是说立场不是一个人可以返回的状态。
我对改革艺术批评的七个建议到此结束。我的道理很简单:所有的改革都伴随着对陈旧思想和幼稚的历史观的严重惩罚。
作者:[美]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马琳、任真良 译(Translated By Ma Lin, Ren Zhenliang)
原文刊载于《画刊》2020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