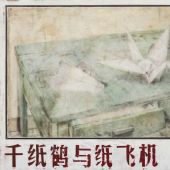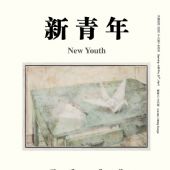在夏禹近期的画作中,家庭成为叙事的核心——在树下合影的兄妹、为母亲照相的儿子、在孩儿额头上写下“早”字的母亲,等等,无一不吐露着家庭成员之间的默默温情。亲情在中国人心理结构的塑造方面至关重要,它是个体情感的温柔乡和庇护所,同时又是家庭内政与社会交往的重要驱动(曾经的中国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亲属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在如今的三线城市和乡村之中仍某种程度上存在),但是,关于亲情的表达在当代文化语境并非新颖,夏禹的画因此看起来有一些怀旧,不那么时髦。与其说夏禹是对一种行将消逝之物充满留恋,不如说是在有意地认同或回归——他所讲述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曾经遭遇的情感体验,这些共同体验也许悄然塑造了我们所称谓的“民族性”?
夏禹用坦培拉技法作画,与直接画法相比,坦培拉无法产生边缘锋利的笔触,覆盖力也很弱,它只能在不断的皴擦与荏苒光阴之中形成一种半透明、毛茸茸的画面质感。利用这种质感,夏禹发现了一种清凉、纯洁的绘画语言,这种语言与他的叙述恰如其分地互相融合,使得他的表达呈现一种友爱气质,充满关切,又不温不火。挂在晾衣绳上的衣物随风飘摇,在夏禹饶有兴致的表述下,让人体会到一种对日常的敬意。嘲讽一样事物或责备一个时代十分容易,我们的批判性总是错误地根植在与现实的敌意之中,而夏禹宁愿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去打量那些再熟悉不过以至于被忽视的生活情状,正如他在崇奉的前辈丰子恺先生那里所学到的。
在夏禹充满叙事色彩的画作之外,还有一些更为单纯宁静的作品,画面描绘的是一些毫无时代特点和戏剧冲突的喑哑事物,诸如平淡无奇的盆栽或者默默无闻的花坛一角,这些无聊之物在夏禹笔下蒙上了一层特殊的温润——我们似乎可以窥探到某种端倪——夏禹希望自己的绘画摆脱叙事的填充转而探索更为纯粹、洗练的绘画语言——即使不讲述中国故事也能辨认出口音的绘画语言。
“新青年”暗示了一种抱负,一种想要作为的冲动,夏禹在他的绘画中表达了对“新”的见解,求新并非意味着不假思索地与旧事物决裂,而是与过去建立一种恰切的关系。借助于“新”,夏禹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恪守,此时恪守却成为一种温存而激进的姿态。
展览时间:2014年4月26日至5月26日
展览地点:蜂巢当代艺术中心
图片提供/蜂巢当代艺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