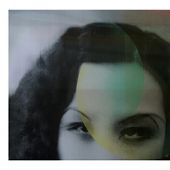虚线,作为一种视觉识别符号,是交通规则中的灰色地带,它提示了超越、掉转及变轨,成为交通运行中的调节机制、自由意志。本次展览的两位艺术家韩磊和孙彦初,他们的创作实践恰好体现出这种“虚线”机制,并且触及了更为开阔的语言边界和图像逻辑。
除此之外,两位艺术家之所以做并置展出,一方面,鉴于他们同为河南籍艺术家的这种地缘脉络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他们作品内在的某种互动关系上。
孙彦初喜欢漫无目的地的游荡,与他相遇的,是中原荒野中的衰草、枯枝、野狗、歧路、流浪大篷车……它们暗合他的心境,并成为他的镜子。这种与荒野交手所产生并疯狂生长的诗意,或许是孙彦初不安之心的明灯,他依赖这种诗意释放并削减自我内心的戾气与暴烈,为欢愉和平静腾出更多存储空间。拍摄于他来说,近乎于“解恨”:对于能量的挥霍,以及对于视觉打击力的伸张。这种依托快门和暗房定影的黑暗、色情与暴烈,在韩磊早期的创作里,能找到一种相投的气息:不管是肥硕的相面术般的各色人等影像,或者是排布扮演的小丑、裸女形象,抑或是根植于乡间的“民间惩罚”系列。
但我们要展示的,正是后来变轨的虚线图像逻辑。在韩磊的近作里,他用光栅材料制作的那些女明星旧照,来触及时代记忆以及附着于此的神秘观看。光栅这种材料在1990年代常常应用于广告或日常家庭中,比如在家庭客厅墙上挂的风景框里,就能看到因为不同角度而展示的不同风景图像。他把这种现在看起来有些低科技的材料提请到当下的技术语境中去用,并且觉得再合适不过。而近期韩磊制作的光栅照片里,采用的图像更为宽泛,比如常规的花花与一些有故事的著名雕塑资料照片,他在一件作品里置入相同照片不同观看效果(比如正片与负片效果),或者置入不同照片,这提醒我们,除了记忆向度,韩磊还对观看提出了思考。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通过观看行为体会到了图像观看的运动性,而非凝视,因为这种本来需要凝视的图像由于材料的闪烁不定和观众站位的“无中心”,导致观者必须处在一个不断移动的观看状态之中,才能无限接近于图像的最佳观看视角,这个视角的获得,是对图像意义生产的摆布,也是对于观众观看习惯的拨弄,他力图使观众变得更加勤奋,甚至他们也从未确定一个自己满意的观看视角,而观众通过反复游移所获得的这个视角,既不是照片所确立的那个最佳观测点,也不是电影那个本身有时间线的观看逻辑,它是介于照片与电影之间的一个“临时避难所”。
而他基于商业活动中常见的明星广告拍摄的视频短片,经过慢放,去除商业功能,将已逝且不被察觉的瞬间延长为戏剧性的仪式展示,使得在方向不定的风中飘摇的印有明星形象照的旗帜,如同一则专门用来捉弄人的寓言。
在孙彦初的《迷途》系列中,孙彦初有别于早期与现实执意决斗的相遇,而是有意拍摄旅途中乘车路过的那些一闪而过的乡间路口——这个“还乡”的最佳通道,通过“快闪”激化了艺术家本人的某种忧虑和不安,“疾速”的行驶使这种“快闪”获得了一种半催眠的观看体验和还乡的精神图像,而由快门执行的拍摄指令却与炭笔画的笔触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回应,对丝绢材料的使用,也是孙彦初想借此试探和观摩图像与绘画中间那些暧昧不明的地带,也就是说,他有意模糊了二者向来生分的界限;在他6☓6画幅的新作《风尘记》里,看似还是出门拍摄,实则是使用“场景”,进而获取要使用的图像,通过“截取”动作将均质的场景延伸为惊险、离奇而幽默的戏剧;在《虚构集》里,或许是基于对图像不断阅读的过程,加之小时候受给邻里乡亲画画的父亲的影响,孙彦初开始启动绘画这一媒介,通过“篡改”和“涂抹”的动作,在图像上,诋毁原有图像已经固化的意义,利用媒体上读到的乡村凶杀故事,以及所使用的图像的时代烙印,在图像上,经过覆盖、嫁接和调侃,从而修筑新的情节,以强化另一种看起来更加成立,并且显得强大的图像叙事逻辑,但作为观众,我们从他保留的依稀的原图像残留物中可以看到这两种叙事所露出的中间地带。
文/海杰
图/主办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