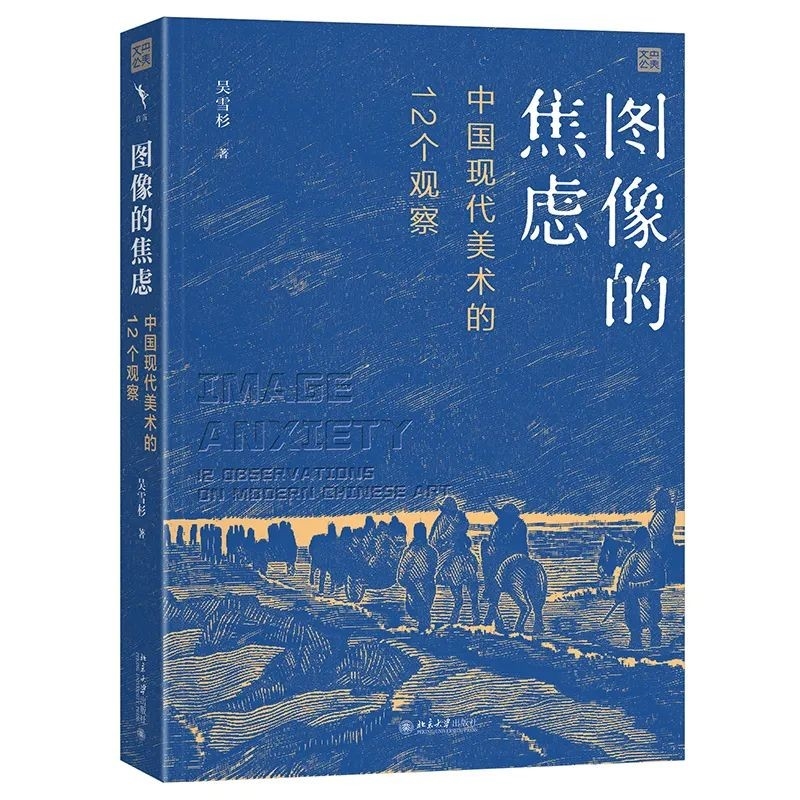30年前,当1989年黄永砯去巴黎参加“大地魔术师”的展览,并选择留下的时候,也许令福建的一些美术界人士感到喜悦——一个让人头疼的“捣乱分子”终于离开了。现在,这位艺术的“捣乱分子”却永远回不来了。2019年10月20日,65岁的艺术家黄永砯先生,在巴黎永远的离开了他的艺术世界。
“捣乱分子”:从厦门达达到《大地魔术师》展览
黄永砯,1954年生于福建,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中最重要的一员,1977年,黄永砯考入浙美油画系。回顾黄永砅的成长史,反抗、批判精神一直都在。其“反叛”的端倪从大学就开始,毕业创作他就直接拿着工业喷枪和喷漆而不是画笔来搞创作。黄永砯也一再批判艺术体制,一再强调美术馆是坟墓,美术馆展出的所有东西都是僵尸,不可能在美术馆里学到艺术。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厦门一所中学做老师,在1980年代中期发起了“厦门达达”艺术团体,这是1980年代美术最极端最叛逆的美术运动群体,最著名的行动是在一次展览之后把所有的作品一把火烧掉了,黄永砯在焚烧的现场,用石灰在地上写上口号:“不消灭艺术生活不得安宁”——当然,黄本人不是这话的彻底实践者。这一切似乎事出偶然,对黄来说却难说不是精心筹划。多年之后谈往事,黄永砯提到,当别的艺术家想要在地上画个太极图案的时候,他当时并不赞同,认为这样会改变行动的意义。
1986年,黄永砯、林椿等人在福建创办“厦门达达”,是85美术新潮最具有颠覆精神的一个艺术流派,于1986年9月发表《厦门达达——一种后现代?》,公开宣称建立这个团体的目的是在全国性前卫运动中进一步“制造和参与混乱”。实施了一系列“袭击美术馆事件”。
1987年,黄永砯创作了最具的代表性的装置作品——“中国绘画史和西方现代艺术简史在洗衣机洗两分钟”,这件作品足以使黄永砯被写进中国现当代美术史。黄永砯的作品并不仅为追求视觉上的美感,题材多数涉及到于中国历史和神话故事,因此车轮、廊桥、亭台的屋顶、活的蝎子、玻璃制成的鱼等等都曾经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1989年5月,黄永砯应邀到巴黎参加《大地魔术师》展览之后,定居法国。
“制造混乱”:东西方艺术的混合者
定居法国后的黄永砯认为法国给了他一个新的语境,尽管开始语言不通,到今天语言可能依然是个障碍,但“一切障碍都不影响交流”。法国生活也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官方身份,他不再是中学里的“黄老师”,而是作为艺术家和一些西方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在一起工作。
从讽刺、抨击移民问题的《通道》《黄祸》,到反美国霸权的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蝙蝠计划》,再到讽刺美国在阿富汗政策的《2002年6月14日的一场足球赛》,黄永砯的许多作品对当前的时事事件都进行直截了当的评说。黄永砯与蔡国强、徐冰、谷文达被合称为实验艺术“四大金刚”,是装置艺术的代表人物。不过对于这种称呼黄永砯本人并不认可。
在意大利,他把400公斤的大米煮成饭放在美术馆大厅里,这些饭煮了一个星期,后面的还在冒热气,前面的已经慢慢霉掉、臭掉,他认为这个东西象征着美术馆作为一个消化系统,是并没有能力去消化艺术的。这个展览被命名为《不可消化之物》。
黄永砯一再强调美术馆是坟墓,美术馆展出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僵尸,不可能在美术馆里学到艺术。美术评论家、策展人费大为曾经问他,“你为什么不把你焚烧作品的照片、录像和文字全烧掉呢?”黄永砯给出了一个不是太有说服力的回答,“如果连照片都没有了,谁会来相信你呢?”
“千万不要相信黄永砯”
黄永砯通过空间装置探讨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试图寻找一种可以超越国界以及意识形态冲突的表达方式。黄永砯的艺术魅力就在于他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哲学、文化、政治思考,而不只在于艺术技巧和手法本身。他用自己的创作挑战传统艺术观念、信仰以及逻辑,将中西方的文化观念符号并置,以展现其中的紧张与冲突关系。
费大为认为,黄永砯的这种矛盾也可以用禅宗来进行比较,两者说的就是一个道理——语言是不能被传达的,语言是没有用的。但是禅宗,光是《五灯会元》就有20卷,啰哩啰嗦讲的就是一句话“千万不要相信文字”。
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讲座上,费大为对大家说,理解黄永砯的要点就是:“千万不要相信黄永砯。”黄永砯知道了这话,表现得非常高兴。
黄永砯的离去无疑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损失,但他已创造的艺术作品,仍会影响着中国当代艺术今后的面貌。
【挚友悼文】
永砅是天才——侯瀚如悼黄永砅
黄永砅是天才。天妒天才,向来都是我们不愿意相信的“规律”。但是,这一回却应验在他的身上,多么得不可思议,更令人悲愤交集,欲哭无泪!
永砅以如此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离开我们,难道是他与生具来的、出人意料的创作方式的又一次令人惊愕的表演?我们多么希望这只是一次表演而已。可惜,这却是最后一次!四十年来,他总是以一种让人无法预料的机智和挑衅,在每一个他出现的地方,或者举重若轻,或者逆流而上,用“艺术”的方式,在现实的高墙中穿刺出某种孔洞,让我们得以“参见”真实本身。也就是说,他让我们“顿悟”,欣然又不安地发现,真理其实并不存在;但是我们不得不无止境地给自己找麻烦,把“寻求真理”看作无上的使命,以便感受到某种“生活的意义”——无论面对的是个人的自我质问,还是社会和政治的不公和暴力,我们都必须质问“为什么”,再想想如何把问题反转过来,再问一遍。永砅正是透过种种令人意料不到的“袭击式”的行动,或借用“达达”之名,或把中西艺术(书本——或者即“作品”本身)放在洗衣机里搅拌成为一团“糟粕”,或者干脆把几十种昆虫和爬行动物放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互相争斗,演出一出活生生的“世界剧场”,甚至使一条没有皮肉的巨蛇浮现在海洋之边,随之引领其穿破世界大都会的心脏……他让我们“参透”了世界的本性——如果本性是可以被想像的。他的每次行动,都多少掺和着荒唐谬误的成分,有时又显得残忍无情,但最终却无害于人,一笑了结。同时,现实和真理,继续在互相纠缠较量,不分高低。早在三十多年前,永砅就确定——应该是他唯一自认为可以确定的事情——艺术就是制造“完全空的能指”,以见证和解决这既没完没了又无法被见证,更不可能解决的较量。
永砅要达到的是超越常理,即,超越一切——无论“东西南北方”或“古往今来事”的讲道理的意愿,还有它的欲施于人的体系行为,或者说,政治。他公然挑战“理性主义”——不是因为理性本身不符合“真实”,而是当它成了“主义”时,就成了暴力的源头。他试图证明,真正接近理性,亦即公义的途径,正是挑战政治体系的理性本身。而这种战事,不仅仅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引用一切被“理性主义”所排斥的“非理性”或者“极端理性”的思想系统,比如《易经》、禅宗、炼金术、《山海经》《圣经》、维特根斯坦、福柯等等,来干扰我们的视听,打破我们的“成见”。它同时也是一个和各种维持“理性主义政治”的机构,从医院、监狱、学校到美术馆等等不停较量的过程。最终“沙的银行”只会落得成为“银行的沙”的下场。“世界剧场”,借着“艺术自由”的名义,为我们展示着世界的恒常——没有恒常即是恒常,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存在、政治、权力、现在、过去、未来、资本、思想、道德、美丑,诸如此类,其实只是不可理喻的“恒常”的不恒常的、在混沌中挣扎的表演。而往往被视为最高境界的“艺术”只是这种表演过程衍生的呕吐物而已!
换言之,永砅总是主张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各种事件的真相,既可以相信,更加需要怀疑。矛盾,悖论,就是存在的真正内核。按此逻辑,我们多么希望永砅总是有理的,他离我们而去的“事件”不是真的。但是,命运却像他“悟通”了的那样,把我们捉弄了:这次的离别是真的。
不过我们还是需要不断地寻找机会,向他道别。其实,我们是要不断地寻求从他那里得到启示,因为,就像他一贯倚重而又质疑的占卜术,他的思想和行动就是我们不会枯竭的灵感源泉。
永砅是一个哲人。他待人接物谦卑诚恳,同时又分分秒秒显示出强大的自信和智慧。他在感悟到“真”的同时又总是体现着“空”。更加重要的是,他永远站在被边缘化的人和事的一边,用他特有的想像力和批判力为“另类者”发声。而这种声音和他的身影一起,永远缠绕着我们的心灵、梦想,还有“现实”。
他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的一切;他的离去,让我们不得不再改变一次……
侯瀚如
2019年10月20日塞纳河畔伊夫里,永砅、沈远和言的家
蔡国强:念永砯
永砅永远要与众不同。陈箴去世时,他唠叨着别做得太复杂隆重,让死者平静些。但他为陈箴写的一句话让我几次用在朋友的悼念上:只要大家都想他说他,他就不死……今天用在永砅上!真的没想到……
90年起,在巴黎的这群艺术朋友,永砅沈远、天娜诘苍、陈箴徐敏、大为雁雁、瀚如和艾布丽娜、培明……都是人穷志大、恩爱夫妻,对家人尽孝、对朋友温暖,让我和太太红虹每次去巴黎就是春天,舍不得回日本。大家轮流请我们,每天聚一次:沈远家永砅负责洗碗,我们这么多人来他就下厨……徐敏接了结婚宴席的活,大家一起去当厨师把钱赚了。这群人开朗乐观,谈艺术、人生,相互支持、彼此批评,永砅的话尖刻但点到为止。玩笑时,严肃的永砅也会仰天大笑!
8~9风~波后,我们这群人突然像流浪的孤儿,面向世界的困难和挑战外,还要面对国内局势下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常一起讨论“战略战术”……
永砅是我和红虹的福建同乡,祖籍泉州,应该是生长在厦门,简历总写中国厦门。他会闽南话,但不说,以为他不懂,他却来议论我和红虹的闽南语对话……
我英语不行,永砅法语不好!大家笑他像个走私的,说他入海关,人家一问话,他就开始脱衣服!让人赶紧喊停。
一开始,沈远在马路上卖画支持永砅,生活好转了才做自己的艺术。她崇拜他,几次口误把“永砅说”讲成“毛主席说”……
1991年,我们一起在日本福冈参展,大家都住制作人山野的家,自己烧饭生活,不去餐馆,制作费都用来做作品,他买来几十车水泥“吐拉”一路。每天黄昏,日本的全国天气预报,日语的“最高强”(最高温度)听起来像闽南话“蔡国强”。永砅有次忍不住发牢骚,“展览都没开幕,怎么每天都说‘蔡国强’、‘东京蔡国强’、‘大阪蔡国强’……”
今年夏天,我回到1990年做《中国明天》展的法国南方布耶(Pourrières)村。永砅曾用易经符号做地基的那块地,已经盖了村民的房子,不知道房间是否也是易经构造,住了是否好命。
1999年世纪之交,威尼斯双年展由哈罗德·塞曼(Harald Szeemann)策划。我做“收租院”,陈箴“打鼓”,永砅代表法囯馆——就像日本人爱我一样,法国人很爱永砅,还有二十多个中国艺术家。这是西方世界最大、也是最后的“中国年”! 永砅给人感到是愤青,又是老学究。他常常问左答右令人模糊,但他认为的原则,一点都不允许模糊,比如与台湾相关的写法他很敏感……做艺术也不模糊,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做,总要搞清楚。
他思考细而深,但应该不兴趣被人感到高深。2016年卡塔尔的中国当代艺术展,我是策展人,把最大展厅给他,他讨论展览的目的、如何做有效,还提到要适当给些作品说法更容易让主办方接受,让我印象深刻。
很多中国艺术家好说老庄佛禅,永砅是真正用作品说、用方法论做、也用人生悟……虽然他常用八卦算命做作品,但我印象那些更多是艺术方法论和哲学范畴,他似乎不太拜佛、迷信风水这些……不像我们!重要的是他懂得玩,玩老庄哲学、玩西方达达、以东玩西、以西玩东、玩美术馆系统……是个大玩家!
永砅也大玩自己的脑力和体力,作品工程再大都自己上,是个典型的劳动人民!他家庭幸福、健康自律,随身带根跳绳,方便到处跳,不像我四处找健身房。我们以为他会成为生命恒定、细水长流的百岁老人。陈箴年轻就有病,大为曾紧张自己的心脏早搏,我和永砅都瘦弱,笑大为,“我们都死了你还会好好的”。
这几年和永砅虽然不常见,但他在这里那里的作品都能看到。人死了,新作也就看不到了!
就像他说的,我们想他说他,他就还在。艺术史说他,他就不死。当然我们如果和永砅谈论艺术史树碑立传的事,肯定要被他笑话。
永砅的恣态就是这样,死也死得干脆。
年纪大一点,不断有朋友离开。初冬时节,大地有回春时,人只往寒冬无归路……
蔡国强、吴红虹2019年10月21日
编辑/林路
图、文材料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