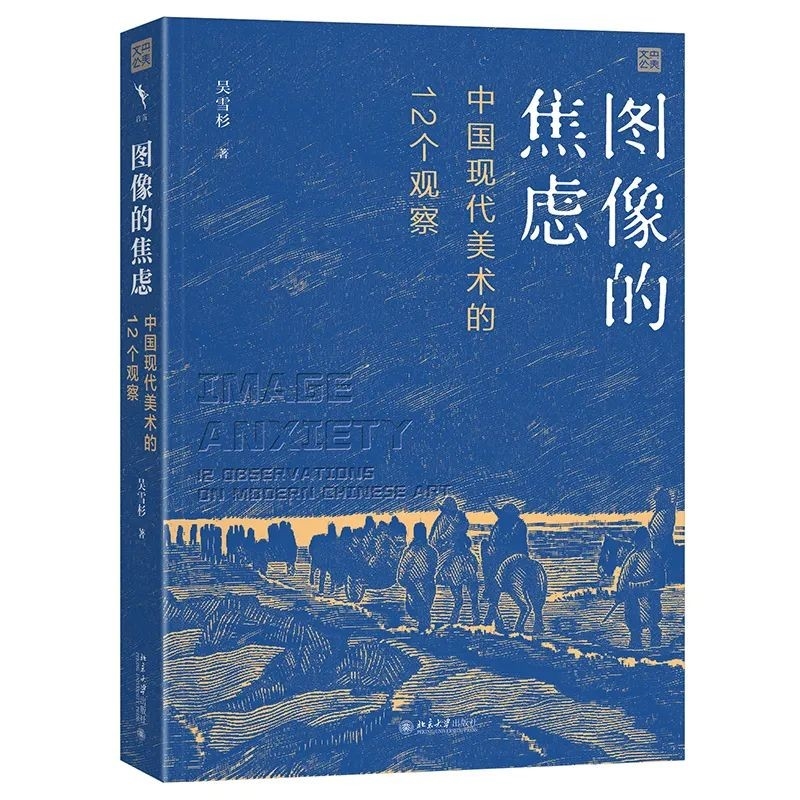近日,由宁波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方寸象溢——周至禹教授艺术作品展”在宁波市扬帆美术馆顺利举办。本次展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2张风景的素描,是周至禹先生一年来围绕身边普通景象所做的素描写生。以他高度的敏感对周围的风景进行观察,这种观察敏锐深刻,既是自然的风景描绘,也充满了令人感动的精神表现,素描以木炭为媒介,既有着版画概括的黑白灰效果,也有中国画的写意笔触和肌理。周至禹以丰富多样的画面,松动自如的素描语言,富于张力的内部结构,构成了其风景素描的艺术特征。他用最简单的纸笔,描绘不起眼的景致,最终在完成的画面中流露出浓浓的诗意和宏大的情思,蕴含了人文关照和命运思索,充分表现出对艺术的执念和对生活的深情,在一张张绘画里营造出一片精神的“洁净之地”。自然风景的审美情怀和主观感受表现作者对自然的热爱与钟情, 丝毫不会受制于景色的“不完美”和尺幅的局限也就契合了这次展览的标题核心:方寸象溢。从这些风景中可以看出,周至禹的艺术主张:以自然为胸襟,澄怀得心性。自然物与自然景,就是心中物,心中景,以平常心观平常物,寓物象以造意。眼前所见之物,为心性所经历之物,周教授描绘的正是他自己的精神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任由诗意蔓延……
这次展览的第二部分是78副版画作品,以超现实的画面表现了在城市背景下人的精神与生活状态的丰富想象。这些是从小说《我的城邦》插图中衍生出来的系列创作,呈现出周至禹对诗歌的热爱,对文学的热爱,反过来又滋养了他的绘画,让他的绘画作品充满了诗意和远方,阅读他的作品,我们也能查看到一些细节和故事,绘画充满了文学的隐喻、夸张和符号,但是,从根本上讲,他的作品充满了诗歌一般的音乐节奏感,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一如生活中的他,纯真纯净纯粹,高度自律和勤奋,追求卓越,热爱真理和艺术,就如同他在作品中呈现的,他的灵魂总是生活在云端,向往着康德所形容的浩瀚星空。
这两部分相互映照,形成自然与城市,写生与表现、现实与想象的几重关系,在展场的柱子上和白墙上,张贴了周至禹先生撰写的一些诗歌句子,例如:一无所有的天空充满了一无所有的美丽。这些诗句与画面相烘托,展示出对当代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一种诗意和哲思。
景如“诗”
在一些并不特殊的周末或夜晚,无论天气晴好、阴云密布、光色迷离或路灯昏沉,周先生恰如一位独行者,出现在他熟识的校园和城郊,用简单的纸张和炭笔,描绘视野所及。这些写生地,有他时常路过的校舍林荫、蜿蜒小道,也有他舒目远望的江岸水色、城池天际,还有踟蹰难行的幽寂野岭和欣然向上的楼宇工地。实际上,目击之象并不新奇,也无“乍见之欢”。这些日常所见的天地一隅,如何蜕变成一幅幅素描作品,不仅在技术上考验画家的营构之法,也在“现象”之外反观画家的“胸臆”,即主体叙事的视角、立意和表达。
对世界的感知、解剖和自我治愈,几乎成了一种执念,鼓动着艺术家保持对生活的爱,以激情之躯面对人类“必死性”的虚无,践行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正因如此,画家周至禹笔下的草木山川、光阴月色成就了一片片“洁净之地”,让我们诗意地栖居。 实际上,他描绘的正是他的精神世界,聚世间众物之灵而炼得超然心绪和物我交融之境。而在这个世界中,诗意无限蔓延。想来,作者竟于微小处和不觉间,绘就天地纵横。不竟让人想起德国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在《远景》中所描述的:
“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闪闪发光。那也是夏日空旷的田野,森林显现,带着幽深的形象。自然充满着时光的形象,自然栖留,而时光飞速滑行。这一切都来自完美。于是,高空的光芒照耀人类,如同树旁花朵锦绣。”
心如“镜”
十八世纪的埃德蒙·伯克在《论崇高与优美概念起源的哲学探究》中认为,人们在面对优美与壮观景色时,因受到视觉或听觉上的冲击而自然生发出“优美”和“崇高”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心理与情感反应。它们有着相异的视觉表情和主观体验,这在周至禹先生的风景画中也可以找到相类的例证。而更让人惊异的,则是在周先生为数不少的作品中,优美的宁静和崇高的激情并存不悖,其“矛盾统一”让人感受到巧妙的平衡和拿捏,可谓“淡泊中见清奇,平直中见戏剧”。
周至禹先生的风景作品,并不有意展示人类知识,而对意外的“撞见”兴致勃勃。他把写生过程当成了视觉的狩猎之旅,不停地寻找那些“视觉现场”,在经历了百幅作品后依然保持初始的激情。然而,这种“撞见”和“寻找”,并非散漫和闲游。作品何以动人?这一问题,会提醒画家保持对“感性”和“理性”的敏感,并找到恰当的平衡。例如,乌云遮蔽的太阳、树木掩映的路灯,被画出了肃然圣洁的光辉意象;平静安然的水面、林荫浓郁的树丛,被绘成了闲适无争的世外风物;混杂无序的荒地,瓦砾破败的废墟,被表现出超然物外的原始情境。这显然已远超写生的普遍目的,心灵观照跃然纸上,确实无法以偶然“撞见”概言。显见的是,画家一旦进入写生状态,即进入创作潜意识,这些意识完全来自于个人的专业素养和思想自觉。在此层面上,理性沉思所对应的“心灵镜像”,从视觉之美中浮现出来,与之凝结,难分难解。
无论是素面朝天的炭笔风景写生,还是精心营构的文学插图,都在作者的主体中得到贯通,而内化为“自在的风景”和“心灵的风景”。风格至此已然不是关键,写生现场的视像直觉和肆意激情,与插图的理性构思和奇幻表达,殊途同归地凝聚起来,展示了画家的心灵史和技术史的有机统一。
画如“象”
当风景画进入生活,它便开始影响我们观看和体验现实风景的方式。
在周至禹先生的作品里,一组组形象和技法的对比,让我们体会到了他试图回避图像记忆却又关照个人经验的努力:城市与乡村,人工与自然、天空与大地、光照与阴影,焦黑与皓白、粗粝与柔畅、虚淡与浓实。这些作品来自理性控制下的直觉,既是随机的、流淌的,也是结构的、有机的,但见不到固有的模式,也不落入个性的窠臼。这种诗性内核的风景画,不是风格化的,而是人格化的、意象化的,摒弃了技术炫耀和先入为主的程式设定。
艺术家在为公众提供视觉享受之外,对社会的贡献还至少包括两个层面:阐述现象与提出问题。这向来吸引着公知意识强烈的周先生。从他早年版画的乡土风格,到《魅城》的超现实主义,再到素描风景简明质朴的黑白手法,他不仅在主题选择和表达方式上主动蜕变,还将源于个人经验的问题意识逐渐强化,在作品中暗示出一条有迹可循的表达之路。虽然对于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超越了艺术家的能力职责,但是能否在作品中提出问题,已然成为划分艺术家良莠的标准之一。
绘画写生,也许是探讨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最佳方式,用于连接物质之象与精神之象。对于周至禹先生来说,它既是即兴,也是沉思,写生即创作,直觉即理性。因此,这一系列作品模糊了“不确定性”与“永恒性”的界线,不断地聚焦与弥散,唯让思想不被锈蚀,诗魂不被俗化。
方寸须臾,象溢万千。
图文由艺术家及主办方提供
编/张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