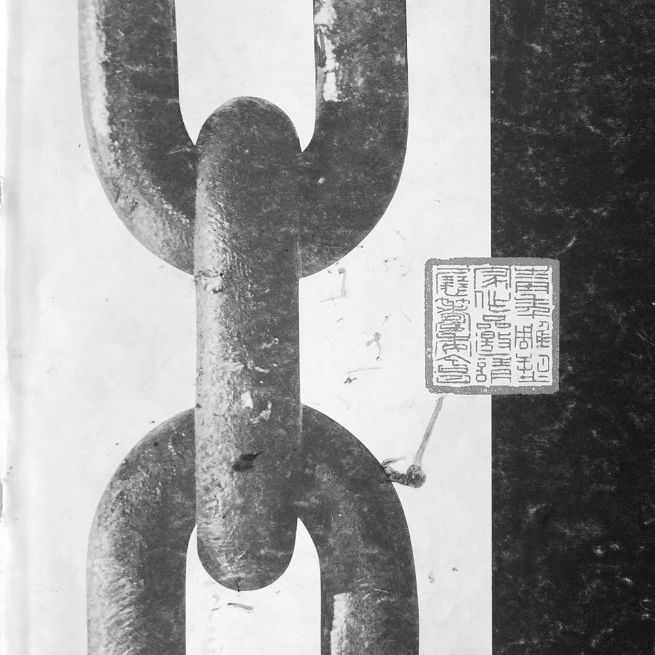小学爱临摹古代英雄侠士 同学在教室给他办画展
靳尚谊1934年出生于河南焦作,太行山南麓的一个煤炭工业城市。父亲靳允之是煤矿职员,也作过中学教员;母亲吴佩兰是家庭妇女,曾任小学教员;靳尚谊的弟弟叫靳尚诚,也是中学教员,他的家庭可说是教师之家。
靳尚谊天生喜欢画画,在焦作读小学时最爱图画课,经常临摹连环画中的古代英雄侠士,同学们从家里拿来纸让他画,把画贴在教室墙上,给他办过一个小画展。
从未学过素描 被北平艺专录取
1947年靳尚谊读完小学离开家乡住到北平外婆家,同年考上北平私立“九三中学”。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靳尚谊15岁,在一位亲戚的鼓励下,报考北平国立艺专(现中央美术学院)。他第一次听说素描,第一次使用炭条画石膏像参加考试。因从未学过素描,素描成绩排甲等最末一名,靳尚谊被北平艺专录取后,艺术生涯从此开始。
靳尚谊进入北平艺专不久,学校就与华大三部美术系合并建立了中央美术学院,校长为徐悲鸿先生。
第一次摸油画 为工厂画毛主席肖像
1950年夏天,我们在南京浦镇机车厂体验生活时,工厂请学校画一幅毛主席油画肖像。这项任务应该由四年级学生靳之林完成,他学过油画。我当时才一年级,好奇又兴奋,非常想试试,我跟在靳之林后面,帮他画。我们根据毛主席标准像的照片,在一米高的画布上打上格子,先画素描,再涂颜色。我觉得用画笔一笔笔把颜色涂在布上,再把它们衔接起来,真是有意思极了。这是我第一次摸油画,我想我就是从这时候起开始爱上油画的吧。我工作得极为认真、努力,几天就画完,由于素描还行,画得基本上像。靳之林又帮我调整了颜色,算是完成了任务。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摸油画的经历。
第一次临摹欧洲人的油画原作
1954年“苏联展览馆”在北京建成,同时苏联的大型展览在北京、上海、武汉巡回,展出了很多苏联艺术家的油画作品。49年入校至今,虽然已经是研究生了,但没有真正学过油画。在素描课堂上每个人画过三张油画作业:一张头像;一张半身像;一张领袖像,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油画,我不了解,也没见过。这次在苏联展览上,我才第一次看见欧洲的油画原作。
展览期间学校决定让研究生去展览馆临画,自己挑选临摹的作品。我选了马克西莫夫的一幅《铁尔皮果列夫院士像》:这幅画是穿着白衣服的坐像人物,偏古典的造型,颜色微妙、含蓄。苏联大百科全书对这张画的评语是技术上达到“炉火纯青”。白天我们都在展览馆临画,旁边常常有观众,我记得杭州美院一女生也临了这张画。肖像临完了以后大家互相交换意见,由于不了解西方造型体系的要求,仅仅认为比较像,还不错。但是我知道表面可以,实际根本谈不上掌握造型、色彩的要求,油画的妙处在哪里也不清楚。马克西莫夫的油画技巧那么高,我们是望尘莫及的。
世界上的事就这么巧合,没想到我仰慕的这幅画的作者马克西莫夫,以后真的成为了我的老师。
第一次坐火车 去兰州乌鞘岭深入生活写生
1954年读研究生的时候,艾中信先生带我、蔡亮、葛维墨三个人到甘肃兰州乌鞘岭深入生活。那是我们第一次坐火车,艾先生坐卧铺,我们都是硬座。先到西安呆了几天,然后跟石鲁一起到兰州。兰州铁路刚修到那儿,站台上还没房子,一下车就是空的站台。兰州破破烂烂,我们到时太阳刚刚升起,蔡亮诗兴大发:“噢,一个城市的黎明!”
兰州铁路工程局的一个作家叫洪流,把我们带到乌鞘岭。虽然是夏天,乌鞘岭却下大雪,我们住在账篷里面。我画了好多速写,回来以后艾中信画了《通往乌鲁木齐》,当时我准备考油画训练班,什么都没画;葛维墨画了唯一一张比较好的《走向生活》,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蔡亮也画了一张,画的是勘探队员借住在藏民家里,油灯下藏民补衣服。
1954年,去黑脑村的惊险一幕
我也出过险情,54年下乡,到太行山宣传总路线,从保定进山,没有交通工具,骑着马走了100多里路。马在太行山的山沟里,窜来窜去,窜进树丛中的小道,路旁的树把我一下子给刮下马,幸亏因为树矮没摔着。从早上一直走到天黑,才到黑脑村。住在村里搞宣传,那个时候老乡还留着剪了辫子的长发,很穷,吃的极差,但因为刚解放分了田地,心情很安定。
第一次油画人物肖像写生
在油训班课堂上,马克西莫夫让学生们了解了素描的结构和西方油画色彩体系的要求,每个人都跃跃欲试想实践一下。我记得第一次用油画笔在画板上画写生肖像是在我们的宿舍里,画的是附中的女孩叫任翠然,形象、生动、可爱。当然更多的是同学们互画素描,我还保留着那时候我给蔡亮画的素描肖像写生,现在看来多么幼稚,但又多么认真啊!
坚持不懈的动力之一 来自老师马克西莫夫
最让学生们兴奋的莫过于看老师作画,马克西莫夫常在我们面前作画,笔笔到位,很快就出现效果,真是痛快。我记得有一次在近郊温泉上了一个月的外光写生课,我们分住在老乡家里,天气很热,午睡之后,我们走到外面,只见马克西莫夫穿着背心,顶着炙热的太阳,背后插一把白布遮阳伞正对着巷子里的黄土房子画着。看来,他根本没有休息。为了捕捉自然的瞬间光色变化,为了抓紧时间,他从不睡午觉,投入地画画,忘记周围的一切。多年以后,当我画得累了,也偶尔想起当年老师的样子。俗话说“身教胜于言教”,这也是我坚持不懈的动力之一吧。
毕业创作 老师的点评对我打击很大
马克西莫夫要求我们画一张情节性绘画作为毕业创作,为了确定题材,我反复了多次,总是不够满意。
1957年,中国和苏联成立了混编登山队,首次登上了新疆帕米尔高原的慕士塔格峰,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于是,我决定选择中苏联合登山这个题材。为此,我做了多种准备,先画了身穿登山服的运动员的素描,又请当时美院附中的混血同学做模特写生,然后再去八达岭画冬天的雪景,还画了模特穿上登山服在雪地里的写生。重点画了雪天中,天光和雪的反光生成的复杂色彩关系在人物衣服上呈现出的色彩状态。忙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毕业创作《登上慕士塔格峰》。
创作完成后自己并不满意,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水平也不过如此。大家的毕业作品集中在一个教室里,请董希文先生来讲评,他对我说:“你的画气不贯”,这句话对我打击很大。董先生的感觉很准,一语中的。中国画讲“气”,我没有做到整张画气的贯通,说明造型、色彩以及画面的处理做不到浑然一体,表达得吃力、生涩、不顺。我清楚自己的水平,深刻地感觉到未来的油画之路还相当漫长和艰难。
我与《开国大典》的那些事
1949年国立北平艺专的学生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那时候,我15岁,一年级。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学生会搞“红五月”创作活动,每个学生都要画重大题材的创作。我没学过创作,也不会构思,但是去天安门看开国大典是我难忘的经历。我画了一个开国大典时升旗的场面,近景是乐队吹号的局部特写;远景是升国旗,有点像宣传画。画得乱七八糟,很不好,别人看了也说不像样子。画虽然不好,但是“开国大典”却与我结缘。中国革命历史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董希文先生的《开国大典》,作为董希文先生的学生,我和这张画有过值得回忆的渊源。
董希文先生的《开国大典》这张画命运之扭曲可称中国之最,“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革命历史博物馆要求董希文先生把《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换成董必武,董先生只能遵命。1972年,《开国大典》面临第二次被改,但是董希文先生患癌症住院,不可能改画了,别人也不能在他的原作上动手。我和赵域奉命为革命历史博物馆临摹董希文先生的《开国大典》,在这张临摹画的构图上,去掉高岗,刘少奇改成董必武,原画中的林伯渠露个头部,现在要把他改成无名之人。这张《开国大典》由我和赵域共同临摹,我画人物,赵域画其它部分。临摹接近完成的时候,革博从医院把董希文先生接来,董先生撑着病弱的身体看了画,笑着说:“还不错”,指出主席的脸有点方,可以再饱满一些。回去后不久 ,董先生就去世了。《开国大典》是一张壁画式的油画,董先生画的人物不仅像,而且色彩饱满,用笔爽快。虽然我们临得还不错,但是我知道,自己达不到他的水平。
“文革”以后,历史人物被平反,《开国大典》又要经历第三次被改的命运。董希文先生的原作当然不能动,革命历史博物馆又开始在这张临画上打主意。当时我正好有事外出,就请闫振铎在我们临的那张上恢复董希文先生最初画的样子,高岗、刘少奇、林伯渠都出现了,现在革命博物馆展出的《开国大典》就是这一张。
文化大革命不仅改写了这些建国元勋的命运,也几次三番篡改了一张艺术作品。在黑暗的中世纪宗教国家发生这种事情不奇怪,但是在中国恐怕是绝无仅有。这种艺术为政治服务到甚至不惜牺牲艺术品的做法,对艺术家来说是多么可悲,在人类艺术史上又是多么可笑。
“文革”艺术现象实录 我一生中画得最大的画
那是一段荒诞的历史,中央文化组居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改画组,我是改画组负责修改毛主席头像的人,没想到我的肖像画水平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文革时期各地都需要画领袖像,需要画革命题材的历史画。1966年中央美院还举办了“毛主席肖像画学习班”,我们都是那里的教员。工农兵人人学油画,涌现出众多业余画家。他们画的大部分是宣传画,构图简单,色彩单一,红、光、亮为主调,素描倒是提高了。我记得1976年我曾在邢台一条大街的路口,画了一张18米高的毛主席像。这大概是我一生中画得最大的画,我的助手就是不会画画的俄语老师。
第一次出国看欧洲原作 伦勃朗是我的至爱
1979年9月,我随中国美术教育考察团赴西德。这是第一次出国,除了五十年代看过俄罗斯画家的作品,我没看过欧洲油画原作。这次虽然来去匆匆,但是很多艺术家的作品,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伦勃朗,作品色彩强烈、好看,用笔奔放、老到,非常有力量,真是我的至爱。
画廊老板要给我办绿卡
1982年我在美国呆了一整年,各大博物馆都看过,仔细研究了西方艺术的发展脉络。我了解到自己油画的问题所在,也找到了提高水平的办法。这时恰逢一位画廊老板让我画一张肖像,我就按照自己对油画新的理解,着重实践突出体积和空间,加强边线处理,使作品的层次厚度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画完后,美国画廊老板很惊讶,他没想到一个中国油画家能如此准确深入地表现绘画的对象,他提出让我留在美国,用“技术人员优先”法则为我办绿卡。我没有同意,我认为为画廊画画毫无意思,我要画自己感兴趣的题材。我拒绝了他,年底我准时回到中国。
学习油画的难度和残酷
油画技术对西方人来说不成问题,就像笔墨对中国人一样。伦勃朗同时期,我只了解比利时的凡代克、鲁本斯这三大家。在荷兰博物馆我看到和伦勃朗风格差不多的画家有很多,以前全都没听说过。他们的风格跟伦勃朗相似,也是透明画法。仔细看他们的画比伦勃朗确实差一点,也正是这一点差距导致这些画家从艺术史中消失了,这就是学艺术的残酷性。我们每个人都不能降低标准,只能力求做到最好,不能凑合。学习时一定要选择历史上最好的画家,并且要经常研究那些最好的画家里最好的作品。这点是不能含糊的,这就是学艺术的难度。第一:每个人必须有最高的要求,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要求不能降低,心目中要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第二:达不到最好就退出历史,学艺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这个职业的特点不是谁规定的,是历史形成的。
怎样理解油画这个画种
油画这个品种为什么吸引人?美在何处?因为它的基础是真实,在素描中称为体积空间。体积需要三维空间,三个面才形成一个整体,所有物体之间要连起来。画画时常说空气把人物连起来 ,意思就是所有的边线跟背景都能做到浑然一体。要画出立体感,无论远近都能立体的处在一个空间之中,才能有造型上的美感,这种美感发展到抽象美就是层次的丰富和厚重,也叫力度。 感悟到这种抽象美,才能画好油画。如何能感悟呢?画素描而且是那种全因素的素描,里边有立体空间、结构、明暗关系。素描画的好的人,才能领悟到这种油画的抽象美。对于一张好的素描的评价,经常是用生动、整体这样的语言,这实际上是符合形式规律的,就是具有抽象美的。
研究油画的色彩就是要懂得光照下的色彩,而不是概念中的物体本色。色调、光源色和谐的色彩,表现体积浑厚的有力量的美,西方油画的美感就是由此而来。虽然有人认为西方追求真实的艺术品种都落后了,但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喜欢具有真实感的油画,因此我称油画这个品种为通俗的画种。(文章摘自《靳尚谊全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