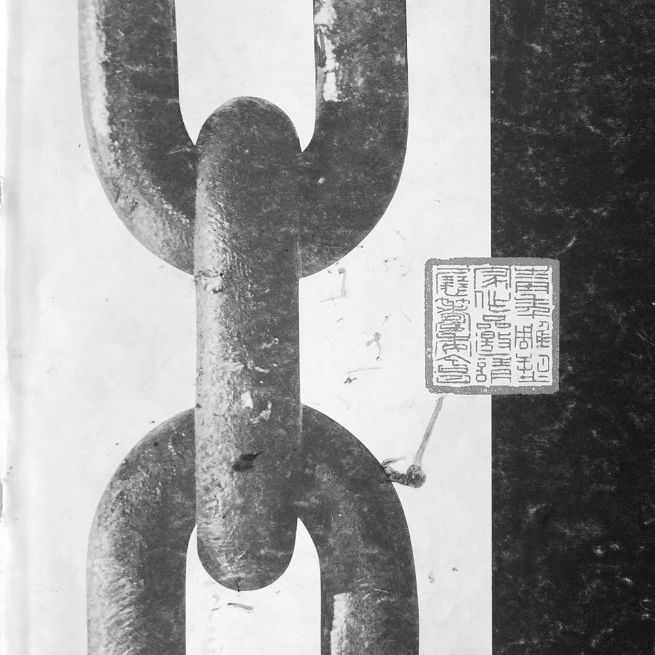中国古代山水画中的境象,在西方人眼中是“透视学之前的世界”,似乎比文艺复兴以来讲求焦点透视的“视幻空间”落后。然而被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称为“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坐标”的北宋沈括,却批评了画家李成类乎焦点透视的“仰画飞檐”,指出这是不懂得“以大观小”和“折高折远”、“妙理”的缘故。
此例似乎可以表明,在观察和表现世界上,古代中国画家独具手眼,未必落后于西方,不是不能“仰画飞檐”,而是不去“掀屋角”,今人更不必缺乏自信。最近,《美术观察》的编者提出一个问题:美术理论建设与“他者眼光”的关系。确实,20世纪以来,无论美术基础理论建设,还是美术史和美术批评,都存在一个卓然自立与它山之石的关系。
这是因为,百年以来中国艺术与文化的发展,既离不开中国传统,又置身于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历史条件下,所以在论及美术如何发展时,鲁迅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对于美术理论,各位先知的认识也大体如此。
20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现代美术理论的建设,除去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外,大体离不开三个来源。一是当代改革开放的美术实践提供的新知,二是传统美术史论优秀传统的继承,三是外国美术理论有益因素的借鉴。
回顾近三十年来美术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在总结当代改革开放美术实践经验和继承传统美术史论优秀传统方面虽然也有收获,但论其规模和影响都远不如对西方美术史论批评的引进、移植和借鉴。当然,引进的理论中,一种是纯理论形态的成果,一种是美术史研究中的理论。
纯理论形态的引进,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萨特、马尔库塞的理论著作。第二类是西方现代的文化理论、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比如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理论、苏珊·朗格的“生命形式”理论、阿恩海姆的“视知觉”理论等。
上述两种理论之不同,在于“西马”的文艺理论,对于艺术社会性论述为多,对艺术的社会本质有深刻的认识,但对艺术本体的论述有所欠缺。而西方现代的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从不同角度接触了艺术本体问题,在不同层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并没有能够阐释中国美术理论中的独特问题。还有一种来自西方的美术理论,这就是西方美术史家的美术理论观点。它是随着美术史著作与方法的引进而引进的,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影响不断扩大。这些西方专家译介过来的成果,他们来中国做的学术报告,他们对中国年轻学者的指导,都产生了不小影响。
西方的美术史家,包括西方研究中国古今美术的专家,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们钻研学术的精神、他们对中外交流的贡献,都应该给以充分评价。也应该看到,他们治史中的理论见解,有些反映了不同民族美术的共同问题,甚至揭示了客观真理的一些方面,并没有他者的局限。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的诗句提示我们,了解山外他者对庐山的观察,可以克服自己的局限。西方美术史家的“他者的眼光”,无疑也对开拓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很有启发,何况实现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呢。
不过,历史的经验表明,理论的建设,在今与昔的关系上,只能以继承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为基础,对西方学者所见不及的优秀民族传统,尤其需要珍视。在中与外的关系上,又不能不提倡学习借鉴外来文化而反对生搬硬套,关键在于消化吸收,在于保持民族特色与民族文化价值观念,而不是丢掉本民族的好东西
我本身是搞美术史的,主要研究中国美术史,所接触的外国专家的理论,不少是见于美术史著作中的理论,包括西方研究中国美术史专家的美术理论观点。突出的感受是,他者眼光,一方面打开了我的眼界,启发了我们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反映他们对中国艺术文化的了解还不很够,他们的认识难免受西方传统认识的局限。
最早对国内美术界发生影响的贡布里希是英国的美术史家、艺术心理学家和艺术哲学家。他的《艺术的故事》、《艺术与错觉》和《图像与眼睛——图画再现心理学的再研究》等著作,颇有真知灼见。其“预成图式”的理论,深刻地阐明了视觉与文化的关系,对我们认识传统图式的继承与发展很有帮助。然而,他在论述中国古代山水画的时候,却忽视了中国画家对传统图式的高度重视。在《艺术发展史》中他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中国艺术家不是走到室外,坐在某个对象之前对之速写,甚至通过一些奇怪的方式学习艺术,即沉思默想并专注于如何画松树、如何画岩石、如何画云这些让他们获得技巧的东西。他们通过研究名家之作入手而不是从自然入手来学习艺术。
其实,不少中国画家虽然从临习古人入手,但他们不仅重视师古人,而且特别看重有了来自古人“预成图式”之后的师造化。不过中国古代画家心目中的造化,不仅仅是客观世界个别对象的形貌,而是大自然的生成、运动与对立统一的内在联系,以便“万趣容其神思”地“畅神”。不难想象,贡布里希的上述论断,是对比西方模拟自然的传统而来,以致对中国画家的师造化缺乏深知。
来华较多的高居翰,是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绘画史学者之一,80年代以来频繁来我国访问,出席学术会议、讲学交流。其《中国绘画》、《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山外山》、《气势撼人》、《不朽的林泉》和《画家生涯》的译本先后在两岸出版,影响十分广泛。
他善于从社会学史的角度,研究绘画的意义与功能,寻找绘画发展的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把对美术的研究从内部引向外部,从大家名家引向无名作品,把画家的生涯与市场的需求联系起来,把个案研究与全局性思考结合起来,也常将中国绘画史放在一个宏大的世界背景之中,从而有所发现,有些论断确有一定深度。
然而,高居翰的《关于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后历史”的一些思考》却是典型的“中国绘画史终结”论。以之比较德国著名的美术史家汉斯·贝尔廷的“艺术史终结”论,既可以看到所谓的“终结”都是指单一的、线性的艺术史或绘画史,也不难获悉高氏观察中国绘画线性发展成熟的标准是真实再现自然世界技巧的完善,其着眼点同样沿袭了西方模拟自然的传统。
唯其如此,高居翰虽然看到了后期中国绘画史上那种不直接师法自然的风格创造,却不太理解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与写意笔墨,他在莫菲讲座丛书“中国绘画的三种另类史”中批评“中国绝大多数理论家和批评家以及阐释其艺术实践的艺术家中间写意优于写生这种看法已呈现出教条的特征”,并且提出“写意是中国晚期绘画衰落的原因之一”。
高居翰之所以一概否定17世纪以降简约而率意的写意画风,就在于他没有从绘画本体着眼,不认为写意是文化问题和趣味问题,更没有把写意的提炼与伪写意的粗率认真区分开来,看不到真放中的精微,而是认为市场的需求导致了简约率意缺乏质量的写意画的发展。如果认真地研究金农、李、吴昌硕等人的写意艺术,谁都不会认同这种比较表面和片面的看法。
世纪之交以来,另一位对中国美术史研究发生影响的柯律格,是英国研究中国美术史和物质文化史的年富力强的重要学者。他的《长物志: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明代中国的园林文化》尚无中译本,而《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中国艺术》和《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已经翻译出版。
柯律格的研究强调艺术作品影响社会环境同时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打破了前人著作以美术家美术作品为主的研究角度,从看重作品的艺术质量转到着重其传播途径,从研究单个美术品转到研究特定图像在不同美术门类以致其他视觉文化中的分布和演变。他从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角度对美术史的研究,新颖而别致,开拓了研究的领域,对我们很有启发。他不仅研究“画”,而且研究“图”。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审美价值的“画”和不具有审美价值的“图”,虽均属视觉文化,但性质不同,各有功能,长期以来并行不悖,不存在谁压倒谁的主流地位的问题。柯律格却称:“到1707年为止,作为个人表现的绘画(按即画)较之于作为地形、地貌记录的绘画(按即图),似乎已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这一论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的《雅债》,从人情往来与礼物交换的角度重新审视画家文徵明,把美术史作为更宽广的学科,并试着与其他领域所关心的知识课题相联结,不但揭示古代文人雅士在世俗生活中的书画应酬这并不超脱的一面,而且揭示了“雅债”这种友谊式的应酬并不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现象。不过,也正像作者自己深感不足的那样,本书对于文徴明艺术的风格与笔墨却略而不详。
我不赞成用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待当下的美术史论研究中的问题。艺术史论的研究,既有跨文化的一面,又有民族价值观和民族特色的一面。不过,需要明确的是,他者眼光,虽对我们有启发,但不能代替我们以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被动仿效照搬来的鞋子,未必适合自己的脚。
英国美术史家苏立文,曾经来中国参加抗日,是20世纪系统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的第一个西方学者,是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泰斗,著有《东西方美术的交流》、《中国艺术史》、《山川悠远》和《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早已为中国的美术界所熟知。
他亲身接触过很多中国美术家,也颇有20世纪中国美术品的收藏。他为西方了解中国艺术所做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但引人注意的是,他对徐悲鸿的选择并不理解,以致认为徐悲鸿“与毕卡索和马蒂斯同居于巴黎,他似乎对此完全漠视”,认为徐悲鸿的绘画也“缺乏刘海粟和林风眠那样的热情和虔诚……几乎仅仅止于合格而已”。
然而这位热爱中国的学者,却能够十分客观地看待中西的交流中“他者的眼光”。他在《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自序中说:“作为局外人,无论怎样好意,都不可避免地缺乏任何受过教育的中国读者所具有的那种天然的有关中国文化、历史和艺术的知识,但是我相信,来自彼种文明的作者,所写的论述此种文明的艺术的书,也自有它们的价值。”
对此,我们更应该加强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自觉,并且以卓然自立的精神在美术理论的建设中发挥它山之石的积极作用而避免外国专家也不欣赏的盲目追随。
整理:郑丽君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