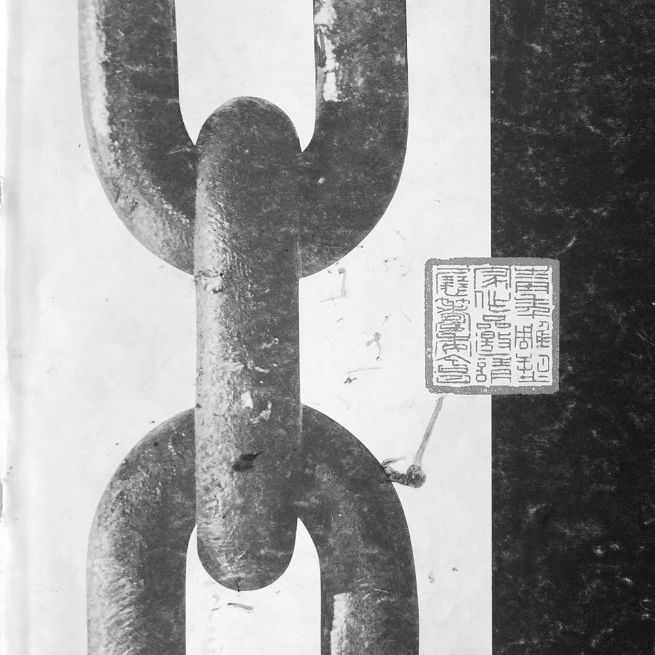文化自觉,是21世纪的中国立于世界并对世界做出建设性贡献与责任担当的文化意识形态。正如提出这一概念的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这四个字也许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在当下伴随互联网技术日益强大的视觉文化情境中,美术教育在“文化自觉”的意识形态建构中承担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
一、大数据时代新思维、新方法的启示
著名的复杂网络研究学者艾伯特一拉斯洛·巴拉巴西在新作《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中,运用大数据技术的前沿成果和对西方社会历史多领域的研究为据,提出“爆发”定律:“无论我们观察哪种人类活动,都会发现相同的‘爆发’理论:长时间休息之后就会出现短时间的密集活动,就像贝多芬音乐中悦耳的小提琴被雷鸣般的鼓声打断一样。事实上,从人们对维基百科的编辑,到货币经纪公司的交易;从人和动物的睡眠模式,到魔术师为了保证魔杖时刻停留在空中而做的小动作,所有的一切都证明,爆发,无处不在。”作者通过大数据分析认为:每个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但我们不知不觉地遵循着一个规律,即一定的缓慢节奏或无变化阶段之后往往是“爆发”的出现。显然,这一规律性总结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常作为口头禅的“暴风雨前的寂静”、“从量变到质变”,都表达了对这种大自然生命节奏的认识。但针对当代人类文明的信息全球化、文化多元交流的特点,爆发理论将“优先级”与“爆发”联系起来,启示我们在互联网时代美术教育的实践方法论思考。
所谓“优先级”,源于这样一个管理学的案例:在1903年的一次聚会上,一位重视效率问题的企业主接到一位公关研究人员的提议:“我能提高你手下人的效率和你的产品销售量,只要你允许我跟每个部门主管谈上15分钟的话。”三个月后,企业主付给了这位名叫艾维·李的职员3.5万美元,以酬谢他对企业效率三个月来的明显提高做出的贡献。而艾维·李与那些企业各部门负责人的一刻钟谈话中所做的,就是要求每个部门负责人在每天离开办公室前,按重要程度的顺序列出第二天必须要做的6件事。第二天做完一件划掉一件,没有完成的,接着写到下一天的清单中。这就是许多管理学书籍中经常提到的“优先清单”。在此,将“优先级”与“爆发”联系起来,则意味着在今天这个信息超量、多种文化交织冲撞的生活情境中,将“什么”作为优先项,就可以将“爆发的节奏”与“什么爆发”联系起来。巴拉巴西从这一角度提出“爆发”定律的野心在于:通过大数据时代研究人类行为规律的新技术、新思维,建构预测未来的可能方法。“不管我们是在研究今天的事情还是16世纪的事情,我们最终面对的问题都一样:如果过去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未来也就难以预测。但是,如果我们的过去突然变得清晰起来会怎么样?那么不管是人类的未来还是社会的未来都将不再是个谜团。所以,为了能够看到未来,我们必须及时回到过去。”即分析过去、当下我们将什么置于“优先级”,我们就可以预测未来。“我们正处在一个聚合点,在这里,数据、科学以及技术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那个最大的谜题—我们的未来,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
就本文提出的美术教育与“文化自觉”的问题思考来说,如果我们将对历史、对当下美术教育的现状分析,与走向明天的中国美术教育有效建构“文化自觉”意识的目标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对起步于当下的美术教育实践的方法论思考,会通过“何为优先级”的解读,而为中国文化在21世纪人类文明新环境中实现振兴的“爆发”做出主动的准备。
中国传统儒道释哲学皆将审美作为修养身心、塑造社会人才或超凡出世人格的文化实践途径,鲜明的社会伦理价值论、内修心性论的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国审美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等以宗教信仰为凝聚点的文化系统的独特品质。正如李泽厚分析孟子思想的伦理主义特征时所言,中国审美文化“一方面它强调道德的先验的普遍性、绝对性,所以要求无条件地履行伦理义务,在这里颇有类于康德的‘绝对命令’;而另一方面,它又把这种‘绝对命令’的先验普遍性与经验世界的人的情感(主要是所谓‘恻隐之心’实即同情心)直接联系起来,并以它为(心理情感)为基础。从而人性善的先验道德本体便是通过现实入世的心理情感被确认和证实的。超感性的先验本体混同于感性心理之中,从而道德理性不离开感性而又超越感性,它既是先验本体同时又是经验现象。”这种“超感性的先验本体混同于感性心理之中”的审美文化特点,集中体现在儒家“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道禅美学“乘物以游心”(《庄子·人世问》)的通过审美的精神修炼路径,如此而区别于西方审美文化通过“形式创造”抵达精神升华、审美自由的从宗教信仰到个体自觉的自我救赎路径。如此,就当代文化处于全球性交流的信息繁杂与超量;多元文化碰撞及价值观冲突的情境下,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与“文化自觉”的关系建构,需要关注将审美感性的民族文化经验养成;通过视觉文化的社会性价值观塑造作为“优先级”,这正是大数据时代新思维对我们的实践方法论启示。
二、实践情境中的方法论一一“优先级”
视觉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它越来越趋于把那些本身并非视觉性的东西予以视觉化。”如此,所谓“视觉的”就不仅是一个关于形象识读的问题,更是文化意识形态问题,即人们用如何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去识读、理解、想象、把握一个计划、目标、观点、现象的“形象”。或者说,面对丰富的生活世界,一个人对形象的直觉反应是如何“自动地”将某种趣味、文化理解方式置于“优先级”。在视觉文化时代,如果说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自觉意识培养必然与民族文化的视觉传统与符号系统发生联系,那么,通过美术教育塑造形象的感受力与想象力,建立视觉体验的“优先级”文化价值观,即是美术教育与“文化自觉”关联的核心使命与实践。人是习惯的奴隶,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反思我们的当下习惯,以求与时俱进;一方面我们又要将习惯看作是“价值”的载体,在历史的纵深中把握它的文化性格与符号意义。通过美术教育使受教育者养成“习惯”,就是使他们的视觉生活经验与表达,成为自觉的价值观实践,为中华民族在未来的“爆发”积累能量——正如孔子在教育理念上特别推崇的: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针对20世纪中国美术变革、美术教育变革的历史过程,中国视觉文化传统中的这样两个特点,需要在今天提出再思考:
1、关注传统经典,并总是在“更新”、“我法”的意义上理解传统。中国传统文人艺术重视对前人经典作品的“仿”,但我们今天看17世纪的董其昌、恽寿平、石涛、朱耷等人对14世纪倪瓒作品的仿作,感受到的第一印象不是仿者仿得如何“像”,而是作者在其中对“我法”的运用。即通过使用“我法”之仿而与前人实现人文精神的沟通,而不是表面技术、趣味的模仿。同时,董其昌画论推崇学习前人经典的“集其大成,自出机杆”论,与石涛画论“一画之法,乃自我立”;“指而为吾法也可,指而为古人之法也无不可也”。在哲学理念与艺术价值关怀上的殊途同归,正标示了中国视觉文化传统中那种深沉的宇宙意识和生命个体与文化史关系把握的人文品格。这个品格进一步可以表述为:
2、通过对经典“符号”的运用与更新,寄托“百年枉作千年调”(《六如居士全集》卷二)的生命价值审美。“中国文人画有普遍的担当意识,不是道统式的担当、道德式的担当,而是生命的觉解。”从孟子“以意逆志”的审美伦理主义到文人画通过笔墨意象的生命觉解,贯穿其中的,正是中国审美文化的个体修养心性论、生命担当价值论的人文精神内核。
注意:这两个特点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变革的语境中,在割裂“超验本体与经验感性混同”的视角下,被更多地进行反面否定性的解读与批判。“仿”成为因循保守的代名词;“千年”传统被视为必须革命之、改造之的“旧语言”。而实施这一革命所使用的武器,则是西方的“写生写实”、“形式自律”的造型技术与美术观念。其在特定的情境下如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为中国美术文化的鼎新革故劈开了全新的视界,另一方面也强力地遮蔽了许多……正是西方美术之车载了中国美术走上现代转型之路,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变革、美术教育变革的几个关键时段中,美术文化的优先级是“西方模式”。今天,中国美术需要从20世纪美术变革的“乘车体验”中,重新反思自己实践方法论的“优先级”设置,以求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实现源自自身文化建设需要的中国美术现代性的道路指认。而这一历史性的机遇,却恰逢21世纪大数据时代视觉文化的到来。
我们已然告别了对自己传统的“革命/保守”;对中西文化“传统/现代”的非此即彼二元论意识形态,作为美术教育实践方法论的“优先级”思考,是力求在互联网时代探索美术教育建构视觉体验、视觉想象、视觉思维、视觉表达的文化自觉价值观,以开放的胸襟在与人类文明多样话语的积极对话中彰显“我法”的魅力,迎接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爆发”的时刻。
如果上述对美术教育与文化自觉意识建构的“优先级”方法论的描述具有合理性,其实践,则还有待在知识话语体系建构、跨文化话语实践研究、教育教学范式与方法建设等一系列基础性工作领域中展开。这是中国美术文化建设在21世纪的新课题,它的影响力将与20世纪初“五四美术革命”的影响力不相上下。
原文载于《美术教育》2015年6月
整理/李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