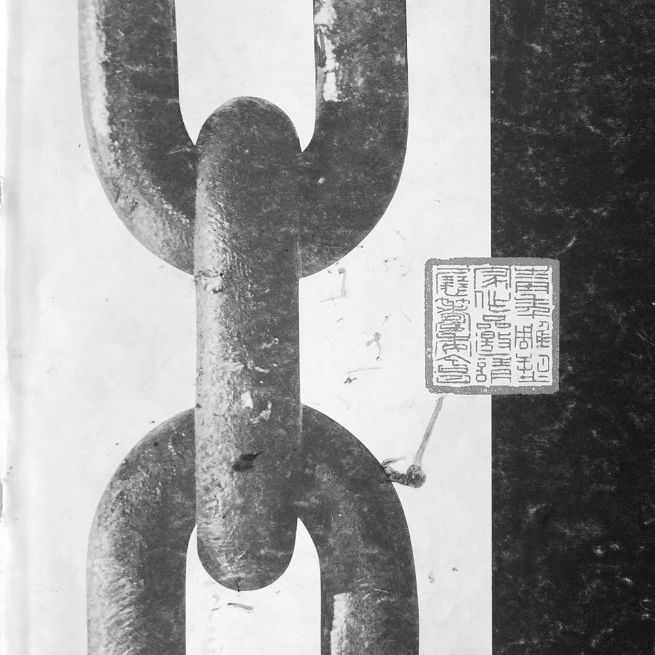长期以来,中国人物画固守传统题材和古人形象,到了明清两代,则更加远离现实。这个现象令人费解。有些人便因此认为中国画家没有描绘现实人物的能力。事实并非如此。大家知道,清末大画家任伯年笔下的肖像画,寥寥数笔,神完意足,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物。有些人则认为中国的人物画家历来以粉本相传,不敢自创新稿,所以只见古人,不见今人。其实,粉本只能束缚一般画工和低能画家,并不能在富有创造性的画家身上起作用。那么,明清著名人物画家如戴文进、张平山、仇十洲、陈老莲、黄慎、闵贞、任熊、任颐等人,为什么都不屑为现实人物费笔墨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国人物画的审美传统上去找原因。
人物画是早期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以“助人伦、成教化”为目的的。《历代名画记》著者张彦远在叙画之源流时说:“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所以,封建王朝设“明堂”或“凌烟阁”为开国功臣造像,彪炳他们的功勋。嗣后又发展为大规模寺庙壁画,为宗教宣传服务,用以教化芸芸众生。从一些存世的图画遗迹来考察,早期的人物画大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那么,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人物画逐渐脱离现实了呢?许多美学研究者认为,大概是在两宋山水画发展成熟以后,人们对绘画的审美要求起了变化,助人伦、成教化的劝善目的,逐渐让位给了怡情养性的审美情趣。
宋郭熙《林泉高致》云:“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之本意也。”这是早期山水画论,标志审美情趣的转变。这个转变,还应该追溯到六朝至唐那一段绘画和文学相结合的历史,知识分子逐渐从画工手里掌握了绘画发展的方向,从而开创了绘画的新时代。被苏东坡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就是一位诗画结合的代表人物。经过五代两宋的荆、关、董、巨,刘,李、马、夏,到元四家黄、王、吴、倪,山水画一马当先,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此时的人物画虽然由帝王将相走向须眉仕女,逐渐脱离人伦教化的功利目的,究竟不能和怡情养性的诗化境界同步前进。
明代文微明评论人物画说:“人物画不难于工致,而难于古雅。”又说,“盖画至人物,辄欲穷似,则笔法不暇计也。”此时山水画又经历了一个时代,尚性灵,追笔墨,文人的意趣更浓了。文说这番话,指出人物画不能追随时代审美思想,基本是合乎实况的。按照文的说法,人物画只求工致和穷似,不求古雅和笔法,如果是指吴中仇英以下诸人,可能是中肯的,但是,从浙派诸人戴文进、吴小仙、张平山的作品来看,工致和穷似或嫌不足,古雅和笔法却无可非议。往后,陈老莲的造型和笔墨,可说已达到很高的境界,而陈的后继者任伯年则更为出色,他所画的吴昌硕、高邕、仲英几幅肖像,既极穷似,而又笔精墨妙,可说已臻化境。
因为有任渭长、任伯年、吴友如、钱慧安等活跃上海画坛,人物画在清末出现过一次中兴景象。但是,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和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的革命思潮是格格不入的,因而只能算是封建艺术在其没落时期的一次回光反照。反封建的“五四”文化运动使许多美术青年投向西方,引进油画艺术,打算另建新的绘画体系,以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他们经历半个世纪的活动,西方绘画在新的知识分子中培养了一定的欣赏基础,可是中国画并不因此被挤出历史舞台,倒是有些油画家认识到中国画的民族特色和伟大生命力,最后转向灿烂的民族传统,改变自己的艺术方向。尽管如此,人物画在题材内容方面脱离现实生活的状况,仍然是和现实的社会进程不相适应的。有鉴于此,有些画家便尝试用中国的笔墨来表现现实人物,他们最初的尝试,有的只重笔墨,不重生活;有的只重生活,不重笔墨。前者不能为新欣赏者所接受,后者不能为老欣赏者所承认。显然,这是形式和内容暂时不能互相适应的现象,和京剧现代化的最初阶段有点相似,尝试失败,并不说明此路不通。
梅兰芳在“五四”之后试演过时装戏《一缕麻》,上海新舞台试演过时事戏《阎瑞生》,说明新内容毕竟要冲破旧形式,在新的精神领域占领一席地。此时中国人物画的现代化,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了。
中国人物画长期脱离现实生活,既受助人伦成教化的思想约束,也受发展到高峰的技法的控制。时至今日,思想的约束早被冲破,而表现技法的传统审美习惯却不易摆脱。实践所要解决的问题,离不开技法的创新,但创新又不能离开民族传统另起炉灶,必须做到既工致而穷似,既古雅而有笔法。有了生活,做到工致穷似似乎不难,难就难在古雅笔法。所谓古雅,从今天的要求来看,当然不是文微明那时的古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笔法。我认为,现代中国人物画就是要达到生意盎然而又笔精墨妙,和发展到高水平的山水花鸟画并驾齐驱。在创新之中不能以只顾题材内容反映现实为满足,还应当充分尊重形式美感的民族标准。
有些只信“内容决定形式”的论者,往往只顾题材内容这一面,忽视中国画表现形式的高标准。三十年来,由于狠抓内容第一,不重视作品的艺术性,使人物画停留在“下里巴人”的地位,攀不到“阳春白雪”的高峰上去。我们应该好好温习一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意见:“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一九八O年第二期《中国美术》上,我总结自己在创作道路上走过一段“图解式”弯路,指出我那幅《中华民族大团结》是政治概念的形象化,《北平和平解放》是新闻报导式的图画。我的意思并非否定图解式绘画的社会作用,而是不满足于局限在图解生活。如果人物画停留或局限在图解生活现实和政治报导,不去探索人们对人物画的更高审美要求,那么,高度发展的摄影艺术就可以取代它。
中国人物画的职责在佛教壁画兴起以前,基本是助人伦成教化。曹植对此解释十分明白,他说:“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臣死难,莫不抗首……是知存乎鉴戒者何如也。”由此可见,人物画鼎盛时期,莫不为封建道德服务。魏晋以后,佛教艺术所反映的思想,超不出善恶、惩戒、因果、报应等人伦教化范畴。所不同者,由宫廷明堂扩大到普天下的寺院佛殿,群众性增强了。唐代山水画从人物画的衬景中游离出来,开拓了反映生活的新境界,《林泉高致》说:“画山水有体,铺舒为宏图而无余,消缩为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体,以林泉之心临之则价高,以骄侈之目临之则价低。”因为:“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须远而观之,方见得一障山川之形势气象。若士女人物,小小之笔,即掌中几上,一览便见,一览便尽。”人物画在这个时期,虽已超出人伦教化范畴,却成为掌中几上的玩物,难以和山川气象的宏观相提并论。
历史上的卫道论者,对中国画这个新的变化表示不满。明代宋镰的话很有代表性:“古之善画者,或画诗,或画孝经,或貌尔雅,或像论语暨春秋,或著易像,皆附经而行,犹未失其初也。……世道日降,人心寝不古者,往往溺于车马士女之华,怡情于花鸟虫鱼之丽,游情于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
今天也还是有人对这条新的审美路线表示怀疑的。最近,山西有位画家写信给我,附来一篇论文,对当前山水花鸟之类文人画的“泛滥”,表示忧虑,主张大力提倡人物画,恢复“助人伦成教化”的遗训。我复信说:“你忧时伤世,为人伦教化呼吁,足见用心之挚。近代中国画的发展,有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山水花鸟画在历史上出现,标志画心与诗心的结合,是精神世界的扩大,是中国文化艺术的进步,不是衰退。今天提倡人物画,决非为了排斥山水花鸟画。”
从这位画家的观点看来,提倡人物画,就是为了恢复助人伦成教化的宣传教育目的。照这么说,人物画的职责,除了助人伦成教化就不能起到怡情养性的作用吗?当然,不能怀疑他的主张是为了恢复封建统治,可以理解他的出发点是出于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目的,但这和助人伦成教化的封建政治目的并无共同之处。
最近读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他对中华民族的艺术文化作了一番从古到今的巡视,窥见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其中一段阐述中国山水画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最后到达浪漫主义的八大、石涛,这个脉络和历来画论的思想发展是一致的。人物画在这段历史中,发展缓慢,退居下游;明清两代,画的多是古衣冠、古人物,停留在无我之境,只有陈老莲画的陈渊明和水浒英雄,任伯年画的锺馗和风尘三侠,反映出画家对他们笔下人物高尚情操的钦慕之情,接近有我之境。这种主观情感的表现,和人伦教化的古代封建意识是显然不同的。现在有些人主张把人伦教化的古老审美传统移用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时代来,或者把人物画的衰落归罪于山水花鸟画的兴起,岂不是把事物的发展看得太简单了吗?
有人问现代人画古代人物和古装仕女,是不是历史倒退或时代错觉?我以为不是。中国戏曲舞台上的传统剧目,都是演的古人古事,我们承认具有借古喻今、评价历史等等审美教育作用,画古代人物、仕女也具有同样作用。在推陈出新的任务中,在传统艺术形式表现现代生活的实践中,戏曲表演程式的束缚比绘画方面还要多一些,所以中国人物画反映现代生活的成果比较大一些,进展也比较顺利一些。但是,如果把三十多年来提倡人物画的成果加以具体分析,应当看到,当前存在的问题还相当多,例如:
一、画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粗糙浮面,不接触事物本质,等同于新闻报导的插图,不能深刻地反映时代面貌。
二、满足于图解政治概念,自以为反映了重大题材,其效果还不及主题鲜明的政治宣传画。
三、一窝蜂,抢题材,报纸上鼓吹什么就画什么,不怕公式化概念化,却怕跟政策跟得不紧。
四、有的追随庸俗趣味,譬如画一对带镣铐的情人拥抱接吻,题曰《刑场婚礼》,还自命为革命浪漫主义。
五、过去画集体创业,现在画发家致富,政策跟得愈紧,作品的寿命愈短。
六、追求表面形似,墨和色搅混不清,有笔无墨,有墨无笔。
七、有的又片面理解笔墨的重要性,一昧练笔,单纯追求所谓形式美,强使形象服从笔墨。
八、画屈原、杜甫,一式明代衣冠,画蔡文姬、崔莺莺,一个脸型,一套服饰。这种颠倒历史,乱用服饰,唐突古人的作品,既有害于审美,也有害于认识和教育的作用。
九、十年浩劫,画花鸟也被戴上黑画帽子,画人物更可以无限上纲,于是,不少人都想躲开这块是非之地。
十、画人物不成,改画山水;画山水不成,改画花鸟;画花鸟不成,改学书法。这一条退路,诱使一些画家走轻便的道路。
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谈谈人物画家的苦经。有些人物画家抱怨文艺领导对人物画提倡不力,似乎还需要继续吃偏饭,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过去大力提倡过人物画,好象现在突然改变方针,不提倡人物画了。这是一种错觉。最近儿年国画市场繁荣,花鸟山水受到宠爱,是因为吸收外汇的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现在大宾馆的室内布置,基本上只请山水花鸟画家效劳,极少请人物画家,难道这可以认为是贬低人物画的作用吗?恰恰相反,这不但不是贬低,而是看重人物画反映时代风貌的特殊功能。我们决不能妄自菲薄,应当信心十足,使人物画担当起更高的审美功能。
有人问,什么是人物画的更高审美功能?可以从上述几个问题的反面来求得答案:
一、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新事,必须以反映这一代人的高尚情操与道德品质为准则,而且要服从造型艺术表现生活的独特手段,即通过视觉的反应,从而打动欣赏者的心灵,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不能以描摹这件事或这个人的表面现象为满足,表面描摹只能起到单纯图解事物的作用。
二、图解政治概念或演绎政策口号,对于海报式的政治宣传画,可能是最合式的,若求之于人物画,难免贬低人物画所应有的审美潜力。这好比舞台上解决矛盾的方法,单靠角色的说教,不靠角色的行动。
三、跟政策、抢题材的风气,多半出子及时反映新事物的好心,关键在于不甚理解人物画的审美职责。在人物画的创作中反映一定的政策思想,也未尝不可,但要正确认识具体政策和政治总方向的内在联系,要了解我们所要表现的是政策影响下的社会动态和人的行为,而不是政策本身,不然画中人就成了政策解说员。
四、造型艺术是否能恰如其分地塑造出现代悲剧人物,譬如怎样表现好“刑场婚礼”这样的题材呢?自从看了陈逸飞的《寒凝大地》,打消了我的疑虑。这幅画真正挖掘到了这个题材的深刻主题。这虽是一幅油画,有它在艺术上的特殊性格,中国人物画是否也能做到如此深刻的审美功能呢?我认为也做得到。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发挥中国画艺术技巧的特殊性格,探索表现主题的新角度。
五、说到画农民,如果单纯画政策,三十年变化多端的经验,足够我们吸取教训了。想当年大跃进,把我们带到了《西游记》式的神话世界。现在的农民又该怎么画呢?生产责任制是个制度,图解不了。那么画发家致富行不行?比如:画一个农民数着钞票走向银行,画农民炕头放着电视机,这些生活现象的确反映了农业新政策影响下的具体变化。但是,光从物质享用的角度来画农村新面貌,岂不是又在叫农民当政策的解说员?要想深刻地反映农村新面貌,决不能把眼光停留在表面现象,而应从表面现象联想到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和历史进程的关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农民相互之间的关系,农民和其他社会人物的关系,从这些关系的总和中来观察和表现农民,这才是根本。
六、追求表面形似,不计较笔墨得失,实际是忽视中国画表现形式的艺术高标准。表现形式高标准是审美功能的重要媒介。我们知道,中国画独具的形式美感,是长期形成的重要欣赏条件,当然也是审美的重要条件。文徵明所指出的古雅与笔墨,正是从这一要求出发,并加以强调的。假使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把“古雅”看成是笔墨情趣的另一词汇,那么就会看到笔墨对于创新的重要性。
七、把笔墨情趣看成脱离内容的纯形式,那是违反艺术规律的。一幅笔精墨妙的图画,所以使人获得视觉的快感,并非由于孤立的形式,而是由于和内容交融着的形式。强使形象服从笔墨,必然导致歪曲形象。
八、美学研究者认为,艺术形象有三种功能:一是认识作用,二是教育作用,三是审美作用。这些都属于内涵的感应默化功能,是不是还有一种属于外在的感官兴奋作用。例如,看了喜剧发笑,看了悲剧流泪,听到好的唱腔或好的表演,情不自禁地发出叫好声,看到一幅精采的好画,使人兴奋得啧啧赞叹不已,凡此种种,感官的直接反应,_也不能不和形象的内涵发生联系,决不仅是单纯的形式美感在起作用。当然,这类反应可以说是审美感受的一种表现。
九、我们承认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发展的一面,也有延续和继承的一面。审美传统也是如此,我们画现代人和新事物,也要画古代人和旧事物。无论画古人还是画今人,都应注意艺术的认识和教育作用。如果这些人物不值得我们敬仰,又何必费笔墨去描绘他们呢。陈老莲画陶渊明和画《水浒页子》,任伯年画锺馗和画风尘三侠,是画家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崇敬,才形之于笔墨的,当然也同时反映了画家本人的个性和人品。我们今天画社会主义新人新事,也应该按照这一艺术规律来选取自己表现的对象。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公式化、概念化、一窝蜂、抢题材的风气,破坏了这一艺术规律,阻碍了人物画到达阳春白雪那样高的审美水平。
十、极左路线对文艺的专政,造成文艺创作十年苍白;国画市场受外贸的影响,花鸟画备受宠爱。人物画家既心有余悸,又遭冷遇,迫使有些人寄情山水花鸟,躲开这块是非之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那种知难而退、见利忘义、热中于名利的人却是可鄙的。
对今天的人物画提出以上的看法,十分粗浅,恳请高见指正。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于北京
本文原载于《文艺研究》1982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