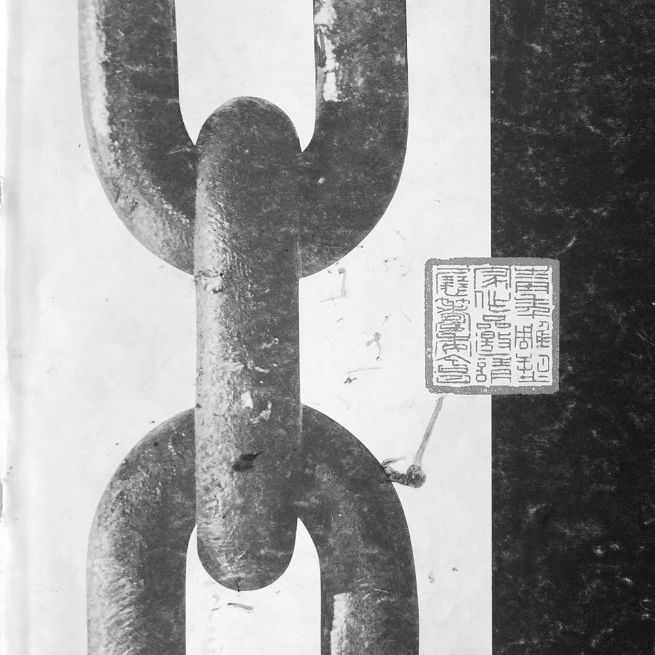一、博物馆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追溯“公共”的意义,我们发现“公共”(Offentlich/Offentlichkeit)一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含义。举凡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场合,我们都称之为“公共的”。如我们所说的公共场所或公共建筑,它们和封闭社会形成鲜明对比。但“公共建筑”这种说法本身已经不仅仅意味着大家都可以进入,它们也从来都不是用于公共交往的场所,而主要是国家机构的办公场所。国家是“公共权力机关”,它之所以具有公共性,是因为它担负着为全体公民谋幸福这样一种使命。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的。在古希腊人看来,公共领域是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因而和必然王国、瞬间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只有公共领域中出现的一切,才能让所有人看得真真切切。公民相互之间进行对谈,从而表达对事物的观点,并使之形象化;彼此差不多的人通过争论,才能把最好的衬托出来,使之个性鲜明——这就是名誉的永恒性。如果说,生的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发生在私人领域(Oikos)范围内,那么,公共领域(Polis)则为个性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公民(homoioi)之间平等交往,但每个人都力图突出自己。亚理士多德所制定的一系列德行只有在公共领域当中才能证明有效,并得到广泛承认。[①]
当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国家和经济的转变是同时进行的。公共领域将经济市民(Wirtschaftsburger)变为国家公民(Staatsburger),均衡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获得普遍有效性,于是,国家消解成为社会自我组织(Sslbstorganisation)的媒介。只有在这个时候,公共领域才获得了政治功能。[②]博物馆作为重要的公共领域,经历了私人占有(dominium)到公共主权(imperium)的过程,博物馆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某种程度上正是社会和国家经济转型的直接体现。
在17到18世纪,美术馆的起源很大程度是源于西方宫廷贵族的、教会的藏品向公众的开放,这种开放真正的背景是平等主义。到了18世纪,卢浮宫的开放就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实现的,它的哲学背景就是平等主义加上民主思潮和启蒙运动的教育功能。在美国早期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中,博物馆和美术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可能取代宗教机构,成为帮助新移民建立一种家庭的和社会的价值的一个重要纽带。所以一个美术馆在一个国家可以成为文化成就的象征,成为精神价值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博物馆和美术馆在结构转型的社会背景里,它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迈向真正的公共性。
事实上,当代美国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教育中心、学术中心,还是休闲中心和娱乐中心。《华盛顿邮报》称:当代美国的博物馆已经成为“新的城市广场”,举办从爵士音乐会到教育研讨会的各种活动,没有任何别的场所能像今天的博物馆一样把各种不同的人聚集到一起。
勿庸置疑,作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公共博物馆,其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具有广泛的教育功能和知识传播功能。那么,博物馆与公共教育之间应达成何种关系才能利于社会的发展?博物馆的公共美术教育该以何种形式展开方能最大地彰显其教育价值呢?
二、博物馆与公共美术教育
早期的博物馆典藏品并不打算做公开的展示,只是反映出典藏者个人的收集兴趣而已。英格兰牛津地区的艾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在1683年设立,堪称世界上最早的这类博物馆之一。1845年英国通过“博物馆法案”,允许乡镇议会运用公共资金设立及维护博物馆。维多利亚女王主政时期,一般大众开始对博物馆产生兴趣,举世闻名的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便是1852年在伦敦设立,也是全球最早的公共博物馆之一,该馆以装饰艺术与工艺品为主,至今仍被视为全球第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因为该馆当时已将公共教育列为营运目标之一。
1880年美国学者詹金斯在其《博物馆之功能》一书中明确指出:博物馆应成为普通人的教育场所。1906年美国博物馆协会成立时就宣言“博物馆应成为民众的大学”。1990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在解释博物馆的定义时,将“教育”与“为公众服务”并列视为博物馆的核心要素。美国博物馆协会的总经理和首席执行官小爱德华·埃博(Edward H. Able, Jr.)认为:“博物馆第一重要的是教育,事实上教育已经成为博物馆服务的基石”[③]
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十分重视艺术教育,例如:哈佛大学从很早开始就要求其政治、法律、商业等专业的学生必须选修音乐、艺术、文学等限制性选修课,使其毕业生无论从事政治、法律还是商业,均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他们不仅经常在博物馆的氛围中受到熏染,而且构建起了自我的鉴赏作品的方法。不仅如此,美国的绝大部分博物馆和美术馆都有着力量强大的教育部门。这些教育部除了拥有固定的有着高学历的教育及艺术史论背景的教育人员,同时还拥有一只庞大的义工团队。教育部的导赏员会针对不同的人群和对象运用不同的阐释作品及解说方法。除此之外,博物馆和美术馆还积极地与学校、社区合作,构建一些美术教育课程,提供相应的体验场所和学习空间。
正是由于对儿童的重视,美国博物馆被视为儿童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之一和最值得信赖的器物信息资源之一。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古根海姆博物馆,馆方专门为不同年龄段的孩童提供与之相应的美术教育课程,甚至于学校当中的部分课程也可直接在博物馆中进行,馆员与学校教师之间形成了非常紧密和和谐的关系,互通有无,共同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搭建良好的平台。美国博物馆对儿童的重视获得了丰硕的回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民教育思想,从小培养了国民的创新意识,而且许多博物馆的捐赠者都是从小经常去博物馆并对博物馆拥有美好回忆的人。
博物馆是实施公共美术教育的最佳场所,同时由于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使得博物馆在提升人类生活品质,塑造人格及帮助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亚理士多德的真知灼见:制定的一系列德行只有在公共领域当中才能证明有效。
三、博物馆的对话式教学
博物馆的收藏、记录与保存的目的,是为了要诠释,或是增加观众对藏品的了解。诠释是研究的结果,可以透过直接的展示、导览、讲解等方法与间接的如出版品的方式传达给观众。一个单独的物件,若是没有经过解释、编排和选择,则无法支援现今博物馆的教育目标[④]。博物馆美术教育中的对话,已经不限于语言领域,而是一个具有博大内涵的“隐喻”。 作为隐喻的对话,不仅是一种具体的方法、一种形式、一种活动,更是一种态度、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精神。
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感知、想象、理解是三个逐渐深入的阶段。这三个阶段需要欣赏者参与其中,对作品进行积极主动、持续不断的提出质疑,积极参与到理解作品中,也就是身入其中,而不是以观察者的身份置身其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提问质疑所要理解的问题,然后通过观察期待事物自身确定它如何“回答”,这正是伽达默尔提出的问答对话模式。伽达默尔指出:“对话就是对话双方在一起相互参与着以获得真理”。[⑤]在艺术博物馆中导赏艺术作品的过程也正是导览员带领观众一起参与到对作品的理解中,“纯粹的讲述方式(就传统的观点而言),是将博物馆资讯呈现给观众功效最差的一种方式。可惜,它也是众多博物馆导览员所采用的一种方式。
保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中指出:“为了理解对话实践的意义,我们不得不抛开把对话简单地理解为纯粹是一种技巧的想法。对话并不表示我想精心构建且需借助另一人的才智才能实现的虚假途径。相反,对话的特征表现为认识论关系。因此,在此意义上,对话是一种认识途径,并且绝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让学生投入到某项具体任务之中的纯粹的策略。……对话是学习和认识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⑥]
由此,对话是一种学习过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学习和认知的过程。对话式学习让博物馆教育者和观众积极参与到对话场域中来,这种经历磨练着我们的知觉、完善着我们的思维,并连接着我们已知和未知的领域。把对话理解为一个学习和认知的过程,亦更加促进教育者以纯然的好奇之心对待学生的认知过程。鼓励他们把生活阅历转化为知识,并把早已获得的知识用做发现新知识的过程。知识、概念、认知的学习在对话中自然建立起来。
在美国的众多博物馆中,博物馆的教育人员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教授不同的项目。每位博物馆教育者在教授艺术的过程中都会融入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且风格迥异。比如:有的博物馆教育者带领学生面对一件美术作品,在整个时段都启发学生用自己的眼光描绘和感受这件作品。这样的博物馆教育者把自己的课程建构在观察和理解学生的观点之上,并相信通过共同的体验,艺术品更高的含义将会展示在人们面前。第二种博物馆教育者会通过激发学习者的信心来引导他们观察不同作品中的相同的特征,让主题随后出现。这两种方式在某些方面非常地相似,两者都使教育者和学习者集中精力,并激发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他们的注意力完全是在艺术品本身,并共同理解了整幅作品的含义。最后,当小组聚集在作品周围的时候,学习者仍然想继续这种探索的历程。由此,教育者知道他的学员和艺术品之间的沟通不是一个终结,而是开始。
四、创造性的博物馆教育
博物馆教育是一门有创造性的艺术。博物馆教育者通过在博物馆里陈设的艺术品来进行教学,能否让这些艺术品在教授过程中活起来是这些艺术品赋予教育者的责任,也是艺术品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好的博物馆的教学方式要能使艺术品和学习者之间产生互动。这种教学模式包括教师如何激发学习者参与的技巧,问问题的技巧,言说的技巧和进一步引导归纳的技巧。在此过程中,了解艺术品本身和授课群体是至关重要的。教师要引导学生们以近距离的方式观察作品并理解其含义,必须时刻能够准确地提供有关于艺术和历史及其他相关的背景知识。教师必须深知互动学习的方法,但是不能把掌握这些知识和方法作为一种目标,而应当把这种方法视为一种能够激发每一位学习者能对艺术品有深刻和独到见解的工具。没有人能够使每一位学习者在每一节课上都能产生这种有改变性的体验。然而,时刻把这种改变性的经验作为我们的目标会让我们的授课变得有连贯性和挑战性,因为你永远不能预先知道你的授课对象会带来哪些已有的经验和对作品独到的视角和看法,这些将使博物馆教育者每一次都感觉到面对新的作品和新的挑战[⑦]。
杜威在其著作《作为经验的艺术》中讨论了艺术的体验和普通经验的不同在于整体性和完整性,艺术的体验在于那种当即的愉悦和成就感。这种经验就是他所谓的和普通经验不同的“一种经验”,我们与艺术的体验是获取“一种经验”的最好的例子[⑧]。杜威的理论恰好描述了我们想赋予博物馆参观者的体验过程。最佳的期望是,观者在画廊里和教育者共同度过的时光在他们的内心产生有别于其他任何经验的体验。在观众离之后,能对一幅或者多幅作品有深层次的了解,这种设身处境,全神贯注地欣赏艺术品的 “特殊经验”能把他们从寻常的生活中带离出来。杜威还注意到艺术的体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时间这一因素,在所有的审美邂逅中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博物馆教学这一背景下。观察不仅仅是看,看不仅仅是瞄一眼。那种强烈的,集中观察的“一种经验”不会就这么结束。它会逐渐地累积,直到产生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杜威所谓的“高潮”把我们置身于一种强烈的欣赏状态下[⑨]。
根据杜威的理论,博物馆教育者让观众聚在艺术品周围,为的是仔细和有延续性地观察,引起学员的关注是第一个要任。即使艺术品通常陈列在基座上,镶在精致的画框里(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多数随意的游览者只会逗留几秒钟。博物馆的环境几乎都非常优美,但有时常会非常吵闹和令人分心。是走马观花,还是停下脚步来审视作品?其实,如果所有的参观者能有自己的探索、自由和创造性的思想;他们能通过对艺术品的视觉欣赏获得延续的意义;他们能带着有感觉、有观察性、有思想性的探索离开博物馆(即使这种探索只是短暂,即逝的);他们感觉到自己获得了知识和成就;每一位参与者都有机会来形成他自己的对作品的印象和想法,而团体的体验则来自于这些个体的体验……那么,这个过程无疑是充满意义的。
作为博物馆教育者,需要让人们参与其中,一起来欣赏和理解艺术作品。教师会暗示参观者调动知识并指导他们如何来欣赏,同时也会尊重他们所带来的知识和个人的经验。教师也是学习者,同时应该必须传达自己也期望通过一起审视、讨论作品对教师本身也是有价值的经验这样的想法。教师的举止应该让观众相信自己非常了解藏品并能够巧妙地将作品和读者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导师将和学生一起亲密地探讨艺术品。每个人从一开始就必须相信通过这种体验,他对作品的了解将会更加深入。
除了博物馆中创造性的阐释和对话的方法外,博物馆应注重与儿童更亲近的沟通。世界各地皆有专为儿童策划的博物馆教育方案,虽然每个国家强调的重点可能不尽相同,但运用最广泛的方法便是导览。馆方教育者可鼓励儿童去探索一座博物馆,而且可在注意安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四处走动。鼓励孩童根据自己的步调与感兴趣的程度来从事发现学习。如会移动的展示品、语音导览、如实物般大的模型,以及人可以进入的真实物品(像潜水艇或矿坑)、视听导览,或是邀请观众触摸、实验、嗅闻、倾听与观看那些奇特、珍稀之物的活动,都是非常难得、刺激、有趣的教育题材。
除此之外,应加强博物馆与学校之间的合作。博物馆与学校的功能是互补的,博物馆能提供真实的对象和实体范例,而教室里的经验又仅限于课本、授课内容、媒材与一些简单的动手实验。一旦博物馆与学校一起合作,便能为青年提供绝佳的教育机会。直接用真品教学,可以丰富学校的学习,因为这样的导览可以将新的经验纳入对文物的看法之中。
不同的人会以他们的方式去接触艺术、理解艺术。在贯彻博物馆对社会教育的使命的同时,博物馆,艺术馆更要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空间。放弃单向的传导方式,让观众表达诉求,并去了解他们的诉求。它所关切的不再只是象牙塔里的话题,它要成为社会话题,才能让广大的社群有参与的空间。它不单作为社会集体记忆的记录者,更要成为社会集体经验的缔造者。作为一所公共博物馆,我希望能为观众带来知识,提供消闲;为他们创造一种深刻烙印的博物馆经验,使他们获得知识,享受到的消闲,渐渐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动力,以提升他们的精神情操和生活内涵。
[①] 《徳》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②] 《徳》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③]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1992).Excellence & Equity:Education &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Museums.
Washington.D.C.: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④] G Ellis Burcaw著,张譽腾等译,《博物馆这一行》,台湾五观艺术艺术管理有限公司出版,第238页。
[⑤] [德]伽达默尔,夏镇平译:《赞美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第69页。
[⑥] [巴西]保罗·弗莱雷著,顾建新等译,《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8页。多纳尔多·马塞多为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的纪念版引言,引自Paulo Freire and Donaldo Macedo, “A Dialogue: Culture, Language, and Race”
i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vol. 65, no. 3, fall 1995, p.379
[⑦] Rika Burnham and Elliott Kai-kee,“The Art of Teaching in the Museum”,Jourm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Vol.39,No.1,Spring 2004-2005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⑧] John Dewey,Art as Experience(1934,reprint,New york:Perigee Bppks,1980)chap.3,”having an Experience” and Philip W.Jackson,John Dewey and the Lessons of Art(New Haven 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chap.1,”Experience and the Arts.”
[⑨] John Dewey,Art as Experience,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