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就在最近这10年,出自女性主义(Fiminism,或译为“女权主义”)视角的当代艺术批评,在国内扶摇直上[1],以至于但凡女性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和展览,便可以此为概念或理论来源,评论一二。
章燕紫和她的作品,自然也在其列。从策展人对其作品的性别属性的强调[2],到个展“危险的平衡”(2023年)的展览空间的政治面貌[3],均有意无意间夹杂着“性别”或“主义”的标签。更有甚者,会说:“她的样貌是可以挑战任何戏剧学院科班出身女明星的那种真材实料。偏偏,燕紫却是一个极具才华的艺术家……”[4]
种种评述,与其说是策展人的附会,倒不如认为是艺术家的刻意“营造”。章燕紫擅长在作品里营造一种浓郁的“女性”气息。无论是纤细入微的笔触,还是恰到好处的渲染,又或浅粉淡紫的色调,乃至充满性别隐喻的水果和器物,似乎都在毫不隐讳地宣称:如此作品,诚是出自一位女性之手。
可微妙的是:若在这气息中驻留太久,就会像陷入迷障一般,感觉前方若有光,却难以起步;自然,也就勘不透隐匿于斯的那方境界——那里,似与性别无关,可又如何能说是“无关”?
——这大约就是章燕紫作品的“吊诡”之处。
第一次在现场看其原作,我也会不自觉地生出这恍惚之感。那时,我唯一能笃定的是:这般境遇终究是无法简单地用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潮[5]来言说的。
 “无间——章燕紫个展”展览现场
“无间——章燕紫个展”展览现场
技术、认知与艺术的合声
关于“艺术个性”与“艺术法则”的关系,我信奉廖内洛·文杜里(Lionello Venturi,1885—1961年)的观点:相较于艺术作品的“个性”,所谓的“法则”才是因时因地而化的短暂、易变与非本质的[6]。换言之,“艺术品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由有思想、有感情、有理智的个人制作出来的物品,个人又是更大的社会环境中的一分子。正是这种总体的状况决定了艺术品本身的意义”[7]。
若因循这一理路,便意味着若想理解章燕紫其人其作,其微妙的“吊诡”之境从何而来,及其与所谓的“女性主义艺术”是何关系——则应从她本人的“个体属性”说起。
章燕紫出生于“文革”时期。将之置于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中理解[8],会发现这是一个值得辨析的年代。
——这一时期,“妇女”被整体性地塑造;在法律上,正式宣示了男女平等的公民权利;在行动上,通过政治运动与行政手段推进男女平等。因其“力量和成就远非一切女权运动能及,因此也超越了任何形式的女权运动”[9]。
男女平权的意识,在章燕紫儿时就已种下,至今仍能脱口而出当年宣扬的“三八红旗手”“妇女能顶半边天”。成长环境对女童的相对宽松,也酝酿出她好奇且叛逆的个性,热衷的“玩具”是医用的针管与听诊器——只是那时,她或未曾料到,有朝一日,这些会成为自己的创作对象,如《挂号》(2012年)与《不痛》(2013年)。
 “无间——章燕紫个展”展览现场
“无间——章燕紫个展”展览现场
——它后起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延续至今。在这一阶段,女性(不再是“妇女”)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意图从“社会”中分离出“自我”,从“群体”中分离出“个体”,从“男女都一样”的性别认知中分离出“女性”。这一时期的主题是“自觉”。与此同时,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开始被引至中国,进入学术研究与大众舆论的视野。
章燕紫的青春期恰与这一阶段的发轫期吻合,即她个人之于女性意识的自觉与社会整体对于女性认知的转型是同步的。初中,她开始系统地学画时,便潜心研究起“美女”,尤其是《红楼梦》仕女图。这一审美趣味大抵持续了20多年,贯穿她的整个成年历程。其高光时刻,应是2004年以作品《红玫瑰和白玫瑰》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铜奖。
1986年,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年)的专著《第二性》(1949年)在中国出版。虽不知这本在20世纪有重大意义的女性主义理论文本是否曾是章燕紫的枕边读物,但能想见,若她对当时风靡的女性主义抱有更持久的关注与热情,多半会在这条“大道”上走得更远。
然而,由其作品所呈现的整体面目反观之,则不难发现其“小径分叉”之处:2012年,在完成《止痛贴》系列后,章燕紫或也完成了自己的创作转型。
 《碎片》系列,“无间:章燕紫个展”展览现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2024年
《碎片》系列,“无间:章燕紫个展”展览现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2024年

 《碎片》系列局部
《碎片》系列局部
如“乙观”所记:“从父母的早年亡故,到《止痛贴》的真正诞生,这场缓慢而持续的疼痛,章燕紫暗藏了10年。”[10]——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这位艺术家终于遭遇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尽管这确乎是她生命经验中的“被动给予”:痛与乐、病症、生死……凡此种种,已然不是“美女”、性别或女性主义所能指责的议题。
就在同一年,章燕紫接受采访时说:“不管有没有‘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女性经验’都是存在的。‘女性主义’应该是‘女性经验’的一种,是女性在社会活动中一种超越性别意识的苏醒。”[11]
可见她并未将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内化为对“自我”的认知或判定;而是反其道行之,从其自身的经验与心态出发,重新定义了“女性主义”。
如上概论,大抵可部分说明这位女性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总体的社会事实”[12]。
把性别作为“方便”
另一部分“总体的社会事实”,就隐含在章燕紫自己的叙述中。她说:
水墨作为中国传统绘画最核心的艺术语言,它之所以被如此看重,与古代中国文人画在艺术史中的位置息息相关……
我一直认为,以文人画为代表的东方绘画在观念的表达上与西方所谓的观念艺术是具备同质化特征的,虽然在不同的时空和场域,但可以算作是东西方艺术史中一个“不谋而合”的文化契合点。文人画的创作是非常“自我”的……
我们看陶渊明的无弦琴、八大的怪石瘦鸟等,那种传神和意在笔外,都是东方式的观念艺术。换句话说,他们的艺术很当代。[14]
或是基于此念,章燕紫才会将传统的水墨语言与当代艺术联系,“圆融”于自身的创作实践中。此间,甚至无关于传统语言的当代“转换”。
只是,这番论断若为艺术批评家陶咏白知晓,想必会感到匪夷所思。她认为只有“出自女画家之手,以女性的视角,展现女性精神情感,并采用女性独特的表现形式——女性话语,凡此种种的绘画”才可称得上是“女性绘画”。与之相对,创作主体为男性的文人画,则是“男性中心权力文化”之表征的“男性绘画”。因此,中国绘画史就是一部女性“缺席”的历史[15]——这……如何能与一位女性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和自我表达,作以“并接”?[16]
 《自得其乐》,纸本设色,铁栅栏,画心26×35cm, 铁栅栏35×45cm,2020
《自得其乐》,纸本设色,铁栅栏,画心26×35cm, 铁栅栏35×45cm,2020
 《自得其乐》(局部),纸本设色,铁栅栏,画心26×35cm, 铁栅栏35×45cm,2020
《自得其乐》(局部),纸本设色,铁栅栏,画心26×35cm, 铁栅栏35×45cm,2020
回归中国绘画的历史语境,陶咏白从性别视角出发所做的绘画史研究,可谓是在陈述一个历史事实。
但具体至章燕紫的成长年代,体现在文艺传习上的性别区隔,则未必那么分明。在强调“男女都一样”的主张下,文人画所照见的山水文明与人生论[17],作为整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因此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技法上,实际已打破了历史语境中文人画的性别分野,成为男女均可感知、均可沿袭的古典艺术。与之如影随形的,还有这种水墨语言所蕴含的总体的宇宙观与人生观。
不难想见,章燕紫在看陶渊明的无弦琴时,其直觉反应定不会认为自己是在看一位男性艺术家的作品,而应是在看一个“人”(甚或是“神人”)的作品。——事实上,或也只有将文人画的创作主体理解为“人”,且同样将自己理解为“人”,才可能在自己的“个体”生命中完成这场超越时空的“并接”。
站在整全的“人”的视角上反观“性别”,会发现:“她”,既非“主体”,亦非“对象/客体”,更非作为“物”或“非物”而存在。如章燕紫所言,“她”只是某种(个性/女性)“经验”。
一位女性艺术家如何在创作中调用其“女性经验”?——在我理解,那只是某种“方便”,即把性别作为“方便”。只因恰巧具备这种经验,便信手拈来,善巧用之,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因此,也就难以将之抽象、概括为一种“方法”[18]。
 《零碎》5 ,综合材料,尺寸可变,2024年
《零碎》5 ,综合材料,尺寸可变,2024年
个中经历,章燕紫曾做过一个类比:古代文人画画,也会画自己书桌上的各种文玩摆件;那么如今,她描绘自己桌上摆放的水果和药品——其实是一回事儿,“画胶囊不过是我的眼睛回到我的生活”[19]。
一旦将目光收敛至自己的生命体验,所谓“中国画的框框束缚”便也顷刻间灰飞烟灭,“忽然觉得很自由”,是自然的。从此以往,章燕紫作品中的“方便善巧”可谓奇多,于此不再赘述。
把性别作为“方便”,这对于那些基于个体经验而创作的男性艺术家而言,亦同理适用。或也正因如此,显现于作品中,“经验”之间的微妙差别往往会带来令人振聋发聩的效果,以至于同样擅长水墨的艺术家徐累在评价章燕紫的《止痛贴》时,会说:
新作品可谓是一针见墨,单论其题材的出奇,已经是丹青百科史无前例的新指。[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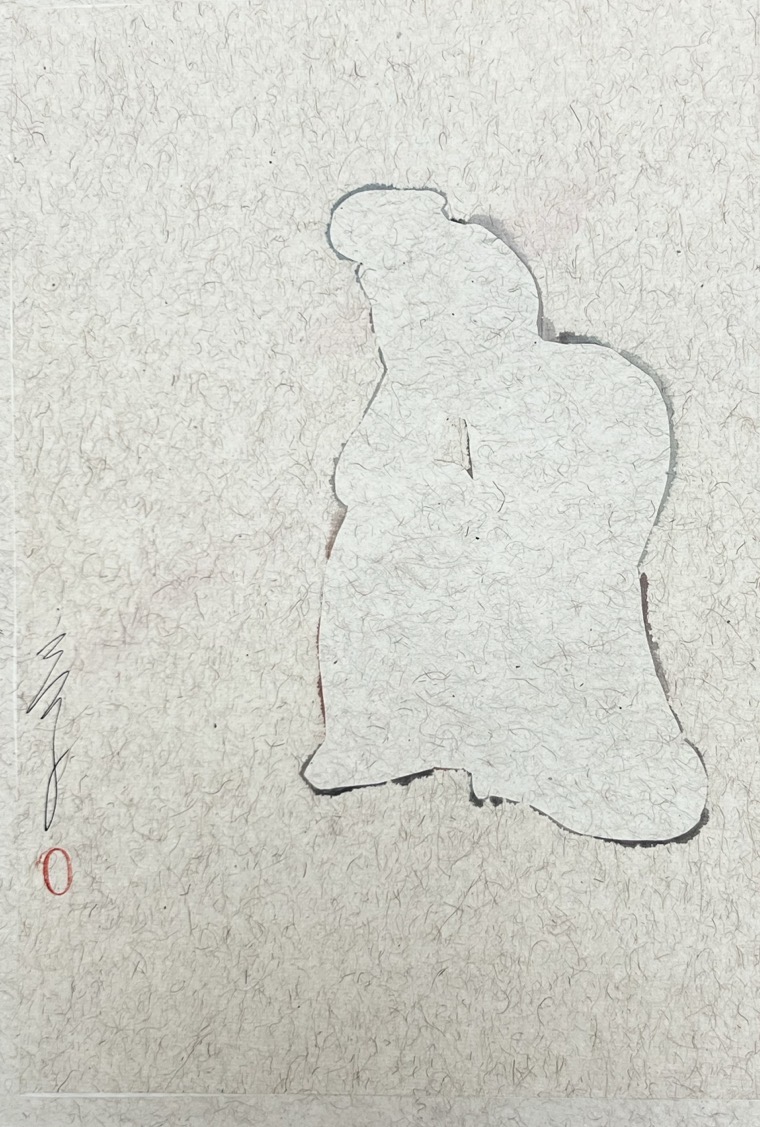
《零碎》6,综合材料,尺寸可变,2024年
超越性别的“大丈夫相”
当我意识到,“她”不过是章燕紫抵达创作的一种“方便”时,那重令人恍惚的迷障,也就烟消云散了。
自此,观者的目光不会再停留在那些看似一目了然的“女相”上——《流光》(2024年)中的嘴唇、《立春》(2022年)中的子宫、《惊蛰》(2022年)中的初潮、《宫》(2016年)中的特殊形制的病床……而是从容地穿过种种“相”,看到其他。
——我仿佛见到了“大丈夫相”。
众所周知,“丈夫”一词,多用于男性;而“大丈夫相”却是超越性别,男女皆可抵达的超世间的境界。在展览现场,我依稀感知到章燕紫的这般希求:即便要探究女性艺术家或女性主义,也不应以“男性”或“性别”为对境,而应超越之——只因男女所在的世俗世界,并非“生活世界”的全部:肉身之外,尚有精神;精神之外,还有“内向超越”。
当我们的艺术家已然在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21]时,我们的批评家却似还未及辨析:是否存在与之适配的理论可做阐释或批评?
 《面对》系列作品细节
《面对》系列作品细节
 《面对03》(局部),综合材料、空心卷轴,2022-2024年
《面对03》(局部),综合材料、空心卷轴,2022-2024年
走出“深渊”
1994年,《江苏画刊》(现《画刊》)第7期上刊载了一篇徐虹的艺术批评文章《走出深渊——给女艺术家和女批评家的信》。此文被视作“女性批评家的声音首次出现……无异于一篇女性主义批评宣言”[22]。
令人深味的是:这篇宣言是同时写给女艺术家和女批评家的。这便意味着此文的“批评”对象,那些应走出“深渊”的人,不只是女艺术家,还应有女批评家——两者宛若并肩奋斗的“战友”,抑或“难友”。文末宣告:
人们应该意识到,没有清醒、自觉的女性主义艺术的现代艺术是不彻底的现代艺术。[23]
自此伊始,对中国女性艺术家的评述,似乎总是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更迭而各种套用。如“性”“母职”“父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波伏娃的“他者”;至后现代,各种主张愈发层出不穷,风头正盛的“生态女性主义”不知还能持续多久……仿佛离开了这些概念,我们的批评家就不知该如何阐释这些出自女性之手的作品。

 《千里追风图》 册页(局部),51.5×1191.5cm,纸上综合材料,2023-2024年
《千里追风图》 册页(局部),51.5×1191.5cm,纸上综合材料,2023-2024年
然需说明的是:我国的“妇女运动”与西方女性运动有着迥然不同的历程,本可作为差异化的经验材料贡献于理论研究。但是,西方学界的女性主义研究,却鲜少将前者作为可资探讨的对象。这便意味着:基于西方社会经验与意识形态而来的女性主义运动与思潮,对中国女性的“经验与心态”[24]终究有多大的解释力,应是予以“存疑”的。
换言之,在采信这些女性主义的概念与理论对中国女性艺术家其人其作进行解读之前,须先警惕:切莫让艺术家“个体”特有的生命经验,成为“他者”[25]的理论注脚。与之相对,或也只有回归每个创作者的“个体经验”,从其内在视角出发,才可能达成一种“理解”的批评;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学理探讨,方可对话、反思时下流行的相关概念与理论。
所以,我会认为,经验研究——从“人”及其“总体的社会事实”出发,或是一条可资参详的艺术批评路径。
就此而言,所谓的“女性主义”,何尝不是又一个需要走出的“深渊”?
作者介绍:
 何贝莉,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副教授。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获汉语言文学和管理学双学士学位。2008年,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人类学专业,在中国西藏山南的桑耶寺做田野考察,以其藏学人类学研究获博士学位。2014年,于中央民族大学民社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在青海果洛的红科寺做田野考察,2017年博士后出站。2019年入职中央美术学院,在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任教,至今。教授“田野考察:口述历史”“影像人类学”“论文写作”等课程。
何贝莉,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副教授。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获汉语言文学和管理学双学士学位。2008年,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人类学专业,在中国西藏山南的桑耶寺做田野考察,以其藏学人类学研究获博士学位。2014年,于中央民族大学民社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在青海果洛的红科寺做田野考察,2017年博士后出站。2019年入职中央美术学院,在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任教,至今。教授“田野考察:口述历史”“影像人类学”“论文写作”等课程。
已出版日记民族志《无始无终:转山》(2020,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学术专著《仪式空间与文明的宇宙观——桑耶寺人类学考察》(2022,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本文原刊登于《画刊》杂志2024年第7期
图片资料来自艺术家
注释:
[1]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中,女性艺术与女性主义批评实际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
[2]参见林书传:《前言》,“无间:章燕紫个展”前言,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2024年。
[3]2023年10月4日—10月28日,章燕紫巴黎个展“危险的平衡”在法国女性主义民主联盟艺术空间 ESPACE DES FEMMES-Antoinette Fouque 举办。
[4]这段话是策展人秦丹丹的评述,载于Village One Art画廊(秦丹丹是创办人之一)的微信公众号“VillageOneArt”,标题为:章燕紫|仙境,2020年11月14日。
[5]参见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6]参见廖内洛·文杜里:《艺术批评史》,邵宏译,第32~33页,商务印书馆,2020年。
[7]格雷戈里·巴特科克:《引言》,载于廖内洛·文杜里:《艺术批评史》,邵宏译,第5页,商务印书馆,2020年。
[8]参见李小江:《女性乌托邦——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第3~3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9]同上,第23~24页。
[10]《乙观头条 | 章燕紫:残酷也是诗性,痛也值得歌颂》,载于微信公众号“乙观”,2023年10月19日。
[11]章燕紫《“女性主义”是超越性别意识的苏醒》,载于《艺术市场》,2012年第6期,第90~91页。
[12]借用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年)的概念“总体的(total)的社会事实”。参见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13]借用佛教用语,指以善巧灵活的方式因材施教,使人懂得佛法真义。《维摩经·法供养品》云:“以方便力,为诸众生分别解说,显示分明。”《坛经·般若品》云:“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
[14]裴刚、章燕紫:《对话 | 章燕紫 异质景观》,载于微信公众号“雅昌艺术网”,2024年3月29日。
[15]陶咏白:《导言》,载于陶咏白、李湜:《失落的历史——中国女性绘画史》,第1~10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16]借用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1930—2021)的概念“并接结构”,以说明在结构(文人画的水墨传统)与事件(艺术家的个体创作)之间所存在的可供探讨的“关系”。参见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导论”,蓝达居、张宏明、黄向春、刘永华译,第10~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7]参见渠敬东主编:《中国文明与山水世界》(第一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18]参见项飙、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
[19]章燕紫、胡晓岚:《章燕紫:区隔与呼吸 伤痛与疗愈|“CAFAM双年展”观察·访谈》,载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官网,2016年12月5日。
[20]徐累:《“止痛贴”:章燕紫的纸上心经》,载于《美术研究》,2019年第3期,第8~9页。
[21]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4卷《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第1~2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2]后更名为“走出深渊:我的女性主义批评观”收录于文集。参见贾方舟主编:《批评的时代——中国20世纪末美术批评文萃》卷一“序言”,第17页,广西美术出版社,2007年;徐虹:《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女性主义艺术批评》,载于《美苑》,2007年第3期,第19~21页。
[23]徐虹:《走出深渊:我的女性主义批评观》,载于贾方舟主编:《批评的时代——中国20世纪末美术批评文萃》卷三,第63~65页,广西美术出版社,2007年。
[24]参见王铭铭:《经验与心态》“自序”,第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25]参见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