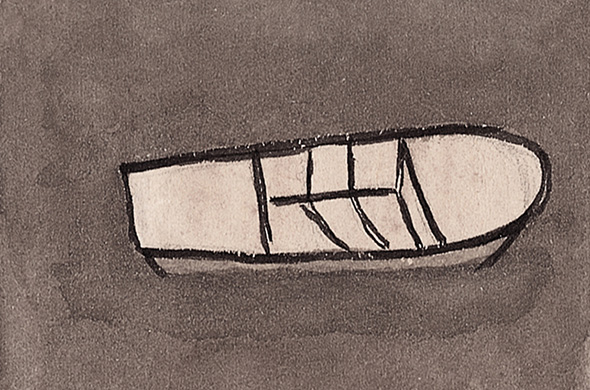
2002年9月10日 巴黎国际艺术城
一、塞纳河边,几个年轻人在玩滑板(旱冰),围观的人有我、一群黑人妇女及儿童,还有其他一些游客。其中一位玩滑板的年轻人微胖、近视,看来是初学,转身时突然摔倒,在人们还在为他担忧时,那几位黑人妇女及儿童已被逗得哈哈大笑,笑得很真,毫无顾忌,甚至前仰后合,直笑得那位初学者不敢轻易再做动作。
二、蓬皮杜中心广场,一位艺人正在表演,他请观众与他配合,学他走“猫步”。这位观众很幽默,走了几步,被告之重走,没想到退回来也是反着的“猫步”。我禁不住大笑,忽然感觉在离我不远处还有一位笑声更大。转过头一瞧,是一位黑人,看来第三世界的人民还是有共通的地方。
2002年9月12日夜12:20 巴黎国际艺术城
今天下午,我在卢森堡公园旁的一条小街道上走着,前面有一对情侣,回头看见我,忽然大叫一声,便快步走开。我感到诧异,有些不解,转身从橱窗的玻璃反复端详自己,觉得挺正常的呀!
记得以前一位朋友说,中国人第一次到丹麦,便被关在笼子里,让人们像看动物一样参观。有时我们看外国人像动物,他们看我们可能也是如此。
2002年9月24日 巴黎国际艺术城
今晚,在艺术城的表演厅,云南的廖老师在办她的独唱音乐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意思,一群欧洲人将不大的音乐厅挤得满满的,廖老师的形象又很中国,略微有点老和胖,露出的胳膊已显得有些松弛,白色的裙子紧攥着身体,尤其是唱到高音处,身上的裙子像要爆开一般。伴奏的是一位中国先生,小眼,短下巴,头发向后背,神情有点傲慢。
前面的两首歌是英文歌曲,我听不懂,曲调也陌生,但廖老师唱得很投入。我想拍些照片,便回去取相机,回来时,看门的小姐示意歌曲唱完才能进入,我等里面响起掌声才进去。接下来的一首歌是一位中国男士在唱,可能是特约嘉宾,歌词仍然听不懂。等廖老师再出场时,高潮终于出现了,她换掉了裙子,重新着一身纯绿色的民族服装,上面有一些不规则的牡丹花图案,只是裤子短了些,露出的厚底皮鞋显得有些怪怪的。
一首熟悉的曲子响起,等她唱到中间,我才想出这歌的名字是《走进新时代》,如果换在国内听的话,可能很平常,但在巴黎,它的意义完全变了。我有些激动,感觉血在向上涌,这是到巴黎后第一次这么激动!我猛劲地鼓掌,却被旁边的国人低声告之,在巴黎听音乐会中间是不能鼓掌的,但为时已晚,全场的人都像听懂了这支歌似的,掌声很响。
接下来是云南民歌,加上她的那些动作(有些像东北秧歌)显得更加刺激!演出结束,观众报以长久的热烈的掌声,可能每个人的掌声中都有个人对她认可的角度,它的过程太有意思了,尽管廖老师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些,她只是很投入地唱完预定的每首歌曲,对她来讲,这已经足够了。
随着歌声的结束,不能说我的感觉在消退,起码在之后的几天里,我嘴上哼的仍是那首曲子,尤其洗澡的时候,更要放声大唱。
2002年10月4日 夜2时 巴黎国际艺术城
昨晚,我在卢浮宫的倒金字塔形厅看了一个时装表演,原以为要两三个小时,没想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当人们起立鼓掌的时候,我以为是幕间休息,感觉还没有在外面排队入场的时间长。
设计师选择的模特不漂亮,年龄偏大,但气质都有些特别,服装也颇有乞丐服的意思。他将情节性带入时装表演,这一点是我头一次见到。一位拉提琴者首先出场,他走到T型台中央与一位模特有种情节动作的组合,模特是一位魅力十足的四十岁出头的女人,舞蹈动作也颇大。设计师是将音乐、舞蹈、时装三样融在一块儿来展现他的设计观念。
这是一次不错的时装发布会,但怎么也不能让我像看廖老师独唱会那样激动!那么记忆犹新!因为它太协调了,协调得让人觉得音乐与时装、情节与舞蹈结合得那么天衣无缝。它也有意外,但当你刚刚感觉到它的意外时,忽然又觉得如此合乎情理,随之意外也消失了。
廖老师的作品则不然,她将所有的毫无关系的东西放在一块,逼着你去感受它、享受它,直至融化它。她把我非常熟悉的以至于熟悉得近乎毫无感觉的东西赋予了新的活力;她那身生生的、嫩绿的、上面有几朵牡丹花图案的服装让整个音乐厅,甚至整个巴黎都充斥着不协调性。巴黎自身的协调感时常让人有种睡眠的欲望,她太需要对比、太需要生涩的东西了。
一位设计时装的国人认为这是一次个性化的时装表演,最终设计师是靠设计来博得人们对他个性的认可,而廖老师的意义已不是“个性”一词所能概括的了。
傍晚回艺术城的路上,又一次见到廖老师,我还是有些激动,可她根本没注意到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从我身边匆匆而过……
2002年10月4日夜3∶30分 巴黎国际艺术城
中秋节那天晚上,巴黎的月亮很圆。
我和朋友去蓬皮杜旁边的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名字叫《十》,整个影片反复在演一个女出租车司机与三个乘客之间的对话,拍摄的角度也只有正、副驾驶两个位置。这是一部阿拉伯国家的电影,它是靠神情与对话来充实着的影片。因为语言听不懂,只能大致猜其意思。导演是有智慧与头脑的,他在用无聊、单一来阐述一种观念,看的过程中也有些不耐烦,有中途告退的想法。
这部“无聊”的电影是我这些天一直在琢磨的一件事,“无聊”能让人忘不掉,能带给人想像,这就足够了。
2002年10月9日 铁塔附近
昨晚,艺术城有三个法国人的演奏会。首先,一位先生扛着大提琴上台,向大家行礼后,忽然发现忘记了带乐谱,赶紧回去取,这是一个小插曲,也只有在艺术城的演出厅才有这种情况,因为这儿的演出完全出于休闲、放松的目的。
廖老师坐在我的前排,休息时她说:“拉大提琴的人就住在我隔壁,几乎每天都能见到,按道理说,住艺术城的人都可称为艺术家了,可这个人每天拉提琴的感觉就像初学者。”这句话使我想起了柯罗,柯罗的绘画也朴素得像初学画的人,有时这些成为人们理想或追求的东西,其实就平淡的在你身边。
2002年10月10日 圣保罗(saint—paul)花园
在卢浮宫,当我见到拉奥孔、荷马、伏尔泰的原作时,不停地抱怨我们当初学画时画的这些石膏像的形已经被翻得走了样,脸上的结构全无,显得平而臃肿。后来慢慢觉得这是对的,因为国人的脸就是平的,这也许是一种巧合。再看我们传统里的汉、北魏石刻面部的感觉,也是无凸凹之感,且丰满而圆润。
当初国门渐渐打开,我们的先辈在西方学会了新的观察与表现方法的同时,却忘记了自己平平的、从侧面看只有鼻部微微突起的脸,以为自己也跟眼睛所看到的充满起伏与凸凹的脸是一样的,于是内心充满了使命感,将一种“全新”的东西带回来,试图来弥补我们前人留下的“不足”与“空缺”。
于是,“新”的中西结合的观念差不多控制了中国美术教育近一个世纪,我们学会了在一张平整的脸上去“挖掘”出丰富的体面,并津津乐道于此,以至于成为衡量人的艺术才能的标准,而要掌握并熟练运用这种能力则要耗掉人的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想起来,这是件既悲哀又有趣的事。
2002年10月17日 巴黎圣保罗教堂
今天,在圣保罗教堂,主教大人身穿紫色长袍,在主持一个葬礼。旁边站着的家属们的表情还没有他显得悲伤。仪式完毕,四个穿黑色西服的男子将木棺扛起,缓慢地向教堂外走去,然后将木棺放入车内。主教大人同家属们一一握手道别,然后回到教堂,脱下长袍,换上西装,开始收拾刚才用过的一些烛台等物品。
穿上西装的主教大人同教堂里祈祷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显得普通而又平常。
2002年10月28日 尼斯
尼斯的海滩安静极了。
我躺在沙滩上,有些似睡非睡。朦胧中海面上一艘巨大的白色轮船正慢慢启动。突然,一阵喧闹声把我吵醒,熟悉的东北方言在一瞬间使我对自己的栖身地产生了怀疑,我定睛一看,是五六个来自祖国的妇女在海边忘情地奔跑、跳跃。不知怎么的,在国外看国人长得都很像,这几位女人长得就像五胞胎,青一色的短发,身体略微发胖,皮肤黑黄,穿着挽起裤角的深色裤。其中一位急不可耐地脱下外衣,上身只穿胸罩,手挥舞着蓝色纱巾,不停地大声招呼同伴给她拍照、录像,看得出她是相当兴奋!弄得躺在沙滩上的人诧异地望着她们……
不一会儿,随着她们嬉闹声的远去,海滩又恢复了本来的平静。
2002年11月7日午后 塞纳河边
巴黎的风小了,这几天雨也停了,平静的天气使塞纳河安静了许多。河水依然是那样黄,云显得很低,紫灰色云的断开处露出了浅蓝色的天空及白的云,在蓝色和白色的衬映下,慢慢移动的紫灰的云有些像烟雾。这时在我身后来了一群老年游客,他们掏出随身带的食物在这里小憩。
我注意到河对面的路上没有了汽车,而出现了一些骑自行车及玩滑板的人。原来今天是星期天,河边的路是专为行人开放的。我刚到巴黎的时候,这条路上塞满了游客。
蓝天和白云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不见了,只剩下熟悉的灰的调子。这种变幻有些像黄山,只不过黄山的云一过来,眼前的风景也随之消失了,而巴黎的云层一厚,河水及岸上的建筑却依然清晰,只不过多添了几分凝重的味道。
此时,游客的谈话声有些大,笑声也显得毫无顾忌,好像在西班牙境内的火车上,人们聊天的声音也是这样,这在法国的地铁及火车上是听不到的。
游人们开始整理行装,拉拉锁的声音有些刺耳,看着他们,想起了前些日子,我在意大利、西班牙露餐街头的情景……
身后的游人走了,周围又重新静了下来,云依然是那样厚,隐约之中,夹杂些似蓝似白的色彩在慢慢移动。也许过一会儿,蓝天和白云就会冲破“烟雾”而强行露出脸来;也许到晚上,整个天空仍被紫灰的“烟雾”笼罩着;也许……会有第三种也许吗?
2002年11月12日 巴黎国际艺术城
奥特维也多是位于罗马和佛罗伦萨之间的一个小镇,车站对面的山上有旧城堡,我们在那儿住了三个晚上。镇上有一家比萨店,没想到这里的比萨是我在意大利吃的味道最纯正的比萨。小店在公路旁,是夫妻开的,女的收钱,男的做比萨,便宜一点的是两个多欧元,加蘑菇价钱要多0.5欧元,如再加火腿则还需加钱。
烤比萨的师傅高个子,鬈发,鼻子很大,戴眼镜,他是用一根长长的铁锹将案板上的生比萨撮起,然后放入炉中,一炉大约能烤出七八个比萨。买比萨的人大多是小镇的居民,有时一个人要买上十几个,买的人一多,高个子师傅的神情及动作就有些兴奋,还常常会和等待的顾客聊天,一不留神就会将比萨烤糊,但大家还是乐于接受糊的比萨。
我们常吃的是西红柿加奶酪的那种,他的奶酪做得特别好,趁热吃,有些像肉的感觉。这里的比萨用料单纯,反而好吃。国内的比萨店将比萨中加入好多种料,如鱼、虾、肉等,这也许是为了符合国人的口味吧。
2002年11月12日 巴黎塞纳河边
近来,巴黎每天都要下雨,天气也有些凉。等雨停了,气温又升回来。那种回归温暖的感觉有些像春天,就是春节刚过的那些天。巴黎的雨水时大时小,小的时候那种毛毛细雨使人想起四五月份的杭州,空气湿润极了,虽有凉意,但仍使雨中的人感受到一丝缠绵的味道。
因为下雨,塞纳河已变得混浊,河水有些泛黄。加上秋天的风大,水面上时而泛起白白的浪花,有些像黄河水的颜色了。夏天的时候,岸两边的树木挺拔,枝叶茂密,河水呼应着树的颜色,绿而清澈,密密的叶子将树后的建筑大部分都遮掩住了。进入秋季,叶子慢慢地散落得差不多了,建筑的原形渐渐显露出来,而树枝集中的地方仍使建筑显得模糊。
灰灰的建筑,泛黄的河水,有些厚云的紫灰的天空伴着散落的秋叶,这就是巴黎现在的样子。
河边的游人已少得多了,我喜欢这样的感觉。人们都集中在繁华的街道,天气凉了,人也爱扎堆,不像在夏天,河边、大街、小巷挤满了人,所以我当时的感觉是这里跟北京一样,没有大的差别。
没有人的塞纳河畔,只有宁静,宁静中也夹杂些凄凉的感觉,泛黄的河水显得比平日硬朗了许多,来往的船只也好像被增添了好多阻力似的,马达声特别大。
河边偶尔会遇见穿着呢子大衣、骑车匆匆而过的女孩子,她们的鼻子被冻得红红的,眼睛也像要流出眼泪似的,这情景在一个月前的阿姆斯特丹见到过,因为那里要比巴黎冷得早些。
2002年11月13日 巴黎国际艺术城
巴黎、阿姆斯特丹、罗马、巴塞罗那、柏林大大小小的面包店的橱窗里,许多制作精致、色泽各异的小点心常常让我驻足观望……
在意大利,我们常吃的是一种中间夹有蛋塔的点心,味道香,就是有点过于甜,因为每天步行,所以吃这种点心两三个小时肚子就饿了。后来发现土耳其卷肉饼还是让我最为钟情的,吃上一个大约能走上五六个小时的路,好像北京的新街口前几年卖过这种食品。
巴黎的土耳其饼是面包夹肉和薯条;尼斯的则要加入番茄酱;维也纳的土耳其饼量很大,可以随意加肉和蔬菜。
这种饼的做法同西安的肉夹馍有些像,但肉夹馍的味道要更香。记得有一年在兰州,吃一种烧饼夹腊肉的小吃,吃上一个感觉不过瘾,随后要了半斤腊肉,中间切一条缝,再将烧饼塞进去,吃完是尽兴了,但头有些晕,因为肉吃多了是要上头的。
2002年11月14日下午16∶00 奥塞博物馆
大约一个月前,在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戈雅让我为之一震,他是在欧洲的美术馆里令我最为感动的人,他同委拉斯贵支大量的作品构筑了普拉多美术馆的灵魂。卢浮宫固然庞大,但面面俱到,也许这亦是它的特点。
现在,奥塞博物馆特展的名称是委拉斯贵支同马奈比较展,但进入展厅,才发现是与两人画风有关系的一批人的展览,这与毕加索和马蒂斯的比较展有所不同。这个展览包括委拉斯贵支、柯罗、德加、德拉克洛瓦、戈雅,距离太近,马奈的作品占了大部分墙面。
与戈雅在巴黎“重逢”显得有些意外,他作品中弥散着的空气的味道仿佛使我回到了西班牙。在普拉多,我曾走到出口,而又急切地返回三楼去重温他的作品。现在,我面前的一张作品是马奈画的一群士兵在射击两个人,构图与戈雅的那张画完全一样,戈雅作品的照片就放在此画旁,马奈的这张画其实也只画了一半,显得有些急躁,可能是戈雅的那张画太完美而使他不得不停下笔来。此时,我更想念戈雅的那张画,不,也许不是单独的某张画,而是全部……
戈雅的作品风格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肖像,一看便有应酬之感;一类是为自己而画,这好像是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艺术家面临的相同的问题。在奥塞,戈雅的作品气息犹在,但这些画的浓度已无法与普拉多相比,因为戈雅的灵魂在西班牙。
2002年11月17日 巴黎国际艺术城
在柏林火车站的餐馆里,有一种熟肉看上去很好看,是一整块五花肉,皮像是烤过,然后再用锅蒸的感觉。这种肉是切成小块,然后夹在面包里,放上番茄及芥末酱来卖的。我们要了一份,吃的感觉不如看的好,味道一般,有点硬,不像杭州的“东坡肉”,味道好不说,肉到嘴里就化了,那种感觉可能西方人永远体会不到。
在北京,我和朋友常去东四的孔乙己酒馆,每次去,“东坡肉”是必点的菜,常常是一块不够,再加一块。
我自己平时炖肉则是将五花肉切成小块,加些调料和啤酒或可乐,煮三四个钟头就可以吃了,这也是比较简单的解馋的办法。
2002年11月17日 巴黎塞纳河边教堂
星期三下午,我去了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院。
它使我想起了我的母校,不是新校,而是王府井的那所老学校。
在材料技法工作室,见到宾卡斯先生,1987年他曾到中央美院讲学,15年过去了,他已成了一个胖胖的犹太老人。他讲课的样子像个面包房的大师傅,系着白围裙,手里拿着瓶子和丝袜不停地比比划划。
宾卡斯约我们晚上5点半一起喝咖啡,趁这段空暇时间,我看了版画、油画、雕塑几个工作室。如果十年前来巴黎美院,我会感慨一番,如今,我看这里的一切却是那么平常,那么似曾相识,学生作品的思路也与国内学生的思维较接近。在路过学校咖啡厅的厨房时,看见一只老鼠正在橱柜边散步,这一情景把我一下拉回王府井的校尉胡同。过去的中央美院不仅有老鼠、蚂蚁,夏天的时候,飞蛾也很多,在教室窗帘的后面、抽屉里到处都是。记得我去百货大楼买铅笔,解开上衣兜取钱,就从里面飞出一只,吓了营业员一跳;还有一次是去厕所小便,刚解开裤子,从里面飞出一只蛾子,吓了自己一跳。我不知道巴黎美院除了老鼠还有没有飞蛾和蚂蚁,但我想,在这座老建筑里面,肯定有一些我未见到的生物。在我们的新美院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即使有,也是偶尔路过此地。我们新房子的装修味道至今仍很浓,甲醛之类不知什么时候能够散去,这也从某种程度阻止了老鼠们生长的进程。如果有那么一天,新美院的房子里面有自己产下的老鼠、蚂蚁、飞蛾或其他什么的,这所学校才会真的变得有感觉了。
我现在是在教堂里写前几天去巴黎美院的事,我坐在后面,在前面,着便装的神父正在给几位老人讲着什么,并不时地用手指着教堂的顶部,几位老人向他指的方向望。此时,他们走到我坐的后边,神父的声音变得大起来,随后他们又朝教堂的门口走去,神父的声音依然很大。
我看看表,快五点半了,我们来到宾卡斯先生上课的门口,他依然在讲。等过了几分钟,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接着我们便在美院对面的一个小酒吧里坐了下来。刚才来酒吧之前,看到美院的老师已经下班,他们走到自己的车旁,掀开后备箱往里面放着什么,宾卡斯还到收发室转了一下,问了几句话,不知是不是问有无信件与包裹。
在酒吧里,近观宾卡斯,他脸上的皱纹多了许多,不过神情倒显得精神。他给我看了一本他编著的技法书,是十几年前出版的,现在依然在用,并准备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来。
自从来巴黎美院,到晚上喝完咖啡与宾卡斯分手,我的身体虽在巴黎,但思维却一直在巴黎与北京之间跳跃,确切地说是在巴黎美院与校尉胡同之间飞来飞去……
此时,神父领着那几位老人又转到我的面前,他用一个大手电照着墙上的壁画,仍孜孜不倦地讲着,他的神情松弛时,几位老人也显得轻松起来……
2002年11月18日 巴黎塞纳河边教堂
今天,巴黎的云层密得好像永远见不到天空似的,气温也降了下来。我顺着河边来到昨天呆过的教堂,现在,这里很静,只是隐约传来隔壁小学校学生玩耍的声音,不一会儿,这种声音也消失了。
大约一个星期前,我去看了毕加索与马蒂斯的比较展。那天下着小雨,在雨中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进入展厅。在欧洲看博物馆,排队是正常的事,我想如果策划者不将两人作品对比着展出,而是分开来的话,参观的人也许不会这么多。
展厅里两人的画穿插着挂在墙上,展厅中央有雕塑,粗略地看过去,像是一个人的作品。我依然是按照我看展览的方式去看,也没太去比较什么。我只是觉得马蒂斯的画更有直觉上的感受,在毕加索的“对比”下,有时他的画像是出自一个女人之手,这在他们的素描中显得更明显一些。
这时,教堂里的人逐渐多起来,我身后不远处,一对夫妇正在翻阅刚买来的书籍。也许,这是教堂的另外一种功能。
2002年11月27日 巴黎国际艺术城
巴黎有很多纪念碑,但对我而言,有一座比较特别,就是在艺术城边上的朝鲜战争纪念碑。这个碑是一个朝鲜地图的形状,底座上刻有“1950—1953”的字样。前段时间,一群佩戴勋章的老兵曾在这儿举办纪念活动。
对于朝鲜战争,我们叫“抗美援朝”,小的时候在电影及教科书中知道的一些英雄就是在战争中诞生的,现在好像不太提那段历史了,在战争中阵亡的法国士兵,或许与中国人有关系。
来巴黎之前,我到过汉城,当时那里正举办世界杯,人气兴旺,像过节一样。平壤我没有去过,但丹东鸭绿江的对岸就是朝鲜的第二大城市新义州,那儿有几个高高的烟囱,时而冒着白烟。
现在,我几乎每天都要从纪念碑前走过,有时会停下来,端详这个“朝鲜地图”,我注意到几乎没有人在意它,也许在以后的日子里仍不会引起路人的注意……
2002年12月3日 巴黎塞纳河边
欧洲人是真正懂得生活的。
如果八九月份在巴黎,你会发现街上的好多店都是关门的,原因是店主全家已出去度假了。在巴黎,平日商店开门的时间都较晚,大部分的超市星期天或节假日也都要关门,有两次经历我印象很深:
一次是在巴黎的马展上,因张平买了一副皮的护腿,我的兜里只剩下1.5欧元,这时又临近傍晚,我突然感到很饿,在马展上有许多卖小吃的货摊,主要是卖类似国内的花生之类的东西,一袋是4欧元,我问了几乎所有的摊主,“1.5欧元”是不卖的。这种思维令我很不解,因为也有一些零散的,如按我们的习惯,别说1.5元,就是五毛钱也会抓一把给你的。
另外一次是在威尼斯。在返回火车站的途中,有一家鞋店,张平看上了一双皮鞋,挺喜欢,可觉得鞋底粘胶处有些缝隙,反复琢磨还是没有买,等出了鞋店又有些后悔,便急匆匆赶回去。到了鞋店门口,老板正在锁门,我们跟他说还是想要那双鞋,他却说已经下班了,只能等明天上午再来,我们解释说一会儿我们就要乘火车去维也纳,他说那也没办法,很抱歉。
2002年12月5日 巴黎国际艺术城
在巴黎,我参观博物馆,常常是乘地铁去,然后步行回来,偶尔是走去走回。有那么几次,回来的时候,想抄些近道,省点力气,于是算好方位,感觉这条路斜插过去,肯定能到艺术城,哪知却越走越远,险些迷了路。
巴黎的路跟北京不同,北京是方方正正的,如果你想抄近路是能感觉出来的,而巴黎的路都是斜的,以至于出现了上述那种情况。
2002年12月7日 巴黎国际艺术城
巴黎的书店中,艺术类的图书比例很大,但大部分画册都是以传统的画家为主,当代画家的画集相对较少,即使有,也大都为较小的开本,绝无国内常见的大部头的个人画集。
一位了解国内出版业的法国人说,按中国现有出版画册的质量,大部分都将成为垃圾,因为中国的出版业、画家都是孤立的,只要出钱,出版就不成问题,而且画册一个比一个做得大;而在欧洲,艺术家、出版商是一个整体,出版商是要对画家负责的,如果出版了一个劣质画家的书,那么,这个出版商可能就要失业了。
我们的做法同韩国有些像。今年6月,我去汉城参加“中韩代表艺术家作品展”,在欢迎仪式上,主持人宣布进行大会第二项,请大家互换名片与画册,也许这就是欧亚的区别吧。
2002年12月13日凌晨 巴黎国际艺术城
今天,河水从混浊又变得清澈起来,确切地说,是变成深绿的颜色了。如果只看水的色彩,好像又回到了夏天,但又比那时的绿厚重了许多,塞纳河又重新静静地躺在那里,只是缺少了岸边绿叶的呼应,显得有些孤单。
雨虽然停了,但天空依然是灰的,我好像已经习惯了这种调子,偶尔露出的蓝色反而让我有些不适应。向西望去,就是和远处建筑接触的那部分天空的颜色在慢慢变暧,这是一种淡绿与淡紫相互交织的色调,虽然大面积的灰有些不情愿,但仍留给绿和紫足够的空间。河水的绿显得有些兴奋,因为它与远方的绿呼应了起来,使紫显得更加刺眼!但很快,绿和紫还是被灰挤出了我的视野。此时,河水已经变成墨绿,而且墨的成分越来越多……
我喜欢这一时刻的巴黎,它虽短暂,但很特别。假如明天我在傍晚起床,那么我所钟情的就会又一次变为现实,而面对只有傍晚的巴黎,不知我是否会有别的期待。
2002年12月13日下午16∶20 巴黎路易十四广场
现在已接近傍晚,我在等待昨天看到的夕阳出现,可望着天空均匀而厚的灰色,恐怕等不到我所期待的了,至少今天是这样。
一个多月前,这里还是人声鼎沸,热闹得像集市一样,现在“集市”已经散了,叶子也随着人群消失了,只剩下孤独的枝干。夏天的时候,路易十四的雕像隐蔽在树叶中,不走近是看不出来的。现在,在广场的角上就能看到,它被干枯的树枝围在中间,好像永远都走不出这片林子似的。雕像下面的草坪,很奇怪,绿得像春天时的一样,上周末去诺曼底的路上,看到乡间田野也是这样的绿。
这时,在我右上方的天空,出乎意料地有了淡紫的色彩,它与灰色挤在一起向左边移动,今天的紫不那么集中,散散落落,在灰与紫的缝隙中,隐约露出些蓝色,蓝很不容易露出脸来,瞬间又被遮盖住了,慢慢地紫也渐渐消失了……
广场四周,画廊、酒吧的灯光陆续亮了起来,在这个时辰,它们成了主角,店主们是不太指望在这个季节有什么大收获的,广场上的座椅空得只剩下我一个人。其实12月的巴黎更像北京的秋末,大约是10月底的样子,它的风景就好比将冬季东北的树挪到了广东,是绿的草坪上面长着浓重的没有一片叶子的树木,等到树木重新长满了叶子,草依然是那样绿。由此说来,巴黎是没有冬天的。
2002年12月22日 巴黎塞纳河边
今天,巴黎的天空很蓝。
蓝的出现,实属不易,也让我有些始料不及,我已习惯了天与建筑融为一体的感觉。蓝虽然占了大部分的面积,但不知怎么,我觉得它并未为自己的复出而显得过于兴奋。在这个季节里,灰是主角,暂时的离去似乎预示着它又要重新归来,有时灰就像一块大的“幕布”悬挂在建筑的后面,这“幕布”的颜色与墙面的颜色像极了,或有一种相互交替的感觉。
蓝使即要逝去的夕阳显得比平日温暖了许多,它既有与蓝共享天下的愿望,又有些为自己的即将离去而哀伤。看得出,它更愿意与蓝呆在一起,虽然在灰中它显得更加刺眼,但它的内心是钟情于蓝的,可无论如何,几十分钟之后,依偎在蓝怀中的它就要离去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此时,灰还是慢慢出现了,对这一点,蓝是早有准备的。灰的来势有些凶猛,它先是散散落落地出现,然后便加快了速度,不一会儿,大面积的蓝被它分割成了许多小块,面对着这些,蓝只是遗憾地望着河水,它是想通过倒影来看一眼自己并不完整的面容,哪知河水在灰的映衬下,变得混浊起来,蓝这最后的愿望也破灭了。
夕阳望着这一切,显得无能为力,因为随着蓝的消失,它也要离去,原本它是要走在蓝之前的,什么时候与蓝能够重逢,也许是它最大的愿望,对于蓝来讲,也是这样的。
2002年12月24日下午15∶35 巴黎塞纳河边
今天,河水的颜色有些特别,是熟赭色,它与岸边的树是一样的色彩了。这使眼前的风景变成了单色画,就像灰与蓝事先约定好一样,水今天也与树、建筑达成了默契。望着这样的风景,虽显得有些单调,但就像人一样,它们也要过节,平日各具特色的它们,今天也要协调起来,毕竟一年这样的日子只有一次。
2002年12月24日下午15∶35 巴黎塞纳河边
今天是圣诞节,天空中灰色与蓝色就像事先约定好似的,各自占了一半的位置,它们就这样安静地呆在那儿,谁也不愿多挪一步。隐隐约约一些白色夹杂在它们的连接处,白在这个时候显得很珍贵,它是必不可少的,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会博得灰与蓝的同情。我不知道是否每年的圣诞节都是这样,至少这是我来巴黎后第一次看到灰与蓝这样地和谐,似乎它们也在耐心地等待圣诞钟声敲响的那一刻……
灰与蓝依旧平静地躺在那里,各自都不愿打扰对方,能感觉到它们都有些疲倦。看来今天无论发生什么,它们都舍不得动弹一下。只有白在慢慢地来回移动,在它看来,今天是属于自己的天下了,因为只有它才显得有些活力。虽然与灰、蓝相比,白少得可怜,但它们都宁愿去做它的陪衬。至少,今天是这样的。
也许,今晚的钟声是为白敲响的。
2002年12月27日 巴黎国际艺术城
巴黎地铁的小偷差不多都是些一米五左右的阿尔巴尼亚或东欧的男孩或女孩,他们上车后,主要目标就是亚洲人,更确切地说是中国人,因为我们是习惯带现金出门的。四五个小孩会围着你不停地转,直到有所收获才下车。
小偷的标记是明显的,他们大多穿着脏衣服。只要他们一上车,人们便都警觉起来,他们似乎也不在乎。我的一位朋友带国内的人来,从机场上地铁,便被这群“小孩”偷去1600欧元。另一个朋友在地铁上被偷,小偷们下车发现不是钱包,而是电话号码本,便追着启动的列车,从车窗将本子扔进来,着实令那位朋友感动不少。
在马德里的街道上,我正走着,突然来了两三个怀抱小孩、手拿地图的妇女向我说着什么,好像是在问路,其实她们是小偷,我当时的反应是“我怎么知道路况?”这时,过来一个年轻人,手拿报纸将她们哄走了。回到巴黎,朋友说,这种偷抢方式在西班牙已流行了十几年,而且小偷们也不改变一下偷法(这些妇女大都是吉普赛人)。这种思维方式也许是欧洲人所特有的,它渗透到各个领域。就像枫丹白露的一个画家,一辈子只想画一个长卷,他已画了快一屋子了,并不断地接纸,每天画头一天遇到或梦里的事情,他说,如果生命结束了,作品也就完成了。我们不会一生只去做一件事,中国人还是太聪明,我们会根据主客观的因素不断地去调整、改变自己。
正如一位在德国呆了很长时间的朋友总结的:西方人像一块石头,中国人则像一团雾。
2002年12月28日 巴黎国际艺术城
在欧洲,常常可以听到欧洲人嘴里说出中文。
在巴黎蒙马特的红磨坊附近,一些性表演场所的门口,几个黑人或阿拉伯人会拦住你,并用生硬的中文说:“你好,公款,发票。”
在佛罗伦萨,我看中一个背包,因价格太高(170欧元),不想买了,卖包的意大利人非要你给出个价钱,无奈之下,我在计算器上按了个10欧元,哪知他突然用中文说:“你该干嘛就干嘛去吧。”也许是中国人“特有”的砍价方式使他不得不学一句回应的话。
在巴塞罗那的毕加索馆,门卫见到我们,用中文说:“您走好。”我当时以为他会说汉语,连忙回应了两句,看到他一脸的茫然,才知道他只会说那三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