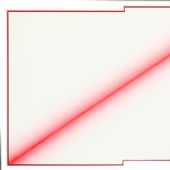艺术家的位置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艺术家都是一些在现实中无力的人。
这句话可能过于偏激,但可以肯定的是,艺术家一定是敏感的人。陈文骥年龄已不算轻,但不管是“八五”、“八九”、或是“新生代”等等那个年代热闹的运动,他都很少参与,而是选择悄悄的站到了一边。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不被承认,事实上凭借高超的绘画技艺,陈文骥当时在圈内已被广为看好。选择边缘,更多是出于个体对“运动”与“煽动”的厌恶。
陈文骥曾经说过:“我喜欢关注被人遗忘的物品和角落。这一切与我的性格缺陷有关,同我不健壮的身体体质有关”。可能是基于性格的原因,或是与童年寂寞的记忆有关,他总是有意无意的与人保持距离,哪怕是老朋友,他也不会特别熟腻。“人”在他的画面中很少出现,与之相反的是,他选择了长时间的与物交流,与景交流,景中空无一人,寂寞而又安全。
1949年后,在这个全新的中国,出于政权的需要,艺术作品无不渲染“浪漫情节”、“英雄情结”,艺术家需要的是“升华”、“提高”,“语不惊人死不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情结进入了中国人的血液,即时在当代艺术的外衣下,很多的艺术作品也没有逃脱掉这一点。对“大”、“批判”、“政治”等集体话语的迷恋,都是这种情结的变相演出。
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多年来,中国对“宏大叙事”的崇拜,以及对个人的忽视。这也导致了“圈子文化”的盛行。事实上当代艺术圈就是一个江湖,讲求的是一个“混”字。每个人都“混”得不亦乐乎,而代价就是艺术上的近亲繁殖。我们在等待了六十年之后,在政治与金钱的轮番打压下,真正能够不为外界所动,用一辈子的生命将自己的个人追求“完成”的艺术家依然稀少。每个人都在表现,都在批判,都在不断变换图式,都在等待震撼与被震撼,却没有人能够耐住寂寞,凝视存在,剖析存在,而这才是西方绘画传统的经典母题。
陈文骥曾说过:“今天的艺术家太热衷于介入社会,太想在政治领域中寻找到一席之地。在太平年月,被宠坏了的艺术家野心也在暴涨。或许说,在艺评家和策展人的误导和纵容下,艺术家太爱管别人的闲事,太爱对社会指手划脚,自我解释的精神则荡然无存”。
泡沫终将散去。“边缘”,可能才是留给真正的艺术家的位置。而除了一个艺术家的自觉之外,陈文骥对“边缘”的偏好,其实更多的是出于性情的本能选择。他自己曾写道:“个体和虚无我以为是艺术家所必须的。由于地处“边缘”,一定是不被关注,有些寂寞,不太热闹的地方。同时又没有绝对的对手,也不会被主流标准所约束,还可以获得一种远距离的思考态度,和我的生存状态很吻合。当一切都安静下来,我发现“边缘”的空间对我已是足够大了”。
跨越“瞬间”
有意思的是,“‘边缘’的空间对我已是足够大了”这句话,不光适合于他的立场,也同样适用于他的艺术创作。
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的眼光总是在一些“不入画”的静物、风景、角落上停留,茶杯、灯管、报纸等等,他在努力的观察他们,靠近他们,将一种很明显的个人的忧郁、自闭的情绪带入画中。在当时,他的名字还总是与写实联系到一起,很少有人意识到他在画面中透漏出的提问,不是对写实的提问,而是对能否抓住稍纵即逝的真实的提问,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总让人感觉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原因,这一点从他对西班牙画家洛佩兹的喜爱上也可以得到印证。正因为如此,他终将超越表面上的写实,进入对存在的追求。
约翰•伯格说过:“形象的静止是永恒的象征。故事、诗歌、音乐属于时间,而且在时间之中表演。静止的视觉形象在自身之中排斥时间。因此其穿越时间的预言更令人惊叹”。
如果说音乐是对时间的占领,那么绘画就是对时间的穿越。在这个愈发被商品、媒体控制的时空里,“更新”成了最高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里,没有之前,没有之后,只有瞬间;而绘画却能够使时空延展,对抗瞬间。“当代艺术”这个词,如果指的是不断更新,追赶愈加“瞬间化”的时空观的话,那就证明还没有认识到艺术真正的力量所在。
陈文骥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曾说:“艺术创作是一种向自己内心挖掘的过程。它能使有限的时间获得延续,也能使有限的空间获得扩展”。在他的画中,似乎并没有为时间安排位置,他无意抓住瞬间。他好像是在一个凝固了的世界中到处查看,一切都是静的,静到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微观的具体
1995年后,陈文骥将画室搬入燕郊。在这之后,郊区的烟囱、街道、屋顶、天空都成为了他的模特,陈文骥的绘画由静物转入风景,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陈文骥的画中,它们像是一个个的人在向我们走来,他不描摹他们,而是为它们一一创作肖像,好像想要在它们消失之前将之抓住,弥漫于画面之中的光线温暖而伤感。
但这种偏于情绪化的表达并没有使陈文骥满足。随着对艺术与自身了解的不断深入,他愈发想要寻找一种更加纯粹、直接的视觉表达,这不是来自于某种策略或是潮流,而是来自于内心的需要。正因为这样,被描摹对象的身份在陈文骥的绘画中的意义逐渐模糊了,他的视线在形体上不断聚焦,抚摸,将精力投入到了形体本身,从中提炼出一种“微观的具体”。这标志着陈文骥告别“叙事”,走入了一个更加纯粹的领域。
写到这里,笔者突然想起小时候,家里没人,闲极无聊,经常会蹲到地上挖蚂蚁洞玩。当注视一个个小小的蚂蚁洞时,视觉会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就像一个镜头,要由正常的观看距离转入微距。慢慢的调整之后,蚂蚁洞在眼前逐渐变大,变得清晰,蚂蚁开始显露出来,然后,每只蚂蚁都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再到后来,我就能区分好多的蚂蚁,甚至会给他们起名字了,这时,一个蚂蚁洞就像一个世界一样大……,这个不断聚焦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有时需要好几个小时,而且不能有人来打扰,否则前功尽弃。
这样,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像陈文骥这样的艺术家必然选择边缘,因为他需要长时间的聚焦,来不断接近他的目标,这个过程不能有人来打断。他持续的凝视,出于生理构造上的局限,这很容易让人感到疲劳(这也是为什么特写镜头只能在电视中少量出现的原因),但陈文骥却自然而然的做到了这一点,这种冷静与坚持在一个浮躁的时代是稀缺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由他的作品联想到北欧的艺术。
有的文章曾将陈文骥的创作与禅联系到一起,但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禅是在思维上不断接近知与不知的临界点的活动,而陈文骥的绘画则是在视觉上不断接近知与不知的临界点的过程。二者接近存在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从这一点上来说,陈文骥一直是一个本分的视觉艺术家。
“边缘”美学
陈文骥曾自谦对色彩不甚敏感,与色彩相比,形体更具永恒感。完美的形体是对瞬间的有效对抗。光产生了明暗,产生了光影,光创造了形体,而这一创造正是通过“边缘”来体现的。有的艺术家甚至说:抓住了边缘,就抓住了形体。
我们从一开始学习绘画,就被告知:边缘是不存在的,边缘是转过去的面。边缘是空间与空间,物体与空间的接触,边缘隐藏着存在的秘密,从维拉斯贵支到塞尚再到莫兰迪,这些大师都熟知这一点。边缘是一种提问,是把握存在的钥匙。这一点,学院早已教给我们,但可惜的是,大多数时间,它都被体系化的教学指向了技术,而非存在。而经过了多年的探索,陈文骥的目光最终落在了此处。
正如他自己所言,对别人来说极狭极窄的边缘之地,已足够陈文骥施展拳脚了。他的画面中的形体渐趋简练,最终只剩下一些规则或是不规则的几何形体,颜色也变得鲜艳起来,他以极大的耐心与高超的技术一遍遍的描画着边缘与边缘之间的细腻过渡;光线不再固定,而是开始在画面之上流动 。在他的笔下,绘画已超越了具象与抽象之间的讨论,看似抽象,其实具象到不能再具象,挂在墙上,无非就是平面上的一段或突兀或圆滑的过渡与突起,陈文骥已经从“画什么”的问题中超越,开始讨论“什么是画”的本质问题。
古老的视觉游戏
将他的新作放到展厅中一起挂起来,会更有助于人们理解陈文骥的意图:在一面面的白墙之上,这些作品像是艺术家与观众开的一个有关“三维”的玩笑(就像那句广为流传的话:绘画是对视觉的欺骗),让人强烈的意识到绘画本质的美丽所在:在平面上虚构真实。这种美感纯粹而又直接,无法复述,只能是作用于视觉。如果用语言勉强转述,可能就只是一个简单的词汇——立体。这就像是一个医生经过耐心的排查,最终找到了致命的病菌一样;陈文骥经过多年的探索,终于找到了绘画,或是视觉中让自己摆脱不掉的神奇所在。这不是一个概括、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聚焦、提纯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操作的具体性,自然而然的屏蔽掉了“叙事”、“意义”等理论的牵绊,并且没有走入美术史的风格重复。它不是来自于预设,而是与陈文骥个人的性情、审美甚至身体状况直接相关的,是一个人的事情。
为什么一个显而易见的“存在”,一旦在平面上用一系列手段再现出来,就会给人带来如此大的满足,而且几千年没有衰减?是否虚构是人类接近存在,再现存在的特殊才能,有了这一上帝赋予的能力,我们对把握自身存在的世界会有更多的安全感,并能从中得以一窥造物主的秘密?每一次人类对绘画认识上的转变,同时也是人类对时间与空间认识上的转变。也正因为这份对“存在”的求知欲,画家这个行当还存在着,而且会继续存在。
结语
陈文骥在画室中日复一日的尽着自己的本分,时间在这里仿佛凝固,外界的纷扰与他丝毫无涉,这种长期坚持的回报,是他正一步步的向自己的目标挺进。喧嚣过后,当大多数人发现自己并没有如想象中那样勇猛精进,只不过是迟钝、麻木而已时,可能只有像陈文骥这样自甘“边缘”的艺术家,才真正的实现了自我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