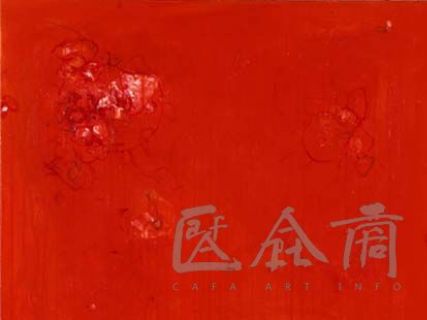
时间:2009-11-4
地点:谭平老师办公室
章燕紫(以下简称章):谭老师您好!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您说,德国留学的经历使您理解了抽象的本质,能请您谈谈吗?
谭平(以下简称谭):嗯,不怎么好回答,什么事都在不断变化……
章:在我印象中“德国”/“抽象”这些词都是很理性的,但您的画给我的感觉还是很感性的。
谭:在89年去德国留学之前,我在版画和绘画的创作中,就已经开始做一些抽象绘画的实践了,但当时的抽象更多的是从风格上借鉴。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我首先对印象派、后印象派、凡高、高更感兴趣,后来是毕加索、马蒂斯,再后来就是抽象的艺术家康定斯基啊,对赵无极等一些艺术家特别关注,当时可能并不理解他们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只是看他们的作品有意思。觉得赵无极的画,似有似无的,又像风景又不是,朦朦胧胧,比写实更有想象力。
章:更抒情。
谭:对!更抒情!在版画上呢,更多的关注版画的肌理变化。原来对对人物的造型、结构这些感兴趣,过渡到抽象艺术呢,关注的东西就有所改变,铜板被深腐蚀后产生的肌理效果,既抽象又具象,从中发现抽象的因素。这种肌理它没有形象,但它又是具体的。所有细微的东西像我们看到的沙砾啊,灰尘啊,它有,你说它是什么?这种质感,对我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当时做的抽象版画基本上是属于这种倾向。
后来去德国以后,体会就不一样了,确实像你说的,德国的抽象是非常理性的。但它也分两类,两大类。我一直说德国是一个分裂的民族,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一方面是非常理性的,还有一方面是非常疯狂的。
章:所以他们有纳粹。
谭:对,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一方面我们看到德国的抽象表现主义的表达的方式和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完全不一样。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更多的是一种绘画语言的拓展,或是一个观念。但是德国的抽象表现主义像是一种本能的行为。那么另一方面,他的理性抽象呢,则更多的是以数字作为基础。很多几何抽象的作品非常理性,从作品开始,计算成为华中的核心部分,里面春在各种模数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理性到了绝对的程度!从这方面来讲,我收获是非常大的。我现在的画画,希望表面看起来非常自由,但背后隐藏非常严谨的结构在后面。
章:抽象也是一种形象吗?
谭:不同的艺术家对抽象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我个人来说,我还真不太愿意用抽象这两个字。我的抽象呢,应该说是一种微观的具象。在我画每一个小的形象,小东西的时候,是非常具体的。但这个具体呢,又非一般的具体,好比说我画一个细胞,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但我的想象是非常具体的,所以我的绘画可能和一般意义上的抽象不一样。
章:是否就是您刚才说的沙砾一样具体的细节,组成的画面最后给人的感觉是抽象的。
谭:很多写意的抽象,一看像山或者像水,像一些我们能识别的一些东西。我的这个抽象,对观者来讲,就是无法识别。就是说,没有什么所对应的东西。我的出发点是以一种非常具体的角度来出发,但得到的结果是非常抽象的。这是一种绘画的原动力在那儿起作用!如果我们只是为抽象而抽象的话,那他的绘画来源往往来源于一般性的审美,或者是抽象的一般规律。我觉得这种抽象仅仅停留在表面。对于今天的抽象艺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他创作的来源在哪儿。艺术对于我无所谓抽象还是具象。不受所谓语言的限制,是一种需要。所以我觉得抽象也是一种形象!抽象也是一种具体的形象!
章:可以这么说,您的绘画是背后的理性支撑着画面的感性,具体的细节表达整体的抽象。
谭:嗯,是具体的形象。
章:您作画时常常随意的运用一些线条,一气呵成,讲究贯气,是否和中国书法有共通之处?
谭:这是一个关于创作方法的问题。一般情况我特别注重创作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太注重作品的结果。我们过去看画册也好,想也好,更多的是想:我喜欢谁的?我要画出什么样的东西?都是这样学过来的,都是看别人的结果。从无数的结果当中选择一个不同的东西做出来。我觉得这种方法是很难的,也是不大可能的。人们总说你像谁像谁,或者说你受谁影响,总是这样。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分析一个艺术家,特别是成功的艺术家,他都有一套完整的方法,从哪儿开始,一步步就自然地走到那儿。所以我就非常喜欢看一些传记啊,了解这些艺术家的人生经历,生活,事业,包括画画的过程。
章:您特别重视过程。
谭:对!每一次绘画时,我都在想,我这一次怎么做?怎么和以往不同?结果不管!但是事实上,你如果选择一个独特的过程的话,自然就会产生一个独特的结果。所以过程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对结果的追求。我要求我十分钟画完一张3米的画,要不离开画布,和画布距离50公分,不看整体,这样画的过程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不看整体,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连着画过去。这样就很贯气。在画国画的时候,你站在宣纸前,你是站在画外,你是控制这个画面的。但是如果一个特大的画,你在画内,你就进入了这个画面。唯一的链接就像锁链一样,必须把它链接起来,此时你和画就成为一体了。
章:那不就是和舞蹈一样吗?
谭:哎,有点儿像。你说像舞蹈,其实这种对贯气的理解,对中国书法的理解,换了一个角度,把那个东西放在更大的范围里去看,会更深切。在一个大画面前,不是一般的说从的整体结构去考虑。我每一次做一件作品,会根据画的大小,根据展览的要求,创作一种方法,首先创作一种方法,然后再去做,这样东西出来后就会是独特的,哪怕画的同样是一块红色,也会和别人的不一样。因为你的方法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章:您说您的画都不是事先设计出来的,这种的画面不确定性,和中国写意画中笔墨的偶然性是一回事吗?
谭:我上学期间就非常喜欢中国画,当时临摹,分析构图啊,也看一些中国画论,这对我后来从事创作特别有帮助。比如构图观,包括:“气韵生动”,对我后来从事抽象绘画特别有关系。但我又不想把这种东西变成一种表面的流露,好像从画面中看到书法的东西,看到写意的东西,就太表面了。要想办法不留痕迹,隐藏在后面。偶然性在我的绘画创作中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偶然性是艺术中一个最精彩的东西。所以,我的画会画好多遍,这么多遍主要目的是寻找机会,把握偶然。画面一旦有了“经营”,就要不得了。
章:就违背了你对偶然性的追求。
谭:对!所以有时十分钟把作品完成后,我会觉得这是最好,我就把它保留下来。这也是我绘画的一个方法。
章:你的画面有出人意料之感,简单却耐看。画面中那些飘忽的,游动的符号,诗意中有些伤感,好像漂浮的灵魂,并不给人恐怖感。
谭:有一段画了很多这种小的圆圈的符号,飘飘忽忽。5年前,我的一些绘画还是一些比较沉重的圆形,很多人看了也有一种恐惧的感觉。那么,随着时间的变化,这种圆形一点点就变成了小圆圈了,以后就变成了点,这样一点点变化,这样从画面中很大的圆圈变成点点时候,似乎就进入了一种空间,这时候,这些符号就开始漂浮了。这和心情有关系。
章:那时您的心情变轻松了吗?
谭:应该是!画面也逐渐地变得轻松起来。可以说,我的创作和我的情绪是非常有关的。
章:版画专业是否能够丰富艺术表达的手段?
谭:版画最重要的还是过程。因为你学版画,每当你拿起一块板子开始做的时候,过程已经开始了,是吧?如何打磨,如何这样,如何那样,腐蚀会到什么样?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腐蚀?将来印在什么样的纸上,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它是一个过程。所以版画的学习,可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上的训练,而是对人的思维方式的一个训练。学版画的后来从事其他工作的特别多,这和他的训练有关系。我们培养一个人画油画,最后出来他是画油画的,专业性比较强。版画虽然在技术上要求很多,但是在个人风格上的要求反而特别少。那么这个人的欲望就可以比较开放的表达。所以学完版画搞动画的,设计的,油画的,摄影的,装置的,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就是,版画的动手特别直接,像油画,国画,还是通过笔,而版画,你的手直接就要接触它所有的东西,但它的过程又是非常严谨的。它和油画、国画还不一样,油画、国画是大家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大家在这个规则里一点点往前走,看谁走的好。但版画不是,版画的过程是自己要摸索的,这么做、那么做,都在找不同的结果,所以学版画还是有他特殊的意义的。
章:有一篇文章说您开始怀疑绘画的意义。
谭:绘画一直是有意义的。怀疑?我在上学的时候觉得绘画就代表一切。绘画似乎就是艺术的代名词。而现在我的看法更加的开放,我认识到,绘画只是艺术中的一部分。这只是对我当初的认识的怀疑。当然,到了一定的时候,不管从事设计,教学等各种形式,都是有其本身的意义的。
章:西方的“抽象艺术”最后走向“极少主义”,有文章说您不止一次谈过想追求极少的感觉和效果,这种极少主义发展下去将是“一切皆是空”吗?所谓“大音稀声”/“大象无形”。
谭:西方的极简主义和东方的一些哲学思想有些相似。
章:禅宗?
谭:对,也是追求少即是多这样的概念。但是西方的极简主义却是把东西越来越抽离,最后成为一个最为单纯的一个东西,像一块颜色,就是一块颜色,逐渐并没有走向少即是多,而是走向表达一个观念,这是极简主义后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而我所追求的极少,确实是多的意思。因为一张画,画得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会感觉他的内涵越来越多,他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所以画画到一定程度时,如果这个蓝,它没有一定的深度,让人有情感的感受的话,那对我就过不去。如果一个红,不能调动我对历史,对中国的感觉,不能有所启示的话,我觉得这个红也过不去。对于我来讲,我是可以画得越来越少,但一遍遍的覆盖,一遍遍地减,减到的那个程度,一定是具有更大的空间,更大的想象力,给人的情感带来更多的满足,那这个作品才算是完成。这个表面看是少,是真正的“少即是多”的意思,这是我所追求的。
章:这个重复,叠加的过程,是不考虑结果的。
谭:结果已经不重要。
作者:章燕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