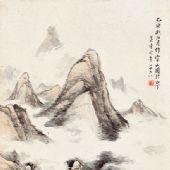又一次饱览了宗其香先生的绘画佳作,在新建荣宝斋大厦美术馆。这座大厦是琉璃厂西街这条难得地保存着的古老闾巷内唯一一座传统外饰,西式内构的建筑。未悬彩绸条幅,未设礼仪花蓝,未列迎宾佳丽,宽敞简洁的展厅入口旁树立一块标牌,说明这是荣宝斋举办的宗其香画展,也预告了本届荣宝斋拍卖会中国画版块宗其香专场即将举行。
近二三十年,无论宗其香生前身后,在中国美术馆等纯展览画廊,经历过不少次相当规模的宗先生个展,与拍卖相关的,这似是首次。
身为美术圈外人,仅凭直觉看画、爱画,每次走进美术展厅,就像走进深山面临大海,往往会油然而生兴奋之感。走进宗先生的这次画展,耳目身心则都立即为之一震。 因为这间占地并不十分宽阔,但却布局疏密可人,走道回转有致的空间中,百幅大小作品,涵盖了山水、花卉、人物传统中国画三大类题材的精品,色彩斑斓,光影流溢,营造出一种独具的清雅氛围。——也许,这仅只是我个别、甚至精神过敏的感受,因为我曾经为他写过传记,对他的作品早成定见?
开幕式结尾的座谈会上,他那些卓有成就的朋友、高足画家、评论家们发言时,却也用“震撼”表达了自己在这个艺术空间的第一感受。
“你的画不能感动你自己,还能感动谁?画一张画先想着卖多少钱,画就毁了。”这是武平梅,宗先生遗孀传述的宗其香诤言。她是我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同学,总角交。
这句话道出了美术大家宗其香艺术创作秘密中之秘密。
在我的同龄或上下的几代人,提起这位画家的大名,似乎并不陌生。如果问起现今的中青年俊男靓女宗其香何许人,绝大多数却都会是一脸茫然。这位上世纪30年代即崭露峥嵘于中国画坛,在艰苦家国环境中历练成长,走出自己独特风格的大画家、徐悲鸿画派重要传承人之一,在波谲云诡的商品和后现代风浪中,没有成为抢眼的弄潮儿,而且几乎已被冲到边缘,被人淡忘。12月2日展览开幕日,我追随一批从未将他忘记的人,画家、评论家、他的亲炙高足和崇拜者鱼贯而来,观瞻他,评赞他,回忆他,灼见纷纭,畅快淋漓,历数他在上世纪大半个后期对中国画创作、创新的贡献;尤其是毕生借鉴西画技法改革国画的成果,向中国宝库输入的珍品;由此,也令我打开尘封的记忆闸门。
回顾宗先生80余年的生活创作道路,也是如入山阴道上,令人目不暇接。民国之初,生于当时首都南京的闾左陋巷;襁褓中丧母,孤贫中成长;头顶仅及画案,就双膝跪在凳上开始帮画师父亲勾线涂色着墨;16岁,尚为南京太平路一家工艺美术礼品店学徒,即携其山水画作参加全国美展,加入成年知名画家赈灾救亡义举,随即被接纳为中华美术会会员;次年又以《双鱼》、《白孔雀》两幅作品呈现于加拿大温哥华中国画展,且均被买家购藏,得酬贰佰银圆。相对于其时他以学徒劳作所得仅可免强维持温饱而言,这是他生平所得第一桶金,而他也悉数捐献给了东北灾区同胞。
两年当中,两桩既无曲折又乏悬念的往事,在一部传记中仅以数笔带过,但却说明,生而贫困,不一定非将人变得卑琐,而且正当其时,我们的这位少年画家已将他那稚嫩的肩背跻入成年同行,承接了一份社会担当。这也是他初次给将来成为大画家的自己画出的道德底线。日后,无论是在硝烟弥漫还是无声无影的人生艺术征战中,身着这层铠甲,他都能全身而过。
这第二桩早年轶事同时还说明,20世纪30年代,少年画家宗其香身居国门之内、市井之中,他的画作即随其年长同行前辈走出了国门,被异邦了解和接受。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也就是宗其香所成长其间那个时段,走过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我们这块国运多舛的土地,已经在逐渐清除满清腐朽帝国的垃圾,摆脱涂炭民众的战乱,步入政治、经济、民生、文化趋稳定升腾,这其实也可谓中国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短短的一段白银时代。中国传统画界,也像其他文化领域一样,志士精英纷纷奋起,探求,思索并实践着改革自身,摆脱困境,走出国门。年仅十五六岁的宗其香向国外画展迈出的这第一步,即仰赖此一社会大背景,又生发于他本人的绘画实力。
看他现今仅存的此时期创作和仿作山水画,如《云山图》、《仿吴仲圭山林幽居图》,其所显现传统中国画技艺之从容娴熟,真已令人不能不惊叹这位少年画早熟的天分。这固然首先得益于他那位民间画工父亲的遗传基因和开蒙技法传授,但也是凭据他本人那点从生到死不知疲倦的刻苦与顽强。可以想象,当时的此类画展,不论国内国外,未见画家其人现身,大约也无潜规则或种种偏见,而仅凭参观者的感官和情趣达成交易,画作本身的素质大约就是独一的决定性因素。就此也可以说,宗其香已经早早实现了他自幼誓立的初愿:好好做事,超越父亲。宗氏画作凭实力走出境外国门这一传统,也是从那时起,贯穿了他的生前身后。由于战乱等种种条件限制,此后20余年,他没有更多海外布展的机会,但是来华商贾游客以至驻跸使节登门求教或求购,还是将他的作品带到世界各地。近30年,宗画在香港、台湾、日本、欧美等地区、国家以丰富多彩的大型个展、合展或其它复制形式得以展示,也都曾得到慧眼真诚热烈的赞赏和收藏。画家本人也随其作品云游异地异国,将更进一步拓展了眼界,丰盈了胸襟。
民族文化走出国门,从来都是双向行。走出去之后,常会满载而归。当年,宗其香第一次送出去了自己的传统中国画,换回来的,除去银圆,似乎还有其它。今天我们已无法确认,初征的斩获是否即刻鼓励了他面向世界敞开怀抱的雄心,但是再看他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也就是在以同等学历考进重庆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毕业前改为美术系)以后,幸运地受到正规现代美术教育,并更幸运地得到一派宗师徐悲鸿亲炙,而且有缘在他的直引下,积极实践他的洋为中用主张期间,其画风已迅速显现一种醒目的转折。就是在中国传统画面上,逐步融入西方的构图、透视、光影表现、色彩运用等等手法和理念。从近年的展览会或出版物上仍常能看到的《芭蕉》、《母与子》、《秋风里》等作品,即可一目了然。其后,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他的大幅作品联翻推出,展览会连年举办,使人也幸运地享受到他的重庆夜景、西南江山、边塞风情以及战争与和平题材、历史题材等等佳作大作频现,则构成了他创作上群峦迭拥的高原。
身为画二代,他不仅弃绝墨守陈规,抱残守缺,被动继承,而且力图超越先人,超越自我,自觉砺炼,不断革新,使自己整个艺术轨迹的时时与世界和时代潮流律动应合。当初在中大美术系受教时,他在西画油画上所下的功夫比国画尤多。这是恩师徐悲鸿针对他对自身条件的因材施教。因此,30年代末开始,法国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大师大卫、德拉克罗瓦、库尔贝、雷诺阿,莫奈、梵高都成了他的良师;其时留法归来不久的徐悲鸿,更是带领宗其香等众弟子走近这些国外艺术大师的导师。
徐悲鸿与宗其香的渊源,也是一段令人欣敬的历史佳话。早年相似的身世,使机缘带来了天然的亲和力,学生对老师景慕追随,老师对学生赏识呵护之间的互动,推出了超出个人的中国新一派——立身根本,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画派。宗其香是徐派理论的忠实实践者和开拓者;夜景,从重庆两江之夜到桂林漓江之夜到河湖海天渔火的闪烁,闹市灯光变幻 ,日月星光探照都由他手握一支中国古老的软笔,写实到了中国古老的软纸上,从而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力。这是宗其香在传统中国画的基础上吸收西洋光影手法上独树一格特的经典成就。80年代后的晚年,随着他的眼界更加高逸,功力更臻完美,自然形成了他创作的又一高原;这也是他仍在不间断、无疆界地吸收绘画艺术精华为己所用的结果;一度,他甚至还尝试过20世纪以来的抽象派。然而归根结底,他的本国、本族绘画功力是那样深厚那样强势,外来的绘画理念手法他借用得再多,也不足以变形异化,更不足以淹没自已的中国画气派与韵致。这也就是为甚麽看宗其香的画,总不会觉得那是日本的欧洲的或是像贾宝玉在太虚幻境看到的水墨滃染,满纸乌云浊雾的不知哪国的,它们永远是中国画,有自己独创风格的给人以美感的中国画。
各门各类的艺术佳作往往是在异议中成长。宗先生的夜景,也是40年代迄今仍有争议的话题。就我这槛外人姑且沿用一句老话来说:托之于言,不如付之于行。习画作画,与许多艺术创作一样,讲究操作实践,亦即下功夫。各行各业的工夫都有自己的落脚点,中国画的工夫,立足点首在笔墨,探讨也还应以笔墨为基础。软笔而欲表现光影,谈何容易!下得功夫,开得尊口。宗先生以其毕生劳作,给我们留下不计其数的绘画佳作,其中的着意表现茫茫暗夜之中水天光影的夜景,重庆的、漓江的、苏州的、渤海的、黄海的.....也是数不胜数。赏画人就是最公正的考官。从20世纪40年代始,宗其香的夜景,始终就是中外私家和博物馆争相购藏的珍品,也是近日荣宝斋拍卖会上竞拍的首选,其实并非毫无缘由。因此,为中国画今后发展繁荣之大计,画界贤者高,似可就此命题继续冷静探讨,反复试验或实践,珍惜自己和他人每一点滴经验成绩,而非轻言封杀。
中国画又一特点当今亦常为人道者,即其气韵。因此论画不仅是技巧,更是画家的人格气质眼界胸怀。再以夜景为例:首先,宗其香时为流亡热血大学生,家国个人前途茫茫,身处饱受战火摧残满目疮痍的重庆,其内心和身外的环境都是一片漆黑。而就在彼时彼刻,为甚麽他要呕心沥血日夜对之观察冥想?那是他透过无边黑暗,用心用眼看到了长江和嘉陵江上的点点渔火,那就是国家民族的希望。于是他提起笔,画出给人信心给人温暖的,富有正能量的作品。就这样,当时已出名的青年画家又一次实践了自己的社会担当。这也就是说,宗其香的绘画创新首先不在一笔一划的细枝末节,而是登临绝顶,放眼四海,挥洒淋漓的大手笔、大胸怀。再进一步说,当今我们的这些赏画论画者,瞻仰大作,抚今追昔,缅怀逝者,更需备足自身气韵,做出堪以向国画发展、交流输入正能量的高见。
2013年岁末
注释:此文已连载在香港《大公报》2013年12月28、29日。有少量删节及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