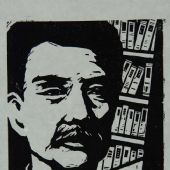我国当代杰出的版画家、美术理论家王琦1918年月4日生于四川重庆,1937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自1952年以来,王琦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教授,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主席、党组书记。
王琦的父亲是一位热心文化教育事业的实业家,他不仅给了王琦一个安定富裕的家庭环境,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浓重的知识氛围。父亲自身就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学根底、并擅书法。又尽其所能地资助文化事业,他是重庆和上海两家出版机构的股东,同时也是重庆两所中学的校董,对于当时的教学方法也有自己的看法,崇拜陶行知和南京的晓庄师范,并以此为范例办自家的私塾、注重和关心子女的教育。比如除了文化课的设置外,私塾还设有劳动课,自家花园里花木菜蔬的一种植。各种各样的家务活、房间及白身的清洁卫生等是这一课程的重要内容。由此影响了王琦一生以劳动为乐、以劳动为美的朴素品德。最令人敬佩的是父亲为私塾请来的教师中有两位是共产党员,这使得王琦很早就接触到革命的道理和马克思、列宁、李大钊等一连串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名字,并立志当一名能够唤起民众的宣传员。另外,眼界开阔的父亲不拒斥任何进步的新知识、新事物,经常从上海订购成捆的“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书以及《莽原》、《语丝》等进步刊物和画报,再加上家里已有的好几书架的线装书、碑帖和字画,使得王琦仿佛沉浸在知识的海洋,广泛又不知疲倦的涉猎,养成了视书如命、以读书为乐的良好习惯并持续至今。这样,较早的智力开发和几十年的知识积累无疑是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不断开阔着他的视野和胸襟。
王琦对于艺术的爱好也始于少年时代。在入学以前,就喜欢用粉笔在地上、墙上作画,画见过的各种动物,临摹《芥子园画谱》和《钦定三希堂法帖》。后来又向袁亭阶教师学习对实物写生,而且成绩一直很好显示出良好的天赋。16岁王琦投考上海美专附属成美中学,1937年在上海美专西画系毕业,从此便开始了漫长而不懈的艺术征途和不间断的繁密的美术编辑、组织工作。
1938年4—8月王琦在武汉政治部第三厅美术科从事抗战美术宣传工作。1938年8一12月在延安“鲁艺”美术系学习。其后在重庆参加革命美术活动,曾在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又在陶行知主办的育才学校绘画组任教并与卢鸿基、洪毅然、王朝闻等合办《战斗美术》杂志。1939年2月首次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木刻作品,此后常为《战时青年》杂志作封面木刻,得到当时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同志的赞赏,同年冬作品人选莫斯科举办的“中国抗战美术作品展”,获好评。
40年代初他与友人发起组织中国木刻研究会,并当选为常务理事,先后参加筹办两届全国木刻展和四次出国展,为中国木刻推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参加9人木刻联展,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周恩来的接见。1948年在香港参加“人间画会”,1949年当选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代表,解放后在上海任行知艺术学校美术组主任。1952年调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同年参加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构图设计工作。1963年,在长春举办个展。1980年与彦涵在日本举办版画联展,年底在国内十几个城市举办个展。1987年在维也纳举办“王琦、王炜版画展”,1988年参加台北的“五元老版画展”,1991年参加纽约东方画廊举办的“力群、王琦、古元版画展”。同年,荣宝斋举办了“王琦、王炜、王仲三人画展”。1991年王琦还荣获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版画家协会颁发的“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1992年10月,日本创作学会长池田大作又向他颁发了“富士美术馆荣誉奖”。
作为美术理论家的王琦,早在40年代就担任过重庆《新华日报》、《新蜀报》、《国民公报》、《民主报》、《西南日报》、南京的《新民报》、香港的《星岛日报》、《大公报》的美术副刊主编,还为“木协”起草了《木刻工作者在今天的任务》的文告,1956年后又历任《美术研究》、《版画》杂志常务编委、《美术》、《世界美术》、《版画》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年—1982年美术集》、《当代中国的美术》、《欧洲美术史》、《差学丛书:美术系列》主编,所以美术理论的研究从来就是他工作的重要部分,先后发表的美术论文有500余篇,其中一部分收入《新美术论集》、《谈绘画》、《艺术形式的探索》、《论外国画家》、《美术笔谈》等书。
对艺术形式的问题王琦先生有过深人的研究,在1979年的《艺术形式的探索》一文中他认为:艺术和科学的重要区别就在于艺术家是用形象化的手段来揭示生活的面貌,艺术家应善于运用生活中各种形象的事物来塑造生动可感的艺术形象。进而又指出探索新形式是为了更深刻地表现思想内容,是为了更真实、完整地表现客观对象,艺术形式的革新应以继承传统为基础,探索新的艺术形式要适应广大欣赏者的水平。这是“文革”以后较早的一篇系统、客观、全面地论述艺术形式的学术论文,为当时的美术形式的探索起到了健康的推动作用。
新时期以来王琦先生一直关注着国内的美术现状,对当代美术中出现的重要的美术思潮、美术现象都有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其《美术笔淡》一书集中了他对美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所提出过的许多非常精辟的见解,产生过很好的作用。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新观念、新形式不断涌入国内,在活跃美术创作、解放思想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极端的口号和行为,诸如主张摆脱党的领导和“二为”方针,认为只要坚持“二为”,艺术家就有会有真正的创作自由,艺术离政治越远才越纯粹,“艺术创作是艺术家的主观反射”以至于“对各种艺术流派一视同仁”等等,对于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美术界的反映,王先生及时地、一针见血地写了《创作自由与自由化》一文,指同西方舆论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指责早在数十年前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的时期就有过,其实质是借口自由来改变社会主义艺术的方向和领导。其实无限制的自由是从来没有的,“自由”在不同阶级、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们那里,有时甚至会产生完全相反的含义,比如绝对的自由在西方由小资产阶级提出时,就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王先生又生动地通过古今中外的一些事例告诉人们,任何一个艺术家,只有当他能自觉地愿意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服务时,他才能在创作上获得自由,反之他就会感到压抑和强制的痛苦。进而王先生又清醒地指出了自由化对于创作的危害,认为绝对的自由会使艺术家自觉不自觉地缩小观察现实的圈子,拒绝广泛和全面地去研究现实。关闭在自己灵魂的孤寂中间,停止在那凭借脱离社会生活的自我反省和任意思想而进行毫无结果的“自我认识”上面。由此可见,坚决地维护党的文艺方针,自觉运用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是王先生理论文章的重大特色。
在《艺术创作的上观与客观》一文中,王先生对艺术史上不同流派的艺术主张与创作实践进行了归纳:1以自然主义为代表的如实反映客观世界的艺木;2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代表的通过作者的主观世界表现客观世界的艺术;3以表现主义等为代表的通过客观表现主观的艺术;4以抽象主义为代表的表现作者主观世界的艺术。进而指出在我们的美术创作中仍然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广大欣赏者能否理解的问题。因此,一方面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方面也应允许多种创作方法并存,让它们在创作实践中互相竞赛、补充,这将无疑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美术的繁荣发展。
在《有关社会主义美术问题的一点思考》一文中,王先生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术应是全体美术工作者的长远奋斗目标,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是确保我们的美术创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不致迷失航向的根本;坚持改革开放又是促进美术创作面貌日新月异并变得更加丰富多采的必需。同时认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国外是艺术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并提倡在表现重大题材和主题的同时,不该轻视题材的广泛性和形式风格的多样性。这一论文不仅具有独特的创建性,更具有现实意义。
在《93东京日中美术研讨会上的基调演讲》中在详细地介绍了西洋美术对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影响后,王琦先生指出:“洋务运动”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实际上是企图把西方现代的先进技术和中国固有的封建思想结合起来,学了外国的本领,却仍要保有中国的旧习。这样的改革是不能触动国民精神之根本的,也无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后来继之而起的“戊戌维新”,方才注意到改革教育的重要性,也在实质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之新局面的到来。他认为西方美术对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影响总体说来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应看到,从摹仿到创造大抵是画家在接受外来影响时所难以避免的过程,特别是一个新画种最初传播进来的时候更是如此。同时演讲也没有回避中国在学习借鉴中曾发生过的一些失误与偏颇:无论何时,中国美术对待外国美术的态度部是与国家的政策同步的。建国初期出现了单方面接受苏联及19世纪俄罗斯美术的现象,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现代美术传统看成腐朽和堕落的而加以抵制和排斥,改革开放之后迎来了第二次西方美术大冲击,王先生对此依旧保持了可贵的清醒与客观,认为这次冲击所带给我们的影响仍然是正负两方面的。从积极的方面看它打破了过去美术创作的单一模式,在题材、形式和艺术风格上,出现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局面,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加强,个性特点突出同时新工具材料的广泛应用,也促进了艺术语言的扩展和变化。从消极的方面看,西方社会流行的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也随之夹杂而来,冲击了我们既定的文艺方针,助长了艺术脱离人民、脱离民族传统、脱离计会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为艺术上的世界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与融合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和时代中,王琦先生这样认真、系统地总结近百年来西方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影响,井指出其中的得与失无疑对于正在奔向21世纪的中国美术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上的一点论述虽然简短粗浅,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王琦先生不是那种躲在书斋里的学问家,他的一切研究都是从实际出发,随时随地关注着现实中发生的各种美术现象和美术思潮,并目始终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文艺方针,既观点鲜明、又以理服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尤为突出。作为美术理论家,他从来善于自觉运用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在繁忙的社会上作之余勤奋不懈,至耕不辍。
——原载《美术观察》1998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