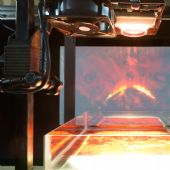摄影是一项特殊的介入、应用和不断自我更新的媒介、载体,在参与当代文化叙事与艺术新秩序及新格局的建构之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继2013年“灵光与后灵光”与2015年“陌生的亚洲”两届摄影双年展后,第三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主题回归摄影母题,以“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来探讨摄影在当代语境中的意义。2018年9月28日与10月1日分别在辽宁北镇文化产业中心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两地同时举办。王璜生、张子康担任展览总监,汉斯·德·伍尔夫(Hans De Wolf)、蔡萌、安吉拉·费雷拉(Ângela Ferreira)、何伊宁组成策展团队。
巧妙的是,展览分为十二个章节,“12”这个数字让人不自觉联想起时髦的“十二星座”占星术,这的确映射了策展团队的初衷。汉斯回忆团队最初决定以“星座”的模式排布的时候,他们“进行了一项非常不寻常的实践”将所有的信息按一定规则排布,“而这将为所有贡献者、所有章节提供一个全新的感受——这不符合任何理性逻辑。”看似星座与摄影展两者并无直接联系,从“星座”到“摄影展”这其中又包含了什么故事呢?星座象征着各种复杂关系的集合,从星座入手,其实就是一次关系的搭建,第三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又编织了哪些关系呢?
影像民主化时代中的摄影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柏拉图的洞穴(论摄影)》一文中开篇指出,“人类冥顽不灵地流连在柏拉图的洞穴之中,仍然依其亘古不变的习惯沉浸在纯粹的理念映像之中沾沾自喜。然而,受照片的教化与受更古老、更艺术化的图象的启蒙截然不同。原因就在于我们周围有着更多的物象在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据记录这项工作开始于1839年。”她所谓的这项摄影工作,在发明的半个世纪内,被广泛运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譬如医疗、科学、政治诉求、宣传等等,那是这项工作最流行的、活跃的一段时期,它的动词化特性被无限扩大。
如今的拍摄照片不需要“累赘且昂贵的玩意儿”,生活在当下的人们,随时随地都体验着物象充斥的吸引力,手机这个“金属器官”(《感官技术——手机:身体与社会》,汪民安,p81页)将原本的书写和阅览模式逐步消解,“影像民主化”的内涵前所未有地滲入我们的生活之中:微信、微博(推特)、抖音、ins、脸书等正无孔不入地入侵生活,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直接方式。无法触及的物象也能在互联的编织网络中无限地簇拥在一起。于是乎,我们的观看方式、思维方式、分享方式也随之改变,一种新鲜的生活方式被重新构建起来。
“从那以后,几乎万事万物都被摄制下来。这种吸纳一切的摄影眼光改变了洞穴——我们居住的世界——中限定的关系”。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在摄影的参与下被完全改变。但,如今的“摄影”又不大一样了,短短几十秒时间内从拍摄到分享的全部的程序皆可完成,这“迅速、便利”的操作过程却使得原本动态化的“摄影”逐渐走向名词化的摄影,简单来说,摄影变成了“影”,变成了像素化的结果,变成我们去传播的那个“物”。“咔嚓”所传播出的速度感、科技感、未来感人无暇思考“为何要拍”。展览的故事建立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之中,试图展开一个平台重拾动词的“摄影”,探讨多元文化时代中的摄影应当何为。
展览欲向观众提问,也重在与观众交流,除了显现的庞大工作——邀请国内外113位艺术家、呈现1000多件作品、同时在两地承办、6000多平的巨大展场以外,策展团队在构思初便埋下了多重线索,这些线索并非单一地存在——它们相互联系,组合成不同的关系,以“关系”视角出发,能帮助我们揭开隐藏在展览表相背后的多重结构。具体来谈,“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第三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构建了各种各样的编码:从讨论主题之中两个要素的关系,到“十二星座化”地编排章节,抑或是展览与北镇、北京之间的受众人群,到展场中空间与展品、作品的安排叙事模式的关系,层层叠叠的关系编织交错,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元的媒介体,一面思考“多元语境之中摄影何从”的反光镜。
“混合”主题与星座布阵
摄影诞生之初,公共性与私密性的关系就被反复讨论,“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可以说是回归摄影的母题,如将公共性与私密性两个词分开来看,都不足以构成讨论本次展览的重点,其主题的落脚点在这两者的“混合”。策展人之一蔡萌关于主题谈到,“这很像电视普及之后的情景,首先,电视带来的冲击导致作为‘公共的’电影院流失了一部分观众,而在家看电视是相对‘私密的’,电影院与家庭(看电视)组成一组公共性与私密性关系。如今,一人一台手机、借助网络、上传到社交平台几乎一气呵成,那么,原本是私人化的拍摄、视角、作品被放置在公共的媒介上,变成了全民化的共享,而展览上又深化了这种公共性,于是,家庭与电影院,手机里的照片与展现场的照片,也正好构成一组公共性与私密性观看的对应关系”。如将公共性与私密性两个词分开来看,都不足以构成讨论本次展览的重点,其主题的落脚点在这两者的“混合”。这也正暗示着作为动词的摄影属性。但这并非拙劣地希望回到摄影被发明最初的状态,动词“摄影”实质强调的是一种思考的方式、观看的方式、一种表达的方式,以及在当今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如何发挥它的作用。
展览分为十二个章节,12这个数字让人不自觉联想起当下最流行的“十二星座”命运说,这的确也影射了策展团队的初衷。策展人汉斯回忆团队最初决定以“星座”的模式排布的时候,他们“进行了一项非常不寻常的实践——将艺术品、艺术家、图片以前所未有的形式组合到一起,而这将为所有贡献者、所有章节提供一个全新的感受——这不符合任何理性逻辑。”坦白来说,尤其是现在的一部分年轻人,深信这些“被人类赋予特殊含义的星辰组合”与人的行动逻辑、思维规律之间有密切联系。回顾远古时期的东西方,均有对占星术不同的诠释,不论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和苏美尔时期的文明印迹,还是《史记》中对二十八宿及四象的记载,“星座”的概念象征着各种复杂关系的集合体,它成为人为构建的人与自然、宇宙之间建的一种非物质化关联,最优化程度上地隐喻了人类的美好意念。如另一位策展人安吉拉•费雷拉(Ângela Ferreira)所谈:“(星座)这是一种高明的机制,可以帮助他们应对世界的浩瀚和复杂。”
窗帘、阳台、墙、森林、陈列柜、液态智慧、灰尘、阴影、神儿(spirit)、反向的凝视、太空飞船——十二个章节如同云图排开,1000多件作品像一颗颗星星,沉浮于浩瀚的星空之中,在四位策展人的“穿针引线”下图像星系被编构出来,指向人类生活、意图、故事也串联着古今、宇宙与自然。
空间对话与展品叙事
本次双年展展出场所跨越首都北京与辽宁北镇两地,两地之间也形成了一定的对话关系,场所的构建承载了概念输出的媒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在首都北京,与作为文化古都“五岳五镇”的辽宁锦州北镇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对话。而面对不同的场域,策展人团队四人联合孙华带领的布展团队,采用了面对不同环境呈现不同解答方式的手法,在人群定位、展品挑选、布置模式上进行了全新的尝试。辽宁北镇展区巨型仓库般的展示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浅灰露骨天顶、原色木质框架与精心调制的灯光色温混合在一起,像是营造了一片太空舱。在无数灯管闪烁的包裹中,观众便置身于群星闪烁的外太空,遨游在一场极具实验性和挑战性的影像旅程里。
北京地区的美术馆展场又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踏入美术馆,工程音箱的声效震耳欲聋,巨大的黑盒子可以吸纳一切,在这里面存放了本次展览中最具体量感的影像作品——甚至不是“摄影”,而是沉浸式的多频道影像装置,其中《来袭》(Incoming)由爱尔兰艺术家理查德•莫斯(Richard Mosses)与作曲家及电影摄影技师共同创作完成。策展人蔡萌透露,“‘Incoming’是战术用语,表示敌人的炮火来了。比如敌军导弹、手雷飞过来了,队友就会喊这句话”。莫斯采用了军用红外监控摄像机,这种技术可测探30.3公里内的人体热量,《来袭》记录了欧洲难民的行径,难民、环境的动态和热量在一种反片银色颗粒质感的呈现下散发出不真实的美感。一方面,这种真实状况与不真实艺术化美感的冲突暗示出作者对政治和社会伦理的思考和诘问;另一方面,从技术的角度出发,摄影在这里的便向着“动词”靠近了。这个动词与摄影发明之初的动词定义完全不同,策展人蔡萌阐释,“在这个变动的过程中,如何将摄影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抽离出来,则成为这次变动的重要思考方向。”
美术馆二楼的两幅巨大的慈禧照片(慈禧,中国皇太后,1835-1908,摄影:裕勋龄,弗利尔美术馆和亚瑟•M•赛克勒美术馆档案)着实让观众震撼,慈禧在其生活年代享受到的摄影术,也正是摄影刚出现的半个世纪后最风靡的年代,她不耐西方素描的久坐要求,遂选用摄影拍照,精致的细节、威严的环境布局、宫廷摆设显现出权威感。除了两幅大型照片,内间还有一个可以坐下来把玩的工作台,桌上摊放着各种照片纸打印后裁切细节,例如慈禧的眼部、服装、鞋、桌案的苹果、座椅等等,可供观众拿在手上欣赏——这俨然是摄影工作室挑选照片的场景。
装置化地展出最后一组照片,采用一种对摄影行动的复古模拟,是本展的句号,它是展线末端的压轴,细细回想,也是一个省略号,观众能在此驻足、回味、思考,握在手上的照片纸提示观众: 数字化时代的拍摄模式、呈像结果与传统的纸质摄影相比,或许缺失的不仅仅是一种质感,一种与人的体温混合产生的胶片质感,更重要的是在心、脑、手的共同作用下发酵的观察方式和思考方式,这不应该成为技术时代便捷生活的牺牲品,尽管身处五光十色的“景观社会”之中,我们仍旧尚存有一点点理想,摄影便是一种可靠的策略——“摄影主要还是一种社会礼仪,一种抗拒焦虑的屏障和一种力量的工具”。
文/张译之
图/展览主办方、策展人蔡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