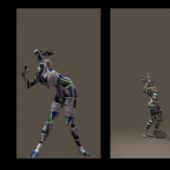2018年9月29日下午五点半,“游移——新媒体影像艺术展”将于33当代艺术中心启幕。本展览通过研究影像作品中影像的自我意识,从影像媒介的本体生发对于展示政治的讨论,“游移”(oscillation,含有“震荡”和“波动”之意)并不是一种折衷的态度,而是一种摇摆不定的价值,一种“震荡”和“波动”。它涉及影像语言的动机、观念表达的有效性,以及对影像作品深层意义的思考。
在新媒体艺术的语境下,当代影像艺术家常常以影像装置的跨媒介手段呈现其作品的整体。他们往往通过双屏或者多屏并置、再造景框,以及画中画的方式和技术手段构建影像的自我意识,其意义产生于影像的动态过程中,游移于再现的不同模式之间:梁半的作品往往利用手机ipad等便捷设备,以多屏并置,其意义游走于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场景之间;卢征远的双屏并置影像装置,在设置了观看空间及路径后,意义即在观看与互视、影像与镜像中产生;晶体星球是罗苇持续几年的跨学科项目,影像和装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种新的崇拜价值(光韵)即产生于流动的创作方式与多维的展陈形式之中;考虑到边框的功能与意义,叶甫纳将电子虚拟的绘画边框加诸影像作品中,在一种疏离美学的基础上,凸显了影像的自主性。辛云鹏的影像作品常常利用影像语言自身的漏洞和其他技术特性,结合双屏并置的展陈方式,突显了影像的自足性以及其与现实之间的错位;同样是多屏并置,叶凌瀚的作品讨论了电子虚拟图像对真实世界的覆盖,同时强调了信息和影像的流动性本质;出于对电子虚拟世界的敏感,01小组的作品将电子信息实体化,同时又将其再度转化为电子影像,这种双重转换正展现了虚拟再现的本质。上述艺术家的影像作品或者影像装置的意义都或多或少在展陈和崇拜之间摇摆不定,同时又通过影像的技术处理达到某种“自反性”和“自我显现”,使观者的观看“游移”于影像的自我意识与新的展示政治之间。
本次展览将于12月6日落下帷幕。
图、文/主办方提供
编/艺讯网
游移——影像艺术的自我意识与展陈逻辑
文/高远
影像艺术的最初出现,是为了挑战博物馆的收藏和展陈制度,使影像真正自由地呈现,而最近几十年间我们已经见证,影像艺术和数字艺术频繁展示于各类艺术机构和博物馆中,同时大量出现在各大机构的收藏名录当中。这就让我们对影像作品的展陈逻辑和再现手段产生了思考。图像和影像并不是文本,文本可以用于对图像的阐释,但图像或影像通过某种技术手段和展示手段可以被赋予特殊的自我意识,可以作为“时代集体想象的无可替代的见证者”。就如中世纪祭坛画中上帝揭开帷幕的自我显现一样,作为画面边缘的帷幔或者框架,提示了图像的自我意识。
符号学家路易•马兰(Louis Marin)也讨论过绘画和影像的自我意识。他将画框与书页文字旁边的空白作类比,页边空白或者画框是一个自由缓冲的区域,它没有可以阅读的内容,但却是阅读进行的条件,同时也是描述符号所需的载体。马兰通过这个事例强调了再现的双重逻辑:一方面,再现(Représentation)是严格意义上的术语,它呈现出模仿的特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象效应,亦即制造虚拟的现实并使人相信;另一方面,再现性设备(画框、视频播放器等)从其自身的功能中获得意义,通过对再现的支持并隐藏其自身,使对象成为可见;由于再现性设备自身的功能及形态,以及机构的权力,它又无法被忽视。通过边缘的作用,意义将在画框内重写。在这里,整个世界都是已知的,我们在一个空无的基础上欣赏(观想)一个艺术作品,画框构建了再现的自主性。马兰借助古典符号学理论中的符号两重性原则,即来源于法国17世纪《波尔•罗亚尔逻辑》(Port-Royal),又名《逻辑或思维的艺术》(作者:Antoine Arnauld、Pierre Nicole)中的古典符号及再现理论。无论是后世W.J.T.米歇尔所谓的自我指涉的“元图像”(meta-picture)还是斯托伊其塔论述的“元绘画”,都与法国古典符号学理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理论强调的是符号的两重属性,它与两类物有关,即作为再现者的物与被再现的物,符号在表现对象的同时也在表现它自身,其最终目的也在于呈现它自身。同一物可以既是物又是符号,它常常作为物去隐藏作为符号之所揭示;同时,符号本身也是一种物,当我们只考虑它作为物的存在时,它呈现出的是它自身的存在。福柯将这两重属性转述为:“其一是进行表象物的观念,另一个是被表象物的观念,符号的本性在于用第二个观念刺激第一个观念。”
雅克•德里达在《绘画的真理》中,就将“画框”提升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他在书中用很多篇幅讨论康德所谓“附饰”(parergon)的问题。在德里达看来,“附饰”所表达的内外之分,实质上就是绘画和影像作品的框架问题:何种事物涉及美的内在价值,而何种事物却被挡在了美的内在本质之外?画框作为分界线,不仅区别了作品内外两个世界,它还牢牢地支撑着中心,使内部成为内部,本体得以成为本体。从德里达的观点出发,正是这个“附饰”在支撑着中心,没有了“附饰”,作品也将无从成立。如此看来,画框——附饰就不再是分界线,相反是它将作品融入了更大的背景之中,是它决定了作品,同时构建了作品的可见性和自我意识。在使作品可见的同时,德里达又进一步论述,艺术作品的物质支持元素——画框、视频屏幕或电影胶片,均存在一种相对的不可见性。正是这种相对的不可见性,构建了影像的自主性。德里达在一篇论文中专门讨论了加里•希尔的7个监视器的视频装置作品《故障》(Disturbance),他认为,将视频媒体与其自身材料属性相关联的做法并不可取,视频即是“新型艺术形式具有特殊性,而且是绝对独立的,不应当被其他事物所束缚。”
古典符号学的两重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方现代“再现”理论的基础,近代以来,再现逐渐被民族志与政治话语所左右。同样,本雅明意义上的“光韵”的消逝也与一种近代以来展示的政治息息相关。祭坛画(影像)的展陈与崇拜也是一个互化的过程,本雅明就将艺术的全部历史归纳为一种崇拜价值向展陈价值转变的过程,艺术从以仪式为基础转向以政治为基础;在当代展陈条件下,一种新的崇拜价值已经显现,艺术作品的展示通过玻璃幕墙、围栏以及大规模的安保措施造成的距离感与不可见性,使古老的崇拜价值再度回归,作品往往在展陈的同时被崇拜。从本雅明式的犹太教卡巴拉教义的“流散”和“聚合”之间的“游移”,过渡到艺术作品的崇拜价值和展陈价值之间的“游移”,当代观看的价值真正存在于影像的自我意识与展示的政治之间。
从形式上看,电视本身就是一个“镶嵌空间”,像画幅一样“镶嵌”于广大的现实之中,构成了再现的“二级话语”;在媒介转换的同时,也将“现实”隔绝于视频之外。1969年德国人盖瑞•苏姆成立的“视频画廊”(Fersehgalerie Gerry Schum)由8位大地艺术和观念艺术家的作品影像构成,其关键在于思考了影像艺术展陈的转换问题。苏姆创造性地将电视视为艺术体验的直接媒介,而不仅仅是通过电视的载体来记录和展示艺术。观念艺术家的作品由电视的新媒介构成了再创造,以电视播放取代博物馆美术馆的展陈,并赋予其转瞬即逝的特性。电视机自身可以视为图像的载体,又可以是艺术品本身。苏姆的视频画廊标示着视频艺术会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而出现,从此,艺术家控制媒介的方式和过程都会产生变化。
在新媒体艺术的语境下,当代影像艺术家常常以影像装置的跨媒介手段呈现其作品的整体。他们往往通过双屏或者多屏并置、再造景框,以及画中画的方式和技术手段构建影像的自我意识,其意义产生于影像的动态过程中,游移于再现的不同模式之间:梁半的作品往往利用手机ipad等便捷设备,以多屏并置,其意义游走于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场景之间;卢征远的双屏并置影像装置,在设置了观看空间及路径后,意义即在观看与互视、影像与镜像中产生;晶体星球是罗苇持续几年的跨学科项目,影像和装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种新的崇拜价值(光韵)即产生于流动的创作方式与多维的展陈形式之中;考虑到边框的功能与意义,叶甫纳将电子虚拟的绘画边框加诸影像作品中,在一种疏离美学的基础上,凸显了影像的自主性。辛云鹏的影像作品常常利用影像语言自身的漏洞和其他技术特性,结合双屏并置的展陈方式,突显了影像的自足性以及其与现实之间的错位;同样是多屏并置,叶凌瀚的作品讨论了电子虚拟图像对真实世界的覆盖,同时强调了信息和影像的流动性本质;出于对电子虚拟世界的敏感,01小组的作品将电子信息实体化,同时又将其再度转化为电子影像,这种双重转换正展现了虚拟再现的本质。上述艺术家的影像作品或者影像装置的意义都或多或少在展陈和崇拜之间摇摆不定,同时又通过影像的技术处理达到某种“自反性”和“自我显现”,使观者的观看“游移”于影像的自我意识与新的展示政治之间。
本展览通过研究影像作品中影像的自我意识,从影像媒介的本体生发对于展示政治的讨论,“游移”(oscillation,含有“震荡”和“波动”之意)并不是一种折衷的态度,而是一种摇摆不定的价值,一种“震荡”和“波动”。它涉及影像语言的动机、观念表达的有效性,以及对影像作品深层意义的思考。
展览信息
艺 术 家:梁半 卢征远 罗苇 辛云鹏 叶甫纳 叶凌瀚 01小组
策 展 人:高远
出 品 人:刘奕
研 讨 会:2018.09.29(周六)14:00-17:00
嘉 宾:王端廷 盛葳 尹丹 鲁宁 沙鑫 石冠哲 沈森
开 幕 式:2018.09.29(周六)17:30
展 期:2018.09.29-12.06
时 间:周一至周六 10:00-18:00
地 点:33当代艺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