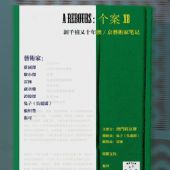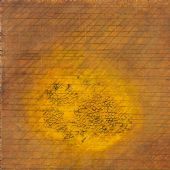2017年12月30日下午四点,由澳门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的“新千禧又十年澳/京艺术家笔记”将在北京王府井澳门中心16楼澳门驻京办多功能厅开幕,展览由兔子和雷徕策划。艺术家蔡国杰、黎小杰、雷徕、卢章灿、谭俊杰、兔子(吴丽嫦)、张恒丰、张可8人参展。展览将持续到2018年1月14日。
蔡国杰
蔡国杰初来自台湾,泰西学艺,从西洋装置艺术之正史,深研极限、实在、剧场化、情境参与、空间艺术之时间化等诸命题,深得学院派后现代之正血。
奈何以解构解解构者,焉能有所得?不得。终日逡巡。
遇女其姝,感其塞渊,从妻氏于归澳门。
一夜觉晓,猛醒,感追慕古风之血脉贲张,遂易辙师古。
然身为当世之人,寓形今学益久,血肉、笔法皆与古人殊异,星汉难到,奈之何?徒有一身古风骨,遂以六经注我之势,取今人之旧方水彩者以为半古,以今拟古,别开生意,曲径而通先贤之致。
绘事澳门地标性建筑景观若干。人皆惑之,以为或游人猎奇者为之,或趋炎媚俗者为之,国杰文人者也,奈何作贼?抑或参之二者,乃有第三种与此二者皆有关且更深刻之可能:兴托风景名物以寄其远,想象一座城市之文化历史,觅其心安处而得之;由是之故,其所绘事者,往往意不在其间。此墙果为此墙邪?此庙果为此庙邪?非也,乃不特定之庙或亭或任何有中式屋檐之建筑也;有甚者,如其本人所言,无非若干“象形字”或各种书法线条堆砌之体积物由以发生之 借口而已。然以此类名物作题亦非全无意义者,主观之笔法造型,主观之文化历史景观,迅猛、不落地者,仿佛若“在风中飘”,私意妄度,乃因国杰“拣尽寒枝” 未得“栖”之故。
或有大人先生者言,“国杰画作之所谓‘书法’笔法,并非传统意义上之书法笔法”。然。较之中国书法之有典有则,国杰所为 “书法笔法”之理念,与西方或井上有一之日本书法更似。虽则与先贤之绪相违,然无妨于我辈由国杰六经注我之自成方圆中,体味其文化信仰之铮铮然。
未尝于弱子时便浸润涵泳于传统文化而自然言中国文化审美,乃先行标定“中国文化”之旗杆,然后不从文史撰述,而“从我们的文物里面找到、萃取,我们的根”,探赜索隐。泰西效学多年,蓦然回首,身周之风景人事皆非昨,幡然醒悟,急急标定所执所立。其所立场者或名实未附,然而其所立场者确乎塑造其人也,利导其所施行之事者也。
曩者相交而游,国杰尝慨叹“崖山以后”…更如今,文化精英与社会精英渐行逾违,分明要被更边缘化的。今贤萨义德定义知识分子者曰:
知识分子乃公知者也,代表一种公开姿态,无有私人之知识分子
或为秩序话语之喉舌,或为穷苦者鸣不平,不擅中庸
破除人群思考问题时成见与简单化之习惯
信奉自由之精神
自觉之局外、边缘者或体制之安生者
现代虚无主义者
心灵之自我流放者
……
国杰何如,略可参之。
国杰又以为,艺术圈时兴之“当代”意识乃西方舶来之物,拿来主义很轻便,而经西方辩证思维力洗礼后,赓续华夏古贤,再辟传统思维体系之现代可能,方是任重而道远。闻此,忽思及阿甘本标定“真当代人”之重要特征,其一便为与当下时潮相去若干步之遥,转言信而好古。国杰真当代。
弃捐不道,慨而慷之:文章小技,无以济世;丹青稗类,尤不如也。去高山景行者远矣。然心所向处,一念执之,乘槎可期,幸甚幸甚。国杰,真是一个幸福的人。
黎小杰
在变得抽象以前小杰很擅于画具象画。如果我们教条、单纯地沿着从描绘对象性的感受到主观意识的抽象,这样的线索去看黎小杰的创作演化过程,我们并不能看出什么独特的见解来,无非是美院油画系科班出身,基本功太好,画腻了,所以改抽象了。其实好多人私下里的最直接动机可能是这样的,但这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小杰的演变和这种时尚没什么关系。
小杰一二年的个展名叫《半空之间》,就是从高楼垂直俯视的视角看到矮楼的天台,这个暧昧的空间域,既上不了天空的崇高和自由,也不接了地的踏实安全感。
如同大幅摇头相机的构图,方方正正、平直呆板,浅空间,大部分面积的画平面都被工整的地砖或带有肌理的地面占据,里面描绘的物体都是最不反映个性但偏有带有很强生活气息的物件,排成一排或抱团几个的花盆,几株无名植物,孤立的椅子,任何局部刻画都非常节制,难以张扬——但它们之间的变化差异实则是被分外认真对待的:颜色或形体、笔触,都在微弱地丰富着、讲究着,都仿佛有一股竭力往外张的冲动,就是没能张得很开——它们在微弱地挣扎着争取自身的个性。
这种气息像极了澳门,但也许是照望京花家地画的也亦未可知;那阵子小杰正澳门、北京两地跑。可是“不会有另一座城市”,因为每座城市都是相似的,“你会发现没有新的城市”,我们的后现代只有一座同样的城市,“这城市将尾随着你”,“你将到达的永远是同一座城市”年少时生长在澳门更强化了这座“城市”,“将一仍其旧”,“你将老去”——好吧,也许这也是在京有合作画廊的小杰后来很少回京了的内心原因之一。认了命了。
从此而后变得不具象了。更苦涩了。
小杰画了很多载体是薄片、小正方形、重复序列纹样的小画片,以此为组件在具体展陈空间中拼组出大面积密集重复的空间作品。他将之戏称为“地砖”。
尴尬的是看着真的像一块一块地砖。
如果看一块单一组件,除了因为手熟,率性而不能不工外,几乎找不出一个夸的词儿。通过反复机械劳动达致的麻木或疲惫,排除任何有意图性的刻画,“一旦动了念,就停下来”。没有可引起肖似性内容想象的色彩或形式。画表面媒材本身的微妙细致、丰富或戏剧张力也被剔了个干净。不是说费劲地画得一模一样,而是看着没有值得注意的区别。简直就是刻意的刻板同质化。
是的,没有留出任何解释的可能性。
为什么要长这样呢?也许是太会画,些微有点画腻了,也许有那么一点是因为日常生活、工作剥夺了细致深入经营的时间精力,但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不能让观者为局部的有意义而凝视灵晕,影响了直接直面作品整体——站在它面前。
只有经过布展时和在场空间的相互作用、经过编排之后,作品的意义才呈现出来。无个性的螺丝钉只是为了服从整体。就像当下社会;就像澳门或每一座城市。
小杰说他追求的意义,首先是作品的大体量赋予的“纪念碑性”——对任一展示空间的改造,空间可以是空洞的、狭隘的、受制于原有功能性的,小公寓、美术馆、大礼堂,通通都被改造,赋予了签名黎小杰style的“纪念碑性”——“纪念碑性”,这一与当下精神,尤其与澳门社会的文化氛围全然脱节的精神诉求。背道而驰、面向落伍了。
而他的宏大,用的竟是他的“砖”,最小、和“纪念碑性”最绝缘的组件。
为什么呢?
“因为在北京学习、生活、创作那些年,留下的余念,想要画大画;可是身在澳门的条件使然,结果就想出了这招。”小杰自觉接受了客观条件的局限性,由之决定了作品的形式,结果却造成了艺术生发环境本身在作品中的在场。他的绘画行为和他的作品一起,从两个不同层面,传达了高度一致的意义。
小时代。纪念碑性的余念。矛盾。挣扎。从命。通过妥协的迂回超越。面对社会诸界人仕,掩藏各种身份,优雅、精致笑容背后的……还是从容,没有无奈了。是的,没有。
卢章燦
托多罗夫说,荷兰小画派的德.霍赫发明了将室外场景当作室内处理的方式,他喜欢庭院——一个“中介性空间”,这里是房子(私人空间)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过渡。本雅明说,自从室内被改造成了百货陈列处,室外临街的拱廊成了巴黎浪荡儿的室内;浪荡儿——有闲阶层与自觉的社会边缘人;闲暇者从街角窗户看人群如看风景,居高临下样子,但其实是跟不上大流。
之所以聊起这个是因为阿燦在不止一件作品中使用了透过窗户看风景的视角,即使端走了窗框,或者窗户变成了一道管窥之缝,风景仍然保有明显的窗外风景的痕迹。窗外的风物总是一阙一阙平行的透视,没有戏剧性强烈的成角透视,这在我们同时代的青年艺术家中好像非常普遍:我们是心灵状态好像又回到了文艺复兴早期或者 更早的中世纪。无论是楼房、栏杆还是树,都采取在等分、相似的秩序排列的基础之下再出现个体的差异变化,就好像当代社会中的我们。
在更晚近的作品里,阿燦脱离了繁芜的物象,而求其意。
通过我主观的观看,在阿燦的新作《伸》系列第一张里,呈现着这样的场景:近处是役形所暂安处,中以一排似树又似栏杆又似纯抽象线条的东西既分隔又通透,远处一侧恍惚无分别、一切尽情融于光中,另一侧林泽深远仿佛若有桃源处。
而在这个《伸》的系列中,任何一张画的每一条边都可以与另一张的任意一边,在图形上完美地接合,组出一件新的作品:两张画,有着四种组合方式,三张,就有二十四种……听上去已然非常恐怖,在技术上,则随组件数不断增加而成为不可能的任务。OULIPO的雷蒙.格诺曾经有一本作品叫作《百万亿首诗》 ,由十首十四行诗组成,每一首的任一行都能与其它九首对应的诗行互换,结果有10的14次方首不同的诗;同样,博尔赫斯总要提起的无尽之书—— 这既是书呆子阿宅独自在书斋子里才有的狂热;也是后现代——去中心化,非等级的秩序感:我们认识型进入了区别于“逻各斯”的“文”的交织结构,从任何一点都可以接上其他一点——陷入迷宫,从一种被动的状态成了一种主动选择的嗜好。是的,阿燦说,他对这种无限组合的可能性深深地着魔,并且跃跃然希望把观者也带到这种趣味中去。
现实生活中阿燦不擅和人容与交接,分明典型让.雅克.卢梭所谓“自然人”形象的典型:外貌孤僻、内里实际温柔。且请每一个内里深处相似的人,也走出门来,看看今天的阳光,也来展览上看一看,我们人性共通的同类。
谭俊杰
太白暮年尚发少年狂气,鲁直七岁吟来已是横秋。在中国的传统,首先是大历史/环 境的文化风尚塑造个人的风格乃至价值取向,而不是个人的经历、成长引发引发风格的变化。谭的来路很清晰,画风长时间以来也很传统。谭的画直接地看看不大出他的年龄。谭的困扰在于这与当下的社会现实隔绝,也不反映当下人的气质心性。以此,谭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的东西。
有朋友说,国画的人普遍有这个困扰。谭周围的同学师兄弟们也颇多蠢蠢思变者:有真变了的,却不知在国画以外更大的艺术圈语境中这是不是真的称得上有新意的;有终于还是脱不开这个太过成熟完善的系统,因为法式旧山水以外的当代生活已然脱节太远,由心变而来对范式的修正---接不上所以更脱不开了。
“你爱的是旧图像还是旧风骨?”“我既不要由旧图像来经营新时代精神状态的时空感位置,也不要由新物像编排旧情志的位置经营。” “那何来思变的需求?”做自己做久了尚且腻味,何况是由完善体系教化出来而非自然生长的自己?人受到外部环境的动容和经久重复的一时腻烦才生出怀疑,也许很快就会恢复平静稳定。
谭说自己的创作不多,多是写生。既然都是旧法式,写生岂不只添生意而不损所谓“作品感”?
也许谭所说没有创作,是指总在个别“写生”中投射自己局部的小心意,而无法在一件山水作品中完整地体现自己的三观?
山水往往是作者世界图像的反映。士人心中的天地气象,朝堂上、江湖中,对个人隐逸、逃脱自由后的独立人格的多寡取舍之类,都反应在可居可观可游,平远深远高远,一角半边,似繁实简、似简实繁等等这些上。用西方风景作比较,西方对风景的爱好据说发生的很晚,地理位置上离人最远的野外在心理上却是人的内面,看来在中国,无奈、孤独的个体意识兴起得特别早,历史很长,长到“个人”已不是“个人”了。
其实谭自觉自己作品的脱离现实,其意识本身就反映了一个现实:有价值的传统与当下的现实关怀间取舍的两难,本就是生在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人该自觉直面的问题。拿它当一个问题而自扰的人不多。
我们把目光集中在谭最近的作品上。与之前的选择相比,谭放弃了所有的可居、可游处,只余深远、高远,人所不能及处,直接充满整个画面。墨色变重,从有笔有墨,到笔完全服从于墨,线条塑造法服从于明暗大效果的营造,有节制的阅读式观看被沉浸式的氛围感受取代了。与近古士大夫文人山水明志表达人生观的趣味相比,也许更接近西方风景画的心境,或者更早远的中古,山水甫被“发现”时,山水=游仙的心境。直呼作《彼岸》,从神秘高山半腰的视野直截出前景,一棵墨色与黑山并不很分明的树横斜、略略探出头,指向远处、西画一样用墨色塑造的、形象暖昧的林泽,再远处是明亮得耀眼的水与丘山。《泉》,四围环抱出一方明亮的水泽(=此心安处)直接占据整个视觉核心,其 与外面联系仅限于通透性模糊的一处洞穴……——这既已不是传统山水的图像,传达的心态也不入传统之流。与所谓“写生”相比,谭在这里是否更多地触碰到了自己活在当下的真实?也许是,但也许那些原以为不是的,其实也是他的另一部分当下真实。
谭终究会于何处安身,未可知。但要紧的是作不断更新的历史环境下寻找传统之继承性地革新可能性的自觉者。
张恒丰
去访问阿丰的时候,他的室友突然冒出一句:“阿丰的画属于冷抽象吗?”这真是一个尴尬的好问题。
“冷抽象”,理智地编排画面各构成因素,通过对设计的实施传递出某种见仁见智的情感(或者非情感);“热抽象”,凭着激情往画布上主观宣泄着堆颜料,产生画面 张力,投射强烈情绪。前者源出于蒙德里安,后者发韧自康定斯基。蒙德里安在画得很抽象以前擅长画很阴郁的树,人人都能通过那棵树感受到自身通感的阴郁;康定斯基原本爱画街景,人人都看出来他画得很激情。这是个很不幽默的笑话,但好像反映了某些局部真理。两位大师的同时代是上个世纪初,那个时代的文学正在提倡“艺术的去人性化”的思潮——参照之下,我们是 不是可以得出一个想法,其实“冷”也是一种激情?可怜我们中的大多数,缺乏对克己复礼式的创作道德教条主义的法利塞式的爱,也没有糙汉子的血气过盛、消耗不尽,所以在批评家那里基本都成了“第三类”,或者“其他”抽象——“综合的”、“中庸的”人——中国人。
如今看到的阿丰颇精彩的作品是长这样的:
颜色限定在颜料管里挤出来的三原色和黑色之间的叠加、覆盖关系。中间一排在整齐排列的基础上再生变化的纵向圆角矩形作为画面的主体物,空间由横向的黑色区域和它们的遮、漏、透等关系隐约交代为前、中、背景三景别:和观众牵连的空间、主体物自身运动的空间、作品内象征的“世界”的空间。角色就那么多,基本语法 就那么简单,就像古典的“三一”戏剧,一则是集中线索来增强张力,二看减去了芜蔓、提取纯粹后的系统里,能发生多少变化——就像思维所谓抽象,几个概念就要概括出你的在世诸端、但并不意味着把问题简单化。几根很克制地流淌下来的线很小心地添加了画面的随意松动性,剩下的全在限定规矩以内。题目很浅白无奇,偏偏抓住了某些重点,《红色的感觉》 ,《蓝黄的衬垫》,结合画面,似乎颇可作深究画面结构意义的线索。
作为抽象画,这组作品虽然气息很强烈,但因为留给观者的自由感受、想象空间很大,如果要“以意逆志”,通过画来“知”阿丰的人,也许可以结合其更早前作品,之所以演化出如今作品的由来。
若干年前,阿丰喜欢画素描,喜欢画单个静物,譬如画一颗玉米。不带过多主观经营,不刻意造作,不轻易地让情绪带动过多的变形。“素描/手艺能让一个人变得精致。”素描的手感让他很舒服,在一种很舒服、很“空”的状态下,其意识深刻最体己的形式感、最真挚的“物”的状态,在画面中自行地涌现出来。最终成品的形式感很强,但却是“移情”而非“抽象(设计)”的结果,这样的形式感是他多年学习以来,自然提炼出的与其人格真实对应的形式感。事成之后,阿丰在画面上附 加了一层设计:他把素描翻制铜版画的技法安排(阿丰是版画专业的)的文字标注直接写在画上成了作品的一部分,松香、沥青、留白……当然还有能让更多人认同 作品是“作品”的勉强多出来的几个梵文字,“大明咒”。这系列作品呼作《万物》,显然,他终于没有将之翻制成版画,所以也不能看成将手稿标注当作作品的 “元(后设)版画”,不是观念作品。
阿丰说自己的素描画得很舒服,画得舒服的素描看的人也看得舒服,为什么呢?让-吕克-南希说:素描在法文、意文里其实就是设计——一切经营有条,没有纵容溢出的东西,这期间的“美”、舒服,是克制、精致的快感;虽以刻画的对象为标定目的,但目的并非 “目的”,而是服务于效力、形式实现的过程,使……实现的快感;ideal的本义其实是完美的形式,和“灿烂星空、道德律令”、绝对者一气的快感;素描模 仿对象,时而依附于物、时而让物服从作者纸上的秩序,最终彻底征服、持有了这物的象——不是像买东西那样虚假的占有、而是更充分的占有,至少在心理上。等等。
再后来,阿丰用素描画了一排瓶子。
摆放得很整齐;前面有一阙空间,后面也有一阙空间,近乎留白,却显然是经营过的,像莫兰迪……莫兰迪是西方静物画的传统,“still life”,与稳定持久的、仿佛永恒的东西有关,通过经营这些又似又不同的东西的关系,它们和空间的关系,昭示了秩序的多样统一、亘古长恒。阿丰的瓶子间画得更少变化,更谨小,更认真而刻板,也许画面中最显眼的它们,其实是在默默顺从于身前与身后两片乍看不显眼的空间。……
其实以上这些都是我看着阿丰作品时的主观臆测,现实中的丰很讷于言,对于自己很克制,而对于别的事物、尤其对于成文的书本话语,每一件都一本正经地按照那桩事物本身的理路来对待,而非实用的“拿来主义”,譬如他写毕业论文时对一些历史所采取的态度,简直认真出了呆气——
通常以为,笃实的人都是简单纯粹的。但因为有太多东西,他都自觉地在身上留下了痕迹,以至于他作品/其人的来龙去脉,就愈发复杂起来。相关联的每桩人或事的 变化发展都有其自己的理路,而这许许多多的相互错综在一起所成全的,看似平淡、实则越平淡越复杂,“有欲观其檄,无欲观其妙”。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 “冷”与“热”,“抽象”与“具象”……这诸种二元对分的概念方法,不仅并不充分概况现实,勿如说,就其出身中就潜藏了被扬弃超越的诉求。我知道,其实我根本没有看清楚阿丰。在今天,“观看”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当然在任何时代也都是。
张可
这里呈现的有两组作品:一组是很现代,现成图像做的拼贴,涉及的是very现代式的色情;另一组是仿铜版画旧工艺做的手工书,说的是古今皆准的爱情故事。它们的共同点是都使我们很尴尬:妙不可言的春宫画,取名《纯真百科百书》,更妙了,可是公开展示实在有违我们社会的审慎道德;葡国文化国父在澳门的东方奇遇爱情故事的绘本,与我们的情感体验隔了N多层的后殖民寓言。
为什么艺术家张可要从那么冷僻、奇特的地方索隐来做这样两组作品——敢于如此不讨巧,这种执拗的动机也许是颇有隐衷深意的?
“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很色情,相反,我觉得这很美好。看,你不觉得屁股的线条很优雅么?”在说这话的时候她的面色十分正经,丝毫看不出一丝狡黠、反讽的味道。
张可用了19世纪的色情照片,这些图像在它们的年代是不宜公开展示的,其色情的快感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因此而得到了增强。尤其像其中的打屁股,是一种道德规训对错误的惩戒纠正,因其是规训而使其露屁股好像是正当的:权力的快感更强化了色情的快感。以艺术的名义它们被挪用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作为“只是其作品的一部分组成因 素”地被公然展示,再辅之以非常庄严的天使图像,教堂三联图的框子,圣龛的框子,古版精装书(往往是严肃乃至神圣题材)才用的茛苕叶纹样和仿烫金工艺,其亵渎意味更重了,但名目上我们却可以说、譬如说:在这里呈现的是道德律更盛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明与暗两个面目,表面上的极度道德正确,底下的被压抑而极度 弹的欲望,这种君子绅士(清教)精神因不合乎人之常性而产生的自相矛盾仍能代表今日社会的许多层面。这里让我们不由想到了巴尔蒂斯的小裸女:同样是Innocence——纯真的、于欲望挑逗无意识的,没有对性与罪性的关联的自觉,“无辜”地被呈现,且在呈现者/作 者眼里这是自然的、非关道德的,是某种朦胧悸动的情愫。看着觉得色情,说明观者的心态是个……嗯,得两说。张可更挑衅,直接就是号称纯真的各式色情。今时今日,艺术作为民主精神的最前线,以艺术之名做任何事都是相对较安全、较正当的,而打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线,无疑也是代表激进自由主义精神追求的公私一贯性。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猜测:艺术家要表达的,是不是恰恰就是,以艺术之名、以现代民主之名,一些东西的过界的权力有些过当了?
好像怎么都说得通。是啊,艺术家只是一个呈现者,多元的解读都是合适的。是谓当代艺术。
与疯狂的放肆相得益彰的是疯狂的无话题性——至少乍看之下真的一丝的话题性都没有:过气的爱情故事,理所当然的后殖民国族认同的寓言故事:《南海姑娘》,葡国现代文化国父贾梅士先生和东方少女的爱情故事,以悲剧收尾了;而在张可的版本里,这个少女却同时也是更伟大的女神的化身——想必是因为她来自伟大的母国。
以突出故事核心内容为主旨的前现代透视(反透视),茛苕叶纹样,烫金,仿铜版印刷效果,完整意义上的手工书。最传统的象征图像:蛇、骷髅头、利维坦、贝壳、代表文化世界的书、帛片、苹果、十字架、旧史事地舆图风格的小渔村、疑似塔罗牌的镜子……
然而有几样东西暴露了作者身为当代艺术家而非旧叙事绘本作者的形象:完全没有使用连续式或补充式叙事法的分离画面,古人不敢用的松散分割方式,每一个独立拿出来、其象征意义也完全充分的画面——对于一个平面架上艺术家而非绘本艺术家而言,绘画的本质就是一个四角框里代表一个完整的世界。
如果观者够细心,还会从中看到许多很奇妙的细节,例如,贾梅士天马行空写就的书卷和南海姑娘的渔网是非常近似的样式,这自然是有寓意的;从《纯真百科全书》中乱入过来的裸女构成的互文本性和对我们沉浸阅读浪漫爱情故事的破坏……这些都需要细细地去品“读”而不是大而化之地“看”,将之归结为一个简单模式化的寓言。
写到这里我们忽然冒出一个想法:会不会张可在这个表面的寓言底下还藏了另一个寓言——男人用爱情成全了他的浪漫情怀、升华了自己的伟大情操,然后就把女人用完了;可是他们不知道,女人实际上明白得很,也更隐忍伟大(是女神的化身嘛),她们装作天真少女,是为了成全她所爱的男人……还是那句话,艺术家只是个呈现者,观者怎么看都说得通——啊!
果然是个聪明人。谁也看不出她是媚俗、讽刺、不露声色的愤怒、挑衅、做一个游戏规则里可以允许的越界、做藏头诗让你来索隐为乐、还是在一系列的精致面孔底下并不遮掩却让你看不透的绝望。
兔子
无奇又最奇特的兔子,我们看她的作品,再看到与创作方式有着内在连贯性的人。一个奇特的人格体。
与许多为了特定内容的表达而选取最适合的形式语言的人不同,在许多时候,兔子放任材料决定技法,技法决定画面形式,画面形式决定画面内容,内容决定思想/情感内涵,但最惊奇的是,这个放最后一位的内涵竟全然合乎她自身的内涵。
铜版画的形式偏向肯定了她以黑白灰关系为主要语法:光、暗、对象在空间之中的孤独、对象间的各种关联方式。
“情绪很纠结,就画一个理不清的线团。”,从此线团就成了最常见的标记,以各种方式、各种态势出现在各种不同场景中——重调一遍,并非画面整体氛围就最适合一个线团为对象,而是线团的各个符号成了代表自我的一个标记。
一方面线本身是抽象画最合用的语言,另一方面在铜版上划线是一件施行上较舒服的事,而舒服往往意味着更少障碍、更多通透,或许也可以说,对作者而言,语言更具“透明性”(也仅对作者而言)。线可以作对象与对象间的联系,或强或弱,统一的一排自成一个层面的线可以和其他层面对象的脱节……
在画面正中间犯一般绘画语言忌的等分上下(左右)两阙,两个分离的不同世界,或者里面承载着各自的、却是内容样貌上有相似的对象,两个世界、相似的人情人性;或者物体穿透两界,发生了形体相通、黑白颠倒的变化;或者这是天地间的分界线,物就压在其上,发生着微妙、幽离的变化,就好像在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夹缝中的人。
……
孤独黑暗的中心一个泛白轮廓光的小黑圆——《Hello!我在这里》
交织的白线球延伸到黑暗空间中的黑线慢慢看不清了,就是《看不清的事实》
画面上开了很多变化多样的黑方,颜色深得看不清,被变化复杂却又秩序井然的线似连非连——《别人的世界》(个人看着像极飘向幽光深处的诸多孔明灯)
……
是的,她给日常发生每一件事或物或情感都标记一个符号,又用画面的抽象关系仿效这诸般种种在真实生活中的关系——当然,该说是她想象的关系——以此为线索,串起了一个可以不断重复、变化组合、又随时会有新的符码进入的系统,就像一本无限展开、可以没有尽头的大书,而这本书的作者之所以可以畅通无碍地写作,是 因为她完全排除其他任何异质的思想、符号介入的可能,是的,是因为她不读书——不是说绝对不读书,而是至少不被任何阅读经验/外部意见造成自身内平滑面的断裂。
我们知道,一般地,具象画意味着依仗具体物的移情思维,抽象画意味着抽象的解码重新构建,然而在兔子这样一种图像生成方式的面前,我们似乎常分不清这究竟算是移情想像还是编码重构。兔子的原话是:“虽然我的作品是抽象画,但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倾向于抽象思维的人。其实我常常觉得我的抽象画长得很具象。”
为什么会有分不清的情况呢?我想起福柯所说的前现代的或现代早期的“相似性的认识型”。
“平铺直叙,没有他者与己区别。”
一个素朴的人看人人都是和自己一样,有着共通的喜恶,他人也是自己的仿本、我也只是“我们“中的一个。只有在遭遇强烈差异性给予的挫折,造成的情绪反扑过程中,“自我”会形成。此时的自我其实已然沦为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些内容、具体知行方式的总和。我们常常会看见许多艺术家的“自我”分明很强大,但创作其实无定式,他很有劲儿、很牛,在抗争不可避免的社会同化力中出来很精彩的东西,而实则,在反对某话语时已被该话语将问题意识同化,仅仅是成为其系统内部的对立者,而不在真的有自己源初的东西。兔子时常选择不去理解与她差异者,反而成全了他的真实一致。她的身体能量没有陷入“解释”的圈套,所以做出了成功的、一致的解释。
她铺开了她的世界,从来没有另一个世界。
她将目之所及统统ab-stract,抽离其被目睹是的发生语境(情境),由此注释了“抽象画”之“抽象”的一种可能:肖似性世界的开展,与抽象最远的一端。
不在发见事物间差异性的表象,而在于建立事物内部的“亲缘性、吸引或者秘密地共享的本性”。外部世界服从某种相似性的原则而平铺直叙着,相应的,在一系列作品中一个画面秩序的世界被建构为形态同构的“小宇宙”,不,或者更直接地,不是被建构、而是直接投射上去。
与之相比,我们这些“当下之人”,这些“成年男性”,究竟有多少治愈不能的现代病?我们刻意地追求事物的差异,在差异中界定出所谓事物“本质”,为了个性而制造个性、为了独立而制造孤立,阶级、族群,所谓同文理念分明也只是用来自我标秉,“高贵者”就刻求差异,“低俗者”就仇恨地把所有事物拉平;而对这位前 现代者,并没有抛弃了以相邻适合(配)、仿效、类推(连类)、交感的建立相似性、建立联系的观看方式。可喜可贺,有一只兔子不在我们这边。兔子是个古人。实在界与她无关,她处在知象征界而守想象界的位置。差异之痛根本不存在,人与人相对着,自己说着自己的话,相互理解上通了就是通了,不通也不强求,而理解达成的主要途径仅仅倚仗“通感”——无需解释。
无需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