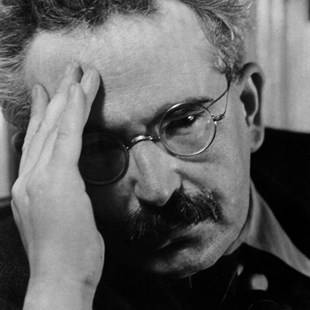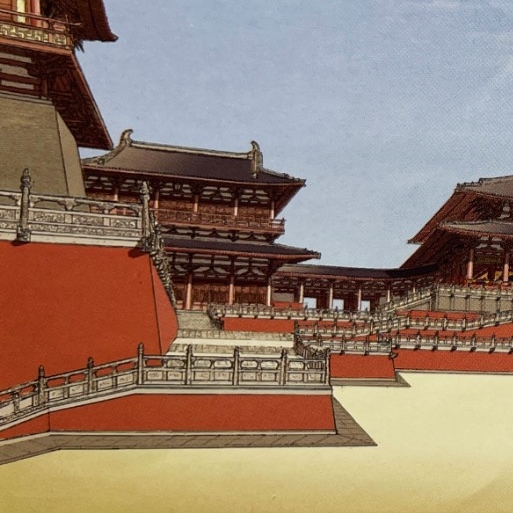译者按:丹托(1924-2013)是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哲学家,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美国哲学学会主席、美国美学学会主席、美国《哲学杂志》编辑,1984年起成为《国家》杂志艺术批评撰稿人至2009年。他在1964年撰写的《艺术世界》一文是当代艺术批评的一篇重要文献,首次提出了“艺术世界”作为机制的命题,影响深远;后来他又提出艺术史的终结论更是引起广泛争论。这是国外多部美学、艺术哲学文选的必选文章,从这里丹托开启了他的艺术哲学之路。
哈姆莱特:你没看到那里有什么东西么?
王后:什么也没看见;我看见的就是这些。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三幕,第四场)
尽管哈姆莱特和苏格拉底分别持有赞美和贬低的态度,但他们还是把艺术比作观看自然的镜子。这种艺术具有事实的基础,虽然在态度上可以大相径庭。苏格拉底把镜子仅仅看作是反映了我们已经看到的东西;所以,艺术好像一面镜子,它产生的是事物表象的无用的准确复制品,因此没有任何的认识价值。哈姆莱特非常敏锐地看到了镜子反射面的突出特征,即它们向我们显示了我们无法用别的方法感觉到的东西——我们自己的脸和形象——所以,艺术就像镜子一样,向我们自己显示了我们。因此,即使按照苏格拉底的标准,它毕竟具有一些认识上的用处。但是,作为一名哲学家,我发现苏格拉底的讨论在其他的理由方面存有缺陷(也许不如这些理由深刻)。如果o的镜像确实是o的模仿,那么,如果艺术是模仿的话,镜像就是艺术。但是,事实上一,用镜子反映事物不是艺术,这和把武器交还给疯子不是正义一样指向反映物仅仅是一种狡黯的反证,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会在反驳中提出一种理论,利用它们进行说明的。如果该理论要求我们把这些归类为艺术,那么,它表明了它的不充分“是模仿”并不能作为“是艺术”的充分条件。然而,也许因为在苏格拉底时代和以后的时代的艺术家都致力于模仿,理论的不充分直到摄影发明以后才被注意到。作为充分条件的模仿一旦被抛弃,甚至作为必要条件的模仿也很快被放弃了;正因为康定斯基的成就,模仿的特征被降到批评话语的边缘地位,结果是一些作品尽管具有这些优点和特质,也仅仅是勉强被保留而已。这些优点和特质过去曾被赞美为艺术的本质,现在却只是幸运地逃脱了被降格为仅仅是插图的命运。
当然,苏格拉底的讨论绝对需要所有参与者都是进行概念分析的大师,因为目标是把一个真实的定义表达式与一个实际使用的术语匹配起来,关于充分性的试验假定,包括了证明前者分析了全部且只有那些后者适合的事物,并应用到这些事物上。虽然遭到普遍的否认,但是传说中,苏格拉底的听众都知道什么是艺术,也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因此,一种艺术理论(在这里被看作是“艺术”的真正定义)并不会有多大用处可以帮助人们辨认出其应用的例子。他们先前的发现这种应用的能力正是理论的充足性需要证明的,问题仅仅是说明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据称,理论的意义就是要说明我们对这个词的使用,但是我们被认为有能力(用近来的一位作家的话说)“区分开属于艺术品的对象和非艺术品的对象,因为……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艺术’一词,知道如何应用‘艺术品’这个短语”。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就有点像苏格拉底说的镜像,反映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这种理论也是用语言反映了我们娴熟的实际语言学实践。
但是,即使对于说母语的人,把艺术品与其他物品区分开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现在,如果没有艺术理论告诉人们,他们可能意识不到他正置身在艺术领域中。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这种领域是根据艺术理论被建构为艺术领域,因此,艺术理论的一个用处除了帮助我们区分艺术和非艺术,也包括使艺术成为可能。格罗康(朱光潜译法)(Glaucon)【2】和其他人几乎不知道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否则他们绝不会被镜像欺骗。
一
假设人们认为发现了一种全新类型的艺术品即类似于在任何地方发现了一种全新事实,也就是类似于发现了某种有待理论家解释的东西。在科学中,乃至别的领域,我们经常是通过辅助假设(auxiliary hypotheses)让新事实适应旧理论,如果所涉及的理论被认为有相当价值而不被立即抛弃的话,这算是足可被原谅的保守主义。现在,如果人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艺术模仿理论(IT)是一种特别有效的理论,可解释与艺术品的因果关系及评价有联系的大量现象,将一种惊人的统一性整合为复杂的领域。而且,用这种辅助假设(即偏离模仿性的艺术家都是任性、无能或疯狂的)来支持模仿论,以反对许多假设性反例,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事实上,无能、欺诈或愚蠢都是可以验证的判断(predication)。那么就假如,既然试验表明这些假设不成立,所以这个理论(现在难以修补)就必须被取代,所以就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尽可能包含旧理论的精华(competence),再融汇那些至今解释不通的事实。人们可能(边读本文边思考)代表了艺术史的某些情节,这和科学历史中的某些情节没有差异,在科学史中观念演变受到影响,拒绝支持某些事实,部分原因出于偏见、惰性及私利,也出于传统(well-established)理论或至少得到普遍赞誉的理论受到威胁(此威胁就是一切的统一都要瓦解)的情况。
一些这样的情节就是随着后印象派绘画的到来而发生的。用广为流行的艺术理论(IT)来说,不可能把这些接受为艺术,除非是无能的艺术(inept art):否则,它们可能受到冷遇,被认为是胡闹、自吹自擂或是疯子的疯言疯语的视觉对应物(visual counterpart)。所以,按照《基督变容》【3】中的根据(还不用说兰西尔画的牡鹿【4】),为了把它们接受为艺术就不需要太多的趣味变化,不需要对理论做大篇幅的修正,而涉及到的不仅是对这些对象的艺术授权,而且是强调这些被认可的艺术品具有新的意义特征,这样,现在就不得不针对它们作为艺术品的地位进行完全不同的阐述。作为新理论被接受的结果,不仅后印象派绘画被接受为艺术,而且把大量的对象(面具、武器等)从人类学博物馆(以及其他的各种地方)转移到了美术馆,尽管什么都不需要从美术馆里搬出来——即使内部进行重新布置,如在储藏室与展厅之间,因为我们希望新理论被接受的准则,是它能解释旧理论所曾解释的任何东西。无数个说母语的人在郊区的壁炉台上挂上无数个典范之作(paradigm cases)的复制品,为的是教授“艺术品”这一表达用语,这就可能将他们的爱德华时期的【5】先辈们陷于语言学中风中。
当然,我谈论一种理论是有些曲解历史地讲,足以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几种理论都或多或少是用IT理论定义的。必须在进行逻辑说明的迫切要求之前放弃艺术-历史的复杂性,而且我要谈一谈好像有一种代替理论,通过选择一种阐述得非常清晰的理论,部分地去补偿历史谎言(falsity)。根据这个理论,所讨论的艺术家被理解为:不是不成功地模仿了真实形式,而是成功地创造了新的形式,与旧艺术被认为(如它的那些最好的例子)完美地模仿了的形式一样真实。毕竟,艺术长久以来被视为是创造性的(瓦萨里说过上帝是第一个艺术家),后印象主义者被解释为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用罗杰·弗莱的话说,他们的目的“不在幻觉而在于真实性(reality)”。这种理论(RT-Reality Theory真实性理论)提供了观看绘画的全新方法,无论是新绘画还是旧绘画。实际上,人们可以几乎解释梵高、塞尚的粗俗绘画(crude drawing)、路奥、杜飞的形式与轮廓的错位以及高更、野兽派的任意使用色彩平面(color planes),还有许许多多引人注意的方式,这些都是非模仿的东西,特别是它们的意图都不是为了欺骗视觉。从逻辑上讲,这有点像在精美的伪钞上印上“不合法钞票”,因此这个对象(伪造与标记)就不能再欺骗任何人。这不是一张幻觉的钞票,但是正因为它不是幻觉的,所以它也不会自动成为一张真钞票。相反,它只在真实对象和真实对象的真实复制品(facsimile)之间占据了一个全然敞开的空间:如果人们需要一个词,以及关于世界的一种新贡献,那么它就是一个非复制(non-facsimile)。这样,梵高的《吃土豆者》是某种明白无误的变形,成为真实生活中吃土豆者的非复制品;因为这些不是吃土豆者的复制品,所以梵高的画作为非模仿品,具有与其假定的主体一样的、被叫做真实对象的权利。借助这个理论(RT),艺术品重新进入最驳杂的事物中,而苏格拉底理论(IT)曾极力要把它们从这里驱逐出去;如果不比木匠制造的真实更多,它们的真实至少不会更少。后印象主义者赢得了本体论的胜利。
正是凭借RT,我们才一定理解了今天我们周围的艺术品。这样,利希滕斯坦因创作了喜剧漫画作品,但是它们有10到12英尺高。这些画取材于日常的小报,相当忠实地投影放大到巨幅比例的家常画框上,但正是这种比例具有价值。一位娴熟的雕刻家可以在一个图针上雕刻《圣母与大臣罗兰》(The Virgin and the Chancellor Rollin)【6】,而且同样在凝视中可以辨认出来,但是如果用类似的比例雕刻巴尔耐特·纽曼则只会是一滴色点,消失在缩小中。一张利希滕斯坦因的照片与一张《斯蒂夫·坎永(Steve Canyon)》漫画杂志【7】上同样的照片是区分不出来的;但是照片无法捕捉到比例,因此,就像波提切利的黑白雕刻画一样,是不准确的复制品(reproduction),比例在这里是基本要素,就像在波提切利那里色彩是基本要素一样。那么,利希滕斯坦因不是模仿而是新的实体(entity),就像巨螺那样。作为对比,贾斯伯·约翰斯(Jasper Johns)画的是与比例问题不相关的对象。然而,他的对象不可能是模仿,因为它们具有非凡的属性,即对这一类的对象的成员进行任何有意的复制(copy)都自动成为这一类的一个成员,这样,这些对象在逻辑上是不可模仿的。因此,对一个数字的复制仅仅是那个数字:一幅3的绘画就是一个由颜料构成的3。另外,约翰斯还画靶子、国旗和地图。最后,我希望这不是对柏拉图的无意的注脚,我们的两个开拓者——劳申伯格和奥登伯格——都制做了真正的床。
劳申伯格的床挂在墙上,凌乱地甩了一些油漆。奥登伯格的床则是一个长方菱形,一端比另一端要窄,人们会认为它有一种内嵌式的透视:很适合放在小卧室里。作为床,它们的售价都高得出奇,但是人们可以在其中任意一张上睡觉:劳申伯格曾担心人们会爬到他的床上,酣然入睡。现在,想象某个Testadura【8】一位普通的演讲者和著名的外行——没有注意到这是艺术,把它们当成是真实物(reality),简单而又单纯。他把劳申伯格甩在床上的油漆当成是其主人的邋遢,而把奥登伯格床的偏斜当成是制做者的无能或者也许是任何“定做”这个床的人的鬼点子。这些可能都是错误的,但是相当奇怪的错误,与惊讶的鸟所犯的错误没有什么特别地不同(这些鸟去捉宙克西斯画的假葡萄)。它们把艺术误以为真实(reality),而Testadura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但是,根据RT,它意味着是真实(reality)。一个人能把真实误以为真实吗?我们如何描述Testadura的错误?毕竟,什么防止了奥登伯格的创造被当成变形的床?这等于问什么使之成为艺术,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进入了一个观念探索的领域。在这里,说母语者是贫穷的向导:他们自己已经迷路。
二
当一件艺术品是人们误会的真实物时,把艺术品误以为真实物不是一个有多么了不起的本领。问题是如何避免这样的错误,或如何在它们被制成的时候就消除了这些错误。艺术品是一张床,而不是一个床的幻觉;所以不会像宙克西斯的鸟那样痛苦地遇到被欺骗的平面。除了保安提醒Testadura不要睡在这件艺术品上外,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这张床是一件艺术品,而不是一张床;毕竟,既然人们无法发现一张床不是一张床,那么,Testadura如何意识到他犯了一个错误?需要某种解释,因为此处的错误是一个非常令人好奇的哲学错误,就像(如果我们假定P.F.斯特劳逊(Strawson)【9】的某些著名观点是正确的)当真实的情况是一个人就是一具材料肉体(meterial body),意即这类全部的谓项(非常敏感地适用于材料肉体)都非常敏感地、并且诉诸无差别标准地适用于人们的时候,就会把一个人误以为是一个材料肉体。所以,你无法发现一个人不是一具材料肉体。
也许,我们就开始来解释油漆污点不可以被搪塞过去、它们是物品的一部分,所以物品不是一张单纯的床——碰巧——上面洒了一些油漆,但是一件用床和若干油漆污点制作的复杂物品:一张油漆床。同样的,一个人不是一具材料肉体——碰巧——有一些附加的思想,而是一个由肉体和一些意识状态组成的复杂实体(entity):一个意识-肉体。那么,人就像艺术品一样,必须被看作不可还原为他们自身的各部分,而且在这个意义上,人是原始的(primitive)。也就是更准确地说,油漆污点不是真实物——床——的一部分(床碰巧是艺术品的一部分),但是像床一样,同样是艺术品的一部分。这一点可以归纳为艺术品的粗略的特征化,而此艺术品碰巧包含了真实物是它们自身的一部分:当真实物R是艺术品A的一部分而且能够被从A分离开、并被仅仅看作是R的时候,不是艺术品A的每一部分都是真实物R的一部分。这样到目前为止的错误就是把A误认为它自身的一部分,即R,纵使说A就是R、艺术品就是一张床,也不会不正确。这个“是(is)”正需要在此澄清。
关于艺术品的声明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是(is)”,它不是身份或论断的那个“是”,也不是存在、认定的那个“是”,或某个用来为哲学目的服务的特殊的“是”。不过,这是普通用法,儿童很容易就掌握了。正是根据这个“是”的含义,给小孩一个圆圈、一个三角形,问哪个是他、哪个是他姐姐,小孩就会指着三角形说“那是我”;或者,对我的问题做出反应,挨近我的一个人指着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人说“那是里尔”;或者,在美术馆里,出于对我的同伴的考虑,我指着我们面前一幅画上的斑点说“那块白色比目鱼(dab)是伊卡罗斯【10】”。这些例子里,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所指出的任何东西都代表了或再现了它被所说的东西,因为“伊卡罗斯”一词代表了或再现了伊卡罗斯:然而,我不会用是的同样含义指示该词,说“这是伊卡罗斯”。句子“此a是b'与“此a不是b”是一致的,当第一个句子应用了是的一个含义,而第二个句子应用了某个另外的含义,尽管a和b在整个过程中都清晰地被使用着。实际上,通常第一句话的真实性需要第二句话的真实性。事实上,第一句与“此a不是b”不一致,仅当那个是始终被清晰地使用着。由于缺少一个词,我就指定这个作为艺术认定的是(the is of artistic identification);在每一个使用情况中,a代表了对象的特定物理属性或物理部分;最后,这是某物成为艺术品的必要条件,即它的某部分或属性可由一个应用了这个特别的是的句子的主语来指定。顺便提及的是,正是“是”在边缘而神秘的宣言中具有近亲关系。(因此,一个是羽蛇神【11】;那些是赫拉克勒斯的支柱。)
让我说明一下。两个画家被要求用壁画装饰科学图书馆的东西墙,分别被叫做牛顿第一定律和牛顿第三定律。这些绘画,当最后昭示于人时,分别如下:

作为对象,我假定作品不可区分:在白色底上有一条黑色、水平线,每一维度和元素都一样大。B解释他的作品如下:一块物质,往下压,遇到了一块向上挤的物质:下面的物质同等地并相反地反作用于上面的物质。A解释他的作品如下:经过空间的线是孤立的分子的路径。路径从边通向边,有一种要超越的感觉。如果它在空间内结束或开始,那么,这条线将弯曲:它平行于顶边和底边,因为如果它比另一条边更接近一条边,那么就必须有一种力来解释它,这是与它成为孤立的分子的路径相矛盾的。
随着这些艺术认定还有许多东西。把中间一条线看成是边(物质遇到物质)就强加了一种确定图画的上部分和下部分的需要,或作为长方形,或作为两个区分开的部分(不一定是两块物质,因为线可以是一块向上——或向下——伸入空的空间中的物质的边)。如果它是一条边,我们无法这样把绘画的整个区域都看成是一个单一的空间:而是它由两个形式构成,或一个形式和一个非形式。我们只要通过把中间的水平线看作是一条不是边的线就可以把整个区域看成是一个单一的空间。但是这差不多要求对整个图画进行三维认定:区域可以是一个平面,线在上面(喷气飞机飞),或在下面(潜艇-路径),或在(线),或在里面(裂变),或经过(牛顿第一定律)——尽管在这最后的情况下,区域不是一个平面,但是一个绝对空间的透明的交叉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想象与画面的垂直的交叉部分来廓清所有的这些介词资格。那么,根据可应用的介词从句,区域就艺术地被水平元素所打断或没有打断。如果我们把这条线看作是经过空间,那么图画的边就不真正是空间的边:空间超越了图画,如果线本身超越了;我们处于和线一样的空间里。作为B,图画的边可以是图画的一部分,如果物质直接走向边,这样图画的边就是它们的边。在这种情况下,图画的最高点就会是物质的最高点,除了物质比图画本身多有四个最高点:这里的四个最高点将会是艺术品的一部分,而艺术品不是真实物的一部分。再一次,物质的各个面(face)可能就是图画的面(face),在观看图画的时候,我们就正看着这些面:但是空间没有面,在阅读A时,作品必须不得不被阅读为无面(faceless),而物理对象的面将不会是艺术品的一部分。这里要注意的是一个艺术认定如何产生了另一个艺术认定,我们如何(与已给定的认定一致)被要求给出其他并仍然被排除于其他:确实,一个给定的认定决定了一件作品可包含多少个元素。这些不同的认定彼此之间是不一致的,或者说一般来讲是这样,每个都可能构成一件不同的艺术品,即每个艺术品包含了可认定的真实物作为自身的一部分——或者至少可确认的真实物的各部分作为其自身的一部分。当然,有无感觉的认定:我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敏感地把中间的水平线读作《爱的徒劳》(Love’s Labour’s Lost)或《圣埃拉斯姆斯的上升》(The Ascendency of St.Erasmus)【12】。最后,注意一下一种认定如何被接受而不是另一种被接受,实际上是用一个世界交换另一个世界。确实,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宁静的诗意世界,只要我们认定上部分区域有明净无云的天空,倒映在下部静谧的水面上,只需要水平线的不真实边界分离开白(whiteness)与白。
现在,Testadura在旁听了整个讨论之后抗议他所看见的是颜色:白色涂成长方形,而且其上涂了一条黑线。他真的是非常正确:那就是他看到的全部或者任何人能够看到的,我们美学家也不例外。所以,如果他要求我们向他展示一下还可以进一步看到的东西,通过指点显示一下这就是艺术品(海洋与天空),我们无法满足,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忽略(如果假设他忽略了,且有一些我们可以指给他的小玩意,而他仔细瞥了瞥,说`哈,是的毕竟是一件艺术品啊',那将是荒谬的。)只有他掌握了艺术认定的是并因此把它构成一件艺术品时,我们才能帮助他。如果他不能达到这个程度,他将永远不能看到艺术品:他将像一个把棍子看成是棍子的小孩。
但是,纯抽象又怎么样?比方说看起来像A但是题名为No.7的什么东西。第10大街的抽象主义者毫无表情地坚持此处什么都没有,而只有白颜料(white paint)和黑颜料,我们的文字认定都不适用。那么,什么可以把他与Testadura区别开?Testadura的外行说法与他的说明无法区别。当他们都同意眼睛什么都没有看到的时候,它如何对于他是一件艺术品而对Testadura不是艺术品?答案(对于每个多样性的纯粹主义者而言,这可能很不受欢迎)就在于事实上这个艺术家通过一种混合了艺术理论和最近及以前的绘画历史的氛围,已经回到颜料的物理性,即他努力用自己的作品予以纯化的要素;作为这个结果,他的作品属于这种氛围,而且是这个历史的一部分。他通过拒绝艺术认定而实现了抽象,回到了真实世界,而这样的认定是把我们(他认为)排除于这个真实世界的,有点类似于青原【13】(Ch’ing Yuan)'的方式,他写道:
我三十年之前没研究禅时,我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当我接近更密切的知识时,我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但是现在,我得到了本质,我沉于安静。我复又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原文:参禅之初,看山总是山,看水总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或另一种文本:三十年前没有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后来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译者附加)
他对他所做的东西进行的认定,从逻辑上依赖于他所拒绝的理论和历史。他的阐释与Testadura说的“这是黑颜料、白颜料,仅此而已”之间的差异,在于事实上他仍然使用了艺术认定的“是”,这样他使用“那块黑颜料是黑颜料”不是同义词的重复述说。Testadura不处在这个阶段。把某物看作艺术需要眼睛无法低毁的某种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历史的知识:一个艺术世界。
三
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先生展出了布里洛盒子的复制品,在整洁的架子上堆放得高高的,和在超市的仓库中一样。它们碰巧是木制的,画得就像一个纸板,那为什么不是呢?来解释一下《时代》杂志的一位批评家的话吧,如果人们可以用青铜翻制人体的复制品,为什么不能用木板制作布里洛盒子的复制品呢?这些盒子的成本碰巧是真实生活中常用的同样盒子的2 X 103倍——这种差异几乎不能归结于它们的耐用性优势。事实上,布里洛生产者可以微微地提高一点成本,用木板来制作他们的盒子而不会使这些盒子成为艺术品,沃霍尔可能用纸板来制作他的盒子而不会不是艺术。所以,我们可能会忘记内在价值的问题,而且问道为什么生产布里洛盒子的人不能制造艺术,为什么沃霍尔必然制造艺术品。当然了,确定无疑的,沃霍尔的盒子是手工制作的。毕加索曾把一个苏士酒瓶上的标签贴到一幅画上,这有点像把毕加索的做法疯狂地颠倒过来,就像是说学院艺术家关心准确模仿,一定总是缺少真实的东西:那么,为什么就不能使用真实的东西呢?波普艺术家费力地用手工重新制作出机器制造的物品,例如,画咖啡罐上的标签(人们可以听到熟悉的赞美“完全是手工做的啊”,但在遇到这些物品的时候,这些话就痛苦地被排除在向导的语言之外)。但是差异不能包括手艺:一个用石头雕了许多小鹅卵石并小合翼翼地建构一件叫做《砂砾堆》的作品的人,可能会引发一种价值的劳动理论来解释他所要求的价格;但是问题是,什么使它成为艺术?又为什么无论如何都得需要沃霍尔来制作这些东西?为什么不是仅仅在盒子上涂上他的签名?或者,把盒子弄烂了,以《弄烂的布里洛盒子》(“抗议机械化……”)名义展示出来或仅仅作为《未弄烂的布里洛盒子》(“大胆肯定产业的造型真实性(authenticity)……”)展览一个布里洛纸盒?这个人是迈达斯【14】一类的人吗?可以把任何他触摸过的东西都变成纯艺术金子?由隐藏的艺术品组成的整个世界等待着,就像现实中的面包和酒一样,经过某些黑暗的神秘,被变成圣礼中的不可辨认的肉体和鲜血吗?千万不要介意布里洛盒子可能不好,更不是伟大艺术。给人突出印象的是它完全是一个艺术。但是如果它是艺术,为什么那些不可区别的布里洛盒子还放在库房里?或者说,艺术与现实之间的整个区分已经打破?
假定一个人收集了各种物品(现成品),包括布里洛纸盒;我们赞美了展览的多样性、独创性以及你所愿意说的好话。接下来,除了布里洛纸盒,他什么都没有展览,我们批评它沉闷、重复、自我剿窃——或(更深刻地)声称他被规矩、重复所困扰,就如《玛丽亚温泉》(Marienbad)一样。或者他把它们堆得高高的,留出一条窄窄的路经;我们踏着我们的足迹,穿过这个不透明的堆积物,发现它是一次让人惊悸不安的经历,撰文称其为消费产品所包围,把我们当囚徒一样限制起来:或我们说他是一个现代的金字塔建筑者。确实如此,我们没有说这些东西是关于库房保管员的。不过,一间仓库不是美术馆,我们无法轻易地把布里洛盒子与它们所置身其中的美术馆分离开来,正如我们无法把劳申伯格的床与它上面的油漆分离开一样。出了美术馆,它们是纸板盒子。不过,洗尽了油漆,劳申伯格的床还是一个床,还是它被变成艺术之前的样子。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这事情,我们会发现艺术家没能(真正地、出于需要地)生产出一个纯粹的真实物。他生产出了一个艺术品,他使用真正的布里洛盒子只成了艺术家所掌握的资源的扩大,是对艺术家的材料的贡献,正如油画颜料一样或如制版墨(tuché)【15】一样。
最终在布里洛盒子和由布里洛盒子组成的艺术品之间作出区别的是某种理论。是理论把它带入艺术的世界中,防止它沦落为它所是的真实物品。当然,没有理论,人们是不可能把它看作艺术的,为了把它看作是艺术世界的一部分,人们必须掌握大量的艺术理论,还有一定的纽约绘画当代史知识。如果倒退五十年回去,这不会是艺术的。但是另一方面,任何事情都是公平的,在中世纪也不会有飞行保险,或不会有伊特鲁里亚打字机消除剂。世界必须准备迎接某些事情,艺术世界和真实世界一样。正是艺术理论的作用(近来总是如此)使艺术世界乃至艺术成为可能。我大概会想,拉斯科岩洞的画家可能永远不会想到他们是在墙面上生产艺术。要等到出现了新石器的美学家,才会是的。
四
艺术世界对于真实世界有点像上帝之城对于世俗之城的关系。某些物品就像某些个人一样喜欢双重公民身份,但是尽管有RT理论,艺术品与真实物之间还是有基本的对比。也许早期的IT理论的构建者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刚刚开始意识到艺术的非真实性(nonreality),也许受到限制只能假设:对象具有的唯一作用(不同于真实)就是成为假的,这样,艺术品必然地必须是真实物的模仿品。这就太狭窄了。所以,叶芝写道“一旦脱离自然,我将永远不再/从任何自然物中取得我的肉体之形。”这仅仅是一个选择的事情:艺术世界的布里洛盒子可能就正好是真实世界的布里洛盒子,由艺术认定的是分开并统一起来。但是我想最后谈谈使艺术品成为可能的理论,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在谈的时候,我将恳求几个我所知道的最坚硬的哲学问题。
现在,我谈几对彼此作为“对立项(opposites)”相关的谓项(predicate),并立刻承认这个陈旧的术语的含混性。矛盾的谓项不是对立项,因为它们每一对的一个对立项都必须适用于宇宙中的每一个对象,一组对立项中的任何一个都不需要适用于宇宙中的某些对象。一个对象必须首先在一组对立项中的任意一个适用它之前居于某一类(be of a certain kind),然后,至多并至少,对立项中的一个必须适用于它。所以,对立项不是相反项,因为相反项两者可能对于宇宙中的某些对象都是假的(false),但是对立项无法两者都是假的;对于某些对象,一组对立项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敏感地适用,除非对象具有正确的一种(be of the right sort)。那么,如果对象是所要求的那一种,对立项按矛盾项行动。如果F和非-F是对立项,那么,在任何一个对立项敏感地适用前,对象o必须是某类K;但是,如果o是K的一个成员,那么,在除另一个(the other)的情况下,o要么是F,要么是非-F。我把敏感地适用于(ô)Ko【16】的几组对立项类指定为K-相关的谓项类。一个对象具有一种K属性的必要条件是:至少一组与K-相关的对立项可以敏感地适用于它。但是,实际上,如果一个对象具有一种K属性,至少并至多每组与K-相关的对立项的一项适用于它。
我现在对K类艺术品中与K-相关的谓项感兴趣。让F和非-F成为这类谓项的对立项。现在,可能的情况可能是,在全部的时代里,每一个艺术品都是非-F。但是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什么既是艺术品又是F,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想到非-F是一个与艺术相关的谓项。艺术品的非-F属性没有什么标记(goes unmarked)。作为对比,一个给定时代的所有作品可能都是G,所以一直到某物可能既是艺术品又是非-G的时候,任何人才会想到这一点;事实上,当G敏感地被视为某东西的属性之前——在这种情况中,非-G可能也被视为艺术品的属性,而且G自身不可能是这个类的定义性特征——而这个某东西不得不首先成为艺术品时,确实,人们可能会认为G是艺术品的一个定义性特征。
让G成为“是再现的”,而让F成为“是表现主义的”。在一给定时间,这些和它们的对立项也许是批评用法中唯一的与艺术相关的谓项。现在,让“+”代表一给定谓项P,“-”代表它的对立项非-P,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建立如下的一个风格矩阵:

考虑到[given]积极的批评词汇,行决定了现有的风格:再现表现主义(如野兽派);再现非表现主义(安格尔);非再现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非再现非表现主义(硬边抽象)。简单地说,当我们增加与艺术相关的谓项时,我们以2”比率提高了现有风格的数量。当然,事先并不是很容易地看到哪些谓项将被增加或被它们的对立项取代,但是假定一个艺术家决定将H自此以后在艺术上对他的绘画有关。那么,事实上,H和非-H都变成在艺术上对所有绘画有关,而且如果他的绘画是第一个且唯一的属于H的绘画,那么每一个现存的其他绘画都变成了非-H,而且整个绘画界与翻倍增加的现有风格机会一块变得富庶起来。正是这个艺术世界中的实体的追溯性丰富性(this retroactive enrichment of the entities in the artworld)让它有可能一起讨论拉斐尔和德库宁,或一起讨论利希滕斯坦因和米开朗基罗。与艺术相关的谓项的多样性越大,艺术世界的个体成员就变得越复杂;人们对整个艺术世界的人员了解越多,人们也就对它的任意成员的经验越丰富。
在这一点上,要注意到,如果有m个与艺术上相关的谓项,那么,总有一底部行,具有m个减号。这一行很容易被纯粹主义者占据。他们一旦洗尽了画布上他们所认为非本质的东西,他们便认为他们提炼出了艺术的本质。但这仅仅是他们的谬见:许多艺术上相关的谓项既完全适用于它们的方形单色作品,也完全适用于任何艺术世界的成员,它们只在“非纯粹”绘画存在的情况下才作为艺术品而存在。严格来讲,莱茵哈特的黑方形在艺术上和提香的《圣者与凡人之爱》(Sacred and Profane Love)一样丰富。这就解释了少如何就是多。
时尚碰巧青睐这个风格矩阵的某些行:博物馆、鉴赏家以及其他人都是艺术世界中的无足轻重的人。为了坚持或为了寻求所有的艺术家变成再现的,也许为了进入特别有名望的展览,把现有的风格矩阵分成两半:那么仍有2n/2”个满足要求的方式,那么,博物馆能够展览他们已定下的题目的所有这些“方法(approach)”。但是,这是一个几乎是纯粹社会学的兴趣的事情:矩阵中的一行于另一行是一样合法的。我认为,艺术突破包括了给矩阵增加列的可能性。然后,艺术家或是非常爽快或是不太爽快,占据了如此打开的地位:这就是当代艺术的显著特征,对于那些不太熟悉这个矩阵的人来说,很难(也许不可能)去承认某些艺术品所占据的地位。如果没有艺术世界的理论和历史,这些东西也不会是艺术品。
布里洛盒子就像“艺术喜剧”(commedia dell’arte)》演员将令人兴奋的不协调带入《纳克索斯岛上的阿里阿德涅》(Ariadne auf Naxos)喜剧中一样,也带着这种同样的令人兴奋的不协调进入了艺术世界。不论与艺术相关的谓项是什么(它们凭此获得进入的资格),艺术世界的其他部分在获得对立的谓项并适用于它的成员时变得更加丰富。那么,就回到哈姆雷特的观点上(我们以此开始了我们的讨论),布里洛盒子向我们自己显示了我们,同样,任何东西也能这样显示:作为拿起来观察自然的镜子,它们也可能用来捕捉到我们的诸位国王的良心。
作者:阿瑟•C•丹托(Arthur C.Danto) 王春辰译
原文刊载于《外国美学》2012年00期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64年10月美国《哲学杂志》(61,19)——译注
【2】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促使苏格拉底提出作为模仿的诗论。——译注
【3】拉斐尔的作品,画的是基督升天的景象。——译注
【4】Edwin Landseer(1803-1873):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学院派画家,善画动物,他的《峡谷之王》,画了一头雄鹿,浓缩了维多利亚时代绘画的风格。——译注
【5】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七世1910年继承其母维多利亚女王之位,这一时期的道德与维多利亚时的严格规范形成鲜明对比。——译注
【6】杨 ·凡 ·爱克(1390-1441)的作品。
【7】该杂志是1947年 Milton Caniff创立的漫画系列故事,主人公斯蒂夫·坎永是二战飞行员。1988年随着创办人坎尼夫去世而停刊。——译注
【8】这是丹托为便于讨论而虚拟的一个名字 。——译注
【9】Peter Strawson(1919-2006):牛津大学哲学教授,英国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著作有《个体》(1951)、《感觉的边界》(1966),《逻辑一语言学论文》(1971)、《自由与抑制》及《分析与形而上学》等。
【10】伊卡罗斯是代达罗斯的儿子,他乘着他父亲做的人工翅膀逃离克里特时,由于离太阳太近以致粘翅膀用的蜡溶化了,而掉进了爱琴海。——译注
【11】古代墨西哥阿兹特克人与托尔特克人崇奉的重要神抵 。 — 译注
【12】埃拉斯姆斯,一,荷兰文艺复兴时期学者、罗马天主教神学家,他试图复兴古代的古典经文,恢复基于《圣经》的朴素的基督教信仰,消除中世纪教会的一些不当行为,他的作品包括《基督教骑士手册》年和《愚人颂》年。——译注
【13】唐代佛教南宗七祖禅师。——译注
【14】迈达斯,传说中的佛里几亚国王,酒神狄奥尼索斯赐给他一种力量,使他能够手触摸任何东西变成金子。——译注
【15】一种黑墨,用于在丝网印刷和平版印刷中绘制图案。
【16】逻辑符号,代表任何对象O ,具有K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