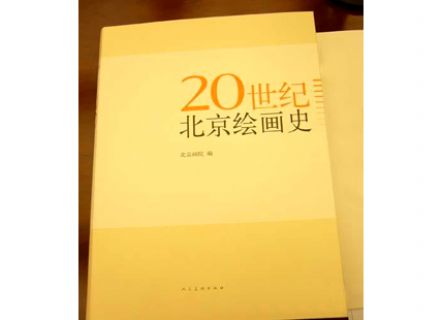
【内容提要】
本文以分析美术史研究中“地域”概念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特征入手,通过对于现当代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状况的追溯,分析了地域美术史研究的梳理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借由对于地域文化差异与地域美术史研究的关系及其方法论的反思,指出地域美术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在本文看来,地域美术史研究的学术贡献在于其小中见大、同中求异,以某种特定时间、地域个案研究的个性特征,为美术史研究的已有范式提供一种校正与检验的契机。
【关键词】
地域性 普适性 研究范式
时间性与空间性:地域美术研究的两个维度
在全球化背景与现代化的进程中,地域文化及地域美术研究的前景与趋向愈发引人关注,无论是对于信息时代与地域美术之间的关系,还是以现代性理论观照与阐发地域美术研究,都成为艺术史研究方法论与范畴内容的焦点。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区分每个国家与地区的艺术史叙事,更已成为世界艺术史界学术实践的核心问题。全球化的多元结构与信息传播技术的高度发达,不但没有消解地域性的价值,反而更加凸显了地域文化的无法替代的可贵特性。
地域美术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承担着双重使命,即当创建普通艺术史的元叙事时,研究者还要针对不同的地域性特征展开叙述,从更广层面上指出其相似和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域性因素。长期以来美术史的研究的逻辑与体例都遵循纵向的时间线索,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到邓椿的《画继》,纪传体的常规体例与时间顺序的前后相接,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叙事的传统方法。长期以来修治美术史的习惯路径,首先需要排年表、列师承、追溯源,虽也有《益州名画录》等地域性美术的专题述评,但对地域美术的横向梳理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唐宋之际的南北之分也只停留于宽泛而模糊的地域分类,实际上更强调某种风格而非地别的差异。
地域性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而其内涵又绝不止于空间上的界定。空间层面不同的地域性往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或者说不同的地域往往展现了同一现象或事物的多个侧面。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很少有学者从时间的角度去考察过地域性,似乎地域性只是时间之外的某种与之二元对立的范畴,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另一种不相干的维度。然而当我们回顾艺术史,就会发现“地域性”中已然包蕴了时间的概念,例如,当今天我们谈到“青铜时代”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魏晋风骨”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盛唐气象”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虽其作为古代艺术史中某一时段的时代称谓,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魏晋风骨和盛唐气象已经消失了,与今日的中国艺术完全隔断不发生任何关联。反过来,艺术史中的“吴门四家”、“扬州八怪”、“海上画派”等也分别代表了某个时代。同时,这些派别、概念、范畴之所以直至今日依然有效,是因为它们代表着某种风格,具有艺术价值的普适性。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艺术史的地域性问题就变得错综复杂,同时也充满着戏剧性。
地域性的研究范畴,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美术史家所需要的“地点”和“读点”。对于某一研究对象的地域性的选取,发挥的空间有多种可能,很多因素可以纳入其中。特定空间与线性时间的混合,可以在某一项研究中奇妙地展现出来。正如人类学家、结构主义哲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谈到自己领略结构主义精髓的感触:
当你忽然发现……可以同时在岩石上面发现两个菊石的遗痕,看到它们微妙不对称的回纹,这些回纹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证明两个化石之间存在着长达几万年的时间距离,在这种时候,时间和空间合而为一:此刻仍然存活着多样性与不同的年代相重叠,并且加以保存延续。思想和情感进入一种新的层次,在那当中,每一滴汗,每一片肌肉的移动,每一息呼吸,全都成为过去的历史的象征,其发展的历史在我身体重现,而在同时,我的思想又拥抱其中的意义。我觉得自己处在更为浓郁的智识性里面,不同世纪,间隔遥远的地方在互相呼唤,最后终于用相同而唯一的声音说话。
一项深入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应力求发掘并展现出这种时空并置的微妙结构,从中追求一种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感。惟其如此,时间维度的历史学含量才能在一项以局部地域为对象的研究中提升其意义。
然而说到底,地域性又首先是一种以空间为依据的分类方式。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在讨论地域性格与地域绘画的关系时提出“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佻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焉。” 不同地域艺术创作风格与样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空间的文化性格决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是艺术史还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历史,必然要在一定的空间中展开,并试图解释在这一空间中独有的审美思维与人文特性。
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断发展、变化,但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展现了文化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烙印的某种特性。尤其在当代视角的大文化格局中,地域(Local)、国家(National)与全球(Globle)的概念呈现了空间分类的不同层面,更寄托着文化政治的差异性与由此带来的不同地理版块异质文化之间的互斥与关联。作为空间层面的“地域性”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可以指一片村落、一处城乡、一个省份、一个国家,甚至地球的东西两方。狭义上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则更加强调对于同一文化共同体内部,不同地域板块或地点的各自考察与观照。在这一点上,地域性比国家性或民族性更具针对性和专属意义。因为由于诸多极具地域性特征的民俗、文化及艺术创作是在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中发展演变而来的,尤其在交通条件有限、缺乏文化沟通交融的时代所形成的相异特点,更保留了地域美术的可识别性。这一点在五代时期已经形成的山水画南北两派的风格分类、传统工艺美术史上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域在媒材技法与审美标准上的巨大差异都可见一斑。
无论是地域范围的广袤或狭小、中心或边缘,一项地域美术研究总是以某种形式的“整体”形态显现。但如果仅从美术史写作的层面,地域美术研究与国家或民族美术的通史相比,始终处于一种支流、局部或从属的地位,反过来,地域美术的多元存在又构成了国家、民族更高一层美术内容的主体。这就要求地域美术研究不能局限于现状考察,而应追溯研究该地域美术的纵向特征,即各个断代的时间段内形成的地域特征,同时要研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地域美术的发展,及其在交叉、流动、迁徙中造成的相互影响,以揭示在特定时空中存在的价值观。正如生活在北宋蜀地的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所追求的,“至如蜀都名画之存亡,系后学之明昧,斯黄氏之志也。” 在这一层面上,地域美术研究关涉到风格样式的衍变规律,通过历史性的关联,完成某种“超越”。
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的晚近历史与现状述评
20世纪以来,随着美术史学研究的门类细化与现实需要,兼受西方现代学术方法的影响,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的个案梳理意识与学术自觉愈发深入。早在民国时期,已不乏地域性美术研究的著述,罗元黼的《蜀画史稿》(1917)、汪兆镛的《岭南画征略》(1928)、王瞻民的《越中历代画人传》(1928)、庞士龙的《常熟书画史汇传》(1930)等的出版成书,已经反映出民国时期美术史学者的地域研究意识,这一过程与以滕固为代表的美术史论家以现代学术方法进行断代史研究近乎同时。
地域画派的概念与影响在美术史叙述中的生成,促动了百余年来中国地域美术史的蓬勃发展。民国初期已经对于地域画派有过的系统的梳理与分类。在民国时期的传统派画家群体中,按照地域性划分其南、北分别以北京画坛与沪杭画坛两大版块为代表。前者代表人物为陈师曾、金城等人,兴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后者代表人物为黄宾虹、潘天寿等人,盛于二、三十年代。上世纪三十年代,地域性又与时代性并列为美术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当时作为上海“中国画会” 的发起人和执行委员的郑午昌在文中强调:
我们既不能忘却我们所处立的地域,尤不能忘却我们所生的时代。在历史进化的过程中,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艺术,同一时代而又有各个民族的独特的艺术,以其环境及历史的条件反映使然也。
在此前后,对于地域画派与地域美术现象的研究方兴未艾,地域派别观念盛行。由于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自民国建成以来首次全面汇集全国画坛作品,此间评论者的印象也更具参考价值。“第一次全国美展汇刊”于1929年4-5月间共出版10期,作者队伍汇集了当时全国著名的画家和理论家,其中陈小蝶的《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以个人印象对于当时的画坛作了细致的阵营划分,依据此次展会中的国画作品风格,将当时画坛分作复古派、新进派、折衷派、美专派、南画派、文人派六派,实际上牵涉了上海、北京、广东三地的代表性画家。如果按照今日约定俗成的革新派与传统派的分类逻辑重新归列一下,则在陈小蝶划分的六派中,折衷派、美专派属革新派或中西融合派的范围,而复古派、新进派、南画派和文人派均属传统派的阵营,且陈氏对传统派前三者的复古、摹古风格均持有不同程度的不满,而毫不避讳对文人派的情有独钟。
在当代学者以特定地域性为范围的民国时期中国绘画的研究文章中,北京画坛、上海画坛和岭南画坛有关中国画的相关研究相对其他地域更为充分。其中代表性论文如薛永年先生的《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2002)、李松先生的《20世纪前期的湖社与京津地区画家》(2003)等文章探讨了民国画坛传统派的理论与实践;万青力先生的《南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2000)从当时北京画坛以南方画家为主流的现象入手,从画家与机构的角度探讨了这种现象的历史动因、时代契机与文化意义;他的另一篇论文《美术家、企业家陈小蝶——民国时期上海画坛研究之一》(2001)则通过美术家个体的研究,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在美术史细节中考察评价艺术家的成就,从而上升到对于上海画坛的整体考察。单国强、单国霖对于隋代以来至清代的京江画派研究、赵力对于京江画派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和艺术渊源背景的研究,曾对镇江地区的地域性画派作出了较为深入的考查。在对于广东民国画坛的专项研究中,黄小庚、吴瑾编辑的《广东现代画坛实录》(1990)收集了岭南地区画家讨论美术的文章,对于这一专题有重要的资料作用;黄大德的相关文章更揭示了当时岭南画坛“方黄之争”的历史细节,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一直致力于广东美术地域性研究的李伟铭以数篇相关学术文章,对于岭南画派中国画论争及其史料的收集与研究,也从某种程度上拓展了这项专题研究的深度。
近十年来对于地方画派的研究著述及其出版,在2002、2003年之间达到了一个高潮期。2002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画派画集》在汇集图像资料的基础上,对二十世纪前期的“京津画派”、“岭南画派”及“海上画派”进行了研究。2003年前后由吉林美术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画派研究丛书”作为一部汇集性著述丛编,对海上画派、松江画派、新安画派、娄东画派、吴门画派、常州画派、南方山水画派、北方山水画派等十五个古代地方绘画流派分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详细评述了各画派的来历、产生背景、画风的形成和转变、主要艺术特点及其影响,首次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地域画派的渊薮与全貌。
目前看来,地域美术通史的研究对象仍然以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最为集中深入。以上海、广东两地为例,在相关领域的研究领域,已有徐昌酩主编的《上海美术志》、李超的《上海美术史》、黄可的《上海美术史札记》、李公明的《广东美术史》等著作,对于两地的整体性地域美术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此外,一些地域性美术研究的工具性资料汇编著作,也为以往地域美术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如王震编撰的《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l872-1911〈申报〉艺术条目索引》、颜娟英女士编撰的《台湾近代美术大事年表1895-1945》等,以及各地域中城县各级的地方志,都成为地域性美术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料和依据参照。
在对于近年来面世的北京美术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以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和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最具代表性。 二者都是国内一流专家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均在不同程度上拓展了这项专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所有地域美术史研究阵营中,北京美术史研究作为地域美术史的特殊性不言而喻,其理据正如《北京美术史》引论中的描述:“北京经历了从原始聚落到城市萌芽,从中土边塞到多民族城市,从少数民族政权之都到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演化过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其地域文化构造宛如古老的地质积层一般,错综繁芜,一言难尽。”北京长期作为都城的历史,也决定了其具有主流示范性和中心辐射性的杂糅特征,从而兼具地域美术独特性与国家美术史的普遍性。
由北京画院组织编写的地域性断代史《20世纪北京绘画史》作为北京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从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各时期北京地区美术发展的历史图景。参加各章节的编撰人员均为在各自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专家,在主编邵大箴先生和李松先生的主持下,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和掌握原始资料,力求客观地呈现历史原貌,分析历史事件、人物与当时历史情境的关系及所起的作用。而《北京美术史》作为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北京美术通史,不但填补了重要的学术空白,而且在研究视野的广度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此书之前,尚未有学者以通史的线索系统梳理北京地域性美术的发展历程。该著作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李福顺教授为首进行编撰,长达八十余万字,编者将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和诸多美术遗存图片相结合,系统书写了自原始社会至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美术发展历程,对北京美术的地域性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区别于其它地域已有的美术文献史。
除了对于北京、上海、广东的集中性研究之外,一些研究针对特定区域与门类,也体现了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如郑工、莫小也等学者各自对于澳门美术史的研究,展现了一个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艺术交汇的独特个案所能体现出的学术价值。在对于不同艺术门类的梳理方面,亦有吴敬贤、汪天亮等学者对于陕西、福建等地的工艺美术史专项研究的著述出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以来一批少数民族地区美术史的面世,丰富了地域性美术研究的内涵,一些专家学者有意识地从中寻找地域性美术的审美特性,发掘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由王伯敏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于1995年面世,作为国内第一部少数民族美术史专著,整理汇集了各少数民族地域的美术史研究文献。近年来,更为详尽深入的相关个案性研究尤以西藏、云南、内蒙古等地域的地区美术史研究取得的成果,在数量、质量上令人关注,如康・格桑益希的《藏族美术史》、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谢继胜的《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吴明娣的《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李伟卿的《云南民族美术史》、王嵘的《西域艺术史》、韩小忙的《西夏美术史》、阿木尔巴图的《蒙古族美术研究》、鄂•苏日台的《蒙古族美术史》、乌力吉的《内蒙古艺术地理》等。这些著作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域艺术的发展,并进一步阐析了宗教对于艺术的影响,对于探讨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发展以及多民族艺术的交融具有重要意义。
综观以往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史料梳理与图片整理的文献汇集,至目前为止仍然是此类研究的首要任务和学术使命。特别是地理位置或文化坐标上相对“边缘”地域的美术,对于一些原始资料的及时收集与发掘,以及诸多尚待填补的学术空白点,应引起相关学者的更多关注,投入更多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一些地域美术尚缺乏通史与断代史角度的整合梳理,从而考察、发现该地域美术的独特价值。
个性与共性:地域美术史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传统意义上地域美术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对于一个特定地域美术发展的专项研究,探求其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继而建构一种美术史发展模式,完成意义的升华。受到现代学术观念与方法论的影响,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对此进行过践行与反思。是单纯“就事论事”、保持其独有价值体系的个案研究,还是将其放置在一个整一的社会文化形态中,观照其普适价值与建设性意义,成为地域美术史研究回避不开的选择。
在西方艺术史方法论的发展史上,有着从地域美术史研究中抽绎美术史研究范式的传统。温克尔曼较早试图通过一项特定地域范围的个案研究来推导出各地域艺术史的统一规律与模式。他认为研究古希腊艺术的目标,是要把人们的认识“引向统一,引向真理,并以此来作为我们在判断和实践中的指南” 。其《古代艺术史》(History of Ancient Art,1764)通过对于古希腊艺术史的深入考察推导出艺术史研究的原则,提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艺术必须看作和它的物质环境和社会背景有血肉联系:“艺术史的目的在于叙述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颓,以及各民族各时代和各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并且尽量地根据流传下来的古代作品来作说明。”对于这种“由点及面”的推广,认同与批判的声音一直并存。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922-1996)认为“取得了一个范式,和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 以此来看,温克尔曼从希腊艺术史中抽绎出的规律与发法论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建构。而同样的方法在艺术史家文杜里(1885-1961)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它所研究的艺术作品失去了个性,而成了某种类型。因此,温克尔曼开拓的道路偏离了历史和美学的标杆。……他把‘艺术家生活’置之脑后,而创造了‘艺术史’的一种类型。”正是这种地域美术史研究推导出的范式,使温克尔曼成为了文杜里眼中横亘在后来艺术史家们面前的“伟大的绊脚石”。
对于地域美术史研究来说,比研究范式更为重要的,是地域文化氛围、地理环境和人文风俗的具体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地域性及其文化氛围,深刻影响、启蒙了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的审美取向与风格追求。郑午昌也在《中国画学全史》指出,画家传、画迹录和画学论“三者互相参证,并及与有影响之种种环境而共推论之,则其源流宗派,与乎进退消长之势,不难了然若揭。” 如此说来,与地域美术研究相互关涉的因素就十分复杂丰富,随之而来的相关问题也存在着多种可能。在笔者看来,对于地域画派和地域美术史研究,存在以下几个容易掉落的陷阱:
其一,方法论的“范式”误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域美术史专项研究的个性特征,与其可能达成的普适性范式,并非直线对应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地域美术史研究对于美术史方法论的真正的建构意义可能在于,这项研究的学术价值不是对于已有模式的重复验证,而恰是对于一种已有的“普范性”模式的校正、反拨与挑战。任何先入为主地“套用”既有方法论范式来进入一项特定的地域美术研究,都可能无法发掘该地域美术的核心特点。因此,在“小中见大”的同时,秉持“同中求异”的精神,即在建构普遍联系的同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个案性,也正是地域美术研究的普适价值所在。
其二,研究初衷上的地方保护主义与“家乡偏好”(权且借用金融学界的“home bias”一词)。研究者的“故乡情结”,很容易变为地域美术史甚或地域文化史研究的动力来源,这种源于集体无意识的乡土情感本无可厚非,也确为一种可贵的文化使命与伦理情操,但正如站在山中望此山的全廓难以尽收眼底,“家乡偏好”也使研究者很难保持一种理性客观的中立态度。如果这种立场又与某种文化权力甚至经济利益相对接,其后果更可想而知。一个新鲜而典型例子,是2009年12月在河南安阳一次考古发现,所引发的关于“曹操墓”的真假及其归属的争议。其后来的一系列由地方政府等各方人士参与的辩论和争夺,事实上已与学术研究无关,与随后“刘备墓”的挖声又起,共同沦为一场争夺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旅游资源的角逐。
其三,过度强调地域文化性格对于地域美术的影响。地域艺术史研究乃至地域文化研究,稍有不慎便会陷入地缘决定论的极端,即过度放大地域决定文化的绝对性。事实上对于地域美术研究而言,地域性不过是某种特定的资源与背景,而非对艺术创作的全部内容,甚至也不是对于艺术创作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清人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论述过地域性对于画家影响的相对性,并举其反例:“视学之纯杂为优劣,不以宗之南北分低昂也。其不可拘于南北者复有二:或气禀之偶异,南人北禀,北人南禀是也;或渊源之所得,子得之父,弟得之师是也。第气象之闲雅流润,合中正和平之道者,南宗尚矣。” 地域并非不可跨越的因素,尤其在交通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日。南方画家寓居北方,西部画家定居东南沿海的情况十分常见,地域文化间的交融互渗是愈发需要重视的现象。未能充分认识到此点,就容易陷入一叶障目、刻舟求剑的尴尬。
其四,地域美术研究的“主流皈依”情结。尤其在当代美术史与美术现象研究上,这一情结与文化权力与美术史研究的话语权有关。面对现当代中国的地方画派,一些学者与批评家试图通过推广某一地域的艺术家、画派来进入美术史的主流叙事。这种趋向的结果是,相关研究片面地回避地域性特征,导致了叙述模式与价值标准的趋同。一些本已珍贵的具体研究,一经“升华”,反而失却了它原初的优势和独特味道。这种趋向的另一种表现是,在一些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地域性”作为一种文化策略,以应对无法与主流文化对话的窘迫与尴尬。
今日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已经愈发依赖于各不同学科方法的参入,需要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通力合作。尤其当今日的美术史研究“不再奠基于严格的材料划分和专业分析方法之上,它成为了一个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各种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的交汇之地和互动场所。” 地域美术史就注定成为地域文化的视觉映像及其意义阐释的重要方式,并折射出特定文化群落独有的精神趣味。
(此文发表于《美术研究》2010年第3期)
于洋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主任,副教授,博士
1、(法)列维-斯特劳斯著,王志明译《忧郁的热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57页。
2、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史怡公标点注释本)卷一,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第41页。
3、黄休复撰,何韫若、林孔翼注《益州名画录》,序(虞曹外郎致仕李畋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上海中国画会作为第一个全国性中国画家学术团体,于1931年由贺天健、张幸光、叶恭绰、钱瘦铁、郑午昌等发起,在上海成立;1934年创立《国画月刊》,1935年创办《国画》双月刊。
5、 郑午昌:《中西山水画思想专刊展望》,《国画月刊》第1卷第4期,
6、 北京画院编(邵大箴、李松主编)《20世纪北京绘画史》由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出版;李福顺主编《北京美术史》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7、 参见(德)温克尔曼著,邵大箴编《希腊人的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8、(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9、 (意)文杜里著,迟轲译《西方艺术批评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
10、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自序,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
11、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史怡公标点注释本)卷一,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第41页。
12、巫鸿:《并不纯粹的“美术”》,《读书》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