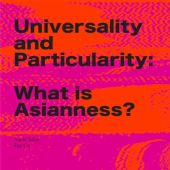“您现在研究的问题是后殖民领域内的问题吗?或是后现代吗?”
“您需要用另一种思维来理解我所研究的问题。”
“那我好像没有办法理解……”
孙歌教授在2019年abC艺术书展的新书发布会上,回忆起她与西方学者讨论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时所产生的对话,依旧十分无奈。基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孙歌教授的研究无疑涉足后殖民、后现代,但在她的论述中,第一步就是试图跳脱并打破这种固有的西方理论体系,再来讨论与重构。但无疑,解构与重构的过程充满了艰涩与迷茫。
由中间美术馆发起,以“为什么‘亚洲’和‘理论’这两个概念的搭配显得格格不入?”这一个问题为起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孙歌教授与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学科讲席教授酒井直树(Naoki Sakai)先生展开了对话,就“亚洲”、“亚洲人“与“亚洲性”等概念,从人类学,社会学与历史学多维度进行了辨析与解读。其对谈收录于《普遍与特殊:何为亚洲性?》一书中, 于2018年出版第一版。2019年,中间美术馆与来自德国柏林的出版社Archive Books合作,分别再版了该书的中、英文版本,于2019年6月的第四届abC书展上发布。
鉴于这本小书的理论性与学术性,为方便引读,我们不妨从中提取一些关键词来展开。
1.“欧洲中心主义”
酒井直树教授在他的个人演讲环节中,从“为什么把亚洲和理论放在一起会让大家觉得奇怪呢?”这个小疑问出发,探讨并批判了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 1871-1945)与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的“欧洲中心主义”式论调。对于胡塞尔等人来说,理论是塑造欧洲精神的一个关键元素,欧洲人需要通过理论作为依靠来进行自我阐释。从人类学意义来说,中国人、印度人、因纽特人与欧洲人被认为存在着“人类学差异”(anthropological difference),然而欧洲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的背景下,面临着一种危机与恐慌,也就是胡塞尔提出的“欧洲人性危机”。为了构建所谓“欧洲人的欧洲人”,法西斯主义的一系列政策使得一些欧洲人愈发难以与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与印度人区分开来。
在20世纪初, 欧洲的国际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支持,但是处于中下阶层的欧洲人由于文化、经济以及知识等方面的缺失,可能远远没有那么自信,这种自信的缺失带来了一种社会广泛的焦虑感。所以当清洗种族制度下“替罪羊”的出现,使得焦虑的欧洲人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战争期间,犹太人被当成了这样一种“替罪羊”。纳粹党出台的《恢复职业公务员职务法案》(Law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意图把反纳粹党和非雅利安人全部清理出公共机构。而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的犹太人胡塞尔无疑被列入此次清理的范围。这种种族清洗的危机与焦虑延伸到了整个欧洲、美洲甚至东亚。这是为何胡塞尔会一再重申所谓欧洲人性的使命是什么,为何他会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和印度永远不可能拥有理论——他被迫失去了自己欧洲人性的资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塞尔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
酒井直树先生认为,胡塞尔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回溯所谓的西方精神和文明的大原则去反对纳粹的具体政策,由此而诞生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他可能自身并不自知。从胡塞尔的例子,酒井直树先生看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即“当一个人被排除共同体之外的时候,他提出抗议的方式恰恰是再去诉诸于这些共同体最早形成时的一些基本原则,来表达他自己的反对。”(P. 88-89)
这是“为什么亚洲不能有理论?”这个讨论的一些历史沿革。将这个问题放在当下公开提出, 看似是可笑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西方学界,依旧存在着“西方”和“非西方”的区别。
除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调,酒井直树先生还反观了“亚洲”这个指称。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 1908-1977)认为指代东方的“东洋”这一概念与西方的“西洋”相对,是缘起于被西方或是欧洲挫败后才产生的自觉。简单来说,如果没有西方通过战争与文化的入侵,东方或者亚洲的概念或许并不存在。那么,关于亚洲的讨论与认识,是否必须借助西方?这种思考让我们每一次在试图复活亚洲这一概念时,总是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关于东洋也好,亚洲也好的知识,不在我们自己这儿,而在西方那儿。
2. 普遍性与特殊性
普遍性是我们常常会用到的一个词,也在逐渐被转化为一种评价标准。何为普遍性?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总结无数特殊性而抽象出来的普世价值?不论作何理解,现在看来,普遍性是一种抽象的一般规律。而特殊性又是什么?似乎从很久以前开始,特殊性就被哲学家处理成与普遍性相二元对立的一个词。有一个很流行的行为叫做“从特殊性当中提炼普遍性”,这种行为无疑是将普遍性的地位抬得很高,因为这样的普遍性被赋予了能够涵盖一切规律的抽象价值。
孙歌教授的观点是从重新审视所谓“普遍性的价值”开始。普遍性在被赋予价值之前,其实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概括能力,这无疑是人类生存发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当概括这件事情被价值化之后,所谓的普遍性价值就不再是概括,它变成了一种霸权性叙述。”(P. 57)这是一种偷换概念式的做法,因为其放大了人类文明中的一个小部分,意图用以作为适用于整个人类的价值。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调就可以被解释成这样一种“普遍性”。
于是,在今天我们呼吁着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时,我们最终期待着怎样的结果?是期待新的普遍性叙述逐渐取代欧美旧有的普遍性叙述吗?这是孙歌教授在思考的问题。如果只是一个地域文明的话语权强过另一个地域,以此来更替旧有的霸权叙述,这其实仅仅是不同文化霸权的无限循环而已。
因而一种新的普遍性价值被孙歌教授提出。而第一步,是需要“相对化”原有的普遍性,不是取代,不是否定,而是尊重它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而将其相对化。新的普遍性应当作为一种不完整的媒介,它依附于不同的特殊性使自己获得价值,普遍性的价值在这里只是为了将人们引导到不同的特殊性里面,从而理解不同的特殊性本身,它应当使特殊性开放。具体到人类文明中来看,新的普遍性应当使得每一种文明向互相开放。
竹内好的很多观点谈到了人和文化的等质性,这一点可以理解为,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存在的价值都是相等的,这一点可以被抽象化的普遍性价值所证明——如果某一种文明能够被抽象出适用于全人类的法则,那么任意一种文明都可以被提炼出这样的法则。然而等质却不等同于均质,我们还需认识到的是人与文化的多样性。新的普遍性提出的价值在于,它不会将所有的多样性强制均质化,而是引导进入多样的特殊性。
这种新的普遍性,似乎颇有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意味,这也是为什么孙歌教授将它称为一种“形而下”的理论。她谈到,习惯于西方理论形态的人很难理解形而下之理,因为“形而下”则必将涉及具体经验,这种不能从中抽象出概念的观点,则不能称之为理论思维。这也是为何孙歌教授一直强调着走出固有思维模式的重要意义所在。
3. 亚洲性
孙歌教授在个人演讲部分回应了酒井直树先生对于欧洲中心主义和胡塞尔的理论的评述,谈到胡塞尔对欧洲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抵抗也被限定在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框架内。孙歌教授总结酒井教授所提及的全球知识界认识人类和世界的方式都是基于欧洲中心论这一思维框架,作为弱势的一方,亚洲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些既定的约束。同时,孙歌教授也肯定了其致力于打破欧洲中心论所遗留给我们的预设,去掉以种族为基础的欧洲、亚洲等分类的观点。
有趣的一点是,孙歌教授在认同酒井教授的同时,却强调了“亚洲”存在的必要性。 她提出“亚洲性”而非“亚洲人”的概念,“亚洲性”的思考像是一个流动的集合,它同样开放给非亚洲人。 基于此,此次德国柏林Archive Books出版社的介入就显得尤为有趣了。德国在历史上也有着分裂与被殖民的经历,时至今日,德国的部分地区仍旧保留着殖民者留下的烙印与特征,文化入侵与霸权的问题也随着殖民的历史存在于德国的文明之中。在新版发布会上,孙歌教授亦与Archive Books的编辑保罗•卡弗尼(Paolo Caffoni)进行了对谈。当在柏林的保罗同样对于亚洲性的问题产生兴趣时,他仿佛就进入了孙歌教授谈到的“亚洲性”思考的集合中。同样的,霸权主义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个空间结构,而在这个结构中的人,未必完全都认同这个空间的逻辑。空间是固定的,但是其中的人员是在不停流动的。这种亚洲性的意义在于,让欧美人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思考。
酒井教授一直在解构,而孙歌教授却一直在建构。看似矛盾的行为却并没有相互对立。因为批判永远伴随着永不停歇的解构与重构。在孙歌教授看来,这其实是“同一个行为的两个步骤。”
笔者注意到在观众提问的环节中,很多观众对于孙歌教授阐释的“新的普遍性”充满了疑问。其中有一个问题让人印象很深刻:当人们在谈论构建亚洲的主体性时,其实就是在强调保留一种特殊性。我们可以很哲学、很抽象地去讨论这些问题,但假如把问题展开,会发现每一个特殊性都无限复杂。这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那种抽象的普遍性——我们在有限的时间与精力下,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看似带有话语暴力的东西去规制它,否则我们将会永远陷入到一种特殊性去。那么新的普遍性价值的构建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孙歌教授的回应是,这个问题有一个预设,即特殊性过于复杂琐碎而一定要回到普遍性,才能使我们有立足之地。那我们是否有反问过自己为什么非要这个普遍性?也许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概括,我们的脑中充满的是碎片,所以需要一种归纳。但是归纳之后,这些琐碎的问题就解决了吗?我们面对的本就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而恰恰是这种抽象的讨论才无法处理这些具体问题。因此新的“普遍性”应当是一种媒介,它引导不同的特殊性得以沟通交流,相互开放,那它的使命就完成了,而新的价值共同体也就建立了。
孙歌教授的回答也许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疑问,因为确实,“这个世界其实可以没有中心”在现在,甚至在未来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回答或者说是这个新的普遍性的提出,其真正意义在于突破,在于引导服从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人跳出这个既定框架去思考问题,在于向依旧自豪于民族文明与西方理论的人发出亚洲性地宣告。如同那个抛向孙歌教授的问题背后存在的预设与固定思维,唯有敢于跳出常规思考去反思,新的方向才能被打开。
一场讨论,一本小书,一些问题,提供的其实是新的路径、新的方法与新的视角,只有挣脱开那些不自觉强加于、依附于我们身上的意识形态与文明,我们也许才能更好的立足于历史渊源与思想基础来审视自身,发出声音。
文/周纬萌
图/除特殊标注外,图片来源于中间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