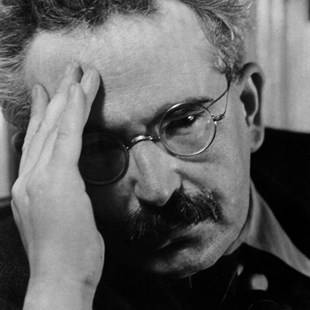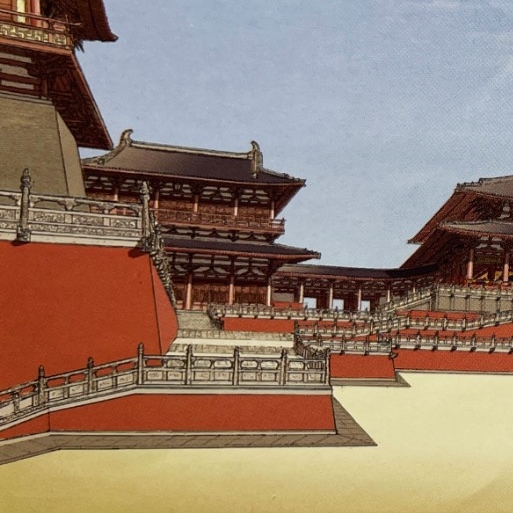关键词:生命政治/ 死亡政治/ 赤裸生命/ 阿甘本/ 福柯
摘要:自然生命一旦政治化,政治就成为生命政治。阿甘本和福柯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生命权力与生命体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阿甘本把自然生命—政治生命、赤裸生命—政治生存这样的二元对立视为整个西方政治基础的原初结构,强调现代政治的关键并非如福柯所说的仅仅是在常态下生命权力对生命体进行算计,而是伴随普遍的例外状态变成常态的进程,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赤裸生命逐渐占据政治领域的核心。“生命政治”实质上就是“死亡政治”。通过概述和论析阿甘本“赤裸生命”、“神圣人”、“极权主义批判”等方面的理论及其与福柯相关思想之间的主要差异,本文得出的结论是:阿甘本并未如他所愿地“矫正”或至少“完成”了福柯的生命政治论题,而是偏离了福柯生命政治的理论轨道,而此种偏离又具有其相应的积极效应和消极后果。
阐发当代生命政治形态相互之间的理论关系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其中各种形态的思想特点,进而把握当代政治哲学的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势意义重大。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福柯、本雅明、阿伦特、施密特、德勒兹、海德格尔等人影响下,在新世纪初阐发了一种新的生命政治。不同于福柯、奈格里对生命权力所持的积极乐观态度,阿甘本基本上对生命权力持消极否定态度。鉴于福柯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都重在历史性分析,划分跨度较大的历史时期(文艺复兴—古典时代—现时代,中世纪—现代—后现代/帝国),阿甘本则提出了侧重于结构探究的生命政治理论。由于阿甘本看到当今世界上所有类型的国家都接连成为居伊•德波(Guy Debord)意义上的“景观国家”和阿兰•巴迪厄(Alain Badiou)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议会制”,当代政治哲学摧毁性地把所有制度与信仰、意识形态与宗教、身份与共同体都分离开来并掏空其内容,以便重复和恢复其明确有效的形式。阿甘本就强调对历史终结的考察必须同对国家终结的探究结合在一起,主张要让一种非国家和非法律的政治学和人类生活来掌控历史性,以揭开国家对历史本原(archē)的遮蔽。①阿甘本虽然原则上赞同福柯的观点:当今时代的关键在于生命,政治也就转变成生命政治,但阿甘本理解这种转变的原因、方式和程度却不同于福柯。鉴于主权者的至高权力始终在生产和决断无处不在的“赤裸生命”(nuda vita,bare life),赤裸生命面对至高权力的生杀大权毫无生存可能性可言,阿甘本要探寻那种不能从中分离出“赤裸生命”却具有种种生存可能性的生命形式(form-of-life)之生命,并确信这种抛弃了赤裸生命的生命形式将成为未来新政治的指引概念和统一中心。阿甘本把那个处于当今已经成为常态之例外状态(state di eccezione,state of exception)之中的生命视为赤裸生命,因为“那个需要既被转变为例外又被包含在城邦之内的最终主体总是赤裸生命”。②在《神圣人》、《无目的之手段》、《例外状态》和《思想潜能》等书中,阿甘本究竟是怎样“修正”甚或“完成”他所说的福柯在20世纪下半叶阐发但未能充分展开的生命政治理论呢?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在哪些方面明显不同于福柯相关思想呢?
一、赤裸生命
在阿甘本看来,在探讨“生命”这个论题时,无论是柏拉图的《斐莱布篇》,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都未曾使用表达简单自然生命意义的词汇zoé,而是使用了表达政治生命意义的词汇bios,区分了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限于家庭的简单生命体(simple vivant)与限于城邦的政治主体(sujet politique)。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一种“政治的动物”(politikon zōon),表明人过着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生活在“快乐与痛苦、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之中。③福柯从亚里士多德这个定义切入,谈论生命政治何以在现代以新的形象崛起:如果说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几千年间,人是具有额外政治生存能力的动物,那么,从现代起,人的生存因其政治和政治策略而遭受危险,自然生命经受国家权力的算计和围困,国家从领土型转变为人口型,国家权力转变为生命权力,现代政治也随之成了生命政治,从此资本主义发展也就得到了政治技术的保障。因为新生命权力通过一系列戒律控制创造了资本主义所需的“驯顺身体”。④
关于身处现代性政治场景的核心,福柯谈论的是“驯顺身体”,阿伦特探讨的是“劳动人”。阿甘本批评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权力的分析缺少生命政治的视角,而福柯的生命政治又从未涉足现代生命政治的典型场所,即“集中营和20世纪大型集权主义国家的结构”。⑤但阿甘本还是高度评价福柯的观点,即自然生命(le zoé)之纳入城邦(la polis)、赤裸生命之政治化,标志着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发生了革命性变革。阿甘本甚至把当今政治发展的颓势归因于人们对这一根本性变革的忽视。于是,阿甘本要在福柯和本雅明的引导下,在生命政治视域内,拷问赤裸生命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及其诸种现代意识形态的理论根源,以期解开诸多历史谜团,使得政治领域变得澄明,使思想回归其实践的召唤。
同时,阿甘本也指出了福柯研究工作的“盲点”:福柯在果断拒斥传统的司法—制度的权力分析模型时,诉诸管治科学的总体化技术和自身技艺的个体化技术这两种截然有别的研究进路,却始终无法在这两个进路的交汇点上聚焦权力问题,他所谓的一种真正的“政治的”双重绑定(现代权力结构的个体化和总体化)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统一中心了。而阿甘本的工作恰恰是要探寻权力的司法—制度模型与权力的生命政治模型之间隐藏着的交汇点,揭露国家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之间的隐秘纽带,并断言把赤裸生命纳入政治领域,从而创造一个生命政治身体,就成了至高权力的原初核心和原初活动。⑥阿甘本由此窥测到现代权力与最古老的国家秘密之间遥相呼应的紧密关系,从而不同于福柯对西方政治史作分段式历史梳理的谱系学分析。
对于赤裸生命与政治权力的紧密关系,福柯认为主要是从现代性开始的,而阿甘本认为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就开始了,因为亚里士多德通过比照自然生命的“美好日子”(euemeria)与政治生命的“巨大困难”而极妙地表述了处于西方政治根基处的难题,而在这之后长达24个世纪之久的岁月里,人们只是对该难题“提供了各种暂时性的和无效的解决方案”,仍以例外的形式把赤裸生命纳入政治之中,未能修复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之间本可修复的断裂。⑦阿甘本看到亚里士多德那个定义已表明赤裸生命隐含在政治上有质量的生活中了,并进一步追问:为何西方政治首先通过排除赤裸生命来构建自己?从古希腊以来,卓越的形而上学使命就是必须永远把赤裸生命政治化,通过排除赤裸生命来确立人之城,而赤裸生命通过被排除在外的方式(作为城邦内部的一个例外)而居住在城邦内。自然生命/政治生命、赤裸生命/政治生存,就成了西方政治根基性的二元对立范畴。现代性延续着这个使命,“现代性只不过宣告了自己对这个形而上学传统根本结构的忠诚”⑧,不断上演着赤裸生命被政治化的大戏。就医生、科学家与至高统治者在共同的领域内对赤裸生命进行决断而言,生命政治视域可界定现代性的特点。通过排除和纳入,现代性不断地在自身内生产赤裸生命,当今通过发展旨在消灭贫穷的民主资本主义也不断地把第三世界人口全都变成赤裸生命。⑨显然,阿甘本尤为强调现代与古代在生命政治二元结构上的一致性、同质性和传承性。
阿甘本之所以要“矫正”或至少“完成”福柯主义论题,是因为阿甘本认为现代政治的根本特征和决定性事实并非是把生命纳入城邦之中,也不仅仅是国家权力对生命进行算计,而是伴随普遍的例外变成常规的进程,原初处于政治领域边缘的赤裸生命领域开始逐渐与政治领域合而为一。⑩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冲突中,赤裸生命既是国家权力训诫的客体,又是政治权力的主体。现代民主既想全力拥护和努力解放自然生命(zoé),又想寻觅自然生命之政治生命(bios of zoé),从而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赤裸生命不仅不能给人以自由和幸福,反而还使人屈从于政治权力。身陷现代民主制困境中的公民就是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神圣人(homo sacer):其生命不能被祭祀,但可以被杀死。(11)阿甘本甚至认为,由托克维尔揭示并被居伊•德波最终确认的现代民主之衰落及其同极权主义国家在诸种后民主的景观社会中之逐渐交汇很可能导源于这一困境:现代民主在历经千辛万苦似乎最终战胜对手并臻于顶峰时刻却无力把生命从史无前例的毁灭中拯救出来,甚至于还成为其最无法和解的敌人的帮凶。(12)由于政治只知道生命这一价值,因此,我们何时能走出这一困境,就何时能彻底清除那种将对赤裸生命的决断转变成最高政治原则的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阿甘本就这样信奉民主与极权主义具有内在协同性的理念,即诉诸鲜血和死亡来把自然生命的“美好日子”赋予公民身份,真正把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关联起来,该理念将可能为一种不再基于排除赤裸生命的新政治之崛起扫清道路。同时,既然大型的国家结构已开始解体,紧急状态已开始成为常态,那么,阿甘本就有可能从生命政治这个新视角切入,来审视国家形式的原初结构及其界限,揭示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缺点恰恰在于没有关注国家形式的原初结构,没有对例外状态予以应有的重视,以至于20世纪的种种革命都撞在国家理论(尤其是例外状态理论)这块暗礁上了。(13)
于是,探究国家形式的原初结构就成了阿甘本生命政治的当务之急。例外是至高统治权的原初结构,至高统治者是例外状态的决断者,是悬置宪法的决断者。至高统治权的暴力通过悬置法律而把无法(anomia)铭刻在约法(nomos)本身之中。从一战、二战至今,至高统治者决断的例外状态“已达到其全球部署的最大值”(14),基于例外状态之双重排除的生命政治机器随时生产着赤裸生命。就重要性而言,施密特的至高统治者之于国家就好比笛卡尔的上帝之于世界。阿甘本认为在施密特所说的“例外状态”中,规范与其实现之间的对立达到最大强度。(15)由法律在例外状态中假定并抛弃的神圣生命,默默地承载着至高统治权,是真正的至高统治主体(sovereign subject,或译为“至高主体”)。(16)阿甘本遵从南希(Jean-Luc Nancy)的建议而进一步把例外关系定性为禁止关系。如果例外是至高统治权的结构,那么,至高统治权就如同施密特所言既不全然是一个政治概念,也不全然是一个司法范畴,也不全然是一个外在于法律的权力,也不是凯尔森(Hans Kelsen)所说的司法秩序的最高规则。(17)至高统治权通过暴力禁止这种例外关系,通过悬置生命而把生命纳入它自身之中,掌控着赤裸生命的生与死。在阿甘本看来,从纳粹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到关塔那摩美军基地中的囚徒,从第三世界的贫穷人口,到发达国家的富裕人士,无论身处法西斯主义制度,还是极权主义制度,还是民主主义制度,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这样的赤裸生命。西方人千辛万苦营造的民族—国家家园对西方人而言仅仅是由自己挖成的死亡陷阱。出于某种政治考量,包括民主国家在内的当代国家都会有意创造出一种常态性的紧急状态,例外状态似乎愈来愈成为当代政治主导性的治理范例。(18)因此,阿甘本呼吁当今社会力量务必要在任何地方打破那个在暴力与法权之间构建起至高统治权的关联,从而把政治哲学建立在摆脱了任何至高统治权与法权之控制的幸福世俗生活之上。
施密特极富创造性且又悖谬地把无法律的例外状态与法律秩序联系在一起。阿甘本利用施密特的至高统治者既在司法秩序之外(拥有宣布例外状态的司法权)又在司法秩序之内(拥有是否完全悬置宪法有效性的决定权)这一至高统治权悖论来说明其例外状态理论。例外是一种排除,可是从规则内部被排除出去的东西,却并不因为被排除而无关于规则。(19)司法政治秩序在行使至高统治权进行排除时通常又把被排除者纳入自己的内部。阿甘本赞同德勒兹和瓜塔利在《千高原》中表达的观点:至高统治权只统治那些它有能力予以内在化到自身中的事物。(20)面对至高统治权的生命,就这样既在司法秩序的内部,又在司法秩序的外部。不难理解:例外是一种纳入性的排除。例外状态逐渐成了常态,这一点被阿甘本视为根本性的政治结构。而作为例外的绝对空间,阿甘本所谈论的集中营,属于军事法的领域,围剿的是赤裸生命,就明显不同于福柯那里作为刑事法领域的监狱,关押的是各种犯人。
二、神圣人
阿甘本称赞本雅明在《对暴力的批判》中发现了赤裸生命与至高权力之间的秘密关联、生命神圣性与法律权力之间的秘密同谋,并探寻生命神圣性这一教条的根源:西方传统徒劳地寻觅其在宇宙论不可穿透性中失去的圣徒。其实,阿甘本发现古希腊不仅忽视生命神圣性原则,而且没有词汇来表达我们赋予了丰富语义的“生命”。尽管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之间的对立对西方政治的起源是决定性的,但该对立还不足以把一种特权或神圣性归于生命。(21)在古代祭祀中,生命本身并不被视为神圣的;只有当生命与其渎神语境、牺牲品与活人世界分隔开来时,才被视作神圣的。无论是本雅明笔下的“赤裸生命”(bare life),还是施密特笔下的“真实生命”(real life),都是被至高统治权力所排除和捕捉的“神圣生命”,也是可以被随意杀死却不准被祭祀的“神圣人”。
阿甘本所说的“神圣人”之所以可被杀死且不得受祭祀,是因为通常是坏人或不洁之人被称作神圣人。“愿其神圣”其实是一个诅咒,被诅咒的人往往是一个被驱逐者、被禁止者、被禁忌者、危险之人、肮脏之人。“sacer”这个拉丁词因兼具“属神”和“被诅咒”这两个对立含义而具有含混性。(22)“神圣人”能被杀死,杀死“神圣人”可不受惩罚,就处在人法之外,处在世俗领域之外;“神圣人”不得受祭祀,就被排除在祭祀之外,就处在神法之外,处在宗教领域之外。这说明我们不能在人法或神法之内来说明“神圣人”。“神圣人”的生命就这样面临暴力的双重例外、双重排除和双重获取。“不能被献祭但可以被杀死的生命,就是神圣生命”。(23)阿甘本要通过“神圣人”来揭示出那个处于神圣与世俗、宗教与司法得以区分之前的原初政治结构(political structure)。(24)至高统治权的政治领域通过双重排除而得以构建。实施这种暴力的至高决断通过在例外状态中悬置法律而把赤裸生命纳入自身之内,神圣人的生命就是被至高禁止所捕获的生命:可被杀死,但不得被献祭。神圣人的身体生动地保障了它可以服从一种死亡权力。至高统治权力(sovereign power)最原初的活动就是要生产出作为自己对立面的赤裸生命,并赋予其神圣性。“实际上,生命的神圣性原本恰好既表达了生命臣服于一个掌控死亡的权力,又表达了生命无可挽回地暴露在弃置关系之中”。(25)阿甘本把至高统治者与神圣人具有的相同结构视为一种对称关系和交互关系:对至高统治者而言,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神圣人;对神圣人来说,所有人都像至高统治者那样在行动。至高统治者的身体与神圣人的身体之间也是一种对称关系:可被杀死,但不可被献祭。路易十四被雅各宾党人斩首证明了其作为神圣人被处死却又不可献祭的赤裸生命特征。至高统治者和神圣人,两者在双重例外、双重排除中合二为一,界定了西方第一个既不同于宗教领域也不同于世俗领域的政治空间。(26)阿甘本由此断定:赤裸生命与至高权力、神圣人与至高统治者的关系要比施密特所说的敌与友、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原初、更为基本、更为紧密。
阿甘本赞同福柯的观点:至高权力的特征性特权之一就是有权利决定人的生与死。“这里,权力首先有捕获的权利:捕获事物、时间、身体以及最终还有生命;该权力在为杀死生命而捕获生命这个特权中臻于顶峰。”(27)作为生杀权的至高权力要求至高统治者在自身内具备可由其权力掌控的赤裸生命。于是,阿甘本认为原初政治要素并不是简单的自然生命,而是暴露在死亡面前的赤裸生命或神圣生命,从而政治生活的首要基础就是一个可被杀死并且因被杀而被政治化的赤裸生命。“神圣生命既非政治生命(bios),也非自然生命(zoē),而是一个此两者在其中通过相互纳入与排除而交互构建的未区分区域。”(28)至高权力对赤裸生命实施的排除和纳入这样的双重暴力从一开始就赋予神圣生命一种醒目的政治性格。
如果说人们往往把公民权利、自由意志、社会契约视为政治领域的关键论题,那么就阿甘本的至高统治论来看,“只有赤裸生命才本真地是政治的”。(29)阿甘本不认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权利让渡说,而接受霍布斯的至高统治者权利论。因为至高权力实际上并不建立在契约之上,而是建立在国家对赤裸生命所实施的排除性纳入之上。通过把自然状态看作一种例外状态,阿甘本认为至高决断直指作为原初政治要素、政治之原初现象的公民生命,这样的公民生命既不是简单的自然的生殖生命,也非有质量的生命形式(bios),而是兽与人之间、自然与文化之间一个无区分的区域。(30)鉴于阿甘本断定原初司法—政治关系是那种把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捆绑在一起的禁止关系,鉴于契约论在不得不面对至高权力问题时只能谴责民主的无能而无法真正思考一种摆脱了国家形式的政治,阿甘本要抛弃所有把原初政治行动视为契约的观点。
从古至今,赤裸生命就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中活生生的知性生命体内。在阿甘本看来,如果说在古代,赤裸生命作为隶属于上帝的生物生命而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在古典世界自然生命明显区别于政治生命,那么,在现时代,“同样的赤裸生命却完全被纳入国家结构之中了,甚至成了国家的合法性和主权的世俗基础”。(31)奠定现代国家基础的,并不是作为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政治主体的人,而首先是人的赤裸生命,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变中被授予至高统治原则的纯粹自然生命。如果看不到自然生命原则与至高统治权原则之统一在至高统治主体的身体之上,那就不可能领会19和20世纪现代国家之民族和生命政治的发展和使命。(32)法国1789年的《权利宣言》原初地标志着自然生命铭刻在民族国家的司法—政治秩序之中。从例外和排除的视角来看,国家就并不是作为一种社会纽带而建立,而是作为为了禁止、为了去除纽带而建立的。把赤裸生命排除在世俗之外而置于家庭与城邦之间的荒无人烟之处,就集中体现了这种去除纽带的举动。阿甘本以为,正是由于禁止关系从一开始就已构建了至高权力的基本结构,福柯所说的现代性之国家政治才有可能变成为生命政治,当代公民才有可能都潜在地成为“神圣人”。(33)阿甘本甚至认为我们公民当下的生命正面对一种史无前例的暴力,周末假期欧洲高速公路上死伤人数要多于一场战争的死伤者就是个明证。
当然,阿甘本强调20世纪最令人骇然的“神圣人”莫过于生活在纳粹主义猖獗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的生命是一种可被杀死却不能被献祭的赤裸生命。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个生命政治运动都把自然生命视为至高决断的典型场所,在由民族主权和权利宣言所开创的生命政治语境中重新界定了人与公民的关系。权利宣言热衷于把自然生命纳入政治生活,把自然生命政治化,不断生产出新的赤裸生命。阿甘本断然否认“大屠杀”这个给灭绝犹太人的纳粹行径套上献祭性光环的语词是一种负责任的历史编纂学用语。因为犹太人不是在大屠杀中被灭绝,而是作为赤裸生命被灭绝。这样的灭绝,既无宗教意义,也无法律意义,而只具生命政治意义。(34)正是在此意义上,阿甘本把纳粹主义政权视为第一个激进生命政治的国家。阿甘本强调公民生命的神圣性与生物性在当代政治中愈来愈重合,以至于我们所有人潜在地都是神圣人(homines sacri)。(35)从古代城邦、中世纪神权国家、近代民族国家,到帝国乃至后帝国时代的国家,每个国家都决定了谁会是“神圣人”。“赤裸生命不再局限于一个特殊地方或一个确定的范畴。它存在于每个活生生存在的生物躯体中。”(36)捕获、决断神圣人之赤裸生命的至高权力实施着极权主义暴力。
三、极权主义批判
阿甘本认识到极权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就是把生命政治化,于是把集中营视为现代生命政治的范本、已实现的最绝对的生命政治空间,进而在一定意义上把集中营看作“我们仍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空间的隐秘矩阵和约法(nomos)”。(37)鉴于集中营诞生于例外状态和戒严法,集中营的司法—政治结构就集中体现了生命政治的至高权力结构。在集中营里,作为至高权力基础的决断之可能性,例外状态得到了正常实现,例外与常规、法律与事实、合法与非法之间的任何区分都已毫无意义,政治已成了生命政治,公民已成了神圣人。“集中营是一个当例外状态开始变成规则时会被开启的空间。”(38)作为现代性关键标记的政治空间,不断出现的集中营现在安稳地驻扎在城市内部,是地球上的新生命政治约法。阿甘本充分肯定福柯和阿伦特对现时代的政治问题作了很可能是最为深入的思考,但又认为此种政治问题很棘手以至于福柯和阿伦特的理论都有失偏颇。于是,阿甘本要致力于通过“赤裸生命”或“神圣生命”这个概念透镜研究政治与生命的紧密交织关系,把福柯与阿伦特的理论洞见聚焦在一起。鉴于福柯的生命政治探讨权力机制对人的自然生命进行的算计以及人的反抗,阿甘本指责福柯直到最后仍在考察人之主体化/屈从化的种种过程(人在把自身构建为主体的同时又屈从于外部权力),而令人失望地没有把其生命政治理论应用于20世纪大型极权主义国家的集中营。“福柯的探究起始于对医院与监狱的大紧闭的一个重构,却未能终止于对集中营的一个分析。”(39)而阿伦特虽然致力于研究二战后极权主义国家和集中营的同构问题,但缺乏任何生命政治的视角,因而看不到现代政治从生命政治向极权主义政治的转变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阿甘本认为,只要我们在生命政治维度内把生物性生命及其需求视为决定性的政治事实,我们就易于理解何以20世纪议会民主能与20世纪极权主义制度进行快速互换,这决定于何者最适合于照料、控制和利用赤裸生命;由此,在左翼与右翼、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公与私这些传统的政治区分都失去其理论意义的前提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以种种新法西斯主义会在欧洲复活。(40)现代民主与现代极权主义存在高度亲缘性,是因为现代欧洲民主是用自然生命(zoē)而非政治生命(bios)来对抗专制主义,现代民主要展现和主张的正是身体(corpus),人的赤裸生命,而非人的自由和特权。“身体是一个双面存在:既承载了对至高权力的屈从,又承载了种种个人自由。”(41)在政治思考中,身体总是与赤裸生命紧紧绑在一起。阿甘本认同霍布斯在《论公民》中对身体的理解:杀死身体这个绝对能力,既构建了人们的自然平等,又构建了西方新的政治身体、政治共同体(Commonwealth)。(42)
阿甘本拓展了当代生命政治的领域,强调在当今时代对生命的决断与对死亡的决断、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之间不再有一条稳定的明确的分界线,政治生活领域不断在向外拓展,至高统治者与法学家、医生、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牧师等愈来愈紧密相连,以至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只有在其所属的共同生命政治(或死亡政治)语境中才具有其真正的意义,而完全建立在例外状态之上的集中营也将在该语境中显现为现代性政治空间之被隐藏的范例。作为第一个激进生命政治国家,纳粹德国不能不提出安乐死这个绝对现代的问题,至高权力通常会以人道主义为幌子对“赤裸生命”这种“不配活的生命”进行决断,决断生命是否有价值,于是,“安乐死标志着生命政治必定转变为死亡政治的那个转折点”。(43)现代生命政治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医学与政治、医生与至高统治者的高度整合和角色互换,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家社会主义抹去了基于优生学的管治与政治之间的差异,在灭绝犹太人的生命政治举动中,管治与政治、优生学动机与纳粹意识形态动机、照料民众健康与对敌作战这两者之间毫无区别。(44)原本分离的政治与生命,一旦具有实质性关联而非工具性关联,任何生命就都成了神圣,任何政治就都成了例外。现代生命政治的新奇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生物存在直接就是政治存在、政治领域直接就是生物领域。政治与生命直接合二为一,生命在其事实性(facticity)中直接就是政治的,20世纪极权主义正是建立在生命与政治的动态合一基础之上。
鉴于列维纳斯与罗森茨威格都认为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巨大新意都在于其果断地扎根于事实性境遇(situazione fattizia)(45)之中,阿甘本就主张我们只有在生命政治的视域内才能充分理解纳粹主义,才有可能弄清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重要关系。其实,在阿甘本看来,列维纳斯早在1934年就已强调海德格尔基本存在论与希特勒思想之间的诸多类似之处,确信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处在西方哲学本身、尤其是海德格尔存在论之中。当然,阿甘本道出了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根本差别:纳粹主义从生物学和优生学出发来决断神圣人的赤裸生命,使得生命政治不断变成死亡政治,集中营不断变成绝对政治空间,而海德格尔“神圣人”却反而自动成了作为“在世中存在的”此在,其间没有任何至高权力可以从中分离出并加以控制的赤裸生命。(46)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海德格尔指责国家社会主义错误地把事实性生命的体验转变成了一种生物性价值。
总之,阿甘本在《神圣人》中提出了三个论点:首先,认为原初政治关系是通过双重排除、双重例外来实施的禁止,从而质疑了国家权力的契约起源论;其次,主张至高权力的根本活动就是生产出那抹去了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自然与文化、神圣人与公民之间差异的、作为原初政治要素的赤裸生命,西方政治一开始就是生命政治,从而质疑了政治自由的公民权利说;再次,强调当今西方根本性的政治范例是集中营,而非城市,从而质疑了种种无视20世纪大型极权主义国家的至高权力和至高禁止对赤裸生命之生死进行决断的空间理论。(47)
至高权力掌控生命,生命直面至高权力;权力成为生命权力,政治成为生命政治。如果说福柯和德勒兹兼顾到权力的管治与生命的抵抗这两个方面,阿甘本则更侧重于至高权力的暴力和赤裸生命相应的屈从,指责福柯和德勒兹并未清晰地定义“生命”。但无论如何,阿甘本还是在《思想潜能》中断言作为福柯和德勒兹思想遗产的“生命”(vita)概念必将构成即将来临中的哲学之主题,并将证明“生命”不是一个医学—科学概念(una nozione medico-scientifica),而是一个哲学—政治—神学概念(un concetto filosofico-politico-teologico)。(48)从整体上说,福柯主要是从积极方面来探究生命政治在富国强民上的建设性成就,而阿甘本主要是从消极方面来揭露生命政治决断赤裸生命之生死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阿甘本比福柯更加谨慎,福柯不认同现代性能在陷于权力展布中的性之中发现自己的秘密并得到解放,他期待一种不同的关于身体和快感的经济学,阿甘本则强调同样已然陷于权力展布之中的身体始终是无力抗拒至高权力的“赤裸生命”了。虽然福柯关注“生命权力”,阿甘本聚焦“至高权力”,但他们在审视西方政治空间时却都有一个聚焦点: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私人生命与政治存在、生物性身体与政治性身体之间没有区分(阿甘本);我们既是动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政治中成问题,我们也是公民,我们的政治在我们的自然身体中成问题了(福柯)。
四、福柯与阿甘本思想间的关系
在生命政治问题上,虽然阿甘本与福柯一样都聚焦于“生命”概念及其与“权力”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考虑到从古至今的整个西方政治的至高权力借助法律暴力来捕获、围剿甚至杀死赤裸生命这一事实,阿甘本确信:应该采取的唯一真正的政治行动,就是切断暴力与法律之连接的行动,解除在例外状态中被绑定的法律与生命关系的纽带;我们具有的基于种种生存可能性的生命—形式(form-of-life)能成为政治的引导和统一力量,并能在生命政治的特定境遇中来防备针对赤裸生命的至高权力,从而弘扬我们的生命—形式的强力。为此,阿甘本通过探究修道(monasticism)范例来构建生命(vita)与规则(regula)之间的复杂辩证法,并强调生命从未是受法律控制的财产。(49)与阿甘本不同,福柯认为国家理由在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限制原则:在18世纪中期之前,实施在个体肉体上的训诫权力把法律作为国家统治理由的外部限制原则,而在18世纪中期之后,实施在整体人口上的生命权力则把政治经济学当作国家治理理由的内部限制原则(50),从而在自由主义框架下治理整体人口。于是,福柯把如何恰当把握国家治理与生命体自由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视为最要紧的政治使命。
第二,福柯把生命政治的诞生定位于18世纪末,强调尽管生命权力与至高权力(或训诫权力)始终纠缠得难解难分,但生命权力毕竟是独特的现代机制,而阿甘本认为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都是生命政治史,并把生命权力视为至高权力的核心而处于至高权力的原初结构之中。福柯虽然认为至高权力与调控权、法律与政治经济学是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关系,但主张从18世纪末起生命权力的历史—政治图式已取代以往至高权力的法律—哲学图式而主导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而阿甘本则不加区分地用法律图式和例外状态理论来探讨整个西方至高权力机制的运行。也就是说,阿甘本并不认同福柯所说的19世纪政治权力发生了重大转型,即政治权力从掌握个体身体之生杀大权的至高主权(或训诫权力)转向调控人口整体生存的生命权力,而是认为超历史的旨在隔离和决断生命的至高统治权从古到今一直起着压抑生命的作用。虽然福柯的“训诫”身体和阿甘本的“赤裸生命”都是司法规章的建构,但福柯因发现传统的至高权力和司法模式不能解答整体人口的生命、身体、健康、幸福等问题而诉诸生命权力和政治—历史模式,阿甘本则认为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社会的至高权力都只是以危机形式向主权结构敞开,阿甘本就未能像福柯那样聚焦权力机制的多样性和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发生的重大历史转型。
第三,福柯探讨生命的治理问题不能不说有先见之明,而阿甘本更是预言生命将是未来哲学的核心概念,只不过相比于福柯对生命及其相关问题的聚焦,阿甘本更加关注的是生命在国家权力机器面前的“赤裸性”。阿甘本与福柯一样,询问生命政治的主体性问题,揭露现代国家和主体本身联手在实施去主体化和再主体化过程中、去除身份认同和再获身份认同过程中所造成的危险后果:个体陷于主体化和屈从化的无限过程而不能自拔。但阿甘本发现在晚期福柯的呵护自身与解放自身之间存在悖谬之处:生活的艺术无须身份认同。那么自身的实践如何能在解放自身的同时获得自身认同呢?因此,阿甘本认为难以把握福柯所说的去主体化和再主体化这个无限的双重运动,转而关注和界定主体化和去主体化、身份认同与去身份认同之间那个新生命政治领域。阿甘本并不像福柯那样坚守那个主体化同时也是屈从化的无限过程,而只是主张在战略或策略框架内成为一个主体,关注生命身体与政治身体之间的模糊地带,关注各种个体与国家组织之间的斗争。即使是这种斗争,也属于个体抵抗性质的,而非革命。面对连贯一致的、成建制的、进攻性的生命政治机器的权力捕获,阿甘本给出的应对措施却是让赤裸生命期待一种不连贯的、分散的、逃避性的政治。尽管阿甘本强调这种“逃避”是德勒兹“逃逸线”意义上的并不逃往别处的逃离,主张把个体对至高权力的抵抗与集体阶级的革命行动结合起来、个人原则与非个人原则共存,但又向世人展现出人类面对世界极权主义猖獗、战争阴影的普遍威胁而深感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至于阿甘本所作的“仅仅在战略或战术框架内成为主体”、“主体介于意识主体和国家权力之间”这样的辩解,即使不是悲观主义,也至少是徘徊在悲观主义的边缘了。
第四,福柯起先关注以往那些基于至高统治权并借助训戒来监视和矫正个体身体的权力技术,后来又聚焦于从18世纪末起针对人口及其相关项所实施的生命权力,强调生命政治诞生于整体人口作为治理对象之时。阿甘本则主张现代生命政治在其前现代至高权力那里有坚实的基础和原初的结构,并通过重新引入施加在赤裸生命上的至高权力而把福柯思想向前向后伸展到整个人类历史。由于这种“赤裸生命”因受双重排斥而被排除在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之外,既不受法律保护,也得不到宗教呵护,所以随时都可能一命呜呼。于是,阿甘本所说的生命政治实质上是死亡政治。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潜在地是赤裸生命,那么,当至高权力针对生命的决断转变成针对死亡的权力时,当神圣人成了活死人时,生命政治由此翻转成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que)。其实,福柯的“生命政治”早就预示了阿甘本的“死亡政治”。福柯在《知识意志》中指出,从古典时期起,西方世界不仅让人活的权力发生了变化,让人死的权力也起了变化。死亡权力成了对积极管理、扶植、调控生命的权力的补充。以必须保护民众的生存为幌子,19世纪以来的血腥战争都表明现代国家的生命权力史无前例地煽动民众相互残杀。把一部分人置于一个普遍死亡的危险境地,以保障与维护另一部分人生存,这前一种权力是后一种权力的背面。“因为权力是在生命、人类、种族和大规模人口现象的层面上进行自我定位和运作的。”(51)福柯早已发现在人口被国家生命权力特别关注之时恰恰就是人口面临灭顶之灾之时。然而,生命政治是否实际上成了死亡政治呢?人们对之应该消极逃避,还是积极部署?如果把死亡政治视为现代性之技术统治的结果,那么,无论是福柯,还是阿甘本,还是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显然都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不过,不同于阿甘本面对现代生命权力而表现出来的渺茫的“无望者的希望”,福柯晚年的自身呵护思想、德勒兹的欲望机器理论以及斯洛特戴克的“免疫生命政治”(Immunitary Biopolitics)理论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积极的生命政治,从而扭转了工具理性批判必然转向“死亡政治”的倾向。因此,笔者完全认同坎贝尔(52)的期待:期待一种不是通过死亡(thanatos)而被思考、而是通过生命(bíos)而被实践的积极乐观的权力技术(technē)。
第五,虽然福柯强调诉诸对集中营的分析来分析社会保障体系和行政机构这样的做法会淡化理论分析的独特性(53),但福柯也并非像阿甘本所指责的那样没有从生命政治视角来探讨20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治,而是主张不应从国家的内在发展及其机制方面、不应从国家治理术角度,而应从政党治理术视域来探寻极权体制的本源(54),从而否定神权国家、行政国家、官僚国家、法西斯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国家之间具有相同的形式和根源。虽然政党治理术的强化和自由主义治理术都会导致国家治理术的弱化,但种族主义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理论源头只能是政党治理术,政党治理术的生命权力甚至比至高权力更会大肆杀戮,纳粹主义已经实施了这种先以净化人种为名来疯狂灭绝犹太人而最终导致自我毁灭的生命权力。
福柯认为生命政治是在自由主义框架下崛起的,考察处于规范状态下的生命权力之治理术、国家治理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动态平衡旨在实现国强民富的最高目标,因而,福柯的生命政治具有积极的、生产的和建设性效应;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却是在至高主权主义的原初结构中诞生的,考察处于例外状态下的主权论,至高权力掌控赤裸生命的生杀大权,因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更多体现出消极的、压抑的和摧毁性效应,尽管阿甘本辩解生命政治机器的去主体化并非单纯地毁灭任何主体性,而是还有多产而诗意的功能。
总之,如果说“校正”意味着把前人有偏差的研究方向扳回正道或把有悖谬之处的见解改正过来,如果“完成”是指把前人未竟事业继续下去或不圆满的事业做成圆满,那么,无论对生命政治之基础和性质的理解,还是对主权者至高权力及其法律图式的态度,无论是对何种权力实施抵抗和批判,还是对整个西方权力机制之结构与历史关系的探究,阿甘本与福柯思想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理论分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庶几可以说,阿甘本的工作并非像他所说的是为了“校正”和“完成”福柯论题,而根本上是在“生命政治”名义下,偏离福柯生命政治研究的轨道,甚至还逆向而动,另起炉灶,自成一说。
因此,笔者既不认同拉比诺(Paul Rabinow)和罗斯(Nikolas Rose)所言阿甘本和奈格里对“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这两个福柯术语所作的划时代哲学部署是误导性的(55),也不赞同米尔斯(56)(Catherine Mills)和其他学者所说“例外”和“常态”甚至“结构”和“历史”的互补甚或综合就能把阿甘本与福柯两人的生命政治学说整合在一起,就可完整地描绘现代西方政治的理论和实践。笔者以为,阿甘本此种“偏离”的积极成果,是重新找回了被福柯弃置的用于权力分析的法律话语和法律图式,试图一以贯之地把聚焦于例外状态并隔离、捕获生命体的至高权力视为内含于人类政治共同体的原初暴力,恢复甚至凸显被福柯权力谱系学所贬损的国家这个至高主权者具有的重要地位,从而进一步把生命政治发展为国家政治。此种偏离的消极成果,就是无视生命政治机器的权力机制的历史演变和权力机制的多样性,尤其是否认福柯所说的“西方世界从古典时期起经历了这些权力机制的一次深刻转型”(57),看不到至高权力与生命权力在相互纠缠的同时还有随着具体境遇的变化而呈现出此消彼长的主导性实施及其所遭遇的具体抵抗问题,夸大了国家主权者在“例外状态”中隔离、弃置和决断赤裸生命的极权主义行为,把仅仅适用于20世纪极权主义的国家主权论普遍化,推广到从古至今的整个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和实践。然而,无论如何,阿甘本不像福柯那样把生命政治视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物,而是向前、向后从两个方向拓展了福柯生命政治领域,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研究国家治理与个人自由之间关系问题上提供了虽有争议但富有建设性的视角。
注释:
①Giorgio Agamben,Means Without End,Notes on Politic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 108-111.
②Ibid.,p.6.
③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98) 9-10.
④Ibid.,p.10.
⑤Ibid.
⑥Ibid.,p.11.
⑦Ibid.,p.13.
⑧Ibid.,p.12.
⑨Ibid.,p.101.
⑩Ibid.,p.12.
(11)Ibid.,p.13.
(12)Ibid.
(13)Ibid.,p.14.
(14)Giorgio Agamben,State of Excep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87.
(15)Ibid.,p.36.
(16)Giorgio Agamben,Means Without End,Notes on Politic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 112.
(17)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98) 23.
(18)Giorgio Agamben,State of Excep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2.
(19)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98) 18.
(20)Ibid.
(21)Ibid.,p.42.
(22)Ibid.,pp.50-51.
(23)Ibid.,p.52.
(24)Ibid.,p.48.
(25)Ibid.,p.53.
(26)Ibid.
(27)Michel Foucault,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La volonté de savoir( Gallimard,Paris,1976) 179.
(28)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98) 56.
(29)Ibid.,p.64.
(30)Ibid.,p.65.
(31)Ibid.,p.75.
(32)Ibid.,p.76.
(33)Ibid.,p.66.
(34)Ibid.,p.68.
(35)Ibid.
(36)Ibid.,p.81.
(37)Ibid.,p.95.
(38)Ibid.,p.96.
(39)Ibid.,p.71.
(40)Ibid.,p.72.
(41)Ibid.,p.73.
(42)Ibid.,p.74.
(43)Ibid.,p.83.
(44)Ibid.,p.85.
(45)Giorgio Agamben,La Potenza del Pensiero(Neri Pozza editore,Milano,2005) 324.
(46)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98) 88.
(47)Ibid.,p.102.
(48)Giorgio Agamben,La Potenza del Pensiero(Neri Pozza editore,Milano,2005) 402-403.
(49)Giorgio Agamben,The Highest Poverty: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xiii.
(50)Michel Foucault,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8-1979),(Gallimard/Seuil,Paris) 3-25.
(51)Michel Foucault,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La volonté de savoir( Gallimard,Paris,1976) 180.
(52)Timothy C.Campbell,Improper Life:Technology and Biopolitics from Heidegger to Agambe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1).
(53)Michel Foucault,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8-1979),(Gallimard/Senil,Paris) 193.
(54)Ibid.pp.196-197.
(55)Paul Rabinow,and Nikolas Rose,Biopower Today, BioSocieties 1.198(2006).
(56)Catherine Mills,Biopolitics,Liberal Eugenics,and Nihilism, eds.Matthew Calarco and Steven
DeCaroli,Giorgio Agamben:Sovereignty and Lif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57)Michel Foucault,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La volonté de savoir( Gallimard,Paris,1976) 179.
作者:莫伟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017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