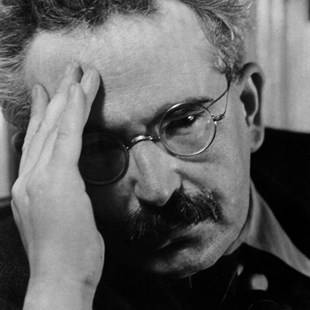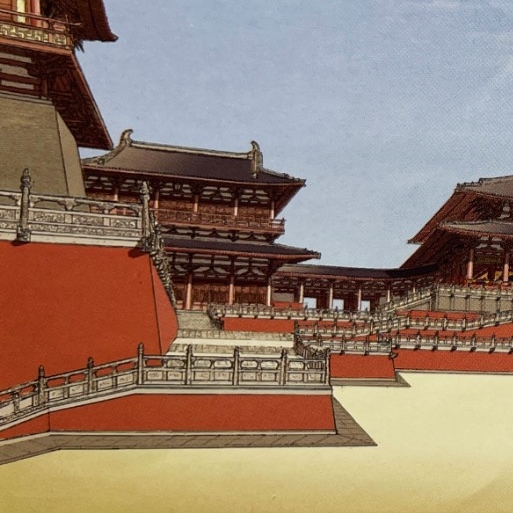艺术批评:没有读者的写作
艺术批评正处于一种全球性的危机之中。它的声音已经变得极为微弱,并且已经消融在短暂的文化批评背景中。但是它的衰落的推论并非实践的山穷水尽,而是与此同时,艺术批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健康。它正在蒸蒸日上:它吸引了大量的作者,并常常得益于高质量的彩色印刷和全球性发行。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批评正在蓬勃发展,但在无形之中,它在当代理论辩论的视野之外。所以它生命力微弱,但又无处不在。它被人们忽视,但其背后仍有市场。
我们没有办法衡量当代视觉艺术写作到底有多少。画廊几乎总是尝试为每个展览至少制作一张卡纸,如果有能力印制一份四页的小册子(通常是由一张硬卡纸制成,中间对折),那么通常还会包括一篇论述艺术家的短文。如果再讲究一些,就还会收录一篇或若干篇文章。画廊还会将螺旋装订的文件与本地报纸和时尚艺术杂志的剪报与影印件放在一起,画廊老板还会很乐意将这些文件复印给任何提出相关需求的人。如果午后在欧洲、北美、南美或东南亚城市的画廊区漫步,你可以迅速收集到一大堆展览册。每一本都印刷精美,开篇的文章都至少有100字。同时,时尚艺术杂志的庞大数量也正迅速增长,虽然从企业经营者的角度来看,这种市场的风险很大。书店中大量的杂志陈列,例如图书零售商伊森(Eason’s)和鲍德斯(Borders)有数十本艺术杂志陈列,在博物馆附近的报摊和大学书店也有艺术杂志。没有人知道艺术杂志究竟有多少,因为大多数图书馆和艺术数据库认为这些杂志都是暂时性的,因此没有被收集或编入索引。艺术杂志的数量太多了,我认识的人甚至都试图去持续追踪。通常,学院派的艺术史学家根本不会去读这些杂志。粗略估计,在欧洲和美国,大概有200本国内外发行的艺术杂志,大约有500到1000本小型的杂志、传单和期刊。没人知道每年究竟印有多少展览册,因为没人知道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画廊。在纽约、巴黎和柏林等大城市都有年度画廊指南,但这并不齐全且没有明确的画廊清单。据我所知,除了高端艺术市场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图书馆会收集画廊印制的东西。当地和国家图书馆会收集报纸,但在我所知的任何数据库中,报纸上的艺术批评都不是一个科目词,所以发表在报纸上的艺术批评很快就变得难以获取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批评确实非常健康,健康得甚至超过了任何读者能读到的数量。即使在中型城市,艺术史家也不可能读到报纸上、博物馆或画廊里登载的所有东西。然而与此同时,如果对健康的衡量是通过认真对待它的人数,或通过与艺术史、艺术教育或美学等邻近类型写作中相互作用的程度来确认,那么艺术批评又几乎已是奄奄一息。艺术批评是大批量产生的,同时也被大批量地忽视。
我自己所在的艺术史领域里,学者们往往倾向于阅读具有丰富历史信息、同时又有一定学术背景的批评:主要指由艺术史期刊和大学出版社所发表的有关当代艺术的论述。专门研究现当代艺术的艺术史学家虽然也会阅读例如《艺术论坛》(Artforum)、《艺术新闻》(ArtNews)、《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和其他一些期刊(数量和刊名不定),但他们倾向于不引用这些论文的来源(尽管一些史学家为这些期刊撰稿,但也很少引用其中的文章)。唐纳德·库斯比特(Donald Kuspit)的《艺术评论》(Art Criticism)是一本外围杂志,尽管原则上应该引起任何批评家的兴趣,但发行量却很小。其余的一些杂志内容较含混,例如《艺术报》(Art Papers)、《帕克》(Parkett)、《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绝佳主题》(Tema Celeste)、《艺术月刊》(Art Monthly)、《艺术问题》(Art Issues)、《艺术快讯》(Flas h Art)、《艺术文献》(Documents sur l’art)等。这份艺术清单逐渐融化成光鲜亮丽的杂志群,在学院内部也少有人问津,如《艺术评论》(Revue de I’art)、《艺术世界》(Univers des Arts)、《玻璃》(Glass)、《美国艺术家》(American Artist)、《西南艺术》(Southwest Art),艺术史学家们通常对这些杂志并不了解。同样,艺术史学家对报纸上艺术批评的认识可以说是一致的:它是一种指南,但绝不是可引用的对象,除非史学家的课题是某位在大众媒体上有接受度的艺术家。如果一位来自火星的人类学家想通过阅读而不是常去画廊来研究当代艺术,那么似乎图录文章和刊登于报纸上的艺术评论文章根本不存在。
那么艺术评论和图录文章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让人们走进画廊,并促使他们购买吗?也许是的。但就图录文章而言,其经济效应似乎并不取决于实际阅读的内容。通常,手头上有一本制作精良的小册子或作品图录就足以说服顾客购买了。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艺术批评是否会影响艺术市场,除非在一些重要的情况下,当围绕艺术家展览的嗡嗡评论声肯定会提高观众的出席率和价格时。以我的经验,除了在特殊情况下,即使是知名报纸的艺术评论家也只会收到少量信件。在互联网上也发生着同样的情况,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过去了,电子杂志和电子邮件中的文本,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被人阅读过,而那些有争议性的内容也使电子邮件泛滥成灾。
简而言之,这就是艺术批评的现状: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但也前所未有地几乎完全被忽视。它的读者群是未知的、无法估量的,并且短暂地令人不安。如果我在画廊里拿起一本小册子,我可能会花足够长的时间来浏览文章,寻找一些关键词,也许这件作品被说成是“重要的”“严肃的”或“拉康主义的”,然后我对其兴趣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在上火车前有多余的时间,我可能会在报摊上翻阅一本时尚艺术杂志。如果我要坐长途飞机,我可能会买几本杂志,打算看完后把它们留在飞机上。当我到访一个陌生的城市时,我会阅读当地报纸上的艺术评论文章。但我不太可能(除非我正在研究这本书)仔细或是带有兴趣地研究这些文本:我不会标记我赞同或有争议的段落,也不会把它们保存起来以供进一步参考。因为它们对于一顿饭来说不够可口:或是轻飘飘的,或是循规蹈矩的,或是大量称赞,或是困惑不解,或者只是非常非常司空见惯的。这样的艺术批评就像是透明的纱巾,飘浮在文化对话的微风中,却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安定下来。
这种健康的活力和绝症的结合,无处不在却又隐形不可见,这种结合在每一代人中变得越来越尖锐。20世纪末的画廊数量比世纪初多了许多倍,艺术杂志和展览目录也是如此。虽然报纸上的艺术批评较难衡量,但相对于人口规模而言,报上艺术批评似乎比100年前要来得少。根据尼尔·麦克威廉姆(Neil McWilliam)的说法,1824年,巴黎有20家日报有艺术评论家的专栏,另外还有20篇评论文章和小册子也报道过艺术沙龙展。这些作家中没有一个是以艺术批评家的身份被雇用的,但实际上有些像现在一样是全职的。如今,即使将互联网上的算在内,批评家的数量也大不如从前。因此,报上艺术批评有可能急剧下降,这与电视和广播中当代文化节目缺乏艺术批评的情况是相似的。19世纪早期的一些艺术批评家受到当代哲学家和作家的重视,而其他人(西方艺术批评的创始人)本身就是重要的诗人或哲学家。18世纪哲学家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实际上是艺术批评的奠基人,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也是该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相比之下,可谓是现代主义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的哲学却是一团糟,因为与其说他是从康德那里寻求更多的依据,还不如说是他想自己站出来说话。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他以一种其他作家没有的方式推动了19世纪中叶的法国艺术批评,他当然也是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极为重要的诗人。格林伯格特别擅长写作,而且言之凿凿,但简而言之,他不是波德莱尔。这些比较也许并不像看起来那样不公平,因为它们是艺术批评正在从文化世界中慢慢消失的征兆。那么究竟谁是重要的当代艺术批评家?举足轻重的评论家的名字并不难列举:《纽约时报》的罗伯塔·史密斯(Roberta Smith)和迈克尔·基姆尔曼(Michael Kimmelman),《纽约客》的彼得·施杰尔达(Peter Schjeldahl)。但是在那些没有足够幸运地为超过百万的出版物工作的批评家行列中,谁被认为是当代批评中真正重要的声音呢?我自己感兴趣的作者名单包括:约瑟夫·马什克(Joseph Masheck)、托马斯·麦克埃维利(Thomas McEvilley)、理查德·希夫(Richard Shiff)、柯密特·尚帕(Kermit Champa)、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和道格拉斯·克利姆帕(Douglas Crimp)。但我怀疑他们在其他人眼里是否就是经典,其背后尚有一大串的名字,如戴夫·希基(Dave Hickey)、埃里克·特罗西(Eric Troncy)、彼得·普拉根斯(Peter Plagens)、苏珊·苏雷曼(Susan Suleiman)、佛兰切斯科·波纳米(Francesco Bonami)、金·勒温(Kim Levin)、海伦·莫尔斯沃思(Helen Molesworth)、唐纳德·库斯比特(Donald Kuspit)、布兹·斯佩克特(Buzz Spector)、米拉·肖尔(Mira S chor)、汉-乌尔里克·奥布利斯特(Han-Ulrich Obrist)、米温·夸恩(Miwon Kwon)、杰曼诺·西朗特(Germano Celant)、乔治·维佐蒂(Giorgio Verzotti)等,共100多人。国际艺术批评家协会(AICA)称,其在70多个国家拥有4000多位会员和分支机构。
21世纪初期的美术批评家不一定都是大学科班出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重要,因为几乎没有人接受艺术批评家的训练。大多数艺术史系几乎从不开设艺术批评课程,除非作为艺术史的主题,诸如“从波德莱尔到象征主义的艺术批评史”之类的课程。艺术批评不被认为是艺术史大纲的一部分,因为它不属于历史性的学科,而有点像创造性的写作。当代艺术批评家来自许多不同的背景,但他们也有一种共同的缺失,他们没有像人们接受艺术史学家、哲学家、策展人、电影史学家或文学理论家那样的训练而接受艺术批评家的训练。但我认为这方面的重要性是有限的,仅仅因为一个领域没有学术平台,并不意味着它不严谨,或者对具有正式训练资格的相邻领域的价值观和兴趣不那么依赖。但是缺乏艺术批评的学术实践,意味着艺术批评是不靠谱的,除了一些有趣的例外,比如纽约石溪分校(Stony brook)的项目。偶尔,艺术批评的自由度令人振奋,但对于一个稳定的读者来说,它却令人乏味。在缺乏艺术批评家的情况下,艺术批评家享有崇高自由度的各种原因之一是:它在十几个学科之间突击和佯攻中,缺乏一个艺术学科的家园。我并不是说:如果批评受到保守或固定的教学方法的约束情况会更好;而是,如果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纪律,那么它就会有某种可以反对的中心。目前,艺术评论家们很少感到阻力。为展览画册和图录写文章的评论家会略微受约束,因为他们所期望的作品可能不受欢迎;为大报写稿的批评家也会有所约束,因为公众不易接受新的艺术,也不习惯接受温和的观点。但是与那些缺乏学术归属的艺术批评家所缺乏的束缚相比,那些束缚的来源就微不足道了。 一门学术学科,尽管可能是充满挑战和矛盾的,通常都会给从业者以两方面的压力:一是同行的意识,二是研究的历史感。这辉煌又梦幻的两方面在当前的艺术批评中都是缺乏的。
这就是我对艺术批评所勾勒的图景: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写批评文章,但没有共同的基础。以学术标准衡量,艺术批评涉及的资金数量极大,即使是适度的展览图录也印数可观,封面和图版都很讲究,而这些在学术出版物中是不多见的。即便如此,艺术批评家也很少以写评论为生。大部分为美国重要报刊撰写批评文章的人一年的收入不到25000美金;但成功的专栏批评家每年可以写二三十篇文章,基本稿费为每篇1000美元或每个单词1至2美元,或者每篇短评35至50美元(我自己的情况可能居中,例如1至20页的文章可得到稿费500至4000美元不等)。活跃的批评家会被请去大学做讲演或受邀参观展览,所支付的费用在1000到4000美元之间。刊登在艺术杂志上的文章价格在300到3000美元之间,这些文章既可以用来增加评论家的收入,也可以引来更多的邀请。相比之下,依靠学术吃饭的艺术史家和哲学家可能一生著述等身,却没有什么稿酬。因此,批评比比皆是,有时甚至是名利双全。但它也为其表面上的受欢迎付出了代价,艺术批评对于读者来说成为幽灵一般的存在。批评家很少知道谁会阅读他们的文章,除了画廊委托给他们的艺术家。公众的阅读是幽灵般的,因为它并不存在。所以这是一种幽灵般的职业,为幽灵服务,然而却又风格宏大。
直到20世纪上半叶,艺术批评才大为不同。艺术批评家们可能更为关注艺术史以及批评本身的历史,常常是从大处着眼,比较他们在不同场合下的判断,或考虑他们的立场和其他批评家的立场之间的差异。像罗杰·弗莱(Roger Fry)和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这样的布卢姆斯伯里派(Bloomsbury)评论家认为他们可以置身事外客观地评估历史的大片区域。贝尔的宣言《艺术》贬低一切处于12世纪至塞尚之间的东西,他称文艺复兴为“古怪的新病”,而伦勃朗则既是天才,也是“当时典型的衰败”。在贝尔那一代,判断本身作为一种更广泛的比较,往往颇具一种大而论之的气魄。相形之下,当代批评家却倾向于不想在展览的框框和特定作品本身之外思考,或者宁愿不在框框之外思考。这样做,有时就是对艺术杂志的一种承诺:不胡来,扣紧主题。
20世纪初和20世纪中叶,美国的批评家也受到了激烈的批评,甚至争论不休。在世纪之交,《纽约论坛报》( New York Tribune)顽固的保守派评论家罗耶尔·科尔蒂斯索(Royal Cortissoz)与除马蒂斯(Matisse)之外的所有现代事物进行了斗争。在一代人之后,《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的后卫评论家约翰·卡纳迪(John Canaday)则用一种如今看来颇为怪异的讽刺暴力与抽象表现主义进行了争论。科尔蒂斯索被称为“广场射手”他发现20世纪头20年的大多数的欧洲艺术都“粗糙、古怪、乏味、傲慢”。在1960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卡纳迪评论了他在一面墙上发现的“一摊干枯、结了块的蓝色海报颜料”,假装这是一位名叫宁古诺·德纳达(Ninguno Denada)的画家画的《蓝色元素》(Blue Element)。他写了一篇关于漏油事件的长篇评论,称其“令人印象深刻,深刻地诠释了我们这个世纪的危机”,并把德纳达与现实生活中的画家温蒂·克萨特(Modest Cuixart)、安东尼·塔皮尔斯(Antoni Tapies)和琼·米罗(Joan Miro)进行了比较,然后拒绝他的“讽刺”与“在大学和博物馆里进行的洗脑”之间区分。很难想象如今《纽约时报》的评论家会如此讽刺(与克萨特、塔皮尔斯和米罗的比较是完全不公平的。即使是克萨特最不受控制的画作也会精心绘制叠加的元素。当然,其真正的目标是波洛克)。
这并不是说评论家们变得不那么固执己见了:我所描述的变化有很多原因,稍后我会更具体地解释。但我的意思是评论家们变得不那么野心勃勃了,这里的野心是指想看到艺术实践的景象而不仅是一件明显孤立的事物。在世的艺术评论家中,几乎没人发表过他们对20世纪主要运动的看法。他们更喜欢进行局部的判断而非广泛的判断,而且对时间较近的进行判断也不太合适。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批评家提供非正式的观点或暂时性的想法,他们避免强有力的承诺。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评论家们已经开始完全回避评价,他们更喜欢描述或重现艺术,而不是说出自己的想法。在2002年,哥伦比亚大学“全国艺术新闻项目”的研究发现,美国的艺术批评把对艺术品的判断列为一种最不受欢迎的目标,而最受欢迎的是对艺术品做单纯的描述。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逆转,就好像物理学家宣布说,他们不再对理解宇宙感兴趣,而只是想欣赏宇宙而已。
这种差异的变化是巨大的,我将努力进行详细说明。当艺术批评在世界各地扩散的几十年里,它也从文化批评的前线退到了更安全、更受保护的领域,即本地化的描述和小心翼翼的重现。我绝不是说批评的知识范围已经缩小以适应多元主义、行话和认识论上的闪烁其词,而这些常与学术左派联系在一起。我认为我们不需要重新获得狂热的现代主义批评家们的那种胸毛浓密的健康。诚然,当代艺术批评中最有想法的往往又是极为保守的人士,但我不认为保守主义对批评有益,它也不是批评的恰当的意识形态方向。像希尔顿·克雷默(Hilton Kramer)这样的批评家已与艺术界最有趣的东西相去甚远。部分原因是他们的雄心使他们无法以一种有希望的方式回答当前的问题。但我想继续使用“野心”这个词,因为它给我的印象是20世纪后期之前的批评是如此的引人入胜,既有激情又有丰富的历史内容。而当代的批评却变得如此薄弱,虽然有大量的资助投入,这些资助是隐形的,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无声的实践。
我不禁要问两个问题:第一,将艺术批评单独作为一种实践来讨论是否有意义?或者说,它是不是具有一列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活动?第二,批评的改革是否有意义? 我将以一个乐观的态度来结尾。
[美]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马琳、任真良 译(Translated By Ma Lin, Ren Zhenliang)
原文刊载于《画刊》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