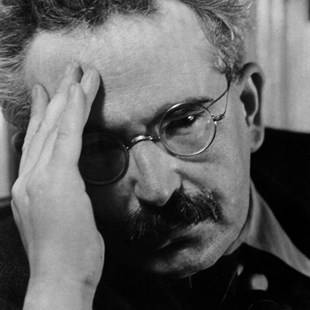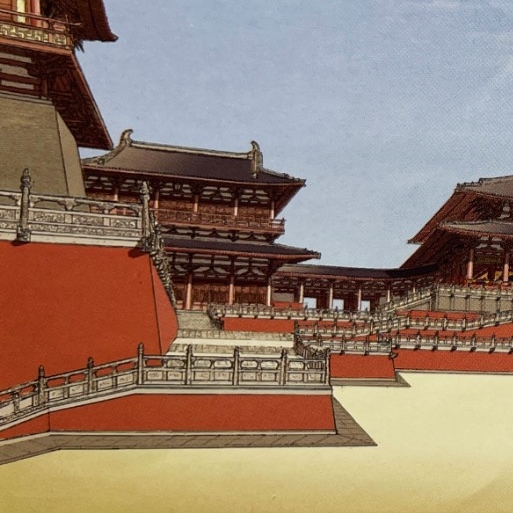如果我要为当下的艺术批评画一幅画,我会把它画成一个海德拉(Hydra) [1]的形象,而且是传统的拥有7颗头的。第一个头代表了受商业画廊委托所写的图录文章(长久以来,这种图录文章都不被认为是艺术批评,因为这些文章总是被期望带有赞扬目的,但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些文章不是艺术批评,那它们又是什么?);第二个头是学术论文,从巴赫金(Bakhtin)到布伯(Buber)和本雅明(Benjamin)到布尔迪厄(Bourdiu),这些文章呈现了一系列晦涩难懂的哲学和文化术语的引用,它们是保守派攻击的共同目标;第三个头是文化批评,在这种评论中,美术和流行图像混合在一起,使得艺术评论只是浓汤中的一种味道;第四个头是保守派的长篇大论,作者在其中宣称艺术应该是什么样的;第五个头是哲学家的论文,作者论证了艺术对某些哲学概念的忠诚或偏离;第六个头是描述性艺术批评,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调查,这是最受欢迎的一种艺术批评,它的目的是热情而不是艺术判断,并以想象力将读者带入他们可能没有看过的艺术品;第七个头是诗意的艺术批评,其中写作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调查,这是艺术批评中第三个最受欢迎的目标,但是我怀疑它也是全行业最广泛使用的目标之一。
以上的说明并不意味着这是海德拉仅有的“头”,或者说这些“头”不能因为其他目的而重新编号。批评家彼得•普拉根斯(Peter Plagens)提出了一种由三部分组成的模式,对于许多作者来说,唯一重要的区分在于学术界和学术界之外的一切之间。这7个头有时候会突然转向,互相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有些时候又似乎会有更多的“头”,或者只是像巴别塔一样的聚集物。但是艺术批评实践的结合能够被想象成为7个或者分离的实践,至少对我而言,将艺术批评进行这样的描述似乎是有用的。
在开始之前,请注意我为7种艺术批评类型而选择的示例。我在这里提到的一些人是我的朋友和熟人,我希望我对他们的评价是平衡的,但是对“批评”的批评是很困难的!它很少被这样做,因此艺术评论并不总是 习惯于文学批评和学术界争辩中常见的那种尖锐的攻击 和回击的过程(除了偶尔会引人发怒的信件,新闻性的 艺术评论通常与辩论相隔离)。无论如何,我的主要兴趣不是我要提到的特定的文本或者作者,而是理解当下视觉艺术如何被描述的一般性问题。
1.图录文章
图录文章是这7种艺术批评中阅读量最小的文章,尽管图录文章的总体数量可以与报纸上的评论数量相当(我在这里谈论的是展览手册中的一般性文章,而不是大型博物馆印刷的书籍中的论文)。图录文章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它们是由画廊委托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实践中,这是一个比看起来更加潜在和微妙的过程,因为我发现撰写图录文章的作者们通常不会想象他们自己被任何一种方式所束缚,他们写自己喜欢的内容,并且他们会十分乐意挖掘作品中的优秀品质。我所认识的评论家并不会因为撰写积极的评论或者避免作出负面的判断而感到压力,而且我被告知这其中并不涉及审查制度。
我自身的经验使我怀疑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我曾经给我的朋友撰写过图录文章,我也接受过画廊和策展人的委托。当我为朋友写文章时,我并不想写任何带贬损的内容,因此整个过程处理得非常平稳。我想那些文章是真实的艺术批评,且恰巧主要是正面的。为我不认识的艺术家、画廊和策展人撰写评论文章则另当别论。一开始,我对画廊主和艺术家希望我修改写好的一部分内容这一事情十分惊讶,好像这篇文章是在餐馆内能够被退掉的一道菜一样。我曾经为我敬佩的一位艺术家,用这样的句子作文章结尾:“一位可爱、过度紧张、令人叹为观止、错综复杂、神秘而悲伤的画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句子,但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位艺术家甚至没有问我是否考虑删掉“悲伤”这个词,她只是简单地将这篇文章从论文中删除了,正如她后来向我解释的那样,她并不悲伤。但是,这篇文章是通过将她与一位18世纪的艺术家相比较而激发了我使用那个词的,我那时候是这样想的,到现在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悲伤”一词确实是合适并且具有启发性的。在其他情况之下,我会与画廊和艺术家之间来回交流,对文章做一点修改,这样听起来更加积极。在我看来,一个复杂而矛盾的艺术家比一个单纯看起来极好的艺术家更有趣,但是图录的阅读方式和雇佣者阅读推荐信一样——文章中只要存在一些关于某事错误的暗示,作者就会遭到被推荐者的痛恨。在大型展览的情况下,文章作者有更多的自由,但这并不能阻止艺术家的反对,而艺术家的负面回应可能意味着这位作者不会被邀请为下一个展览撰写评论。我为一个在维也纳之外的爱赛尔收藏中心(Essl Collection)的地方举办的“未涂绘”(Un-gemalt/Unpainted)展览写了一篇长文,文章所呈现的内容正是我想表达的,但有几位艺术家对我所写的他们的内容提出了反对意见。这种反对的理由不会邀请我去做进一步的讨论:从总体上来说,批评被席卷而去。某一次,有一位艺术家认为我误解了他,这种反应只有在艺术文化中才有意义,因为成功的艺术家很少会受到严肃的批评家或历史学者的批评。自然,在那种与世隔绝的气氛之下,艺术家们认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的作品。
极少人会使用一致的批判性的态度阅读图录文章,一种更典型的阅读体验,也是这类图录文章旨在培养的方式,包括浏览文本,寻找表明作品重要性的短语或概念。图录文章通常表现出绝对的权威性,并附有重要的艺术家名字和作品作为最好的参考,这种文章最好要流露出对艺术家重要性的热情。这种争论不应过于复杂,因为他们需要鼓励那些可能只是在浏览文本的读者。同时,争论也不应该过于明显,因为他们需要维持读者对作品的步履蹒跚的信心。如果一篇文章过于简单,读者也许会得出这件作品并没有什么的结论,因此这些文章 需要略微地增加夸张语调之事,为了唤起读者的开放性讨论,暂停去作全面性的论证。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随意从我的书架上选取一个例子(我的吱呀作响的书架装了大概3000本展览图录): 其中一本是凯特•谢菲尔德(Kate Shepherd)的绘画展览图录,1999年该图录出版时她是圣达菲兰南基金会 (Santa Fe Lannan Foundation)的驻留艺术家。正如基金会的艺术总监凯瑟琳•美林(Kathleen Merrill)在介绍中所说:谢菲尔德的绘画描绘了“盒子、不完整的盒子、线条或在孤立的两个单色域上绘制的孤立的点”。这些盒子和线条十分精美,十分规整并呈现黑色,单色领域是完美的矩形。这篇文章是时任得克萨斯州马尔法唐人街基金会(Chinati Foundation)助理主管的罗布• 韦纳(Rob Weiner)写的。他首先指出了谢菲尔德早期的作品是有比喻性的:她用“优雅而精致”的方式画旗帜、鞋子和花,在某种程度上是十分精细和深刻的。新的作品之所以具有一贯性,是因为“这些作品是由几何学形式中提炼的有限视觉词汇组成的,建立了一个规则在不断变化的经验主义游戏”,最终达到 “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些开放性的句子产生了当代图录文章共有的三种效应:通过将谢菲尔德的作品与主要的艺术运动(极简主义)联系起来激发了高级艺术的野心,强调了艺术家的严肃性(指出她一贯的目的和轨迹),除了艺术家的作品在结论之间保持平衡之外,没有得出其他特别的结论。在韦纳文章的后面,他通过一个更广泛的联系强调谢菲尔德和过去严肃绘画之间的关系——他把她的垂直绘画比作是“一幅经常占据宛如舞台般的中立空间的17世纪西班牙英俊的全身像:有良好的血缘、泰然自若和庄严的神情”。在文章中,他详细解释了为什么她的画作是平衡的、高深莫测的和模糊不清的:
“实际上,弯曲或者闪光点根本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故意留下来的一种开玩笑似的用以颠覆我们期望的手法,而她的手法无疑是最安全的。这种视觉上的破坏,呼唤心灵的省略——词的省略(此处为重点)对于构造是必要的,但应该放置在更大的语境中理解。她的盘旋体是由小心翼翼的线组成的,可能会在思考的过程中突然中断。它是一个脆弱而令人心动的几何形状,要求我们参与其不稳定的结局。”
在像这样的文本中概括其中的争论是不容易的,因为并不存在太多的争论。韦纳试图对画家的开放式构图保持一定的敏感度,在不得出一个明确结论的基础上,他的目标是展示它们的微妙之处。当像韦纳这样的文章起作用时,它们证明了艺术家遗产中的一种信念:暗示了谢菲尔德是一位后极简主义者,韦纳认为她属于源自17世纪肖像画以来的一条线索。这种风格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其他成千上万拥有类似风格的后极简主义画家并没有被提及,或者是几何抽象主义的当下可能性,或者是关于该学科的学术研究,或者甚至是对谢菲尔德早期作品的回应。类似“省略”这样的术语并没有真正解决,也没有对一个单独图像的持续分析。举一个例子,准确地了解谢菲尔德绘画中的省略号到底发生在哪里,并且确切地知道它的效果在哪一方面,和文本中的省略号有何不同是非常有趣的。在韦纳的文章中,谢菲尔德的作品飘浮在一种平静并且接近空白的空间,并没有历史或被批判的负担。
这些都属于为全球成千上万商业画廊写的一般性图录文章。当这些文章被一些重要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委托并且配合主题展或回顾展呈现时,则是另一种情况。 这些论文被包装在大型展览图录中,与艺术史的专著难以区分。这种写作本身就引起了与自身有关的有趣的问题,尤其是当这些文章是如此的保守以至于承受不被阅读的风险,不仅仅是来自购买这些图录的观众(众所周知,在出版行业中,这些大的博物馆的展览图录被买来是作为茶几上的装饰品的),甚至是艺术史学家这一群 体。幸运的是,这些不是我关心的问题。对于当下的艺术批评现状而言,每年都会发表大量相对简短并且质量普通的论文,而且事实上,这些论文并没有被阅读甚至没有保存在图书馆中。
2.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从语气上来说是学术性的,但二者不一定具有从属关系。以这种风格写作,比较好的作者是凯文•迈克•朱拉•利斯(Caoimhin Mac Giolla Leith),一位在都柏林大学研究凯尔特语的教授,他是爱尔兰语言的 权威,也是爱尔兰凯尔特语的姊妹语言之一苏格兰盖尔语的权威(Caoimhin是爱尔兰语中的Kevin)。他将艺术批评写作当作一项引人入胜但并不是正式的职业。像迈克•朱拉•利斯(Mac Giolla Leith)这样不任教于大学的艺术史系,并且利用业余时间当艺术批评家这样的现象在全世界的大学是非常典型的。[最典型的制度性“放逐”的例子是西蒙•沙玛(Simon Schama),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系而不是艺术史或考古系工作。]艺术史系教员并不认识迈克•朱拉•利斯这个人,他们也不知道在任何给定的学期他在哪里旅行,更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迈克•朱拉•利斯作为艺术批评家在世界上享有声誉,不仅与艺术家建立联系,而且与艺术史家也建立了联系。我称他的写作是“学术性的”,是因为他所引用的典故和参考文献不胜枚举。要描述混合语言学、法国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符号学和心理分析所组成的这种工作是不容易的,但是名称和术语在当代艺术世界中却是被熟知的。雅各布森(Jackobsen)、本韦尼斯特(Benveniste)、德勒兹(Deleuze)、瓜塔里(Guattari)、本雅明 (Benjamin)、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索绪尔(Saussure)、拉康(Lacan)等。这些名字是十分常见的,在经常被使用的技术上的术语也存在盲点:客体小a(the objet petite a)、屏幕(the screen)、凝 视(the gaze)、药(the pharmakon)、附属物(the parergon)、他者(the other)、对话式的想象(the dialogic imagination)、增补(the supplement)、延异(differance)、本质(ousia)、特质(the trait) 和块茎(the rhizome)。这样的术语还有很多,就其本身而言没有什么令人反感的。每个学术领域都有其专业术语。迈克•朱拉•利斯(Mac Giolla Leith)并不将这些词语用作行话,也就是说,故意使用这些晦涩难懂的概念去增加文章的权威性,但他确实将它们用作争论的占位符。我的意思是,概念和作者的名字在他的文本中所起的功能和在布道中引用《圣经》是一样的,从总体上增加文章的重要性和说服力,而无需提出单独的论据。迈克•朱拉•利斯(Mac Giolla Leith)的论文经常使用几种理论家和术语,有时候他会非常迅速地从一个理论转到另一个理论,造成的结果便是万花筒般的方法、概念和出处来源的积累进入到了临界规模,这表明了一个更广阔的论证,但不一定是循序渐进地建立起来的。阅读他的文章,感觉就像是批判性话语的密度与在达到该密度过程中的要点是一样重要。
一部分万花筒效应事实上是从艺术界以外的迈克• 朱拉•利斯来到艺术批评界,因此他的早期著作有时存在文法不通、引用尴尬的情况。但是从深层意义上讲,他的写作是可效仿的,并不都是有缺陷的。迈克•朱拉•利斯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实践的继承者,在这种实践中,理性论证本身是值得怀疑的。艺术史学家罗莎琳德•克 劳斯(Rosalind Krauss)经常冒着一系列解释方法的风险,以达到她认为适当的理论密度。当这个方法见效时,艺术反而变得更加难以讨论:提升了它论述的层次并同时终结了更简单的方法。当这个方法失败时,它更倾向于寻找学问之间的联系,与诗中意想不到的暗示玩耍而不是说明艺术作品。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学术性的艺术批评不一定是左派或是反启蒙主义者的。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某些较早的批评实践的直率逻辑,但也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要警惕用隐晦的典故编织而成的画面,在那个时候它们可能看起来是光辉灿烂的,但是它们鲜亮的颜色会逐渐消退。
我称之为学院派的作家们有很大的活动领域。例如,英国批评家迈克尔•纽曼(Michael Newman)就是通过哲学训练才走向艺术批评的。他写了一本关于伊曼纽尔•莱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书,他的著作反映了从海德格尔(Heidegger)到德里达(Derrida) 和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在内的后结构主义思想中许多利害攸关的问题。其他评论家,尤其是那些被训练成为艺术家的评论家,仅设法对后结构主义哲学进行了微不足道的提及。评估这类写作的一个关键点是与原始资料的分离程度。有一种艺术写作的次类型是如此宽泛地提及哲学思想,以至于它有效地创造了一个新的话语,独立于原始的哲学文本。诸如“客体小a”(the objet petit a)(最初是拉康的概念)和“装饰”(parergon)(最初是德里达的概念,在他之前是康德的概念)之类的概念在这样的著作中实际上是新近产生的。我不认为这一定是一个错误。在艺术批评中,概念在它们最初设置的相当连续的传统用法中被重新发现,它们出现在写作模型中,就像在不显眼的泥土中随意发现的粗糙的祖母绿或钻石。在我看来,这是支持看似不准确的哲学和批评参考的最佳论据之一。为何不尝试为一个新的主题去构建一种新的写作类型呢?另一方面,不利的论点是,一连串即逝的典故充分对这部作品作出回应:学术典故往往只是阻碍,用不能分辨的浑浊去结块成文。那么,反过来,打开学术论文到新闻的秒杀中。
3.文化批评
我所说的文化批评是指包括艺术在内的杂志和报纸上随处可见但并不以艺术批评的形式出现的批评。这种类批评的作者喜欢即兴发言,既机警又时髦,既善 辩又愤慨,很讽刺但又很疏离。莎拉•沃威尔(Sarah Vowell)就是一个例子,她撰写各种文化批评。她的网站介绍上称她是作家和“社会观察者”,声称“她写了很多东西,从她父亲的自制大炮到她对电影《教父》的迷恋,再到新罕布什尔州选举和她的切罗基人(Cherokee)祖先曾走过的血泪之路(Trail o f Tears)”。当她在我任教的学校当学生时,沃威尔对批评史和艺术史都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文化融合”(cultural mix)正是大众文化批评家的典型 特征,这类批评家最早可以追溯到劳伦斯•艾洛维(Lawrence Alloway),还包括后来的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戴夫•希基(Dave Hickey)和维克托•伯金(Victor Burgin)等众多作家。他们共同的思路是假定艺术已经完全融入了流行文化,然后从这个视角出发为“高级”艺术辩护,他们有时也会遵循艾洛维某种过时的或被误导的观念(虽然并不全然是艾洛维的 观点)。在沃威尔的著作中,文化融合预先设置了底线,这意味着所有事情都可以在不经意间被调侃,变得有趣且值得一笑。几乎所有认真的、不认真的文化实践——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文化实践都必须被讽刺性地以一种夸张或低俗的视角来看待。[沃威尔在《与柯南•欧 布莱恩深夜秀》( Late Night with Conan O’Brien)和《大卫•莱特曼秀》(The David Letterman Show)中客串了几次,也没什么不妥。]顺着这个思路来看,成为一名艺术批评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艺术批评被消解在更广泛的文化批评中,特别是它的严肃性,很容易被视为是一个愚蠢的失误。
这里有一个来自大众文化批评海啸的例子,作者是一位名叫贾尼斯•德姆基(Janis Demkiw)的艺术家,文章刊登在《劳拉》(Lola)杂志上,并于2001年1月20日在《多伦多之星》(Toronto Star)上重刊,标题是《紧迫、诚实、机智的艺术批评》( Urgent, Honest, Witty Art Criticism)。
9月30日凌晨4点30分,在邓德斯和麦考尔街(Dundas and McCaul Sts.)街角的亨利•摩尔(Henry Moore)雕塑[2],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后后瓦泽利内(Post-post Vaseline)和后雪莉•博伊尔(post Sherry Boyle)”的派对结束后,我们从邓德斯街走回家,经过了安大略美术馆(Art Gallery of Ontario),我们注意到一团黑色的胶泥从摩尔雕塑的平台上流下来,看起来像摩托车的机油,我们认为这有可能是故意破坏文物的行为。再往前走,汽车的残骸像雨点一样洒落在人行道上——玻璃、后视镜、轮毂盖。我们查看了雕塑,发现一道白色的车漆印在了雕塑的侧面。一些消防车(f**)越过路沿猛烈的撞击到摩尔和女王陛下的雕塑,但这座雕塑连伤痕都没有!这是一个有趣的超现实时刻——在整个城市停止运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而且我们知道这些证据将在数小时内被清除。(顺便说一句,我们后来发现,安大略美术馆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整个事件。现在这就是“消防车”艺 术。)这段评论的结论是:摩尔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而且……是任何事情的考验。不过,我还是为那辆车感到难过。
请注意,如果这篇文章“不讽刺就一文不值”(Nothing if not ironic)。[在这里我调侃了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的书《绝对批评》( Nothing If Not Critical)——与之相比,休斯的书简直像一头严厉的恐龙。][2]德姆基标题的第一个词“紧迫”(Urgent)就具有讽刺意味,而摩尔的雕塑“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这个偷梁换柱的结论也具有反讽意味。听起来仿佛德姆基根本在乎那类雕塑,这很有趣。然而,在这种反美学中蕴含着另一种美学——“离奇”(surreal)这个词表明了这一点。文化批评通常取决于高级艺术与大众文化意外并置所带来的乐趣,比如摩尔和车祸。这种写作是矛盾的:实际上,正如某些文化批评所暗示的那样,高级与低级,艺术与大众文化,将其完全不同的部分并置,就会产生某种并不做作的快感。作为艺术的捍卫者,文化批评确实是需要一些笑声的,这证明了高级和低级仍然是可分隔的——反过来,这意味着文化批评最终可能成为严肃的当代文化问题的切入点。
现在有一小部分的文化批评,包括沃威尔的部分写作,对于高级和低级之间的差异确实不感兴趣。测试的结果显示,作家对于讽刺在世的高级艺术并没有多少兴趣。我发现那种被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称为民主“图像狂热主义”(iconophilia)的现象极其罕见:它不会出现在文化研究的大学课堂上,但它在当代艺术中却一直存在;它也不会出现在杂志或报纸的评论中,因为(这些媒体仍然)小心翼翼地区分着艺术与流行图像;它更不会出现在电视媒体上,因为这类媒体认为高雅文化是浮夸的、愚蠢的[比如美剧《欢乐一家亲》 (Frasier)];它也不会发生在好莱坞,从电影《蝙蝠侠》(Batman)到《007之择日而亡》(Die Another Day),都对艺术进行随意的抨击[在《007之择日而亡》中,庚斯博罗(Gainsborough)画作《蓝衣少年》(复制品)被划坏,而在《蝙蝠侠》中,小丑在弗兰西斯• 培根(Francis Bacon)的一幅画上签名,带着一种嘲讽的赞赏]。除了《劳拉》这一本杂志之外,德姆基还为“速溶咖啡”(Instant Coffee)网站发布的电子杂志《星期六》(Saturday Edition)供稿。类似这样的非传统领域是他们趋之若鹜的地方,他们在整个当代文化中寻找乐趣,不会在意所谓的高级和低档。在大多数的文化批评中,高雅艺术就像是浓汤中顽固的面粉块:它们只是不会溶解,但也没有关系,因为味道还不错。
4.保守的长篇大论
拿希尔顿•克雷默(Hilton Kramer)作为长篇大论的保守派的代表是非常合适的。在2001年,克雷默在《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未 署名的社论中提出:
从一开始,我们试图提供的就不仅仅是简单的报道,而是批评。我们所说的“批评”(criticism)是指 “判断力”(discrimination),即对价值的明智判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价值判断并不等同于敌意——尽管从本质上来说,对当代艺术界的判断性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较负面的。何以失败至此呢?因为我们所谈论的是一个充满欺骗的、意识形态哗众取宠的、愤世嫉俗的商业主义盛行的世界。它对我们这个时代说得太多,而在很多圈子里,提到这些就意味着其品位值得怀疑。在这样的场域中,“批评”只是“区分好与坏、成功与失败”的问题。作者很可能就是克雷默本人,这篇社论肯定也反映了他的观点:在克雷默眼中,缺乏判断力和当代艺术的失败是并行的。这位作者希望以“和谐与传统” 的名义,巧妙地创作出与政治无关的艺术。这些价值观有时会让克雷默脱离艺术界。他为画家奥德•纳德鲁姆(Odd Nerdrum)写了一篇有趣的评论。乍一看,按照他的标准,纳德鲁姆似乎是一个理想的画家:纳德鲁姆有着精湛的技巧、对商业主义的蔑视,并且关涉道德问题——尽管很难确切地说它们是什么。克雷默一开始指出,纳德鲁姆在“官方艺术界”并没有取得任何成功。纳德鲁姆的作品否定了“几乎所有捍卫当代艺术正统观念”:他对自己回到伦勃朗“毫无歉意”(unapologetic),他精湛的技巧,以及绘画主题中体现出的道德上的愤怒感让他“像格尔尼卡一样‘现代’”。纳德鲁姆的绘画“以反现代主义为荣,但他们对后现代主义阵营的故作姿态几乎一无所知”。按照这些标准,克雷默应该让纳德鲁姆成为一名重要画家——但他还不能这么说,也许是因为他觉得纳德鲁姆迷失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件很奇怪的事。用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原话来说,克莱默•希尔顿(Kramer Hilton)的生活确实充满了诱惑力——是与现实艺术世界的粗鲁动荡和低迷的雾气相隔绝的。
5.哲学家的文章
尽管托马斯•克劳(Thomas Crow)在有关极简主义和观念艺术的著作中采用了一种更密集、更协调的哲学基调,但哲学家的文章最好的例子也许是世纪之交的阿瑟•丹托(Arthur Danto)。对于克劳来说,艺术运动涉及到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因此需要哲学批评。他们来“是为了提供一个最重要的场所,在这里,要求苛刻的哲学问题可以在大量普通公众面前公开发表”。克劳说,由于哲学退回到了狭隘的学术圈,观念艺术家“可能会合法地宣称自己是最后的公众哲学家”——不过他也警告说:那些所谓的具有哲学意义的“当然……只是极少数人”。克劳的演讲苛刻无情,不过他也承认,“目前这种试图通过语言来探索重建共识性公众讨论的方法是个悖论,因为很多人都被排除在外了”。就目前而言,最好的批评必须“使用绝对恰当的修辞和客观精确的语言”,因为真正重要的是谢莉•莱文(Sherrie Levine)通过三合板表达的对西方绘画的感受,或者是戈登•玛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通过行为暗示出的对极简主义艺术(minimalist)或支持、或反对的窘境。这些作品并没有简化为哲学,因为它们的最佳状态是哲学:它们是通过视觉艺术表现出来的问题和立场,对严肃的批评家来说,这使得他们比用文字表达的传统哲学问题更具有挑战性和吸引力。(我对克劳的一些更具有哲学思想的文章的看法是,这些作品表面上 所体现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像哲学那样有趣或“苛刻”。但是,观念和作品的交叉点具有不可替代的哲学重要性,还有作品在文本中的样貌也非常重要,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做深究。)
丹托的写作风格比较轻松,但他也关心哲学的说服力以及某些艺术作品作为逻辑和哲学问题范例的能力。他的哲学文章——相对于他的艺术批评,我稍后会讲到——倾向于围绕他著名的论断,即艺术史在1963年沃霍尔(Warhol)的《布里洛盒子》( Brillo Boxes)中结束。根据我的经验,有两种读者对丹托的哲学写作和关于艺术史终结的论文特别感兴趣:一类由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组成,另一类主要是艺术家,他们利用艺术史终结论来宣称将自己从与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的义务中解脱出来。对于第二类读者而言,丹托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解除了对历史的最后义务,给了艺术家们一个停止思考自己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历史中的位置的许可。
在探索艺术史终结理论的同时,丹托继续为美国和欧洲的一系列博物馆和画廊撰写艺术批评。这些艺术批评提出了完全不同的问题。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艺术史终结后写艺术批评的想法。如果像哲学家马丁•多诺霍(Martin Donougho)所说的那样,艺术批评实际上已经“从解释学实践(即‘关于’某物)转向了一种新的,不再进行内容分割的多元游戏”,那么艺术批评就有望成为一种全新的东西。根据我的理解,丹托的立场是,他从自己的角度写批评,而任何其他人的评论也是有效的。在历史之后的艺术状态中,任何人的观念都是有意义的,而且一种观点压过另一种解释的状况也没有理由存在了。
丹托的批评大部分是安迪•沃霍尔之后的艺术家,而且夹杂着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判断,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立场。就像写作《艺术史的终结》之前一样,艺术运动、艺术风格、艺术家,以及理念之间的相互比较常常很有说服力。丹托并没有像他自己预想得那样演绎出新的、非艺术史的艺术批评理论,在我看来,批评不可能被理论化。比如,并不存在某种特定的理论可以用来评判抽象主义,那就意味着它必须既可以用来评判波洛克(Pollock),用在其他人身上也同样有效。同样的术语、同样的文本建构、同样的价值观怎么可能用在当代抽象艺术上?从逻辑上讲,在《布里洛盒子》之前将当代艺术批评与批评区分开来的唯一方法是在不使用1963 年之前的论断和概念进行写作。这是有可能的——我可以借用电气工程或者物理学的术语来写一篇关于抽象的文章——但对于许多读者来说,这算不上艺术批评。无论如何,丹托没有这样尝试:他只是写艺术批评,就像他在1984年写的第一篇关于艺术史终结的文章之前那样。他只是要求读者不要再认为他的艺术批评具有超越或低于任何其他评论家努力的历史力量或解释力——但这肯定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严格地说,我认为丹托的艺术批评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人们不可能按照他的要求去解读它;他像是在玩一个多元化的游戏,使用各种不相容的声音,却只提出了一个观点。
我想在此处重申一下,因为丹托这种没有立场的当代多元主义(contemporary pluralism)至关重要。实际上,他认为1963年以前艺术批评中使用的文献并不存在多少引申含义,它们是历史学意义的文献,但是这种文献可以被理解的唯一方式(还有其他方式吗?)是在历史学著作和语境中使用它们。没有历史锚点的支撑,它们是空的,是无法被人理解的。1963年之后的艺术批评也不能仅仅选择艺术家做编年史,因为这种编年史对于那些已经不再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除非是为了证明当时的艺术家被误导了,否则这种编年史毫无意义。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近几十年来一些最有趣的艺术批评可以被叫做哲学,我在这里用的是哲学这个术语。克劳的观点是以极简主义为基础的,而史蒂芬•梅尔维尔(Stephen Melville)对20世纪80年代艺术的解读有赖于解构主义,惠特尼•戴维斯(Whitney Davis)最近关于雕塑的精彩著作也是极好的例证。我之所以在这里把它们归类,只是因为在更大的艺术批评领域中,它们有着将艺术品视为不可替代的哲学功能的共同特征。
注释:注释:[1] 海德拉(Hydra),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
[2]这里指的应是亨利•摩尔的雕塑《两种巨型》( Large Two Forms)之一,1974年以来,该作品一直被放置在 多伦多邓德斯和麦考尔街的街角。——编者注 [2]罗伯特•休斯原书为《Nothing If Not Critical: Selected Essays on Art and Artists》,中译本《绝对批评: 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评论》,2016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编者注。
作者:[美]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马琳、滕红林 译(Translated By Ma Lin, Teng Honglin)
原文刊载于《画刊》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