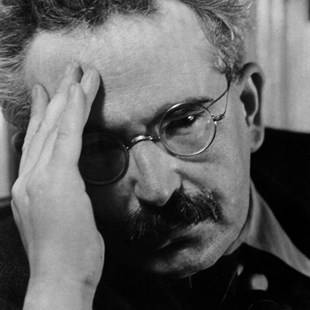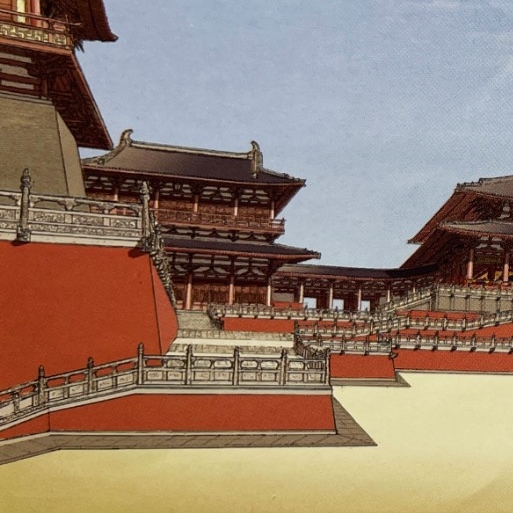当代艺术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交流工具。与之前我们所知道的艺术相比,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因为它受影响于全球化这个我们刚刚体会到、也正在努力探究其结果的现象。
全球艺术
是时候开始讨论全球艺术的性质与目的了。20年前,也就是20世纪末期,初显雏形的全球艺术如同凤凰涅架一般从现代艺术中脱胎而出,并且是站在了现代性哺育的发展和权威之理想的反面。艺术生产随着1989年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格局动荡而扩展到全球,当代艺术,这个长期被用来指代当下艺术的词开始呈现全新的含义。这一空前变动所导致的结果是对任何欧洲中心主义“艺术”观延续性的挑战。全球艺术再也不是现代艺术的代名词。因为对于当代的定义不再只是时间上的,我们也意识到它可以是象征意义上甚至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全球艺术为艺术市场所呈现却又被其扭曲:艺术市场在游走于各国文化之间时,采用的不仅仅是经济机制的策略,它还主导着艺术生产的方向,而对于艺术生产我们的分类仍然不甚明晰。
从全球范围来看,艺术并不意味着与生俱来的审美气质,也不是什么应该被看做艺术这类的全球概念。艺术不是在再现一个新的语境,语境或者焦点消失了,而艺术又因为民族、文化和宗教上的地方主义、宗族化等逆全球化运动而带有一种自我矛盾的特征。很明显它和现代性是不一样的,现代性自我约定的普世主义建立在霸权式的艺术观上。简而言之,当今新出现的艺术是全球的,这和万维网是全球的没什么两样。因特网是全球的,是因为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可以使用它,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容就是全球通用的。我们可以自由访问因特网,同时也可以对这个世界做出我们个人的回应但这也给当局造成了麻烦,引发了后者对之加以控制的欲望。确切地说其原因在于当局面对的这些问题就本身而言是地区性的,但网络传播的信息和意见体现出的创造性不受审查,可以自由流通,因而威胁到了本属于地区性的问题。对于西方艺术批评界来说要接受全球艺术(不仅仅是新的地理范围的艺术)这样个新事物可能是件难事。不过想要让艺术遵循西方模式在相似的体制内行事就有点一厢情愿了。
控制并非政治独有的问题:在艺术批评和美学中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全球艺术在政治层面看来或许极具批判性,不过对于泾渭分明的艺术分类来说也是具有批判意义的。新兴艺术常常模糊了主流艺术和通俗艺术之间的界限,这样一来也就通过本土的传统废止了西方艺术和外族艺术这种陈旧的二元对立,就像是贾斯托·帕斯特·梅拉多(Justo Pastor Mellado)向我们展示的智利和巴拉圭的例子一样。正如杰昆·巴连多斯(Joaquin Barriendos)在本书中的论文所阐述的那样,从西方视野来看,全球艺术反映了种地缘政治甚至“地缘美学”的特征。它是一种象征性资本,即使西方修正派试图通过自我调整汇率来操控他们的货币,这种象征性资本的价值还是会因地而异。带有异域文化特征的差异性开始走俏市场,它同时也成为艺术市场中初到者的准入证。
世界艺术
全球艺术和世界艺术有时候是通用的。不过世界艺术是一个旧概念,是对现代主义的一个补充,由于当时大部分艺术品还陈列于西方美术馆里,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便在其一部战后撰写的著作中对这个概念做了详尽阐述,这是一本关于脱离美术馆的普世艺术的书。世界艺术一如既往地将所有时期的艺术归为人类的遗产。事实上,如果不考虑现代主流艺术下关于美术馆和人类学博物馆的争论,世界艺术这一概念将使得任何来源的艺术都可接受。这已经在国际法中有所体现,其意在保护艺术和历史遗迹。位于东英吉利海峡诺里奇(Norwich)大学的世界艺术研究学院(The School of World Studies)对于这所大学而言算是一个新生事物,它为当今的世界艺术议题提供了一个很明确的范例.该学院前身是其所继承的塞恩斯伯里收藏馆(Sainsbury Collection),其藏品来自于非洲和大洋洲,它们就像是现代艺术形式主义和普世美学中的份子一样也被当做艺术品与现代艺术平起平坐。在学院授课的约翰·奥尼安(John Onians)也持相同观点,他编辑出版的巨著撑起《世界艺术的巨神》(Atlas of WorId Art),内容从石器时代一直至今,与此次项目同时存在的还有世界艺术图书馆。菜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主持的一个类似的项目则收录在《世界艺术研究》(WorId Art Studies)中,该杂志的供稿人全为艺术批评家和人科学家,也就是说两类长期采用不同方法思考、研究的学者。
从某个层面来说,基于现代主义普世性的艺术观和世界艺术这一概念是紧密相连的,现在看来这种世界艺术则有些怪异,就像是它在西方艺术观和多种形式之间,尤其是和异族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艺术”一词使用在异族的创作之上则显得有些武断。将人类创造的任何形式或工作看做是艺术,这是现代主义者的美学范式。世界艺术——一种将创作看做纯粹“形式”的审美概念或者是可以证明世界范围内的个体创造性的证据——在安德烈·马尔罗关于“想象的美术馆”一书中有很好的阐述。事实上,想象中的美术馆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座建筑,一种想象的建构,也是世界美术的缩影。世界美术从来都不在人种学家的思考范围内,他们以特定的文化方式和最为具体的角度研究土著物品。把“种族”、“原始”这类的标签放在这里很可能也成问题,不过这是出于另外的原因。萨利·普莱斯(Sally Price)在其《文明地区的原始艺术》(Primitive Art in Civilized Places)一书中针对西方的艺术观谈到了这一点,她对人造品和艺术品之间的模糊界限做了深刻的阐述。
同时,世界艺术也和文化的身份政治相关,这是现代主义没有阐述的,因此当今的世界艺术仍然坚持其传统,认定视觉创作是文化实践。世界艺术还因为越来越多的前殖民地国家施压索要本国艺术品而备受关注。西方大城市里的美术馆常常因为其作为帝国政治和殖民主义的前沿阵地这一身份而受到谴责,现如今,他们需要重新思考他们的收藏观念以防止藏品流失。大英博物馆就是一例,馆长尼尔·麦格雷格(Neil MacGregor)认为其博物馆“取之于世界,用之于世界”。秉承这一观点,他于2007年主办了一次大型中国秦始皇兵马俑展,吸引来大量观众,这也就更证实了他的观点:不仅仅是收藏,更要推进世界艺术。当时我在罗素大街(Russell Street)见到一个书店,不经意之间,它为我们做出的这种区分提供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书店老板将书分为世界美术和全球美术摆放在同一个橱窗里,虽然两类书都是关于中国艺术的。《中国艺术家》,一本讲活跃于新兴市场的中国艺术家的书,和街对面大英博物馆的展览画册放在了同一个橱窗里,这在20年前是根本讲不通的。
1982年,让-路易斯·普拉德(Jean-Louis Pradel)出版了《世界艺术潮流》(World Art Trends)系列的最后一本,然而里面提到的23个国家多数为西方国家。不过,如今的世界艺术指的是异族的遗产,是从世界层面来讨论艺术的。世界艺术所包含的不仅仅是西方世界保存于其国家美术馆的文化遗产,也涵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事实上,长期以来世界艺术主要为西方美术馆所掌控,在那里,世界艺术就像是殖民时期被放逐被争夺的珍品。为了保护他们的藏品,18家西方美术馆馆长最近签署了一个声明,要保留他们作为“世界美术馆”的地位,要为整个世界服务而不是只为一两个国家或民族服务。世界美术馆这个概念源自于现代性所提出的为世界树立一个普世的范式。而全球主义是对普世主义的一个回应,旨在于市场中传播差异的象征资本。全球艺术实质上和世界艺术有着本质的差别:无论创作的个体怎样定义艺术,全球艺术概念下的艺术实践总是作为艺术产生的,这点和当代艺术实践相同。
世界艺术史还是全球艺术史?
今天,世界艺术史出现了新的争论。世界艺术史和世界艺术研究不一样,它是指全球范围的艺术都可以用做为西方规则的艺术史方法研究。这一问题在大卫·桑默(David Summer)的书中有体现,书中世界艺术史是作为一个副标题的一部分出现的。后来,《艺术史是全球的吗?》(Is Art History Global?)一书的主编詹姆士·埃尔金斯(James Elkins)对此做出了批判。桑默认为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用艺术史的方法来研究,而埃尔金斯则坚持在“区域范围内研究艺术史”而不是以偏概全。在他的评论文章《作为全球学科的艺术史》(Art History as a Global Discipline)中,他提出“五条观点以反对将艺术史作为全球范围的标准。”在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最近出的一本书和惠特尼·戴维斯(Whitney Davis)即将问世的的书中,都谈到了在全球范围内研究艺术史的问题。
“全球艺术史”实际上不能看做是全球艺术的历史,因为后者刚出现20年左右。这个术语暗示的是将当今触角伸向全球范围的艺术史看做是一种方法和学术规则。“世界艺术史”则与此不同,因为它是关于世界艺术的历史,并且正因如此而凸显出两个问题:一方面世界艺术作为一种艺术观透露出的普世主义是成问题的,另一方面世界艺术有其多样性,历史的概念一词却会使得这个多样性的世界艺术只有一个共有的艺术史的历史。全球艺术作为当代艺术则与人们熟知的艺术史毫无联系(而且从现代主义的意义上说,它已经开始脱离艺术史了),世界艺术在欧洲传统中尚未成为艺术史的传统主题,但却受到了人种学和美学界的重视。无论是全球艺术史还是世界艺术史,对于这两者的讨论并不是关于内容或者主题的。它更多揭露的是将西方艺术史全球化的要求(或者期盼),可以看做为伸向初来乍到者的慷慨之手,或者一种新的帝国形式,一种新殖民主义。
我在很多场合提到过,艺术史是一个有区域限制的行当,它只在西方,而且是文艺复兴后的西方才合理。它是为了借助历史的方式来研究艺术而出现的。实际上,当代艺术家出于对后历史(post-history)的认同,故意抛弃了占统治地位的艺术史叙述方式。我在“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Art History after Modernism)这一标目下重新撰写的《艺术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Art?)一书,是针对法国艺术家何维·费舍(Herve Fischer)的一篇文章《艺术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Art)而写的。费舍以1979年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的一次表演活动来支撑其文章的论点。就此,他声称“艺术的历史已经终结了”。当我剪断了这根绳索的时候,也就标示着艺术史的结束。这条掉落了的绳索尽管此前有过线性的发展,却只不过是一种遐想而已。
另一方面,西方美术馆从今往后是否还会、或者将如何呈现艺术史,我们还难下定论。弗朗西斯·莫里斯(Frances Morris)在〈泰特现代美术馆手册》(Tate Modern:The Handbook)中写道: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永久陈列展取代了艺术史叙事,探索“观看艺术的其他方式”。为了对“开放而流动的现状”做出回应,“诗歌和梦想”之类的所谓“观点”为收藏品的“多重解读”提供了可能。博物馆的走廊里还借鉴MoMA美术馆为三十年代的艺术制作谱系图的方式也悬挂着类似一幅图表,但这种方式己然不适用于当代艺术实践。泰特的策划人们因为不能阐明艺术史现状而备受谴责,他们邀请参观者”填补这一空白”并且在明信片上写下他们的“观点”。自从晚期的现代艺术解构了线性历史,艺术史便开始失去了控制,这似乎是拜大多数美术馆的展览所赐。
为了推进其全球化,艺术史往往借助探讨身份和迁徙的后殖民文化理论。早在1989年,宾汉姆顿大学(University of Binghamton)举办的会议就批判了艺术史对于文化理论术语的借用。安东尼·金(Anthony King)在介绍会议的文章中谈到:入们常常以通俗的方式理解“文化全球化”,把它看做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均质化进程。因此,我们需要探寻替代性的方法形成“文化全球化”的概念并加以分析,没有哪个当代问题比这个更重要。会议中艺术史家们对文化理论的守卫者做出了回应,呼吁发起新的、可以在艺术世界的变迁中直击重点的奥伦。
以大师叙述为特点的艺术史书写开始面临危机,但这并没有帮助之前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重新书写他们自己的艺术史或者用其他东西代替之。中国艺术家和收藏家对艺术史持有不同的看法。张晓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992年)就对中国当代艺术这个没有现代主义传统的艺术的诞生进行了嘲讽的影射。'85新潮是对“国家意识形态和艺术制度的反叛”,期间有一次80多个非官方艺术小组参加的“关于现代性的哲学探讨”。情况直到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才有所改变,该展览于当年2月被官方以枪击事件为由被迫永久关闭。接下来的几年,艺术品开始受到市场的欢迎,艺术家与政治之间也断开了关系。直到那时候,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才开始走向世界。GAM小组讨论第二次论坛于2008年在新德里举行,主题是“今天的艺术史在何种意义上是全球性的?”。讨论谈到了一个印度拒绝将西方艺术史的研究方法推而广之的个案。这个讨论触及了当今印度很多备受争议的问题。与西方相反的叙述方式呈现出不一样的观念,逐渐替代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叙述方式,比如印度艺术的民族叙述方式。与会者达成一致共识,他们认为殖民史仍然过分操控了印度的文化主题,引导人们的注意力长期置于异域文化的体验上,而本土的传统与美学在今天的艺术史上却几乎无一席之地。因为殖民观念而出现了艺术史危机,这就促使了一种全新且多样化的视觉研究的出现,并成为了当今策划课程的主导思想(位于伦敦的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 College]是这方面的典范),它作为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式,用跨学科的方法取代了艺术史。
作为象征地域的当代美术馆
全球艺术反对此前“艺术”与土产艺术和流行生产之间的界限,它提倡的是两者的平等性,与艺术史形成对立。正是因为这一特质,西方以外的美术馆才能展示看起来形式繁多、内容各异的艺术实践,即便长期陈列展也是如此。在这样一个全新却又不受欢迎的环境里,西方艺术藏品也会突然看上去有些“本土化”。在非西方的语境下,为了与当地的参观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美术馆在制定收藏政策的时候倾向于与民族的或者社群的意向保持一致,强调给定传统的地缘性特点。在选择和推进它们认同的艺术的过程中,美术馆有足够理由重新思考它们所扮演的角色。它们可以举办国际展览,但近来双年展遍布了世界各地.取代了这些美术馆展示和组织前卫艺术的旧角色。
当代美术馆再也不是为了呈现艺术史而建立,而是通过展出当代艺术来呈现一个不断扩展的世界。这些美木馆的兴起并非步西方传统美术馆观念的后尘,它们更多考虑的是什么可以成为艺术,而不是他们在美术馆中可以做什么事情,后者在不同地方都有相似性。全球化开启了世界的去中心化进程,“新经济”的“自由贸易”意识形态成为了“自由艺术”的修辞,这种艺术不再像此前的艺术那样呈现为一种全责模式,它是自由的,因为市场任由它自由发展。相应地,现代美术馆(MoMA)的标签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当代美术馆(MoCA)所代替。大部分当代美术馆设立在美国,洛杉矶当代美术馆和麻省当代美术馆是人们最为熟知的两个。在蒙特利尔、伦敦、里昂、上海和香川也有这样的美术馆,甚至在韩国还有一家国家当代美术馆。当代美术馆可以说是全球性的,因为它呈现的当代艺术生产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也没有西方现代主义的那种历史性。佳士得和苏富比在他们最近几年的拍卖画册中开始停止使用西方艺术中人们熟知的“现代”一词,取而代之的是根据“当代”和“战后”做出的分类,艺术市场也随之仿效。
亚洲也开始以同样的速度筹建美术馆,并在近20年里拥有了自己的双年展。这种速度史无前例,但其目标仍十分模糊。日本出现支持“地方性(县立)美术馆”的趋势‘它们缺乏收藏也不聘用策划人,而是“由当地艺术家自己举办群展”。森下正昭称之为只做临时展览的“空美术馆”,就像是德文中的“Kunsthallen”(艺术大厅)。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术馆”只是一座建筑的象征性称谓,人们期待在永远能在这里看到艺术的展示。美术馆建得就像机场,等待着国际艺术的降落。这看上去很矛盾(美术馆的兴盛和其内涵危机的矛盾),事实却反映了美术馆与新观众之间关系,这些观众中的很多人对于当下参观美术馆的意义并不了解。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收藏家们(所谓艺术世界的VIP)根本不需要美术馆,他们有的人自己去建美术馆,但这就与当地毫无艺术经验的观众形成了一条鸿沟。
和收藏家不一样,当局致力于填补这条鸿沟,他们在城市里“发展”艺术,传达自身的愿望,并设立所谓的“文化区”。何庆基(Oscar Ho)描述说:香港项目决定建设多家有大型展厅的美术馆,以期吸引大量观众。在上海,当局打算于2010年前新建100座美术馆:“他们要让上海的美术馆多过星巴克。”不过这样的美术馆和他们“吸引普通大众进行文化体验的诉求关系并不大”。为了吸引新的观众,美术馆也许很快就不得不放弃和收藏家美术馆的竞争,而且需要在吸引国际关注是用主流艺术迎合本土观众(比如基于本土环境的视觉文化或者通俗作品)之间做出选择。在中国,美术馆兴建大潮刚刚开始,不过很快就会赶超其他地区的发展。美术馆领导已经开始讨论在国内兴建公共美术馆,来展现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国际成就。(节选)
作者:汉斯·贝尔廷
译者:徐云涛
原文刊载于《美术文献》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