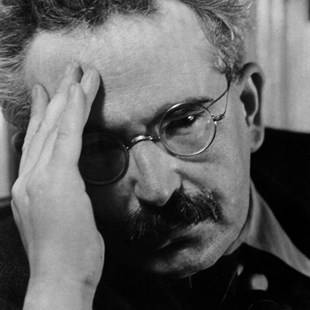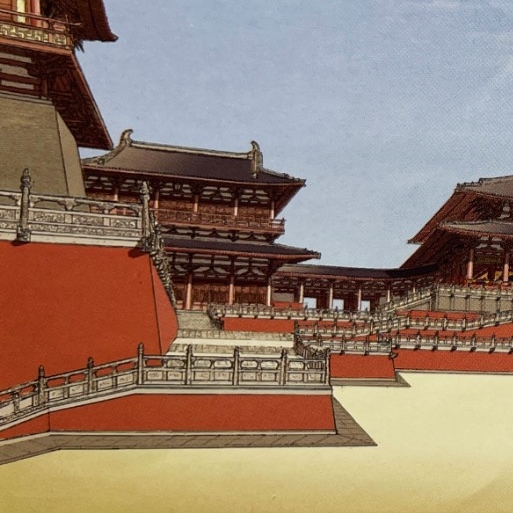内容摘要:本文聚焦于中国艺术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首先回顾了20世纪中国艺术史从无到有、与考古学相伴生的简要历史,指出了作为考古学“补充文本”的尴尬境况。继而讨论了以下问题:艺术史研究进入到艺术无差别时代,“文物群”“艺术史”就是观念史吗?解释性的艺术史:“他”死了还是“我”死了?艺术史越来越与“艺术”无关。本文分析讨论了考古学给艺术史学带来的恩泽,同时指出了后者的学科困境与问题。
关键词:艺术史 考古学 美术考古 文物群 补充文本
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史学与考古学所讨论的对象有很大的重叠性,都有在物质与视觉的层面讨论历史文化。两拨人常常参加同一个会议。学术界热衷于争“正宗”,在某些考古学家看来,考古学是正宗,艺术史是旁门,属于“锦上添花”。而在某些艺术史学人看来两者的关系却相反。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学科,然而在20世纪的中国却一直交缠不清,互有侵蚀。许多会议的参加者就是这两个学科的专家,如几个月前(2020年6月24日)山西省文物局召开的关于云冈石窟研究项目的全国性视频会议,参加者就有这两拨人—当然考古学(及历史学)是主流,它关系到政府的导向和财力的投向。我是与会者之一,不得不含蓄地建议多请一些艺术史和雕塑史的专家。云冈石窟是一个文化综合体,可在多学科多角度观察,自从20世纪初欧洲学者与日本学者考察并发表成果以来,【1】几乎就奠定了考古学的基础与基调。显然它是艺术史的一个主要关注对象,然而话语权主要在考古界。这是中国目前“艺术史”与“考古”两个学科关系的一个缩影。“艺术史”在中国是20世纪逐渐生长变化的概念,虽然我们有关于绘画史的研究很久了,毕竟与西方学术框架有别。中国当代的艺术史学科几乎就是三者的叠合:中国传统的书画史论、中国的艺术史对象(物、人、事)、西方的“他者”眼光。然而,什么是“艺术”之史?艺术史写给谁看?艺术史独门法器何在?如何跨学科而又坚守领地?它和相邻学科如考古学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讨论。笔者近年略有所思,择其要点陈述于后,抛砖以引玉。
一、艺术史:考古学的伴生史
现代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不断得益于考古学的成就。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及日本的考古学家与艺术史家相继来到中国东寻西找,发现了大量新的材料,如汉代画像石、石窟与寺观雕塑、陵墓雕刻与陶俑、敦煌藏经洞出土绘画等,成为除卷轴画以外构建中国美术史更为广泛的基本材料。最早来中国寻找文物(艺术)的西方与日本学者,大致可分为四类人:第一类是收藏家,如1893年,日本冈仓天心及其助手早崎稉吉在中国进行古代美术调查。美国汉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是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的亚洲人类学策展人,是亚洲文化研究的先驱,其收藏品多藏于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史博物馆,于1908年至1910年、1923年两次来到中国,收集了大量文物。第二类是“顺便”发现考古材料的人,本来从事理工科等其他职业,如日本学者足立喜六(1871—1949),1906年至1910年利用在陕西高等学堂任教之闲暇,对西安附近的历史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结合历史文献写成《长安史迹考》一书【2】。第三类是美术史家,如大村西崖(1867—1927),毕生致力于美术史研究,先后五次到中国考察。其代表性著作《中国美术史雕塑篇》1917年出版,【3】是参照现代西方学术体系编撰的专题艺术史著作,开创了中国雕塑史研究的先河。第四类是汉学家与考古学家,如有法国汉学家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到中国北方考察,1909年出版有《华北考古记》,侧重于汉代祠堂与北方佛教石窟。【4】法国学者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步其后尘,于1909年、1914年和1917年多次到中国陕西、四川等地进行考古调查。拍摄大量石窟、汉代祠堂、汉唐帝陵、寺庙等文物,著有《中国西部考古记》,其《谢阁兰的中国考古摄影集》内含照片七百多幅,包含许多现已不存的文物材料。【5】1918年至1924年间,日本学者常盘大定(1870—1945)、关野贞(1868—1935)等人在中国多地调查史迹,资料收入《支那文化史迹》,1939年至1941年陆续出版。【6】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在中国的活动则主要是考古发现,1921年河南省渑池县发现仰韶文化,揭开中国20世纪田野考古的序幕,引发了中国考古的热潮,由此使得中国历史前伸到夏代以前,开始以出土文物改写中国历史。相对于这些大面积的零散的调查,主题集中的当属敦煌莫高窟的调查与盗买。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著名事件,英籍匈牙利人、考古学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1907年来到敦煌,骗走了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其正式考古报告为《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全四卷。【7】而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来到敦煌莫高窟,劫走六千余种文书、二百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等物。同时详细调查了所有洞窟,对每个洞窟做了编号和描述,详细记录了壁画题记。【8】这是敦煌文物艺术品最大的两批流失。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六万余件文物中,约有三分之二被保存于十多个国家的数十家博物馆中。以莫高窟本体和藏经洞出土文物为主要支撑,发展出一个综合性的单独学科“敦煌学”。
二、“美术考古”?
考古学的加入,是中国绘画史成为西方学术意义上的“艺术史”的有力保障,不仅是新材料的主要来源,还在学术方向上引导了艺术史学科的建立。20世纪是中国考古学大发展的时代,考古就是在重修国史,重建中华文明史,艺术史只是其中一部分。20世纪中国每次重要的考古发现,都会导致艺术史的重写:填补空白、与画史和历史文献互动、焦点的转移、价值观的重构。每次重要的考古发掘都会伴随有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角一般是考古队的领队,但总是有那么少数几个艺术史的学者出席。而艺术史学者总是时时关注新的考古成果,出现了一个颇有争议的新词“美术考古”,作为考古学下属的一个分支(虽然其合法性仍有异议)。考古学家有直接的发掘现场体验,握有所有发掘成果的发布权。某些艺术史学者可以凭借私人关系及时进入发掘现场短暂观看。在这种常态下,对于相同的发掘对象(出土物),话语权显然有别。
马王堆1号汉墓发掘不久,《文物》杂志在1972年9月首次集中发表了16篇文章,主要是马雍、唐兰等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做,只有一篇作者出自“美术”圈:画家吴作人《读马王堆西汉帛画后—画笔随录》。【9】而后,才有金维诺等美术史家渐次加入讨论。数十年来,逐渐从一个考古学的话题转变为一个艺术史话题。尔后的更深度的解释,更是艺术史家挥洒才华与想象力的天下。
20世纪上半叶的考察,如日本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本身是美术史家和考古学家,中国的梁思成考察古代建筑,同时纳入的还有寺观的雕塑。线描图体现作者的认识,具有照片不具备的表现力,梁书和水野书的许多精美线描图往往出自作者自己之手,至今仍为典范之作。【10】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考古界分工,线描图由专门的技工绘制,水平远不如梁思成和水野清一辈。其考古报告日益远离“艺术”。随着新的自然科学手段的使用,考古学有“科学化”、技术化甚至工匠化的担忧。大多正式的考古报告,多年来都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而这家出版社是以自然科学出版为主业的。这本身就暗示了考古的标准:能够与自然科学相匹配的价值观。
考古与艺术史在文物研究的链条中侧重于不同时段,考古学主要在前期,做基础工作,遗址调查、发掘、辨识,解决时代、属性等原位问题;艺术史侧重后期,做解释工作,解决文化与历史问题。一些不太依靠“发掘”出成果的文物遗址,如敦煌研究院,“考古”与“艺术史”的关系就颠倒过来了,艺术史研究成为主流。
三、艺术无差别时代
两个学科的亲缘关系,首先在于共用对象,都是视觉材料,都是“文物”。且由于艺术史学科的新倾向:“艺术差别”渐被忽略,看重历史价值而放弃艺术价值。“文物遗存”是一中性名词,而“艺术品”则是有相当程度的价值判断成分。一个墓葬或遗址的所有遗存物件,都是文物,都值得考古学家重视。而其中是否有“艺术”则难说了,艺术史家似乎在这里就该有明确的分工:你们做其中那些“艺术”的部分。然而,近年的艺术史研究偏偏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随着“艺术”标准的弱化,进入到艺术无差别时代。佳作与次品(甚至废品)概念的差异已然消解。如几乎所有的中国书法家都认为王羲之是顶级书法家,其作品一直最值得重视。然而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晋唐时期的抄经工匠的书法也能称“优秀”书法吗?我们研究汉晋简牍上无名氏的隶书,只具有“查漏补缺”的意义吗?我记得前年我主持了一个宋代艺术的讨论会,美国加州大学的李慧漱教授讨论了一幅南宋绘画《西湖清趣图》,【11】她说,多年前她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看这幅画的时候,一些老先生对此画不以为然,或认为艺术水平一般般,无甚价值。后来又有一次我主持美术史博士生论坛,请《美术》杂志社的主编尚辉先生来参加,他对许多博士生讨论的艺术作品十分意外,认为很多作品不够水平甚至很糟糕,将在待淘汰之列,多年以后无人知晓。显然,传统的艺术史研究重视的是“艺术性”,优秀的艺术品质。或许这是美术家们对美术史学科的期待,汲取传统艺术精华,作为新作品的参照。而现代的艺术史研究放弃了这个任务,没有将读者设定为艺术实践家!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西安美术学院工作时,该院一位顶级画家语重心长地劝我少研究唐宋古代的东西,多关注美院的画家。或许这是美院环境使然。美术创作是主体,美术史论是“补充文本”。随着西方20世纪现代艺术的兴起,打破了固有的艺术价值观,“艺术”进入多元价值时代。优与劣随时可能转化。记得90年代初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一次中国画国际讨论会,有人问高居翰教授,你们为什么研究那些二流、三流的画家?当时他研究的明清画家如张宏、李士达、张复、吴彬,一般中国学者并不关注。【12】高回答说,因为研究这些画家才能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他同时的一流画家。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托词。西方学术界许多人认为,研究一流的艺术家如晚清任伯年,与研究上海申报的一个香烟广告同样重要。还有“艺术”吗?实际上这是研究目的的转型,由如何“艺术”转向如何“文化”,“艺术”虽可保留,只是“物质文化”的元素之一。
四、“文物群”
考古的对象一般是“文物群”,不是单一的文物,即环境中的文物群,层位关系、组合关系、位置关系及历史演变关系等。而艺术史研究也在逐渐远离单一艺术品,即使是卷轴画,也常常置于历史脉络中制造一个“艺术品群”的生态环境,再将具体作品置于其中。除作品外,还有人与社会、经济、民俗、宗教等参照系。与此相伴,艺术史转型的第二个倾向是,由单一门类研究转向综合研究,即由绘画史(如卷轴画、壁画)转到多种材料一起关注,尤其是在墓葬美术、宗教美术这些艺术史的“亚学科”。从单一的门类艺术品到“文物群”。还是以马王堆为例,早先的讨论主要是T形帛画的主题辨识,后来巫鸿带来新的视野,【13】不仅将整个墓室纳入,还将T型帛画的使用方式与葬礼过程纳入其中,棺椁、随葬器物、丝织物、方位、礼仪等等,而跳出了争辩帛画内容的窠臼。他对满城汉墓的解读也是如此。几乎将整个墓葬活动看做一个类似“装置艺术”与“行为艺术”的对象。古今在此打通。这更是一个典型的物质文化研究,“艺术”在此退场。墓葬、石窟、寺庙,本身就是文化综合体,是群体合作、长时段累积而成,不是石涛绘画作品意义上的“艺术”,综合元素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原位的“史”的追溯。这个意义上与考古学没有分歧。
五、“艺术史”就是观念史吗?
众所周知,艺术史有内史与外史之分,前者一般指作品之内的元素,如画面构成、风格、师承传统、材料技法等等,后者一般指作品以外的因素,如人缘、政治、经济、信仰等等。20世纪的艺术史研究,有由内至外的倾向,有跨学科的倾向。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艺术史就是观念史”。
科林伍德的观点影响了一代人—从欧美到中国,他说:“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14】在他看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口号的引申。后来的中国延伸版还有“工艺设计史是观念史”。艺术史被置放于思想史的阴影之下,无所不被笼罩。在许多方面,如同当代艺术一样,“艺术”只是一个名义,或是一种技巧—如何有效地传达思想观念。“艺术史”所剩下的“史”却不能变。可是我们知道,敦煌壁画的工匠作者、汉晋简牍的书写者、民间窗花的制作者都不是以“思想”或“观念”为特色的。比如,我们解释当代民间丧葬用品(纸糊的汽车、电视、楼房等物),一定要归结到当代哲学思想吗?思想史代替艺术史,无疑是取消一切专门史,忽略了人类感受与表达文明的多样性,全世界只有思想史了。想想不妥。这是消解“艺术”之极端行为,要不就是对“艺术”失望之极,懒得置之一词。窃以为,艺术家与文学家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有各自的思想体系,而在于“艺术”与“文学”的不同。
六、“他”死了还是“我”死了?
还原原作还是制造自我?研究者是隐形还是现形?
艺术史有三类写法,对此我有过简略的论述。【15】针对的是不同的读者人群。第一种艺术史,可称为中国艺术史的传统。这种艺术史研究,是以艺术为核心,而不是以历史为主。如南齐谢赫的《画品录》、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艺术”的艺术史,写给艺术家和鉴赏家看。第二种是“史学”的艺术史,写给历史读者,众多接近考古学、历史学的艺术史就是此类,已然成为当今艺术史学的主流。虽然中国传统的学术一直就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不同,然而主流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还是钟情于还原历史真相,呈现客观事实,揭示对象之高妙。可以举每年大量完成的中国各大学艺术史博士论文为例。第三种可称之为“解释性”的艺术史,则拥有更多爱好思辨的人群与年轻粉丝。自20世纪以后,艺术的标准已经开始解体。对于什么是“好的艺术”众说纷纭,以致搁置。“如何解释”本身成了最重要的目的。这就是第三种艺术史研究,可称为“解释的艺术史”,强调新的方法、新的概念。受惠于哲学的解释学、视觉传达心理学,由作品本意释读转为观者(解释者)感受认知。
或出于“思想史”辐射力,第三种艺术史研究就是加强解释者自己的“发现”与认识,生发出新的观念、与众不同的观念是其思考规则。这是侧重于大视野的、大开大合、贯通古今中西的文化观照,需要深厚全面的学识与浪漫的想象力。的确,历史的真相存在于解释者的语词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追求历史的绝对真实性是无意义的。有一位著名艺术史家问我:古代艺术品再好,属于往昔的荣光,你在哪里?在有些艺术史家看来,艺术史的材料如同艺术家创作的原料,组合自己的作品才是目的。的确有人这样做。其解释会产生一些新奇之意,然而却有“六经注我”之嫌。当然,“六经”本意就在不同的解释中生成,又不断变异。虽然我们知道艺术史是后人的描述,多有主观的成分,可是我们始终追求历史的原位和客观性。从根本上说,艺术史揭示的是贴近“艺术”事物的客观原貌,首先是真实性,其次一定要有深度。而这两点恰好是历史学研究的重点所在。与历史学一样,艺术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对材料进行充分认识与解释,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构成众人的共识。落实到艺术史层面上,就需要研究具体的实物、作品,乃至一个画派,一种潮流。这种研究可能强调细节和实证。艺术史更多属于历史学,以拂去遮蔽历史的灰尘、重现历史的真实景象为目的。
真实就是力量!真实在历代学人不断的、叠加的甚至有些混乱的互动中呈现,解释者在其中或有所发现,或拨乱反正,每个解释者融入到他所解释的对象之中,物我两忘,这个历史过程本身就充满人文诗意。对象“他”活了,解释者“我”也活了,由此嵌入历史而永生。史学家们的互动与共存,造就了艺术史。反之,如果过于追求“新意”“别致”甚至惊世骇俗,难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七、艺术史越来越与“艺术”无关
20世纪中国的考古学似乎是艺术史学的“母体”,其伟大的成就甚至模制了艺术史的面相。在中国现代的美术史学科建立的这个时期,在考古学的引领与支撑下,其资料来源可粗略分为前后两半:前一半为田野调查,后一半为发掘(墓葬与遗址),大量考古材料使得视野大扩充,焦点转移。考古学给予艺术史学许多恩泽,如提供了大量的新材料,解决了这些新材料的基本认知问题(如时代、属性),以更为综合性、联系性的视野加强了艺术史的历史厚度,尤其为解读无名作者群的制作提供了解决之道,扩大了艺术史的读者群。两者呈现出一种亲密的联姻关系。不仅于此,艺术史在“跨学科”思潮的鼓励下,与相关的人文学科如民族学、宗教学、文学、民俗学、典章制度史等不断融合。这种深度融合与跨界,使得艺术史学受益匪浅,得以壮大。但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艺术史的迷失。过多的跨界就是渐进式的走失,必然导致本学科的隐退。艺术史越来越与“艺术”无关。
艺术史,不是考古学的“补充文本”,也不是历史学的延长线。历史学的强项是文献与文本,考古学的强项是物质材料与空间遗迹,艺术史的强项应该是视觉材料的解读,在于视觉表达方式的历史认知性。“艺术”已经走失,“视觉”该如何召回?有必要重新确立学科自信心、重新确认读者群。
艺术史如何回归本位?本位何在?这是一个难题,我们从业者必须直面并寻找出路,由此必将迎来新的转型升级。
注释:【1】[法]沙畹《华北考古记》,法文版1909年,中文版2020年,中国画报出版社。[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1951年至1956年作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陆续刊行,16卷32册。中文版,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2】[日]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3】[日]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篇》,国书刊行会大正六年版、昭和五十五年。
【4】[法]沙畹《华北考古记》,法文版1907年,中文版2020年,中国画报出版社。
【5】[法]谢阁兰(色伽兰),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6】[日]常盘大定、关野贞《支那文化史迹》,法藏馆,昭和十五年。
【7】[英]斯坦因,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上海书店1987年版。[英]斯坦因,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法]伯希和,耿昇、唐健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文物》1972年第9期。
【10】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
【11】李凇主编《“宋代的视觉景象与历史情境”会议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2】[美]高居翰《山外山》,英文版1982年,中文版200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3】[美]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1页。
【14】[英]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1946年第一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4页。
【15】李凇《图说新语—中国艺术史演讲录》,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19年版,第272页。
作者:李凇
原文刊载于《美术观察》第3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