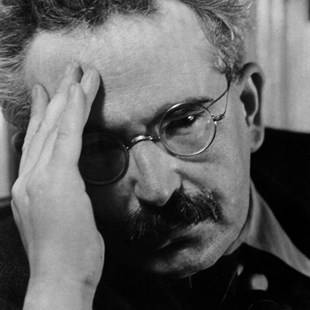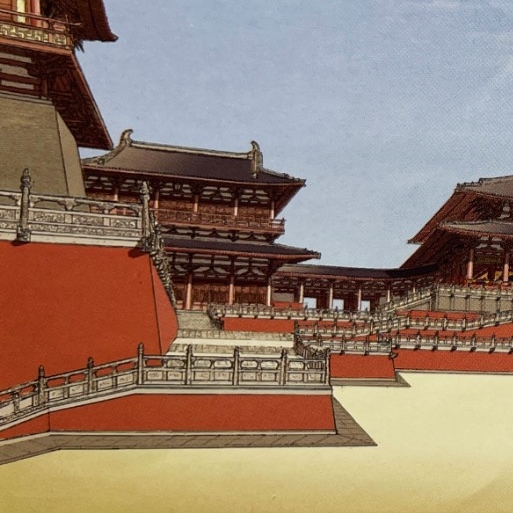对原始艺术的这种新的反应显然超出了美学的范围;渴望、道德价值以及广泛的生活概念的整个复杂情形都被囊括其中。如果说殖民帝国主义使得这些原始物品变得唾手可得,那么直到新的形式观念兴起后,它们才激起了人们的美学兴趣。不过,只有当人们认识到原始艺术的那种直觉、自然和神话本质上也属于人性之后,这些形式观念才能与原始艺术关联起来。这些观念甚至影响了人们对原始艺术的描述。那些调査过原始图像的物质和部落传统的老一代人种学家,通常会忽略他们的创造中那些主观的和审美的方面。在发现原始艺术的过程中,同样片面的现代批评家们也只依赖其感情去参悟原始艺术。它们是没有成文历史的原始人制作的艺术,这一事实使得它们变得更富吸引力。它们赢得了特殊的威望,因为它们是无时间性的,直觉的,与自发的动物行为处于同一个水平,自我包含、无反思性、私密、没有日期和签名,除了在情绪中,不带任何因果的迹象。在对原始艺术的这种新的热情背后,是历史、文明社会和外部自然的贬值。时间不再是一个历史维度;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时刻。而物质关系的整个困境,一个被决定的世界的梦魇,作为个体被致命地束缚于其中的历史时刻的当下的那种不安感——所有这些都在一种超越时间的、内在的、永恒的艺术的观念中,被自动地超越了。那些欧洲人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一度认为是落后野蛮的人民所创造的艺术,经过一个令人惊叹的过程,成了那些宣布要放弃这个世界的人们的美学规范。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展伴随着国内深刻的悲观主义,而在这种悲观主义中,“野蛮”的牺牲品所创造的艺术被提升到了超过欧洲传统的高度。除了可剥削那里的人民,殖民地还成了人们逃避文明世界的世外桃源。
然而,对原始艺术的这种新的尊重仍然属于进步的思潮,因为野蛮人及其他落后人民所创造的文化,如今被认为也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高级的创造物,不是西方发达社会所发现的战利品,而是人类的财富。不过,这种洞见不仅伴随着逃离发达社会的行径时有发生,也伴随着对那些物质条件的漠不关心;正是这些条件在残忍地摧毁原始人,或将他们转化为屈辱的、无文化的奴役状态。而且,出于对帝国主义权力的兴趣,对某些土著文化形式的保存,可以在新的艺术态度的名义上得到那些自以为完全没有政治利益的人的支持。
因此,说抽象艺术仅仅是对已经穷尽了的模仿自然的反动,或者说是发现了一个绝对的或纯粹的形式领域,乃是对这种艺术的正面价值及其潜在能量和运动资源的无视。而且,抽象艺术的运动范围过于广阔,准备时间过于漫长,与文学和摄影中的类似运动(但却有着相当不同的技术条件)的关系过于密切,最后,其时间和场所的多样性过于广泛,因此无法将它当作一种自我包含的发展,直接导源于美学问题的某种内在逻辑。在几乎每一个要点上,这个运动都带有包围着现代文化的不断变化着的物质和心理条件的印记。
艺术家们的公开声明——某些被引用在巴尔的书里——表明了,走向抽象艺术的步伐伴随着巨大的紧张和情感上的激动。画家们通过伦理的和形而上学的立场来为自己的做法辩护,或者在为自己的艺术辩护的过程中,攻击先前的风格,将它们视为令人厌恶的社会或道德立场的对应物。并非模仿自然的进程已经穷尽了,而是对自然的评价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艺术的哲学同样也是生活的哲学。
1. 俄国画家马列维奇(Malevich)这位“至上主义”的奠基者,用非常富有启示性的术语来描绘他的新艺术。“所谓至上主义,我的意思是绘画艺术中的纯粹情感或感觉的至高无上地位……1913年,在我试图将艺术从客观世界中解放出来的令人绝望的斗争中,我走到了画方块的形式,展出了一幅画,这幅画除了在一个白色的底色上画了一个黑色的方块外,什么也没有……我展出的并不是空荡荡的方块,而是主观性(或无客观性)的经验。”(巴尔,第122—123页)
1918年他在莫斯科创作了一个被称为“白上加白”(White on White)的系列作品,包括一幅白底上画上一个纯白方块的画。在纯粹性方面,这些画作似乎对应于数学家将所有数学问题还原成算法,又将算法还原成逻辑的努力。但是,在这种“几何”艺术背后,潜藏着一种情感的重负,这也许可以从一组相关的,标题为《金属声音的感觉、飞行的感觉、无限空间的感觉》(Sensation of Metallic Sounds, Feeling of Flight, Feeling of Infinite Space)的画作中来加以判断。即使是在名为《构成》(Composition)这样的画作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抽象的形式特征是如何依赖于想要在一种具体的时尚中,将古老的绘画实践那种主观的、专业的元素加以孤立和外化的欲望之上;如何依赖于倒过来发端于艺术家的冲突和不安全感的欲望,以及将艺术视为一个绝对的私人领域的观念的欲望之上。巴尔分析了由两个方块构成的一幅画,将它视为一个“等价物的练习:红色的方块,较小但在色彩上更强,在其对角线的轴线上也更活跃,是自我彰显的,而在它的背景中则是那个黑色方块,它更大,但在色彩上更沉稳,在位置上也更静态”。尽管巴尔将这类绘画刻画为纯粹抽象画,以区别于几何设计(这类几何设计完全来自某种再现),他却忽略了这幅画与马列维奇另一幅画,即同样复制在他的书里的《提水桶的女人》(Woman With Water Pails, 1912)之间的联系。这个以立体派的风格设计出来的农妇,肩挑一副水桶,正设法保持平衡。在这里,对作为一个基本的美学原理的平衡——这个原理主宰着两组对立的因素之间的关系——的关切,体现在一个“基本的”风俗画的主题中;被平衡的对象不是人,而是被悬置的、无机的元素,以及含混不清的形式。尽管人的主题只是虚幻的,而且被伪装在立体派的方法之下,对挑水的农妇这一母题的选择,仍然泄露了一种性兴趣,以及艺术家走向其独特的抽象风格的情感语境。
艺术家作品的主观条件在抽象风格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立体派艺术与前立体派艺术之间的相应关系中,也许可以得到证实。在创立立体派之前,毕加索充满忧郁地再现了马戏团演员、小丑、演员、音乐家、乞丐,通常身处社会边缘,却自得其乐;或者在自行排练,就像那些远离公共演出舞台的波希米亚流浪艺人。在一幅画里,毕加索画了两个正在做平衡练习的杂技演员,一个已经成年,体格强壮,虎背熊腰,稳稳地坐在跟他的身材一样结实的立方体石头上;另一个年轻的姑娘,非常瘦削,只是一个勾勒出轮廓线的、未经立体塑造的形式,正踮着脚尖在一个圆球上练习平衡动作。对杂技演员来说极其重要的平衡经验,他的生命本身,在这里被融化进艺术家的主观经验之中,这位艺术家204是个关注线条与块面的调节,将它们视为其艺术本质的专业表演者一而这正是使他从社会当中疏离出来的形式化了的个人活动,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生命。在他的艺术与立体主义作品之间(在立体主义作品里,形象最终消失,且让位于乐器、酒瓶、扑克牌及其他可操纵的人造物品的细碎的几何元素),还存在着一个黑人人物阶段,人物相貌在其中被扁平化为原始的或野蛮人的脸,身体则被简化为由粗劣的、夸张的线条所描绘出来的无人格的裸体。这类人物形象的类型并非来源于生活,甚至不是来源于社会的边缘,而是来源于艺术;但是,这一次,它来自一种部落的、孤立人群的艺术,在别的地方被认为低于西方人,仅仅被当作富有异国情调的景观或供人消遣的对象。只有画家们将他们视为纯粹的、未经毁坏的艺术家,凭本能或土生土长的感受力创造艺术。
根据这种分析,我们很难接受巴尔对马列维奇之走向抽象的解释:“马列维奇突然预见了欧洲艺术向着其迈进的那个逻辑的和不可避免的结论。”也无法接受他在白色画底上画一个纯白方块的解释。
2. 在其出版于1912年的著作《论艺术的精神》(Uber das Geistige in der Kunst)里,最早创作出完全抽象的画作的画家之一康定斯基,不断地谈到内在必然性,并将它视为选择形式要素的唯一决定性标准,正如内在自由,他告诉我们,乃是伦理学的唯一标准一样。他并没有说再现已经穷尽了,而是说,物质世界是虚幻的,外在于精神的;他的艺术则是对现代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反叛。所谓唯物主义,他将科学和社会主义运动都包括在内。“当宗教、科学和道德(经过尼釆的最后一击)已经分崩离析,当外部基础即将倾圮,人类的目光就离开了外部,转向他的内心。”在他那个时代,正如他自己的兴趣以及有类似动机的人们的兴趣一样,他也尊重神秘主义、通神学、对原始的东西以及种种“通感”实验的狂热崇拜。有色彩的听力(通感的一种)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感知在那时已经模糊并集中在感知者当中,而不是等同于一个外部来源。他更有美学价值的评论通常是出于这种态度写出的。“草地上的绿色、黄色和红色的树,只是……树的一种偶然的物质化形式,当我们听到树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内心感受到这些形式。”在描述他最早的抽象画的时候,他说:“这整个描述主要是对画作的一个分析,这幅画是我在一种强烈的内在紧张的状态中相当下意识地画出来的。我感到的某些形式的必然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记得当时我大声地自言自语,给自己下命令,例如‘这个角落必须画得重些’。观众必须学会将这幅画看作是对一个心境的图画再现,而不是对外部对象的再现。”(巴尔前揭书,第66页)
最近他又写道:“在一幅画里,一个点有时候比一个人物形象能告诉人们更多的东西……人类已经发展出一种新的官能,使他得以超越自然的外表,触及其本质,其内容……画家需要小心翼翼的、安静沉默的,几乎无关紧要的对象……拉奥孔身旁的苹果是多么安静沉默啊。一个圆圈甚至更加安静沉默。”(《艺术手册》第6卷,1931年,第351页)
3. 现在我引用走向抽象的艺术家们的第三种公开声明,但这一次是一批富有攻击性的艺术家,意大利未来主义者,他们很难被说成有逃离世界的欲望。
“我们从意大利发布这份革命的、爆炸性的宣言,以此我们在今日成立未来主义者团体……我们赞美任何形式的原创性、大胆和极端的暴力……欣悦和感激每天的生活,为科学的凯旋不断地迅猛地加以改变……一辆飞奔的汽车要比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还要美丽。”(巴尔前揭书,第54页)
巴尔无视马列维奇和康定斯基艺术中道德的和意识形态方面,但他无法不注意到意大利未来主义运动与柏格森、尼釆,甚至法西斯主义的联系;在分析未来主义艺术的形式时,他试图表明它们体现了宣言中所肯定的那些品质。
但是,如果说未来主义有着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方面,那对巴尔来说就不可能是纯粹抽象艺术。它“近乎抽象”,因为它显然指涉了画布外的世界,而且仍然带有再现的因素。
然而,“纯粹的”抽象艺术的形式,看来确实不带任何再现的或逃避主义病态的痕迹——蒙德里安的新造型主义作品以及后来的构成主义和至上主义的设计——但是它们在其作为肌理和形状的材料方面,在其精确的表现品质、非个人化的光洁和干净(甚至在其设计的微妙的随意性)方面,均受到了有关机器的流行观念和准则的影响。
然而,无论是未来主义还是“更纯粹”的机器抽象形式,都不能被解释为只是既存技术的简单反映。尽管机器在古代就已经存在,而且在某些国家的最近一个世纪里占据生产的核心地位,这种艺术却是过去25年里独特的现象。19世纪中叶,当机器早已被认为是现代工艺的伟大成就,优于当时绘画之时,进步的工业家们的趣味则倾向于写实艺术,蒲鲁东还能将库尔贝的绘画和最新的机器当作真正的现代作品来加以赞美。甚至,某些艺术家个人对机器的痴迷,也不一定会导向一种机器抽象形式的风格;阿历山大•内斯密斯(Alexander Nasmyth)、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和萨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大抵都是自然主义画家,和现代技术的先驱者之一列奥纳多一样。机器哲学时代的法国艺术,亦即17世纪的法国艺术,占主导地位的也是理想化了的自然主义人类形象。而在非机器的罗可可风格主宰法国的时期,人作为一台机器的流行观念也被其捍卫者们和批评家们等同于一种就事论事的感官主义。《人是机器》(Man the Machine)—书的作者拉•梅特里(La Mettrie)的论敌们会兴高釆烈地指出他死于暴饮暴食。
更为重要的是,晚近拥有最先进技术的发达工业国家,美国和英国,并没有产生机器抽象的风格;这两个国家的建筑在采用功能主义的抽象形式方面,也是最落后的。另一方面,这类艺术的发展发生在俄罗斯、意大利、荷兰、法国,以及后来的德国。因此,将艺术解释为对既存机器的反映,显然是不充分的。首先,它不能解释当技术已经拥有一种国际特征之时,各地的“机器风格”却呈现出种种差异。在底特律,里维拉(Rivera)画的机器壁画乃是作为工人的工作世界的写实的工厂形象;而在巴黎,莱热却打碎了机器的各种要素,将它们组合成立体派的抽象,或者将富有生命力的事物当作典型的僵硬的机器形状;达达主义者则用机器人或重新构造的人来即兴地创作无厘头的嬉戏之作;在荷兰,新造型主义建构准建筑单元的作品;在德国,构成主义一至上主义的形式模仿机器设计者的素描和模型,而不是描绘机器本身。而与众不同的未来主义者们,则试图重新体验运动中的机器及其能量和速度的那种稍纵即逝的一面。
这些差异并不只是不同地方的艺术传统在共同的现代材料上发挥作用的结果。因为,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意大利发现一位蒙德里安,难道意大利不是拥有刻画精细的形式的文艺复兴传统么?同样也可以在荷兰和英国发现未来主义者,难道荷兰和英国不是印象主义的先驱者所在地么?
同样的批评也可以适用于相应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抽象来源于现代金融制度的抽象性质,在这种金融制度中,控制资本和人们交易行为的一叠纸张,釆用了在数字和标题上操作的形式。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最先进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是最晚出现抽象艺术的地方之一。
机器抽象形式在现代艺术中的兴起,并非因为现代生产釆用了大机器生产的方式,而是因为人类与机器被不同社会中相互冲突的利益和情境所投射的意识形态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因此将人视为机器的现代观念,强调的更多的是其经济学的含义,而非生物学的含义。它指的更多的是人类机器,而不是人类动物,并且暗示了对身体运动的有效的控制,并且臣服于某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外在目的。而这就与古老的机械观大为不同:这种古老的机械观关心激情,用内在的机械力量来解释它们,有时候还从中推导出一种愉快、实用和利己主义的伦理学。
当巴尔将未来主义的一个分支归结于他在巴黎的经验时,他意识到208了当地条件的重要性。但是,他并没有费点心思来解释为什么未来主义会出现在意大利,而不是别的地方。意大利作家将它描述为对翁贝托(Umberto)统治期间意大利盛行的传统主义和昏睡症的一种反动,在这么做时,他们忽略了这种反动的正面价值及其对意大利人的生活的影响。意大利的落后最强烈地被当时的人们感受为一种矛盾,而且成为1910年前最令人气恼的话题,特别是在北方,那里刚刚经历了最快速的工业化过程。那时意大利资本主义正在准备发动在特里波里的帝国主义战争。意大利,这个资源贫乏却要在各个帝国中竞争的国家,急切需要扩张以达到那些资本主义强国的水平。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削基础上的工业发展的滞后,加剧了文化上的不平衡,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随时准备进行帝国主义冒险。与此同时,作为对这个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古老历史环境的急剧变化的反应,意大利还涌现出了过程和实用哲学——一种夸张的反传统主义特征的军事实用主义。已经获得了新的能力和现代城市利益的中产阶级接受了新的条件,将它们视为进步的和“现代的”;他们在抛弃意大利的落后,召唤一个跟上时代步伐的、全民族觉悟的意大利方面总是大声疾呼。知识分子对地方上的贵族传统的攻击,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一致;他们将技术进步、富有攻击性的个性和价值相对主义,提升为一种有利于帝国主义扩张的理论,并且用古老与现代,或者过去与未来的抽象的意识形态对立,来模糊帝国主义的矛盾后果以及阶级之间的真正冲突。由于意大利的民族意识长期以来建立在她的博物馆、古老的城市和艺术遗产之上,因此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必然会带来一种文化冲突,而在艺术家们当中,这种冲突釆取了最为尖锐的形式。作为现代生产中最先进的工具,机器对艺术家们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些艺术家早已对只有传统和次要地位,在一个落后的地方性的意大利国家中看不到希望的状况感到绝望。他们热衷于机器,并不是因为机器是生产的工具,而是因为机器代表了现代生活中的动力的来源。当对工业化过程的感知导致直接参与其中的工人们走向一种激进的社会哲学之时,跟小资产阶级一样与生产相脱离的艺术家们,却只能抽象地或仅仅从表面上,仅仅从其产品和外表,在新的交通形式、汽车、铁路和新城,在城市生活的节奏,而不是在其社会原因中,来理解这一工业化过程。因此,未来主义者开始将这一运动理想化,他们将这个运动感知为,或者将运动概括为,主要是一种机械现象;在这种感知和概括中,对象的形式变模糊了或者被摧毁了。一辆汽车的动力系统、转动着的运动、运动中的“长犬”(拥有20条腿——按喻指火车)、小汽车、空间中的形式演进、战争中的装甲车、舞厅——这些都成了未来主义艺术的典型主题。他们的画布上充斥着放射线、无处不在的力量的象征性刻画、冲撞和相互渗透的物体。在印象派绘画中,运动只是休闲娱乐的景观的一部分,而在未来主义作品里,它却是急切而又充满了暴力,是战争的先驱。
未来主义的某些手法,有关抽象及交互渗透的形式的更为宽泛的观念,无疑来自立体主义。但是,重要的是,意大利人认为立体主义过于审美化,过于理智,缺乏运动的原理;但是,他们却可以接受立体派分解稳定的和清晰划定的形式这一做法。这一点拥有一种直接的意识形态价值,尽管从本质上说它只是一种美学手段,但是在未来主义者看来,稳定和清晰的形式等同于古老的意大利艺术,因此也就等同于过去本身。
在意大利之外,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一种僵硬的建构对象的机器的质量,机器产品的质量以及工程师设计的质量,对画家来说都意味着不同的形式,甚至意味着其作品的更为宽泛的表现特征。古老的艺术范畴被转化为一种现代技术的语言;本质被等同于效力,单元被等同于标准化了的要素,肌理则被等同于新的材料,再现被等同于摄影,素描被等同于规则的或带机械痕迹的线条,色彩被等同于颜料的底漆,设计则被等同于造型或指导性计划。画家们于是将他们那种无用的古老活动跟现代生产的最先进技术和强化形态联系起来;正因为技术被抽象地认为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带有它自己的内在条件,而设计工程师则被认为是现代世界的真正的缔造者,因此,从他们较早的表现主义、立体主义或至上主义的抽象,走向更为技术性的风格,就不再是跨了一大步。(甚至康定斯基和马列维奇20世纪20年代也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改变了风格。)在将其设计方法适用于建筑、版画、舞台和工业设计时,他们仍然是抽象艺术家。他们经常将其作品看作是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抽象计算的美学上的对应物。假如他们也承认一种幻想艺术的替代方案——在某些方面也与他们自己的艺术正式相关——那只不过是作为自由的一个正常区域,或者是对他们自己那种强大效率的有益身心健康的放松罢了。与未来主义者不同(他们的进步概念是盲目的叛乱性质的),他们希望通过清醒的技术和设计的逻辑来重建文化;带着这样的希望,他们认为自己是生活新秩序的不可或缺的美学先知。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更多的人与德国和荷兰带有社会民主倾向和自由倾向的建筑师们合作。他们关于技术在艺术中的规范作用的观念,一方面主要受到战后欧洲工业的严厉的理性化过程的限制(这个过程的主要表现就是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将其视为受到美国威胁的落后资本主义的唯一希望),另一方面,也受到改良主义幻觉的限制(这种幻觉因战后经济困局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繁荣而大为走俏)。这个幻觉就是: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住房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成本中大显身手的先进技术,将会解决阶级冲突,或者在技术人员的效率习惯和经济计划中,至少有益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建筑还是要革命!这事实上是建筑师、画家和《新精神》(L’Esprit Nouveau)杂志的编辑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口号。
随着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到来,埃里•福尔(Elie Faure)之类的批评家号召画家们放弃他们的艺术,改行做工程师;而美国及欧洲的建筑师们,对不断增长的经济压力非常敏感,却弄不清是什么原因,他们都要将建筑等同于工程学,否定建筑师的美学功能。在这些有技术官僚倾向的改革者们都共同拥有的、极端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乐观的机器意识形态在现代文化中的崩溃。当生产受阻,生活水准下降,艺术就以技术进步的名义被放弃。经济危机期间,机器抽象风格成了次要的风格。它们只影响到了极少的年轻艺术家,或者说,他们倾向于巴尔称之为“生物形态抽象”的东西,倾向于狂暴或神经质的书写,或者倾向于在空荡荡的空间里蠕动的变形虫式的、柔软的低等生物。一种反理性主义的风格,即来源于1917年至1923年时期的达达主义艺术的超现实主义,成为主导风格。除此之外,还兴起了新的浪漫风格,充满了空洞的空间、骨架、奇形怪状的生物、废弃的建筑物和灾难性的地球形态等等悲惨形象。
选自《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
沈语冰、何海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