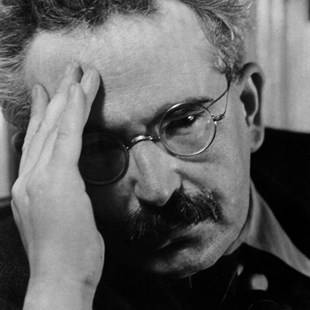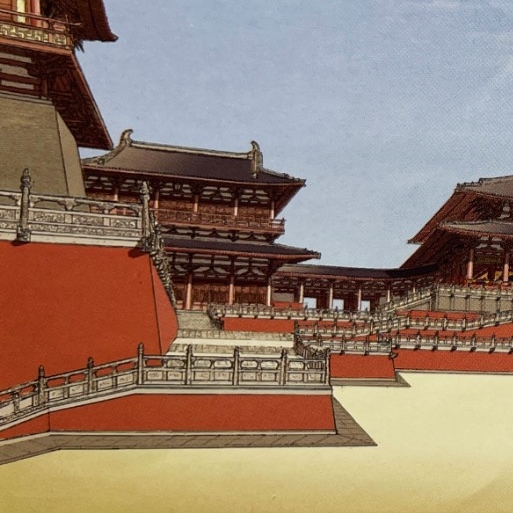空间有观看的方法,这么说的话看起来似乎空间中有视觉的参与。当你进入其中,它就在那里,它一直在等你。【1】
詹姆斯•特瑞尔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特瑞尔创造了作品中丰富的躯干,多次通过在空间中暴露光的物质性提出关于感知的性质的见解,他的闪烁而转瞬即逝的装置激起了白日梦的力量,通过最简手段——如果更严格地从技术层面来说——吸引观众进入一种光芒四射的氛围之中。为了古根海姆的这场展览,特瑞尔按照他最具扫荡性的大型项目的惯例彻底改变了博物馆。赖特的圆形大厅头一次只能被人们从下面体验,大量空间在头顶漂浮,而不再是透明的、可以看穿的。除了艺术家用来揭示和增强空间的光亮性质的结构之外,没有物体占据大厅。《太阳神阿顿的统治》重新具体化了特瑞尔对他所谓“非间接经验艺术”的强调,尽管它是特瑞尔安装过的最大装置之一,但它给每位观众带来的是精致、深刻的遇见,带来的是光线、色彩与空间的狂喜。就像特瑞尔曾经说过的那样:光是强大的物质,我们和它有一种原始的联系,但对于如此强大的事物来说,它在感觉上的存在是脆弱的,在质料允许的范围内我尽可能多地去塑造它,我希望达到这样一种状况,我带着你,让你去看,让它成为你本人的体验。【2】
特瑞尔的创作背景不仅包括视觉艺术,也有心理学和数学,他比大多数艺术家更多地考虑了科学和艺术之间的界限。特瑞尔曾经说过他的实践本身不是科学的,相比回答问题,他对提出问题更感兴趣。【3】尽管如此,长期以来他一直更多地作为科学家来处理这些问题,析出一个既定的形式或现象来作为调查重点,合理地分析其特点。多年来,特瑞尔都在根据具有广阔类别的个人分类学进行艺术创作,这种分类基于结构上和感知影响的相似性。他通常为那些大而直线型的空间——其美学研究实验室的中间地带——设想某些装置类型(比如“黑暗空间”[DarkSpaces],“甘兹菲尔德”[Ganzfelds],“空间分割系列”[Space Division Constructions])。尽管一个给定系列的每个作品都是唯一的,但每组作品发展的连续性使特瑞尔可以依次通过一个变量来创作,来检测每个调整是如何改变整体的感性经验的。如果一个实验产生了特别引人注目的结果,一个新的系列就可能出现(“楔形系列作品”[Wedgeworks]就是从“浅层空间结构"[Shallow Space Constructions]系列中发展出的),如果一个系列的可能性已被耗尽,它就可能会被抛弃。这种几乎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迫使许多作者围绕着某个连续的系列来研究特瑞尔的创作,这是一种由艺术家的自我书写暗中支持的方法。【4】
特瑞尔详细提出这种发展角度是在1966到1974年之间,他在位于加利福尼亚海洋公园的前身是曼德酒店的工作室里创作了一个开创性的系列,在这期间,他只参加了一个公开的展览,即1967年在帕萨迪纳美术馆举行的展览,因为这个展览相对独立而且可以由他的工作室进行装置操控。他最早的作品名为《墙角投影》(Cross Comer Projections),采用高强度的投影来创造充满活力的几何形式,它们看起来在空间里盘旋,但如果仔细审视的话就会发现是光跨越两个墙壁交界处的简单平面。它们中的第一个作品是《阿福鲁姆I(白色)》(Afrum I [White],1967),它的形状是一个发光的白色立方体,悬浮在房间墙角的半空中,后来的作品改变了立方体的轴心及其与地板的关系。之后,特瑞尔将在版画系列《第一缕光》(First Light,1989—1990)中描绘这些立方体的变化,连同基于金字塔式的、楔式的、水平的等其他光的形式。1968年,特瑞尔开始使用戏剧凝胶来过滤光,探索颜色可以产生什么变化,他不认为这些作品是幻觉,因为“你看到了什么,事实就是什么”,这是光的物理表现,我们总不是单纯地去看,而是训练我们的眼睛【5】,使它变得过于便利以致不能看穿事物,他坚持所选材料的真实存在、合成物的不可分割的形式,他的一系列创作模型显示了与像丹•弗莱文(Dan Flavin)、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这样的极简主义艺术家实践上的相似性,和这些艺术家不同的是,特瑞尔彻底放弃制作客体,并且不强调创作过程和任何潜在的概念框架。就像他在1988年说过的那样:“这不是极简主义,也不是概念作品,这是感知作品。”【6】
或许我们最好将特瑞尔与极简主义之间的关系理解为重点的转移,在策展人兼批评家约翰•科布兰斯(John Coplans)为特瑞尔1967年展览设立的主题里,他引用了莫里斯对艺术的号召:“让关系离开作品,让关系仅仅成为空间、光和观众视野的一个功能。”【7】当然,投影会使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们所站立的空间里,但他完全拒绝了客体的覆盖,这就比莫里斯走出了更远的一步,就像他在1993年写的那样:“首先,我不和客体打交道,感知就是我的客体;其次,我也不和形象打交道,我想避免联想的、象征的思维;第三,我的作品没有重点的和特别的地方要看。没有客体、没有形象,也没有重点,那么你在看什么?你在看你的观看,这是在回应你的观察以及看到你自己在看什么的自我反省行为,你可以通过眼睛观看的触摸使感觉延伸出去。”【8】
离开“墙角投影”这个项目后,特瑞尔越来越试图以更充分地融入建筑外围来消除他作品中明显的客体。尽管使用了相似的技术和感知原则,为了改变整个房间,他的“单墙投影”把光投射在一个单一的平面上,比如《普拉多(白色)》(Prado[White],1967)中墙似乎消失了,创造了一个通向远方未知空间的通道。相比较“墙角投影”,这些作品更多地体现了特瑞尔的主张,即他的作品与其说是绘画,不如说是雕塑。在把光投射到墙的平面上的时候,这些装置创造了一种形象的关系,同时又具有深度内涵,这些都随着观众视线的变化而摆动。“浅层空间结构”(Shallow Space Constructions)转换了这种策略,用光来建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建筑,《罗宁》(Ronin,1968)是这一系列的第一个作品,它紧跟着“单墙投影”中的一个作品《托林(白色)》(Tollyn [white],1967),在《罗宁》中,一道有锋利边缘的假墙占据了房间的一个垂直角落,在实际存在的墙和新的墙之间造成一个缝隙,从后面照亮的时候,这个裂缝看起来就像是实体面,阴暗的墙消失了。如果这种环绕实体墙的断裂扩大的话,产生的影响将会更为强烈,就像在《雷泽尔》(Rayzor,1968)中那样,或者,更近一点说,像在《双重伦多》(Rondo Double,2011)中那样。像之前的投射作品一样,这些装置都拒绝物理和感知空间之间的界限,培养一种特瑞尔所谓“建筑空间”的东西,在这里,观众将把光和空气理解为弥漫的笼罩的物质存在。
在门多塔,特瑞尔发现他可以密封每个房间,使其与外部的光隔绝,并消除尽可能多的建筑内部细节来产生更强烈的效果。特瑞尔使这些墙、地板、天花板像是被钛白漆穿上了光滑的外套,移除了原有的附着物、模塑和电器插座,只剩下他可以完全控制的纯粹的矩形空间。设备和光的固定装置被完全从视野中隐藏起来,鼓励观众通过自己的感知功能去解释那些看到的东西,而非通过技术,这种变化了的模式将成为特瑞尔未来几年装置的基础。米温•夸恩(Miwon Kwon)认为这种“无缝结构”将他与同时代的艺术家区分开来,在这基础上,他还提出,“那些白色立方体的中性色实际上是不够中性的”【9】特瑞尔不关注那些画廊或博物馆由来已久的特性,而是破坏其权威,把它们归并到他的感知场地。通过压制一些偶然的细节,特瑞尔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建成环境的界限转移到它们之间的空间之中,在这个竞技场里,观众们或许可以开始通过整个身体而非仅通过视觉来体验光。
像《阿福鲁姆I(白色)》(1967)这样的作品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投影形式,而是包含非结构的周围环境在内的整体空间布局,1970年,卫乐比•夏普(Willoughby Sharp)发现特瑞尔“打破了创造强烈审美体验时对物质客体的需要……对环境的感知成为体验作品时整体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将其作为背景来认识”【10】就像阿伦•卡普罗(Allan Kaprow)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把抽象表现主义绘画扩展到环境和行为上一样,特瑞尔把极简主义的形式语言扩展为明确的以时间为基础的格式,要求观众的充分参与。科普兰思(Michael Fried-Coplans,艺术论坛的共同创始人之一)曾经向特瑞尔介绍了迈克尔•弗里德(Michael Fried)对极简艺术的尖锐批评一一“艺术与实物艺术”,特瑞尔似乎遵循了弗里德的建议,他试图创造一种关于光的体验一一这种体验“按照定义的话事实上要包括观看者”,而且这种体验的“持续时间”是“无尽的、模糊的、连续的”【11】他的投影和“浅层空间结构”系列都通过否定瞬时理解以及为观众在空间里的移动提供显著不同的体验而强调了时间性。
借用弗里德带有嘲弄意味的术语来说,这种“戏剧性”充分体现在特瑞尔的《门多塔旅馆里的停止符》(1969一1974)装置中,其中包含一组光的体验的改变,他通过探索单一的、中性色的空间如何回应光线条件的变化扩大了其感知研究。更重要的是,特瑞尔的这个作品也标志着他第一次尝试将外界的光线融入密闭的空间,在白天和黑夜这两个分开的部分里,他战略性地将工作室开放在附近的交通灯、霓虹灯、过往车辆的大灯和春分前后的太阳(白天)这样一些光源下,构成了持续2-4个小时的体验。特瑞尔把自己的装置不仅当成根据内部系统进行的环境操作,而且也当成积极应对外部刺激的实体。他提出了“感知空间”的概念,将其描述为一个空间向另一个光源空间的开放,光通过开口大量扩散。由于所有的光都来自另外一个空间,感知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该空间的一种表达方式。【12】
在《门多塔旅馆里的停止符》中,海洋公园工作室以最原始也是最短暂的方式表现了这种表达力,之后的“观天空间”和“空间分割”系列将会充分实现以下这些可能性:前者通过拆除建筑物屋顶的一部分来创造一个同时是室内和室外的房间,后者则利用带有孔洞的隔墙将画廊分成两个不同的空间。这些装置形成了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所谓的“观察室”一一搭建平台表面上是为了看向另一个空间,实则将观看体验本身作为启示。【13】特瑞尔把他的中和策略转移到私人画廊、博物馆和收藏家的家里,建筑上的变动可以视为对空间进行光敏处理和“调音”的方式,就像他先前从管风琴技术中挪用的“停止符”一词所暗示的那样。事实上,考虑到特瑞尔对“把我们带到这里的乐器,以及乐器带我们所到的地方”的一定兴趣,我们应该把每个装置当作光的共振器,它们会依据尺寸、形状、体积产生反应,尽管它们也要和其他同类一样符合某些结构原理。【14】因此,尽管“观天空间”可以在天花板的自由视野里随处存在,向天空开放呈现的是圆形还是方形、大还是小、离地面高还是低却都要依赖所在的房间和外界光线的情况。
有时,特瑞尔会选择搭建独立的结构,来满足装置项目的特殊需求。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这些独立空间包括了从形状为立方体或圆柱体这样简单实用的结构到建筑特性不再由所处位置决定的更为复杂的设计。比如,特瑞尔最近完成了《阿格瓦•德•拉茨》(Agua de Luz,2012),这是一个在尤卡坦丛林深处的金字塔,观众可以体验到甘兹菲尔德系列之一——身临其境的无缝环境,使游客陷入色彩的迷失领域,而且作为一个由屋顶水池包围的观天空间,它没有感知上的限制。玛雅金字塔像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同时期其他建筑一样,主要用于天文观测,充当太阳和月球事件的观测台和记录地。特瑞尔认为这是第一个感知空间,在外部光线中产生了一种内在体验。【15】他还建立了在不列颠群岛发现的史前凯恩斯以及东亚东南亚佛塔基础上的结构,通过将自己的独立空间置于这些古老的建筑风格之中,特瑞尔将光作品的时间经验与人类古代的宏伟规模相结合,引用了特定地点的遗失了的、几乎是神话般的历史。在这些作品中,艺术家保持甚至扩大了对其装置的中性色区域的控制,同时构筑了本身远离中性的象征性、概念性习语的空间。
在工作室之外或者他设计的建筑之外工作时,特瑞尔经常不得不考虑到一些场所没有理想条件。虽然他坚持超越惯例,但仍然存在着某些结构性局限。他说过:空间不是中性的,其中的一些比其他的更复杂,它们越复杂,中性就越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对这些场所做岀反应,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作品。【16】因此,1982年,特瑞尔在西雅图艺术中心将承重柱纳入了三方空间分割装置《阿姆巴》(Amba)中,次年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中,类似观天空间的《霍弗》(Hover)、《蓝色行走》(Blue Walk)和《红色绕圈》(Red Around)(均创作于1983年)的光的环境占据了博物馆独特的弯曲走廊和天窗。他组合了硬结构和半透明牛皮纸来设计这三个部分,使日光和电灯混合起来,在布置上不同于古根海姆的那个装置。这些作品的混杂性质源于他们所在空间的不寻常特质。与科学研究一样,特瑞尔作品的逻辑进程也充满了偶然性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特瑞尔通过调整其他更“纯粹”的装置的特征来检测出新的可能性。
对于特瑞尔来说,他把放置装置的建筑最终当作贝壳,为其中发生的内部经验设定条件和背景。“它不是制造存在的结构,它创造和定义了背景,”特瑞尔说过,“光如何进入空间,结构如何达成这一效果并创造出作品.作品都关于观看,对观众负责。”【17】在古根海姆,日光从博物馆的眼睛进入,远高于观众的头顶,特瑞尔的新作品通过覆盖天窗的外环、通过更收紧的中央孔洞汇集了光亮,光从这里倾泻到从博物馆天花板上悬吊下来的巨大组合的最深一层。像在其他复杂的空间中一样,特瑞尔围绕建筑的特性(和特色)设计了《太阳神阿顿的统治》,确定了与建筑物中心的空隙相关的装置形状和尺寸。这个装置把LED灯具(发光二极管)排成一系列环状物,使五颜六色的五个同心椭圆环绕着日光的核心,回应博物馆螺旋结构的模式。无论装置的基础系统有多么复杂,它们的作用很简单:让观众以全新的方式来感受古根海姆现有的空间。
《太阳神阿顿的统治》是特瑞尔设计的最大的感知空间之一,它使用的大量的电灯止人想起了令人身临其境的《甘兹菲尔德》,但在古根海姆,人们仍然处于这一领域之外,从公共的观赏空间来吸收光的视觉和情感力量。这个区域和这个作品的垂直定向让人回想起观天空间系列,但是这系列的作品从根本上依赖于无中介地暴露在天空之下的状态。《太阳神阿顿的统治》非常近似特瑞尔为伦敦千年体验博览会创建的混合装置。《夜雨》(2000)由一个椭圆形的房间组成,这个房间在高处通向一个不断在蓝色、红色和紫色之间变换的区域,批评家阿德里安•塞尔(Adrian Searle)将这个作品描述为“像透过一片薄云看太阳,或是黎明出现在天空中错误的地方……朦胧的光线以奇妙的颗粒状的、可触知的微光充满了整个房间……装置确实对你发生了作用,它在你的头脑中留下了斑点似的关于颜色的记忆”【18】。由于技术的进步,《太阳神阿顿的统治》改善并扩大了《夜雨》的效果,使用了更加复杂和强烈的颜色排列。古根海姆的背景决定它明显占用了更大的空间,而不是更加混乱的展厅。
或许《夜雨》和《太阳神阿顿的统治》最有力的先例在特瑞尔的“空间分割”系列里,观众们在没有身体参与的情况下通过一个大的开口观察感知空间。在这个系列最早的装置之一《里塔尔》(Litar)里,矩形孔洞看起来像是另一面中性色墙壁上坚实的灰绿色嵌板,不过,随着观众的到来,像嵌板的东西慢慢获得了一种深层次的感觉,一种朦胧的气氛注入了墙后难以测定的空间,观众们对开始时环绕的光部分地视而不见,察觉到另一边空间的特性与他们所在的空间有很大的不同。感知的肌肤在穿过孔洞产生了,它尽管是无形的,但仍然是物质的,单单由两个空间之间光的变化而产生在眼睛之中。之后的《夜路》等作品在感知空间中加入了电光源而有了更大的色彩范围,《里塔尔》(Litar)引人注目的地方则在于它仅仅使用观众空间的环境光形成了这个边界。这个感知空间“本身没有任何东西,像摄像机一样看向另一个空间,它通过一个开口或是孔洞来从另一个空间获取所有的能量……房间不是空的,有东西在那里——其光线的特质和你所居房间的光的特质非常不同”。【19】
从特瑞尔曾表示过的对于视觉仪器的兴趣来看,他求助于相机不是巧合。在几次采访中,他都用照相机来解释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他也已经在众多装置中明确地纳入了相机暗箱。《门多塔旅馆里的停止符》装置中有些运转要依赖于面向海洋公园城市灯光的小孔所产生的投影,《罗登火山口》计划至少有一个空间将包括沙漠天空的类似图像。最近,在独立空间《第三呼吸》(2009)这一装置中,安装在观天空间地板上的镜头把一幅天空的图像投射到下面黑暗的房间中,重现了十九世纪许多相机暗箱的表格格式。当然,暗箱的历史更长,要追溯到数千年前;启蒙运动时期它在西方哲学中变得尤为重要,出现在了笛卡尔、洛克、开普勒以及牛顿等人的著作中,据文化史学家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介绍,在十七、十八世纪,暗箱呈现了“界定和确认观察者和世界之间关系的重要意义”,将感知主体确定为“孤立的、封闭的、独立的、个人的”【20】,人们的身体和感官经验被机械设备和预先给定的客观真理世界之间的关系所取代。在暗箱那个漆黑、空荡的房间里,根据自然规律投射了外界现实的图像,形成了感觉本身的类比,在一个注视着的内在的眼睛之前,理性的光芒清晰地闪耀出来。投影由小孔这个精确又奇特的点产生,提升了其逻辑上的权威。站在暗箱中,观众接近观看的那个点,但仍然从根本上与其分离,无形中观察着小开口对面墙上现实的表演。
当然,当代和启蒙运动时期对于主体性的概念被一些复杂的认识论转变分离了,但特瑞尔在讲述中转向启蒙运动典范来了解世界和人类所在,这事实上是很卓越的。尤其在他的空间分割系列中,特瑞尔对暗箱的经典结构做出了两个重要的调整。首先,他从根本上扩大了孔洞,使得没有图像被投影,而是“通过将空间及其体积与将要穿过的光能相联系,使光在整个空间中到处扩散”【21】。这使得感知空间可以在没有特定聚焦对象的情况下表现进入的光的性质。其次,虽然启蒙运动时期暗箱的概念只涉及先验的观众,但特瑞尔创造了一个与相机(感应空间)和外部世界分离的限制性观看空间。这种空间的不确定状态削弱了历史上与相机相关的掌控感。由于不确定看到了什么,观众的理智试图通过已有的感知惯例来整合现实,把感知空间交替地当成一个平面、一个有雾的空房或一个空房间。
把这种体验解释为幻觉是对特瑞尔提出的基础性挑战的误解,像《里塔尔》这样的作品把感知视为一个时间过程,使用了几个世纪以来都用来促成感知是瞬时事件这样一个观念的结构。当意识到感知空间的深度后,观众就会后退,实体表面就会穿过孔洞重新出现,观众必须考虑到这两种观念在解释现实时同样精确这一可能性。不管是通过有意识的欲望、人文学习还是生理特征,我们的身体和思想都会选择理解周围环境的方式,在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之后,特瑞尔的作品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视觉的真实性不在“普通的生活中,因为它被隐藏在它自己的视觉对象之下,我们必须研究那些先于我们的眼睛进行分解和改造的特殊情况”【22】。特瑞尔称这种矛盾状态是作品的定律,指的是一些矛盾的掌故,禅宗佛教徒用它们来引发一种与十八世纪欧洲的猜测不同的启示。【23】他还声称“光中有真理”,所有的光都是通过特定材料在特定温度下燃烧产生的,暗示着某些超出经验事实的东西。【24】特瑞尔喜欢回顾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囚徒们坐在一个有火光的洞穴里,认为他们看到的阴影构成现实,事实上真实的现实超出了他们的感知能力。同样地,我们也是通过解释我们不完美的感知工具所接受到的信息来拼凑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的,就像科学家们基于百万年前从恒星发射出的光来收集关于宇宙的信息一样。对特瑞尔来说,真实在这些之外,它仅仅在超越理解时才能够被作为存在而感知。
这种模糊的存在是特瑞尔艺术的核心,他的装置鼓励一种冥想状态,从用全身感觉的物理过程形成的“看到正在观看的自己”的理智行为,转向某种更加原初的东西。特瑞尔把这种体验描述为“无言思想”的条件,类似于盯着篝火的余烬或者深深沉浸在书中的心灵专注。【25】“通过视觉的渗透进入空间,”他说,“你可以栖息在一个意识空间中,而不用身体进入,就像在梦中一样。”【26】和一本书不同,他的装置实际上是对这种情况的反应,就像“感知空间”一词所表示的,它意味着有些东西正在进行感知,“它就像相机的眼睛,空间以某种方式进行观看,以潜意识的方式进行观察……就像走进一个拥有这种特殊观察方式的大型相机的镜头。”【27】
读完这些评论,我们可以认为《太阳神阿顿的统治》像一个巨大的眼睛,盯着博物馆里的观众,并试图以其光明的力量将观众包含其中。以日光为核心,它甚至可能会让人想到传统上被视为天空中漂浮的眼睛的上帝的全能之眼。特瑞尔在为他的装置命名时向阿顿神(Aten)致敬,阿顿神是古埃及的神,代表着太阳圆盘向外发散光,象征着全知全能的、鸟瞰的视野。特瑞尔花了多年时间做空中摄影师,一再让人注意到他在飞行中花费的时间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都是非常显著的。然而,这些经验的定义方面却不是那么尽在掌握,而是陷入了深深的迷失中。特瑞尔讲述了“当你处于仪表飞行的时刻,你不知道东西都在哪里,你也不应该相信你自己认为的你在哪里”,并描述了“空间中的空间,并不一定由风暴、云层或其他类似事物所勾画”,而是由光的性质、观看、所在地区的空气性质所描绘。【28】如果说《太阳神阿顿的统治》模仿了天空之眼,其中旁观者的眼睛却远远超岀了上帝的眼睛,反映出我们自己有限的看法。
特瑞尔在飞行和航空摄影方面的兴趣与他的只能用杰作形容的《罗登火山口》(1979)有着密切联系,在用了七个月的时间飞越美国西部寻找理想的地点,用以对《门多塔旅信里的停止符》中的光学效应进行更为永久性的研究之后,他在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东北方向找到了这个熄灭的火山。在那里,艺术家正在创造出一系列的空间,展示包括太阳、月球以及遥远的星星和行星在内的“光中的’天体音乐’”【29】完成后,该项目将会包含特瑞尔各个主要装置类型的实例,并形成一个大型的裸眼天文台。不同于大地艺术的其他作品,尤其是迈克尔•海泽(Michael Heizer)和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的作品,《罗登火山口》的装置是地下的,使得火山口的表面保持相对不变。特瑞尔的目标不是为了联系自然,使自然与其交流,而是尽可能多地保存火山及其周边地区引人注目的轮廓和景观。《罗登火山口》独特地接纳和扩大了自然的光辉,成为特瑞尔作品的盛大显现,这是当代的纽格兰奇,人们可以像朝圣者一样在古老的自然景观中体验光芒的力量。
像特瑞尔一样,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也致力于与大自然的有机和谐——他的意思不是“把冲击眼球的外在方面视作一个场景的视觉形象或者相机的玻璃面,渗透于外在形式或文字的内在和谐才是决定性的性质”【30】。尽管两位艺术家及其作品有很多差异,但在特瑞尔的“无言思想”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赖特的“内在和谐”观念的影子。赖特对自然的看法可能基于美国超验主义的精神表露,但他意识到了它们在建筑空间中可能的改变。古根海姆对日光的彻底开放证明了这一点,它还结合了葱郁的种子形状的花盆、圆形大厅中提供流水配乐的喷泉。博物馆的早期设计包括屋顶天文台,中央圆顶和螺旋结构让人回想起未动工的马里兰舒格洛夫山的戈登斯特朗汽车公司和天文馆,在另一个未实现的项目中,赖特甚至计划在亚利桑那州流星火山口边缘建一个度假胜地,这个地方靠近罗登火山口(距赖特的第二故乡西塔里埃森也不远)。
赖特对美国西部开放景观有着始终如一的热情,这使他找到了一个最佳合作伙伴,古根海姆首位负责人希拉•雷贝,她是推动艺术非客观性的开拓力量,在一个早期的目录中,她曾经比较非客观绘画的沉思与“仰望星空的浩瀚,人们不会要求意义、象征、主题、感觉或知识上的解释,人们向上看,感受到广阔的美丽,当目光重新落回地面时,面对的困难似乎变小了”。像赖特一样,雷贝也支持几何形式的重要性,尤其是被天体启发岀的那些。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古根海姆建筑平面图中的系列重叠圆圈做出了贡献。事实上,行星和月球往往是椭圆形的。正如特瑞尔喜欢说的那样:大自然热爱椭圆形。他也注意到,我们的两只眼睛正好形成了椭圆形视野中的两个焦点。'【31】罗登火山口能够吸引特瑞尔注意的原因之一在于罗登火山口可以让他在一个曲线空间中进行创作,而不用牺牲对他的作品感知效果来说非常重要的中性。古根海姆提供了一个相似的场所,但是在《太阳神阿顿的统治》中,他就需要将圆形大厅的圆形形式重新配置为椭圆形。
特瑞尔在罗登火山口的首要任务是塑造火山口的边界,创作出沿着其略呈椭圆形区域的光滑而完美的水平边缘。倾斜站立的观众从下面可以观察到天空拱顶的现象,天空的形状从遥远的平面变成几乎有形的圆顶。在火山口的最低处,有一个孔洞通向“火山口之眼”,有一个圆形观天空间在下方。艺术史家马克•泰勒(Mark Taylor)将这个空间称为一种“迷失多于指向,偏离多于定位”的轴心,并且作为暗箱,使人产生了一种“实际上是在我自己的眼球里的奇怪感觉”【32】。尽管特瑞尔搭建的圆形观天空间不止一个,但由于其位于《罗登火山口》装置的核心位置,火山口之眼在特瑞尔的作品中处于首要地位。它是最“眼睛”的眼睛,是天空之眼,现代罗马万神庙供奉的不再是抽象的古代神,而是与大自然的交融以及人的感知行为。在古根海姆,特瑞尔遇见了这个与火山口相似却是人造的场所,谁又能对火山口广阔的、开放的形式或天穹的玻璃拱顶的模仿袖手旁观?即使从上往下看,博物馆的圆形形状也与城市无情网中的火山口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雷贝对博物馆进行委托时,她写道;“我要的是一个精神的寺庙,一座纪念碑!”赖特试图借助长久以来自己对非西方古建筑(特别是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古庙塔)的兴趣来满足这种要求。我们所知最早的一些建筑结构多用来进行天文观测,亚述古庙塔也是从神秘的巴别塔的灵感而来,巴别塔的建筑者们试图触及天堂,却使人们遭受了被不同语言分开的惩罚。对古根海姆来说,赖特创造了一个“乐观的亚述古庙塔”,转变了传统的形式,取代了对上帝的渴望以及分裂的社会,博物馆把天空拉低到共同空间里。设计围绕着两个交叉的核心——一个用来确定朝着街道标准缩小的外部,另一个则是在确定朝着日光逐渐减弱的内部,螺旋状向下直到圆形大地板。在回顾特瑞尔装置经验的一个描述中,建筑历史学家尼尔•莱文(Neil Levine)把穿过古根海姆的路径形容为“这是一条发现的旅程,通过这条路回到了知识和经验可以被再次利用并与他人分享的地方”。通过关闭俯瞰护栏的激进姿态限制观众的体验,特瑞尔孤立了博物馆这部分的设计,把圆形大厅改造成一个共同冥想、共同集会的场所。“我对人们通常看不到的东西感兴趣,”他说,“当你有了在其他正常环境中的体验,它就会呈现一种梦境的清醒,经验领域存在于我们文化感知的知识限度和我们的身体限度之间。因为作品也存在于这两种限度之间,它们与我们如何建构现实有关。”【33】
走在曼哈顿炎夏的街道上,观看特瑞尔展览的观众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梦幻般的状态。仰望古根海姆中央的孔洞,他们可能会感觉空间在回以凝视,日光的瞳孔被起伏的色彩包围。特瑞尔用《太阳神阿顿的统治》装置复燃了雷贝把博物馆当成寺庙的观念,把这一建筑改造成了人们可以沉思自己与宇宙的关系、沉思自己的感觉的地方。通过在社会性上和感知上激活空间,这个作品促进了共同冥想时间的延长,这种共同冥想既是个人的经验也是一种集体经验。
注释:
【1】James Turrell, Sensing Space, Seattle: Henry Art Galle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2.p.51.
【2】James Turell, Mapping Spaces, NewYork: Peter Blum Edition, 1987,n.p..
【3】James Turell, interview with Julia Brown, in Occluded Front: James Turrell, ed.JuliaBrown, exh.Cat.LosAngeles: Fellows of Contemporary Art; Larkspur.Calif:LapisPress, 1985,p.46.
【4】Craig Adcock, James Turrell':The Art of Light and Sp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90.特瑞尔论述自己的每个装置类型的最好表述见 Peter Noever,ed.,James Turrell: The Other Horizon, Ostfildem Ruit, Genuany: Hatje Cantz,1999.
【5】Turrrel, interview by Bown, p. 22.
【6】James Turrell, interview by Kim Bradley, Artspace, 13, no. l, winter 1988-89, p. 50.
【7】Robert Morris,“Notes on Sculpture Part 2”, Artforum, 5, no.2, October 1966, p.2L见John Coplans, Jim Turrell, exh.Brochure(Pasadena, Calif.:Pasdena
【8】James Turell, “Early Flight”,in Air Mass: James Turrell, ed.Mark Holbom, exh.Cat.,London: South Bank Centre,1993,p.26.
【9】Miwon Kwon,“Rooms for Light on Its Own",in James Turrell, London: Gagosian Gallery, 2010.pp.72 and 71.
【10】Willoughby Sharp,“New Directio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Sculpture",Arts Magazine, 44,Summer 1970,p.37.
【11】Michael Fried, "Art and Objecthood", Artforum, 5, no.10, June 1967, pp.15 and 22.
【12】Turrell, interview with Brown,p.22.
【13】Georges Didi-Huberman,“The Fable of the Place",in Noever, James Turrell, p.48.
【14】James Turrell, interview with Richard Andrews, in James Turrell: Four Light Installation,ed.Laura J.Millin, exh.Cat.,Seattle: Center on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Real Comet Press.1982,p.12.
【15】“Powerful Places: An interview with Turrell”,Places, 1, no., 1983, pp.35-36.
【16】Turrell, interview with Brown, p.13.
【17】同上,P-15.
【18】Adrian Searle, "Damien Hirst was supposed to be there..."The Guardian, December 22, 1999, http://www.guardian.co.uk/culture/1999/dec/23/artsfeatures,millennium.
【19】Turrel, interview with Andrews(1982), pp.l0 and 13.
是
【20】Jonathan Crary, 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ss.:MIT Press,1990,PP.38-40.
【21】Turell, interview with Andrews(1982),p.l0.
【22】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New York: The Humanities Press,1962,p.244,转引自Didi-Huberman, "TheFableofthePlace",p.49.
【23】Michael Govan,“James Turrell”,Interview, June-July2011, p.l04.
【24】Richard Whittaker,“James Turell. Near Flagstaff, Arizona, February 1999", in The Conversation: Interviews with Sixteen Contemporary Artists(Delray Beach.Fla.:Whale and Star.2007),p.228.
【25】Adcock, James Turrell, p.212.
【26】Turrell, interview with Brown, pp.38 and 14.
【27】Turrell,interviewwithAndrews(1992),p.50.
【28】James Turrell, interview with Richard Flood and Carl Stigliano, Partett, 25(1990), p.94:Turrell, interview with Brown, p.19.
【29】James Turrell。“Roden Crater",in Holbom, Air Mass,p.58.
【30】Frank Lloyd Wright,"The Japanese Print: An interpretation",in Frank Lloyd Wright: Essential Text, ed. Robert Twombly,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2009.pp.140-41.
【31】James Turrell,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February7,2013.
【32】Mark C.Talyor.Refiguring the Spiritual: Beuys.Barney,Turrell, Goldworthy,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pp.126 and 127.
【33】Turrell, interview with Brown, p.41.
纳特•特罗特曼/文
兰丽英 赵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