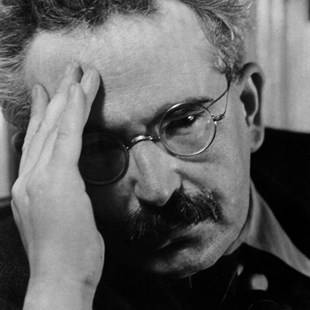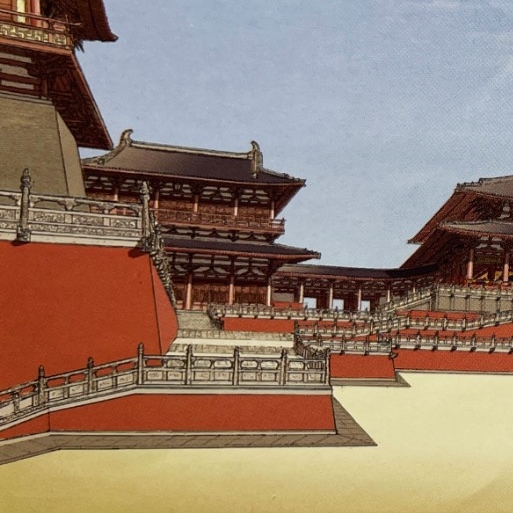一、到目前的研究经过
1952年3月的《美术研究》165号,载有岛田修二郎教授从日本京都高桐院收藏的传吴道子笔“中观音、左右山水图”三幅中的“山水图”,发现“李唐画”的落款,以本件山水图的构图及皱法看来,与南宋院体山水画的主流夏珪、马远一家的画风甚为接近,因此“被认为可能是南宋较早期时的作品”。自是以后,便在美术界引发了不少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自从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比从前更易于参观之后,对于具有“皇宋宣和甲辰(六年:1124)河阳李唐笔”落款的万壑松风图及高桐院山水图得以有一个较佳的比较机会。一般研究者以这两件图画之间所见的画风上的断层,认为如果是属同一人的不同时期的作品,将很难令人了解,而持这种看法的人又成了主流,于是变成一种趋势,如果肯定一方,便得否定另一方。
这种不同见解之趋向明朗化,是在1961-1962年之间,当时在台中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收藏品正在美国四所美术馆举办巡迥展览。当展览结束后,于10月4、5两日在纽约举办讨论会。讨论会上,对上述两件作品的见解便明显的分裂为二。讨论会的内容曾经摘要作为复印本,分发给中国美术史研究人员,因此我们得以知道其大致的情形。据规定要引用这复印本的内容,必先征得发言人的承诺,虽然如此笔者以为本讨论会在经过十数年后的今天,相信当时的发言人的意见可能已各有不同,更重要的是当时正值中国绘画史研究的创造期,因此这些发言当有一“时效”上的限期,为了能够更简略的记载其主张,以便传达中国绘画史研究史上的一个横断面,不得不无视于规定,对发言人的内容,以不具名的形式介绍如下。
(1)万壑松风图(以下简称松风图)与原传燕文贵笔,后由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认为是李唐作品的团扇形山水图“奇峰万木图”的主要特色都在结晶体状的岩石上。
(2)据文献记载,李唐曾学唐画(李思训),而松风图上的水的处理方式甚具古意。
(3)松风图绝不是周臣等专以模写明画的画家之作。本图是北、南宋交替期的作品,至于图上的年款及李唐笔等字迹当承认其真。
(4)松风图和江山小景图卷(以下简称小景图卷,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传李唐笔,无款),虽然形式与规模有别,但很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松风图的岩石的手法显然较小景图卷更有劲力,其间差别,举例说有如郭熙笔早春图与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溪山秋霁图卷之间的不同。
(5)松风图是李唐的杰作,但有严重的磨损,小景图卷岩石的部分泥金点也有严重的腐蚀,从其没有意义的描线看来,可以证明此图很可能是曾经过加笔或重作的作品。
(6)松风图是李唐的代表作,就画风来说,也当信其为真,制作期可能稍晚,当然也有可能是精密的模写作品。
(7)松风图与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所谓范宽画很接近。小景图卷和册页,连同松风图都很可能含有二组或二人的手笔。
(8)松风图是正笔。可能是颜料的变化影响致使画面也起变化。
(9)高桐院山水图对画中两个人物的解释,不符合南宋的画法。相当的简洁明快,宁可说那是属于明代的而不是宋代式的画法,或许是属于宋代的,但其设计却甚为大胆而果敢。高桐院和故宫的李唐画不可能同时认为是李唐的画。松风图岩石上的皱法,具有被刀削掉一样的效果,这种效果正好符合北宋的画。虽然画上画有使人想起周臣(明代所谓院派画家,仇英之师)所画如同黑影画的树木,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反对宣和六年(1124)的款记。
(10)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李唐画,看来原就是周臣的典型,太过于强调斧劈皱。落款是所谓的“暗款”。文献上虽属常见,但此画的落款具有相当古老的特性,到元代止,可说并不普遍。
(11)高桐院山水图属南宋时代作品。虽是接近李唐时期,但并非杰作。
(12)高桐院山水图就界线的质与手法说太过呆板。既没有强调的地方,也看不出任何变化。是由平凡的李唐继承者所作的南宋时代的作品。
(13)高桐院画就整个来说,缺少画家的品质,找不出可以期待于一般大画家作品所能感觉到的强有力的自发性。
以上论点是否适当,笔者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但令人感到兴趣的是整个内容告诉了我们1960年代初期的中国绘画史研究的状况。假定我个人也参加这一讨论会,提出的意见,可能也和以上众说没有多大的不同。就整个来说。当时可说是中国绘画史研究才起步的阶段。
此后发表的有罗樾(Max Loehr)教授的论文:“Chinese Painting with Sung dated Inscritptions”By Max Loehr, Ars Orientalis IV, 1961)。罗氏提到松风图,首先他认为这件杰作上蓊郁生动且老练的修养工夫所表现的设计,虽然很难和同属李唐的一连串作品连在一起,但是它作表示的样式却和马(远)、夏(珪)派所具有的广范围的各种墨法有相当接近的关系。此外他并引用喜龙仁氏的《中国绘画》一书,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本件画作是李唐艺术在画风发展中的中期之作。更引用威廉·维勒(WlIiam Willetts)氏的《中国美术》(“Chinese Art”2 vols. By William Willetts A pelican Book. 1958),并介绍岛田教授的松风图否定论。
自从岛田沦文发表以后,到目前为止,己经发表过的有关李唐山水画的研究论文中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教授的《李唐与高桐院山水画》(Li Tang<c.1050-c.1130>and KÖtÖ-in Landscape By Richard Barnhart.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May 1972)一文。班教授为了要挽救松风图与高桐院山水图在构图上的差异,提出了一个方法。那就是将高桐院山水画上,目前在右幅的对话观瀑的一幅和左幅对调,把高桐院山水画假设成一种离合山水的形式。如果我们考虑到原来的画在经过改装时,自然免因裁剪致使画幅缩小的话,那么高桐院山水图二幅,很可能象班宗华教授所说,原属离合形式,因此在左右二幅调换后接在一起的结果。很可能是在画面中央安置了一座主山。班宗华氏对这样假设的可能性提出了一个证据。他指出目前克利夫兰美术馆收藏传周文笔夏冬山水图屏风也采用这种主题构图,无论山的形状或树的形状,显然都借自高桐院山水图。此外他又指出以伯夷、叔齐拒食周禄隐居首阳山采薇遂致饿死的故事为主题的传李唐笔的图卷为金人占领华北后之作。并认为其笔法很象高桐院山水图,因此可能是宋室南渡后的绍兴年间之作。本件作品在岛田论文中也曾以补记的方法提及。
班宗华氏的结论是想从李唐富于变化的艺术中把握松风图、采薇图卷与高桐院山水图之间的差别。因此他的见解自有其说服性。高桐院的两幅山水图可以成为离合山水形式一事,在日本也早经人指出。如果把对话观瀑一幅的上边补绫取走,使画面可以往上多增加一些,那么和下边的岩石、树木等的连接将会更完美。如此一来可使人怀疑这高桐院双幅,原来是否就是屏风装。中国的屏风在日本可以看到较早的的可能是模仿唐朝形式的旧东寺收藏的山水屏风,这种形式直到近世仍可看见,是属于日本所谓的贴交屏风(译注:是将各种没有连贯性的不同的书画适当地混合贴成的屏风)为主,至于日本常见通景屏则比较少。
于此我想说的不止是要追求松风图及其他两种故宫本李唐画、高桐院山水图两幅、采薇图卷,与晋文公复国图卷等在画风上、形式上的关连而已,我的目的还想试图解答李唐从北宋徽宗朝的宣和画院离开后于何时在南宋高宗画院复职的一个问题。据文献,李唐南渡后复职时的年龄有的说是近八十,也有的说是逾八十。假定是在八十岁时正当高宗初期进画院的话,松风图当是作于七十岁以后。这样高龄的画家,在短期内能否完成从松风图转入高桐院山水图那么大的画风上的变化,实是一个问题。大部分论者认为两图之中如果承认一方,必然就要否定另一方的理由。正是因为他们的脑海里始终无法摆脱这一年龄问题的缘故至少以我个人表说,便是一直受此先入为主的观念所支配着。至于班宗华教授则以采薇图卷为绍兴中之作。但并未提出推定的根据。究竟是绍兴中何时之作呢?绍兴年号自1131年改元后,到1163年6月高宗让位给孝宗,共达三十二年,是宋代使用同一年号最久的时期。
二、有关李唐的文献
李唐和其他南宋画院画家一样,几乎可以说没有同时代的记录留下来。目前比较可采信的是宋末元初庄肃的《画继补遗》,其记载如下:
“李唐,字烯古。河南人。宋徽宗朝曾补入画院。高宗时在康邸,唐尝获趋事。建炎(1127-1130)南渡,中原扰攘,唐遂渡江如杭。汇缘得幸高宗,仍入画院。善作山水人物,最工画牛。余家旧有唐画胡笳十八拍,高宗亲书刘商辞。每拍留空绢,俾唐图画。亦尝见高宗称题唐画晋文公复国横卷。有以见高宗雅爱唐画也。”(《中国美术论著丛刊》收。排印本。)
李唐到临安(杭州)一事,宋末邓椿也曾在《画继》卷六、山水林石一项中做简单的叙述。
“李唐,河阳(河南省孟县)人。乱离(北、南宋交替时)后,至临安,年己八十。光尧(高宗)极喜其山水。”(《画史丛书》收。排印本。)此为第一次出现李唐南归时年龄为八十之说。《画继》是继《图画见闻志》之后,记载北宋熙宁末到孝宗乾道三年(1167)之间的画人逸事的书,因此与李唐活跃画坛的时期较近,所以八十岁这个年龄的数字应该是可以信赖的。
夏文彦《图绘宝鉴》(以下简称《宝鉴》)虽然就全书来说,间有不可采信的,但所记却远详于前引二书。
“李唐,字希古,河阳三城(河南)人。徽宗朝曾补入画院。建炎间(1127-1131)太尉邵宏渊荐之,奉旨授成忠郎、画院待诏,赐(最高荣誉的)金带。时年近八十。善画人物山水,笔意不凡,尤工画牛。高宗雅重之,嘗题长夏江寺卷上云‘李唐可比唐李思训。’”(《南宋院画录》——画史从书本,及光绪十年钱唐丁氏竹书堂刊本)。但国学摹本从书、津逮秘书本所收《图绘宝鉴》中邵宏渊则作邵渊。可能是厉鄂编《南宋院画录》时,因无法从诸书找出太尉邵渊之名,才改为邵宏渊的。那么究竟这一个连《宋史》列传中都找不出传说的邵宏渊何以能成为李唐的推荐者呢。想必是元末夏文彦的时代另有所据。
庄肃说李唐在高宗时曾趋事。高宗出生于徽宗大观元年5月乙已(1107),和宣和初年(1119)之间有十二年的差距。《画继补遗》说是南渡后,或因靠亲故,或因送贿、夤缘得入高宗画院。依此,及当时暴发户的武臣行状看来,似是和邵宏渊大有关系。张安治氏在《宋代杰出画家李唐》(《美术研究》1981年之二)一文中,以为卖画的李唐因得中官之助,乃以“待诏之作”奏闻,于是得入画院之说较妥,而以《采薇图卷》中宋杞的跋文所记的为不可能,因此认为夤缘较为正确。如果李唐之入画院是在绍兴末年,则宣和六年(1124)作松风图时,年龄当在五十岁左右。其后约三十年间,无论画坛上或画家所遭遇的社会环境,以及围绕绘画的各种条件都在变动中,都有可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李唐,促使其画风发生变化。因为这数十年之间,正是天下大乱的时候,任何价值观念都在这段期间失去了本来应有的样子。
三、金人占领开封及画院与绘画遗品的去向
开封在熬不过粘罕所率金兵的长久围攻之后,终于在靖康二年(1127)二月沦陷。从此后金人对宋的政策看来,我们可以知道,金不但是详细调查、连根夺走金银宝玩之外,同时还具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深的憧憬,而急于想摄取这些文化成果。就绘画来说,以金元好问为代表的题画文学的盛行,以及以王庭筠为代为的文与可、苏东坡式的枯木竹石图的制作等所表示的高度文化成立的背景。都必然的与金之占领华北有关。尤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开封与西京洛阳的沦陷而遭没收的庞大数量的书画,及百色伎艺人的被送往北方累积的结果,必然有很大的影响。
这种金人对宋的政策,首先,可以在开封之前沦陷的西京洛阳看出。南宋徐梦萃(靖康元年——开禧三年<1126-1207>)《三朝北盟会编》(文海出版社排印本,以下简称《会编》)卷六三、靖康元年11月18日己卯条说:“粘罕在西京,令人康求(宋)大臣文集、墨迹、书籍等,又寻富郑公(弼)、文潞公(彦博)、司马温公(光)等子孙,时唯潞公第九子殿撰(文)维中,老年杖履先奔走出城,乃遗一妾一婴儿,粘罕既得,抚之良久,衣服珠玉为压惊,复令归宅。”
《会编》卷七十三、靖康元年12月23日甲申条又载:
“金人搜监(国子监、太学)书、(大)藏经、苏(轼)、黄(庭坚)文及古人书籍、资治通鉴诸书,金人指名取索书籍甚多。又取苏、黄文、墨迹及古文书,开封府支拨见钱收买,又直取于书籍铺。.”以上记载,充分流露出徐梦萃对这些原以为野蛮人的女真人的作为大为惊奇的样子。
同书卷七十七,靖康二年正月25日乙卯条,记载金人搜求诸色人(各行各业的人),文如下:“金人求索诸色人,金银,求索御前祇候、方脉医人、教坊乐人、内侍官四十五人。露台祇候(或系祇候天于观象之官,不详)、妓女千人。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等家歌舞及宫女数百人。先是,权贵家歌舞及内侍人,自上(钦宗)即位后,皆散出民间,令开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寻。又要御前后苑作、文思院上下界、明堂所、修内司、军器监工匠、广固塔材兵三千余人。做腰带帽子、打造金银、系(係)笔、和墨、雕刻、图画工匠二百余家,其他艺人一百五十余家,令开封府押赴军前。开封府公人,争持文牒,乱取人口,攘夺财物,自城中发赴军前者,皆先破碎其家计,然后扶老携幼,竭室以行。亲戚故旧,涕泣叙离别,相送而去。哭泣之声,遍于里巷,如此者,日日不绝。”(旁点笔者所加,以下同。)又同书卷七八,同月29日己未条载:“又取应拜郊合用仪仗、祭器、朝服、法物,并应御前大辈、内臣、诸局待诏、手艺染行户、少府监,将作监、文思院等处人匠,(略)又押内官二人、又十六人、后又十人、并百伎工艺等千余人赴军中,哀号之声、震动天地、民情极皇皇(惶惶)、迫于冻馁、又多剖剥者,悬五十(千)贯以止,绝域不戢”。同卷同月30日则记载:“金人又索诸人物。是日,又取画匠百人,(略)学士院待诏五人,筑毬供奉五人,金银匠八十人,吏人五十人,八作务五十人,后苑作五十人”。丁特起《靖康纪闻》29日所载内容与此符合,而丁特起又云,系出自“目击而亲闻”,绝无违误。可见这些记载都不是捏造的。当然金人押走的,不止于人,此外应该还有古画、教坊乐器等。百色伎艺人的押送北方,在其他城市也不断地进行。无论人与物遭掠殆尽,中原的中华文化似乎要被消灭了。
在此之后,除了将徽、钦二帝及诸王、诸妃送往北方之外,众多中国文物仍不断的被搬往北方。至于徽宗如疯如狂建立的艮岳被破坏了,倾其大半热忱建立的五岳观烧毁了(靖康元年11月27日),神宗元半官制大改革的象征之一的尚书省也遭烧毁了(靖康元年12月15日)。如今开封街上所存的只是提供肉块做为买卖对象的遗骸市场。至于所剩的艺术品,不过是像郭熙所画玉堂(学士院)的“秋山平远图”这类壁画而已。
这是中原画坛的一大浩劫,我们以此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大断层的时期诚不为过。因为当时的中国画家习业的第一步始自“传模移写”,如今他们失去了可以为依据的模范作品,同时也失去了可以为师的画家。
然后,未来的高宗,先以一个未具任何继承帝位名分的皇子开始他长期间的逃难生活。皇帝想逃,军队听说金人来了也争先恐后弃城而逃。逃亡的军队立刻变成群盗。
这位皇帝终于在建炎四年(1130)正月25日行幸到浙江省南端的温州,当时可说逃亡也是行幸之一。定临安(杭州)为行在是在绍兴二年(1132)正月的事,此后到宋金第一次和谈成立之绍兴八年12月之间,相信高宗也没有办法悠闲的从事他向来喜爱的风流韵事。虽然庄肃曾批评说“高宗虽天下俶扰,犹孜孜于书画间”(《画继补遗》卷上)。事实上.高宗到处行幸,相信并无多少时间耽溺于书画之中。
《图绘宝鉴》所说“建炎间(1127-1162),太尉邵宏渊荐之云云”,可能是出之于夏文彦独有的胡言乱语。因为此时绝无暇也无钱设立太平逸乐期间才能产生的画院之类的制度。当时的局势所最需要的是制造更多的兵器甲胄,制造兵器还待增加税收。国难时期首要在节约、裁冗费。因此建炎年间不得不大行裁官(《玉海》卷127)。初期甚至连教坊(教乐舞的机构)也废了(南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三——《学津讨原》收,以下简称《杂记》)。所谓教坊的工作包含公家宴会、祭祀所需舞乐等,是国家的重要机构之一。自孔子以来,历代对音乐一向慎重其事,如今连此教坊也不得不裁去,直到绍兴十四年才能复设,在建类三年4月庚申,更将少府、将作、军器监改隶工部(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二,《国学基本丛书》改排印本,以下简称《要录》)。其中将作军器工监在绍兴三年十一月复置,少府监则始终并在工部之下。
综观上述史实,南宋之能够设置画院,最早也当在绍兴二年,以临安为行在以后的事。如果我们考虑到靖康中,几乎所有画院画工都被送往北方,及南宋对金政策的演变,从常识上看,最早也只能说是在绍兴十年代中的某一年。且绍兴十二年到绍兴十九年间,为增税所采行的各种措施,例如经界法施行期间,想必无暇建立画院。当然这种观念也许只是日本式的看法,对于传统文化最高保护者的皇帝来说,说不定认为这是必须尽速设立而早已付之实现。
当然,官制上的图画局(院、画院)或系继承北宋末而来。《会编》卷107,建类元年6月5日癸亥是张邦昌的伪楚国成立后不久的事,同日见有何志同等的差人押收翰林书艺局著缘艺学李恭佐的状纸一事。但此事并不就能做为南宋初建炎初年复置翰林书艺局的证明。因为这不过是说,长久被虏于贼寨的北宋宣和书艺局的艺学,很幸运的逃离贼手而已。
高宗建炎以后,这类北宋官制可能仍旧留下来。问题是这些官实际上有没有在运用。前面提到,为裁汰冗费而裁官,对于本来就有没人的官衔,自然不可能成为裁减的对象。
如果是设立了画院,并安置了画家在内的话,那么必定是在精通金内情的秦桧秉政,并于第一次和谈成立的绍兴八年以后的事。因为战争期间,当然文臣的发言权相对的会减弱,但是一旦恢复和平,则传统上注重以文治国的中国,自然文臣的主张会渐渐增强。当时的武将,不必问出身,所需要的只是刚勇具统率力,能招徕众多强壮的部下,并以忠义为标志的就可。每个武将都很年轻,中兴最大功臣之一,封至郡王的韩世忠其出身便不甚清楚,只因他强壮而勇敢,稍知军事,但并不具文臣所有的任何修养。据王明清(南宋初人)《挥塵后录》卷一一,绍兴壬戌十二年(1142)条世忠曾自云:“世宗不识字。此乃解潜为之,使某上耳。”以是得罪秦桧,翌日解潜即遭贬单州(江苏)团练副使,南安军(江西、大庚)安置,竟死岭外。此事从《要画》绍兴二十一年8月壬申条,弥留时韩世忠自己说的:“吾以布衣百战,至位公王”一语也可看出。中兴功臣之一的张俊是盗贼出身,甚至文臣中说不定也有不识字的人,因侥幸夤缘当上知县知州的。关于太尉邵宏渊其人,也可看做是在这样的乱世中,于原有秩序崩溃时崭露头角的人之一。当和平到来的同时,文臣方面便开始对武臣的攻击。以微不足道的理由或诬告而被降职贬官的在所难免,甚至如岳飞竟惨死大理狱中。
只要我们看一下南宋政权的这种内情,便可以想到画院开设的时间当在秦桧独占政权的时期,也就是第一次宋金和约成立的绍兴十一年(1141)11月到秦桧死亡的绍兴二十五年(1155)10月之间较为适当。当时国内虽有盗贼出没,不过内政政策相当成功,和约的订立也节省了军粮的费用。但这只是在第二次金军南下的绍兴三十一年(1161),9月前的一段短暂的苟安时期。在此期间,从北宋转入南宋画院的画家们,除了李唐以外,据记载,其复职皆在绍兴年间,这也许可以做为决定南宋画院开设时期的参考资料。今从《南宋院画录》追寻其事迹如下。
刘宗古,汴人,宣和间待诏。成忠郎。绍兴二年,进车辂式称职复职。除提举车辂院事(《图绘宝鉴》,以下简称《宝鉴》),绍兴二年虽然未免过早,但似乎也看不出可以做为画院画家的积极理由。
杨士贤,宣和待诏,绍兴间至钱唐,复旧职。(《宝鉴》)
李迪,河阳人。宣和莅职画院,授成忠郎。绍兴间复职,历事孝光二朝。(《宝鉴》)
李安忠,宣和画院,历官成忠郎。绍兴间复职画院。(宝鉴》)
苏汉臣,开封人。宣和画院待诏。绍兴间复官,孝宗隆兴初授承信郎。(《宝鉴》)
朱锐,河北人,宣和待诏。绍兴复职,授迪功郎。(《宝鉴》)
李端,汴人,宣和待诏,绍兴间复官。(《宝鉴》)
张浃,同上。
顾亮,同上。
李从训,宣和待诏,绍兴间复官,补承直郎,画院待诏。(《宝鉴》)
周仪,宣和百王宫待诏,绍兴间复官为画院待诏,补承直郎。(《宝鉴》)
周仪,宣和待诏,绍兴间复官。(《宝鉴》)
焦锡,宣和院人,绍兴间复为画院待诏。(《宝鉴》)
以上主要是依据《宝鉴》,至于《画继》与《画继补遗》的记载则略有出入。又《南宋院画录》卷二所载画家中,是否从宣和画院复职到绍兴画院,其实情不详的有胡舜臣、张著二人,连同李唐在内,共为三人。之外,可说所有人都已复职绍兴画院中。
此外,卷二所载其他画家,也大部分成了绍兴画院的待诏。尤其有趣的是《画史会要》卷三(《南宋院画录》卷三收)所载肖照略传,其文如下。
“肖照,濩泽(山西)人,靖康中流入太行为盗。一日掠入李唐,检其行囊,不过粉奁画笔而已。”照雅闻唐名,即随唐南渡。(唐)尽以所能授之(肖照)。肖照于绍兴中入画院,补迪功郎,画院待诏。据现存崇祯四年豫章朱氏刊本《画史会要》卷三之文,与上引文字大有出入,唯绍兴中入画院一事则同。
在被金人送往北方的三千汉人(据明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华世出版社排印本。——唯人数似嫌太少)中,逃亡的相信不在少数。北遣的路途虽然不得其详,但很可能是在出开封府北青城后过太行山脉,然后可能从山西省代县到太和岭和云中(山西、大同)一带,向东转入河北省经蓟至韩州(吉林省)(《宋史纪事本末》)。这条路上,象太行山脉便是北遣途中逃亡的人的最佳藏身地点,同时也是要袭击这些逃亡的人的盗贼最好的藏身之地。《要录》卷一五八,绍兴十八年闰8月庚申条有如下记载。
“亲卫大夫忠州刺史鄂州驻扎御前选锋军同副统制梁兴卒。(梁)兴自太行山率其徒,奔岳飞于江夏,从军凡十年”。所谓“率其徒”,似乎不难想象其出身,据推测所率领的也有可能是盗贼之辈。
如此看来,从宣和画院复职到南宋最早期的建炎画院的便只有李唐一人。那么《宝鉴》所指推荐李唐的太尉邵宏渊究系何等人物呢?
四、太尉邵宏渊
前文已述及,《宝鉴》一书除了《南宋院画录》所收本以外,皆误以太尉邵宏渊为邵渊。
不过加官至太尉的邵宏渊之名,并不见于《宋史》本传中,只散见于《宋史》本纪及《会编》、《实录》、《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会要》)等书。此外《杂记》(聚珍版收),明钱士升《南宋书》的《李显忠列传》也可见简略记载,南宋史浩、周必大的文集则载有其除官时的诏书全文。从这些记载所得的结论是,邵渊即使就是邵宏渊,也绝没有做到太尉。《宝鉴》的作者夏文彦作李唐传时所据何典,如今已不得其详。或系原典有误,或系因于夏文彦误写,不得而知,但要提及邵宏渊这一并非很有名的人,必定有其理由。
还有一个可能被误为邵宏渊的武臣。绍兴三十一年3月丁未,金军攻陷濠州(安徽、凤阳)时,有一名叫邵宏渊的,因进退维谷,结果缒城投拜,信口指名而降。但是此人后来即杳然不见记录,大概不是被误为太尉邵(宏)渊的同一人。
据《宋人传记资料索引》(鼎文书局),邵宏渊是大名(河北)人。因韩世忠之荐,授阁门舍人。绍兴年间与金人战于真州,大捷。时称中兴十三战功之一,乃授定远军节度使。惜笔者学浅,竟找不出载阁门(賛宣)舍人,大名人,定远军节度使等的文献。只是此索引的记载原系《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印行)的翻版。
绍兴初年韩世忠大行荐人,如系经他推荐为阁门舍人(宣賛舍人),则必在韩世宗死前的绍兴二十一年以前。但是邵宏渊的官职既然不过如此,是否够资格举荐一画家,实有疑问。据《要录》卷一七五,首见邵宏渊的名字是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10月丙子,自拱卫大夫忠州防御使两浙西路兵马辖至殿前司前统制的记载。此后的邵宏渊官运亨通,升迁迅速,于同年十一月壬辰因累立战功转为宣州观察使。二十九年9月辛已殿前司中军都统制邵宏渊,添差荆湖北路马步军总管,罢从军。因殿中侍御史汪澈奉诏荐,宏渊奋不顾身,真万人敌,因此移江东总管。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丙辰虞允文采石矶大捷之前,邵宏渊为步军司左军统制,与池州都统制李显忠夹攻金军,因王权怯战而退,终于失败。又同日侍卫步军司左军统制邵宏渊率左右二军至真州,这是有名的真州(江苏仪徽)之役战端将启之时。第三日邵宏渊和金军的肖琦交战,据赵甡之《遗史》,此役邵宏渊因酒醉未醒,并不亲临战阵,只在青浦桥之东指挥将士,遣三将迎战敌军于桥上。但是当军队撤退时,民众却大声叫喊“邵太尉在西府桥阻止蕃人”。扬州民众也说“如果不是邵太尉在真州和蕃人力战,则扬州人将逃避不及”等等。到后来,甚至说邵宏渊驰马力战迎敌,至数回合,至遍体鳞伤。原来邵宏渊的力战迎敌之誉,实起自民间,后来的好事者并不追查其真实性,乃请建宏渊祠堂于真、扬二州。这可说是意外得来的名誉。以上系以《要录》为主,补以《会编》写成。此时邵宏渊是侍卫步军司左军统制,距武官最上阶的太尉尚远。至于真州之战,确是收在孝宗乾道二年(1166)8月甲午所立《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格目》中。《杂志》甲集卷一九的战功格目第十一里,将邵宏渊的真州青浦桥之捷和刘琦的早角林、李宝的密州唐岛之捷,三者并举。但《宋史》卷三二则云“步军司统制邵宏渊,逆战胥浦桥,败绩”,所载完全相反。南宋孝宗朝熊克所作《中兴小说》一书,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来,被指为讹谬甚多,《要录》注中虽然常引用《中兴小记》的记载,然而对真州之役却未曾引用。至于采自《永乐大典》本的《中兴十三处战功录》,虽然举出刘琦、李宝的胜仗,但对邵宏渊的事也只字不提。于此不说《会编》,光说《要录》,其注引赵甡之《遗史》的地方又加说明如下:“甡之所称西府桥即胥浦桥也,今并附此,更须参考”。可见《要录》的作者对其真实性也感怀疑。邵宏渊后来遭遇贬职,或者此是原因之一。《会编》三十一年10月17日丙辰云:“邵宏渊,以六合报捷”,虽然如此,而《实录》的记载整个看来,似乎隐约地都在说南宋军队失败的情况。
邵宏渊之被称为太尉,在前在后都只有此时而已。当然《宝鉴》所说“太尉邵宏渊”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最后官至太尉的邵宏渊”,一是“官拜太尉的邵宏渊”。
中兴以来,武官升迁很快,这可以《要录》卷一八三绍兴二十九年6月丁未的记载看出。洪迈也在《容斋三笔》卷五提到武官官品称谓过当的事。他认为旧制太尉须当过节度使后才可任命,但是今日除授已无此古意。(《要录》绍兴三十二年12月庚辰“臣僚言云云”。中兴后,除授太尉的,今不依其先后,可举出韦谦、杨政、刘锜、田师中、刑孝扬、钱价、刘光世、张复、韩世忠、成闵、郭仲荀、郑藻、李显忠等人,都是在节度使之外加上检校官的太尉的。但是如前所说,南渡以来,武官的叙迁甚为紊乱。如同《杂记》所说,正是“由事用人,非常典也”。虽然如此仍不见有邵宏渊除授太尉的记载。过当称为太尉的例子只见于绍兴三年冬10月己巳,被逮捕的邵青称浙西安抚大使统制官王德为“太尉”一事而已。邵宏渊于绍兴三十一年11月符离(安徽、宿县)大败之后.地位已大不如前。当时的官职是检校少保宁远军节度使招讨副使(旁点笔者所加)或许也曾加有太尉之衔,但今己无从查起。此后有关邵宏渊的名字,只以蠲放(解官职)或黜降(贬官)等记载,见于《会要》、《宋史》而已。当和平来临时,国家渐维小康状态,此时即使有军功的人,也往往以各种理由被黜降或蠲放。邵宏渊也于孝宗隆兴二年5月辛丑,由江西总管“责授靖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仍徽其盗用盗用库钱也”(《宋史》本纪卷三三)。这种不算犯罪的犯罪事例,常发生于军中,在和平时期便会成为问题。有关邵宏渊出现在史书的最后记载是乾道四年(1168)正月4日,下诏说,责授靖州团练副使,安置南安军(江西、大庚)邵宏渊任便居住。并说邵宏渊是老将,虽然符离之战违反军纪,真州之役则仍有功故。
以上所述有关邵宏渊的故事虽嫌过于冗长,但仍看不出任何做到“太尉”的资料。为何真州之役,民众竟称一个不过是部队长程度的侍卫步军司统制邵宏渊为太尉邵呢?如同注一九所介绍,也许是因为中兴以来叙迁的格式已经破坏,只是美称之为太尉而已。至少《宝鉴》记载“太尉邵宏渊云云”的内容,很可能是根据《要录》、《会编》及目前已经散失的赵甡之《(中兴)遗史》的记载而来。
如果说李唐因邵宏渊的推荐得进入画院的话,按推测最早当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前后,最迟在孝宗隆兴元年(1163)。如果因其他画院画家的记载而认为在金主亮(海陵王)的南征开始后的南宋政治状况中,根本不可能采用画院画家的话,那么邵宏渊之推荐李唐的下限时间当在邵兴三十一年(1161)。但是这样的推测,必须以《宝鉴》的记载具有某些真实性为前提。
结果假定绍兴二十六年重入画院(秦桧己失势,但和平局势仍继续存在)时为八十岁,则制作《松风图》的时期(宣和六年款)当在五十岁以前。那么对松风图、高桐院山水图、采薇图卷、晋文公复国图卷各画的画风之所以不同,自当会有另一种解释,于下拟介绍李唐各作品的画风。
五、有关前文的若干补正
前文曾述及金人占领开封时,古画几乎完全被押送北方。不过《要录》卷一二九(《续通鉴》122)则有如下记载。“绍兴九年(1139)6月已酉朔,签书枢密院事楼炤与东京留守王伦(元丰七年——绍兴一四年<1084-1144>)同检视修内司,趁入大庆殿,过斋明殿,转而东,入左银台门,屏去从者,入内东门,过会通门,自垂拱殿后稍南至玉虚殿,乃徽宗奉祀老子之所,殿后有景命殿。复出至福宁殿,即至尊寝所,简质不华,上有白华石,广一席地。祖宗时,每旦北面释殿下(拜天子),遇雨则南面拜石上。稍北,至坤宁殿。屏画墨竹,芦雁之属,然无全本质(破损甚严重)。他殿画皆类此。自福宁(殿)至钦先、孝思二殿。钦先奉诸帝,孝思奉诸后,帐座供具犹在。(略)入睿思殿门,登殿。(略)过玉华殿(略)。登瑶津亭,亭在水间,四面楼阁相对。(略)”
楼炤、王伦何故入开封不详。据《宋史》王伦、楼炤传及楼钥撰王伦神道碑等看来,可能是与为金右副元帅兀术(宗弼)协定国界事。王伦在此不久即被兀术捕杀。绍兴九年六月一日当天的《要录》记载非常生动,尤其“趋入大庆殿云云”一文,正表露了久违故都开封而不得入的一般北宋旧臣怀旧之情。文中记载“至坤宁殿、屏画墨竹芦雁之属,然无全本矣。他殿画皆类此”。文中加有旁点的殿舍,据郭熙《林泉高致集》《画记》(参照《美术史》一O九册拙稿)等,原本当存有郭熙制作的大壁画,如“半林石屏”(玉华殿)、“四面屏风、松石平远”、“一大图”(遥津亭)等。可是《要录》并未提及。“他殿画”中是否也包含这些郭熙的壁画在内,或被金人剥走,如今已无从查考。从金时李、郭派山水画之盛行推测,恐怕是金人(仕金的汉人士大夫)把它送往北方去了。或者正如邓椿在《画继》卷一。《论近》中所说,郭熙的绢画早被剥走,收在内藏库的退材所中。
不管如何,遗留在开封的壁屏画摧残甚为严重,街区荒废也很厉害,对南宋画人来说,已成为难于接近的地方,因此在他们看来,即使留有北宋大画面绘画,其存在已等于毫无意义,当然不再可能成为传模移写的材料了。
六、郭熙古典画风的瓦解与《松风图》
李唐壮年时期曾在徽宗朝活跃过,但是从史书来看,徽宗对郭熙却有不同的意见。其一是拙稿有关郭熙论文中也曾介绍的郭思与徽宗谈话(《林泉高致集》《画记》末文,也就是很可能是郭思后序的部分)的情景。但是在这一对话里,徽宗所强调的只是其父神宗对郭熙的眷顾,并不曾表示徽宗本身的任何见解。如果勉强从中抽出徽宗个人的意见的话,顶多是“(郭熙)画全是得自李成”这一句而已。正如第五章所说,在徽宗朝,不管理由如何,恐怕郭熙在殿阁的壁面或屏面所作的大部分画都被剥走了。
在徽宗朝,宫廷画坛渐渐形成一种不能接受,也不能享受郭熙画的气氛。正如嶋田英诚君在《徽宗朝画学》(《铃木敬先生还历纪念中国绘画史论集》1981年12月吉川弘文馆。以下简称《纪念》论集)一文所沦,徽宗为栽培士人清流中的技术人员所设的画学,于即位初年的大观四年(1100)就已废止。此后并未能像算、医两学一样,得以重设,而是由翰林图画局负责宫廷画工的栽培工作。至于穿绯紫之服及允许佩鱼,都是政和、宣和间给予画院画工的异数特权。因此笔记、杂史之类所能见到的以试题简拔画人的办法,可能也是在画院举行。考题如宋初寇准的“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画继》卷一,徽宗条,此二句五言诗,论者有以为是采自韦应物的《滁州西涧》的,虽不见于四部丛刊收寇准《忠愍公诗集》,但据宋吴子良《吴氏诗话》卷下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等,知是宋代脍炙人口的名句),或用《乱山藏古诗》诗中的一句(《画继》卷一徽宗等),或用“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去马蹄香”(宋俞成《萤雪丛说》)、“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宋陈善《扪虱新话》卷九)等的唐诗的一、两句,都是一般所熟知的。
虽然如此,但是只据这些故事,便下结沦说徽宗朝的绘画制作是以诗画一致为理想的话,未免有思考过于简略之嫌。因为以中国的诗,尤其象绝句那样,必须把情景或境界做极度的浓缩才能成立的短诗类韵文学,仅采其中一节或一句,事实上不可能具有太大的意义。例如《乱山藏古寺》的试题,得第一名的是先画满了整个画面的荒山,再在画幅上面露出旙竿,以此表示“藏”的诗意。《画继》并未记载其荒山如何表现出,但是如果整个画面都是荒山,仅加上旙竿的点缀,这样的作品究竟能否成为山水画,是相当可疑的。至于“踏花归去马蹄香”,以数只蝴蝶追逐马蹄痕来表现,更令人有猜哑谜的感觉。
自中唐泼墨画发生以来,中国山水画的最大理念之一,不用说是在扩大画家的想像力(小川裕充“唐山水画史上的想象力——自泼墨到《早春图》、《潇湘卧游图卷)”(《国华》1034-1036,1980年6月)但是这种情况的想象力当属画家本身问题,不能求之于观赏画的享受方面的人。虽然墨迹的污点可做为连想的起点,用来形成雄伟的山水画,但是我们不可能要求观赏的人也能够假借联想的力量,从这雄伟的山水画反过来想到它是开始自一滴墨迹的污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徽宗时代为强迫观赏的人发挥想象力或是联想力,遂使山水画的基本命题逆转了呢?
如果在徽宗时代曾以一句诗作为试题,使应考的人作画的话,看来似乎有两个意义。一是提示一两句诗,用以测验应考人是否记得起整首诗句。这个政策可说是在徽宗将画家分为士流与杂流加以教育的指导方针的延长线上。第二当时在弃放自北宋初累积下来,而由郭熙所完成的几近完壁的古典画风。当然在此所谓古典画风这一辞汇,与西洋美术史上的使用倒未必含有同样的意义。因此就这一点说,也许把它叫作中国式古典画风比较妥当。这种画风也就是郭熙山水画的画风。如果我们要以抽象化的辞汇来表现,那么郭熙山水画的画风正好可以摘要如下:具有严密、明快的空间结构,正确的远近法,精致地表现出部分与全体的调和等特色。不过这些特色中,却有很多部分是与西欧的古典画风具有相通的地方的。
但是象这样几近完壁、不具缺点的山水画,虽然必定具有能够感动观赏人的力量,却也往往会给观众一种压力,使他们难以忍受,因为绘画的完整性似乎也可以否定叙情感。这和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情况完全相同。徽宗虽然完全承认郭熙在绘画上的的成就,但是他之所以非把属于古典画风的郭熙的绢画从殿阁的壁面或屏上剥走不可。很可能是因为背后有这种感情作祟的缘故。
其结果便是郭熙画风的瓦解。而瓦解的结果,很容易引起“重返本家”的现象。如果以简单的图形思考法来看,那就是倒流到李成与范宽画风去。这两个画风原是形成郭熙画风的两大因素。这么一来难免要把绘画的历史性、自律性的发展扭曲到相反方向去了。以一两句诗作为试题,使应考人作画,其意义只能说是在追求造形上的非完整性。目的当在把观赏的人带进作者一方,使他们也跟随作者去体验作者制画时的感动,并给观众一个发挥想象力的动机,让他们重新把画面构造得更完美。试题不过是其象征性表现而已。况且从这种试题还可产生增加叙情感的范围的好处。我完全不能同意有人把徽宗画院的绘画制作的理念,看做是假借试题以选拔人才的诗画一致的表现,并把它当做是文学与造形的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文化形态的调和。因为使绘画成立的因素及属于文学部门的诗成立的因素,本来绝不会有完全符合的事。虽然有人说,两个具有完全不同的表现手段与方法的艺术形态之能够完全调和一致,正是中国画的特色。固然这样的强辩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但是遗憾的是,问题在于这样强调中国画的特色的结果,都隐藏有一种危机,很可能使中国画坠落成为拒绝中国人以外的人们去了解的地方艺术。
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万壑松风图》轴,具有徽宗在位后半期的宣和六年的款记。就时代说,这当是《画继》卷十所说徽宗最为宠遇画院画家的时期,也是徽宗最积极指导画院的时代。而本件作品——姑不论其真品或模写的问题——正告诉我们,徽宗指导画院的理念,在具体上不得不朝向“返本归源”去做。
虽然某些论者试图从本件作品寻找郭熙“山水训”的影子,可是所谓在形式上主山非常壮大、或是长松亭亭而立的形容辞句,并不具任何重大意义。无论如何,当本作品和郭熙“早春图”两相比较,便可发现如果没有表现充分的块量感,就无法使主山具有“大山堂堂”之感。至所谓“长松亭亭”也者从《松风图》前景的松树树丛的描写看来,只能说很单薄,有如嵌进主山的岩石里面。
不管徽宗如何指导画院画家,在北宋时的李唐山水画显然表现着更为强烈的复古倾向。如果《图绘宝鉴》的记载可信的话,据说高宗曾说“李唐可比唐李思训”。这是否是想以同姓的李唐来比美青绿山水形式的创始人李思训,不得而知。不过即使李唐所采的画法,具体上是青绿山水形式的话也不足为怪,因为《松风图》的现状正是浓彩的青绿山水,可为证明。
从前每当保持某种距离观赏本件作品,或看原色版复制品画面时,总有一个疑问。怀疑本图包含下边的树丛在内的整个画面,可能都是深色的青绿山水。当1982年2月我访问国立故宫博物院时,看到了十三张大版的彩色局部特写。从其放大的局部,证明了我向来的想象是正确的。原来以放大镜无法看出来的青绿或石绿描线,经过这些彩色的放大片,得以从本图的前景松树树丛看出。这些松树丛正好在松风图中心位置上。这是左下方(本文的左右都以观赏者的立场表示。也就是面对画面时的左、右)水流方向与从右下方来的山径的交点,这个交点同时也是从右上方的白云往瀑布方向下斜。及从左上方往方解石形状的岩石棱角方向下来的这两道构图线巧妙地集中的地方。如果这些松树树丛只是象现在这样,看来一片墨色,且平板地嵌进主山内的状态的话,只能说是在强调偏平的毫不足取的作品而已。光从这点看来,至少可说李唐是朝着与徽宗画院的指导理念不同方向前进的作家。所谓不同方向,便是接受北宋末、南宋初复古机运而加以发展的方向。
对这种北宋末、南宋初复古的机运,亚历山大·梭巴教授曾试图从画家的名字中去寻找旁证。梭巴教授发现画家名字中有很多具有“古”字。于是想借此解释这种复古机运(“Early Chinese painting”P.41-42.By Alexander C. Soper “Artist And Tradition”197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不管《图绘宝鉴》在文献上的可靠性如何,李唐以“晞(希)古”为字,他所希求的必然超越了郭熙的时代而及于更古时代的画风。一方面诸书所传徽宗指导画院的理念,完全未被具体化。松风图在某一方面看来,画面上的每个部分可说都是以北宋画风画出,是一幅完全排拒简略化、省略化的山水画。但这并不就是说松风图具有象郭熙“早春图”那样以严密的远近法来支配的画面。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用三层次(前、中、后景)远近法来做明快的空间表现。它是以巨大岩山为主要景物,占据正面的大部分,至于表现远景的,只有如同藤蔓的远峰而已。其结果就北宋山水画来说,它只是一幅显然缺少平衡的作品。如果本件作品的著彩量,只有目前所能看到的那一点点的话,那么可说它是一幅连空气远近法的表现效果都弃而不用的作品。而这种空气远近法的表现效果正是青绿山水所具有的。因此我以为当初的形状绝不是这个样子。原是构成最前面的景物的土坡及松树露根的部分一定都具有很深的青绿与代储的彩色——也就是说用青绿山水的赋色原则,将在补色关系的色彩使用于邻近之处,而松树的树叶则以石绿著彩,这种彩色与背后的茶色岩石成了强烈的对比,结果必定使绿色的松树树丛很明显的浮出画面。至于中景的树丛则在背后留白以表示前后关系的明晰性——这种手法早已在传李成笔“晴峦萧寺图”轴或“早春图”中以较写实的形态加以使用。至于米友仁所作的一些画则使用与松风图同样的云雾形式。
看这件作品使人感到困惑的是面对画面右下方的皱法。几乎可说是运笔的滥用。既便是“唐代细皱”的遗意也使人难以了解。不过正如李霖灿教授所说,这件画上几乎没有苔点(李霖灿著《山水画皱法、苔点之研究》,1976年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丛刊》甲种之二),因此画本身可说仍墨守北宋自然主义描写的基本原则。至于“多皱”的这个问题,只能解释为起稿线与画在赋彩后的画面上的墨皱,在彩色剥落后依然残留下来,遂致混在一起成为杂乱的皴痕。至中景涂成墨色的一块芋头形的山峰的表现,也大略可以做这样的解释。
本图也可看到一个趋向,那就是郭熙画风瓦解后,似乎有退回到源流之一的范宽山水画画风的倾向。且表示更进一步靠近南宋画风的特色。画面上虽然表现出山的块量感,却缺少范宽山水画原来很可能具有的几乎可以观把照者也包含进去的巨大空间的表现。虽然松风图与徽宗画院的绘画理念有何种关连不详,不过无论如何本图的画风所属年代确是在郭熙与马远、夏珪之间。至于本作品的主山虽然壮大,但意外的是它却很明显的倾向南宋山水画。例如第一,因为没有守住严密的三阶段远近法,因此缺少了对“远”的表现意志;第二,只以前景和中景表现空间;第三是自郭熙古典画风瓦解后,要“返本归源”却只在表面上表示接近范宽的画风。从这些看来,实际上却是因为美术风格的自律性发展的结果,更倾向于南宋。在细部点上去的石绿点或以没骨法使用石绿颜料描绘草丛的方法,都与从远寺,金地院分藏的夏、秋、冬山水图的描法相似,且个个画题,象露出的树根、水流及主山的斧劈系披法等等,在在都表示本图的特色,与其说是近于北宋,不如说是近于南宋的画风。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场来看的话,那么无论任何人观赏本作品时,姑不论主山的块量感,就整个画面来说,不得不感到南宋所谓“院体”逼近在眼前。
自郭熙早春图(1072年)制作后仅半世纪间,北宋的山水画竟改头换面成非常完美,但过分造作的构图及表现空间的形式。这种改变是用前述四条构图线来决定其构图,所以很容易看出。这种构图的形式,属几何学构图的缘故,藏有一种很容易改变成为南宋院体山水画的对角线构图法的可能性。这是和早春图之将整个画面区分为大小块面,再将其细分而后以自然主义手法分别表现明暗的手法,在根本上可说完全不同。因为在前者是以画家的几何学构、图法做为出发点来作画,而后者的构图法却可说是用作者的连想去分割画面,然后再将自然重新加以构成。
七、从万壑松风图轴到江山小景图卷,奇峰万木图册页
江山小景图卷所表现的画风比松风图更接近南宋。也就是说,它离开北宋山水画卷更为遥远。画卷本身的保存比松风图好,但近景部分的树丛仍不免使人看不懂。也许恢复原始的色彩,说不定能够在这些目前看来描写不清,树与树的重叠不分明的地方.看到意外明确的远近表现。因为本画卷原来应当是和松风图一样属于浓彩的青绿山水形式。包括岩山的著色在内,本画卷是以鲜艳的青绿、石绿、群青、代赭等颜料涂满。画上并不具有李唐的款与印,不过如果将它当作李唐作品的话,那么也应当把它看做是表现李唐复古嗜好的一幅作品。从现存卷的中间开始,可以看到一条小径,断断续续穿越在目前已经变黑的树林间,缓缓的向左上方蛇行。这条小径就是这幅画的基本构图线,对画面的动线的设定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整个画卷似乎就是以这条细细的山径为轴线而构成的。小小的墨点并非是描点,而是以苔点的功用点在各处,正如李霖灿教授早就指出,在墨点上甚至还加了泥金。于下让我们来看它的细部描写。
近景阔叶树的树叶用墨线勾勒,在勾好的轮廓内整齐的填进了石绿及青绿的彩色,与松风图的树法之平行使用墨线与石绿线——也许松树针叶的表现,除此以外别无他法——的方法完全不同。它是采用象《芥子园画传》第二册《树谱》所见的夹叶法中的介字点或是个字点(同上)的形状,以极填重的勾勒线和填彩画成。这样的树法在考察可能属于南渡后的李唐的作品《伯夷叔齐图卷》的一些模写作品时,可说是相当重要的资料。岩山的针叶树的描法颇近于松风图。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那是上下宽度极窄的画卷,其画面本来就很小的话,大约也就可以了解那是出于同一笔者的手了。在接近卷尾的主山明、暗部交替出现的部分,应该很少有涂上浓厚颜料的可能性,不过以广阔的江水为背景的这些暗部周围所画上的苔点,及留在明部内侧,和暗部的泥金的苔点的点法等,看来不止是单调,同时还令人有拙劣的感觉。总之本画卷的苔点数量虽少,却也很少具有苔点本来应有的表现效果。
画面上的水几乎扩及画卷上边边缘。波浪的表现及其自如的运笔都非常流畅美好,表示本作品即使不是李唐笔,也应当置于马远“十二水图”以前。
虽然没有任何保证说这幅画卷的原状就是目前这样的长度,但它的结构与著名的“溪山清远图卷”相近,因此可以想象原卷并未被整修过多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作者画它的时候是从卷首到卷尾都维持近于俯瞰视的视点来安排景观。这种作画视点的采用法与中国山水画之在同一画面上采用上下移动的视点来作画的情形不同。因此就这一点看来,本件是非常难得的作品。再和表示北宋画风的传燕文贵笔“溪山楼观图卷”或许道宁笔秋江渔艇图卷相比较的话,看不出有后者那样巨大的空间表现,也没有微妙的摇摆不定的视点的移动。本画的作者最关心的是近、中景。他以忽隐忽现的蛇行的连续小径,做为表示画卷景观联贯的决定因素,用来加强近、中景的表现。卷首上方只安排点缀性的远景部分,其左方则留下余白,以不加画笔来表示水。无论从远近法上,构图上或空间表现上看来,本画卷可以说已经是属于南宋的画风了。即使从泥金苔点的使用及塔形山的结构——如见于具有肖照落款的山腰楼观图的山——和阔叶树的叶子使用已经定形的个字点式的夹叶法等看来,相信也可以引出同样的结论。
高居翰教授认为是李唐笔的传燕文贵笔“奇峰万木图”(Chinese Painting. By James Cahill 1960 Skira)是一幅兼具松风图、江山小景图卷所见的形状与描写形式的小册页。从它所表现的三度式空间,尤其意图向深处扩张的表现看来,可说比松风图、江山小景图卷二画更具北宋式画风。正如高居翰教授所说,传称为燕文贵笔,当然是错误的。
八、晋文公复国图卷与采薇图卷
对南宋朝廷,尤其是高宗来说,最大的课题当是如何收复被金人占领的华北之地,这也是“雪耻”所必须之笔。然而从后来韩侂胄对金战争的表现看来,显然可以说这一个收复计划本就是没有实现的可能,因此高宗的认真程度如何是不免可疑的。所以对南宋来说,当时的大事件不如说是受有“庆元伪学之禁”的影响。因为这正是以收复北方失土为前提而发生的。
不过高宗朝也常有臣僚上奏有关收复华北之议。徽钦二帝一直被扣在北方,如果没有这样的收复故土之议上奏的话,南宋政权的维持势将更为脆弱。
《会编》卷九十五记载自靖康二年四月廿一日至同月廿八日间发生之事。时康王尚未即位,张邦昌以金的傀儡就伪楚帝位。康王本身则基本上虽然渐有迁往江左之意,却依旧观望局势往来山东、河南间以监视张邦昌行动。就在廿一日,大元帅府参议兼东南道总管赵子崧榜晓谕一文,今摘要如下。
“都城官吏、军民、僧道、耆老等世受大恩、各怀忠义,……谅其本心必不忘赵氏。各宜安居,无生疑惑。”同卷九十九期日不详,有关于在滑川(河南、滑县)的事,故当为同年四月二十四日左右之事,记载渊圣皇帝(钦宗)曾血书诏文于禁上日:
“宋德不兴,祸生莫测。联嗣位以来,莫知寒暑、寝食,惟安汝赤子,以卫我社稷,蔗几共享太平。不幸用非其人,兵未抵京,谋已先溃。使我道君(徽宗)而降,金族为虏。百官偷生,势不获已。所不忍闻者,京师之民舍命不顾,弃金帛宝玉欲以赎联。此最可伤恨,不得与斯民同生共死,后之社稷恐非我族。兴言及此,涕泪横流。卫士潜归,啮指书襟、敷告中外宗族、忠臣、义士,奋起一心,为联雪北顾之耻。毋忘、毋忘”。当然钦宗、高宗雪耻之语决不止此。
“伯夷、叔齐采薇图卷”、“晋文公复国图卷”二图制作背景,当受有宋代这种时局动荡的影响。《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所见夷齐事迹,自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八以来,对其事实自不免有投以疑问的人。但是就算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伯姪(译者按:当作兄弟。)间互让继承权,并劝练即将讨伐暴君封王的武王。一旦不为武王所接受,便以恥受周禄而双双隐君首阳山,采薇饿死,以全其对殷商的忠节。这是久已脍炙人口的故事。至晋文公重耳的故事,自《左传》、《史记》卷三九《晋世家第九》以来,也久为世人所知。这一个故事写晋文公重耳历经艰难到即晋侯之位,并称霸春秋的经过。晋重耳因为内乱,不得不避乱狄、卫、齐、曹、宋、郑、楚、秦诸国。于十九年后得以归晋即位,其后并尊崇周室,遂至春秋五霸之一。因此“采薇图卷”含有鼓舞沦陷金人的华北汉民族对宋表示忠诚的用意。“晋文公复国图卷”似乎寓意于表示南渡的宋室决心光复华北的意志。至其制作时期自当定于金之占领华北,及宋室南渡以后。
现存四件采薇图卷,应当都属于后摹作品,但是即使是经由后摹之本以推测的原本,也根本不象松风图。而且就算前者是故事山水图,后者是典型的山水图作品,情形也是如此。前者的自然描写简略而单纯,几乎不可能使人想到会是经由受过宋代自然主义洗礼的画家之手完成的。不过前者也可看到小景图卷所见到的个字点式的夹叶法,只是描法较为拙劣,接近卷尾的水流出口也可看到类似宋代山水画余晖的描法。岩石上所用的皱法,几乎可称为大斧劈披。树木形状比起松风图,小景图卷来,曲折异常,倾向南宋院体山水画上的形体主义。松叶并非“车轮叶”,所画针叶相当长大。
复国图卷每段都很正确的写下宋本左传的文章,画则略胜采薇图卷,但毕竟不可能是李唐真笔。只是复国图卷的自然表现仅用于区分各段。至于人物方面虽然也具有白描人物画的性格,比起可能受有李公麟影响的李唐人物来,其自然描写仍属稚拙。不过岩石和土坡的描写法、树法,都具有与松风图、小景图卷相似的地方。至形状的歪曲化这点,则又与采薇图卷的形体主义相通。尤其相当《左传》僖公廿三年之条“及楚、楚子饷之日,云云”的一段——画绢断于本故事之前——的岩山背后所描绘的涌起的云,与米友仁山水图诸作所见的白云形状不同。复国图上的云的花纹比较米氏的发达得多。
这样看来.在松风图以后,李唐山水画的表现,可说是顺着奇峰万木图、小景图卷、复国图卷、采薇图卷的先后进行的,而小景图卷与复国图、采薇图两卷的制作时期.正是宣和六年(1124)到建炎(1127-1131》之初的不到十年间之事。对已经八十岁的李唐来说,在这不到十年的短短时间内,有这样不同的自然表现,实在是令人难以了解的。
九、关于高桐院山水图双幅
本双幅正如班宗华教授所主张,属可离可合的山水图。当然并没有确证表示这双幅是离合山水图,不过从每幅都是四十三公分看来,当初从中国带到日本时很可能是横幅百公分的大幅。或因不适合日本建筑中装饰挂幅的空间,也就是所谓“床之间”的墙壁,才不得不施以日本人擅长的整修法,分开为两幅。其后又经几次改装,边缘渐被裁剪,遂成目前的样子。如果当日舶载到日本时是一幅宽大的画幅的话,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作者何以采用左右完全不同的季节为主题。姑不论此事,只从构图说,在中央偏左处配以近距离的主山看来,与松风图主山的处理并无多大不同。本挂幅暗部与明部的对照非常明显,尤其右幅使用如同刷子一笔刷下的墨面,正好与左幅主山正面的明部成了显著的对称。但这样的明暗分配法早见于小景图卷。右幅的树木可以看到浙派山水画常见的甚为曲折的树形。这种曲折的树形在传为马麟笔的静听松风图上,曲折得更为极端。而同样的芳春雨霁图册页上的树木则歪斜得更为怪异,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我们不如说高桐院右幅的树木,无论就树叶的形质把握或露出的根部的描写上看,都比较地接近松风图或小景图卷。始不论其形态如何,从针叶树与阔叶树配合在一起,再加上右幅的枯木,然后在其背景又布置以润墨画成的树林,遂使这一树丛比小景图卷的画面显得更为自然。右幅水流的描写并不很适当。至于左幅从阴暗的岩石间落下的悬瀑,其形体在感觉上与松风图近左侧的小瀑布非常相似。一般说来,平常从这类缀景的形态、曲线等可以看出作者常用的老练手法。因为一个作者要使用不同的曲线,本甚困难,这只能说是相当少见的某种革新。
右幅近景的岩石上,以宽阔的直角交错的斧皱构成,虽然因笔数繁多,致无法做更佳的表现但却也不至坏到须责备画家技法拙劣的地步。以跨越双幅之间的主山为界,其右上方重叠两座远山。相信不止笔者一人从这远山的表现与描写法吞出与李公年笔山水图相似的地方。不过后者的空间表现更为广大,更近于北宋的画,从其用墨法可以看到画家用心纤细周到。但是高桐院本也绝非不善于用墨法、构图法。左边直线斜下的山腰与隔水的小山腰构成了倒三角形。从这倒三角形之间布置远山一点看来,可知本画仍有北末画的遗意。至于北末一部分画家只在山的鞍部置远山以表现远的方法,在本图并未使用。
画中人物甚为微小,与景观不成比例。但却可看出徽宗画院的指导方针,这方针试图引导观众随画中人的举动,运用连想以完成山水画。如果想给一个诗题的话,那么右幅也许可以称之为卢仝煮茶图。至于蓬发背着大葫芦的人物的动作,正好隐藏着促使观赏的人去追想并体验作者意志的契机,而这正是徽宗画院的基本指导方针。至于左右两个长袍人物,以浅学之故,实想不出适切的诗题与故事。
左幅从飘零的树叶看来,也许是秋景或是冬景。右幅当为秋景。在图面上并不缺少这样的季节感及表示季节感的缀景。我们既已看出这一幅图与复国图卷、采薇图卷有相似的皱法——当然以复国图与采薇图都是后摹本为前提来看——则此图之属于“李唐画”之类的说法也是可以采信的。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是松风图的落款。以学过石鼓文的李唐的书体来说,未免不够味道。至于高桐院画上被人刮去的款署的书体,看来也不能说是具有书法修养的人写的。
笔者目前最想提出的一个假设是本高桐院山水图双幅是绍兴二十年代,李唐进入实质上复活的画院以后的作品。图上板状的岩石及其形状,阔叶树林的表现,粗大的墨点融和在画面中,及叶子已经落光的树木等看来,如果以溪山清远图卷为夏珪笔的话,那么本双幅图可说是相当近于夏珪山水画的作品。同时以近景和中景占据大部分画面的构图手法,及似苔点又似描点的点法看来,与其说是近于松风图,不如说也是一样的更近于夏珪图。而这些正应该看做是李唐对夏珪的影响。
究竟要把本作品看做是杰作或是凡品,应当是关系于鉴赏人的观画资质的问题,因此在这里不拟置评。只是本作品已不再是十数年前那样置于不易观看的状态。正象我们坐在松风图前从事数小时的观摩研究的努力一样,我们也必须对高桐院山水图做同样的努力。因为从瞬间的观照所得结果,和经过长时间与作品面对面仔细观察研究所得的结果,虽是两回事,然而对美术史家来说,却都是极重要的做学问的初步作业。
研究者如果只根据瞬间观看的印象,从本作品所获得的嘈杂的画面感情,便推测这是浙派作家的作品的话,只能说是一种愚蠢的观照体验,不过是显示了对浙派认识的肤浅而已,因为浙派的绘画,归根究底只是单纯的视觉印象的组合。这是因为浙派的画家对视觉印象背后的自然缺少观察眼光之故,同时也是因为浙派缺少一个人原则,无法以戏剧性的手段将成立中国山水画的自然观照及其有机性的视觉印象组合为一的缘故。然而从高桐院山水图双幅中却找不出任何一个地方有这样的缺少部分。
十、结语
前文所论难免冗长,结论是如果以松风图为李唐五十岁或五十岁以前的复古式作品的话,那么其他作品象奇峰万木图或江山小景图卷、晋文公复国图卷、采薇图卷的厚本,便可适切的纳入高桐院山水图之间。那么为什么在不足三十年之间,一个画家在个人的画风上竟会产生如此大的变化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自然必须追求。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在于北宋末发生的复古运动,及其结果促成的青绿山水形式的盛行,和因宗室贵族的喜好而流行的小景画。青绿山水形式具有远近表现法的性格,接近于空气远近法,属于不适合表现的画风,原本就带有必须重视画面的平面处理与偏平性的宿命。我们所知道的北宋末、南宋初的青绿山水画的遗品虽然有限,但是对元初再度出现的复古运动的结果所产生的青绿山水,却不愁没有例子。且从这些画归纳的结论也与北宋末、南宋初没有多大差别。虽然使用近于原色的鲜艳色彩来画山水画,的确会给画面带来华丽的感觉,但却只能产生与郭熙山水画异其本质的作品,因为郭熙是以自然主义式的表现为第一目标的。因此当代画坛这种趋势,可能也是促成徽宗时代郭熙画之从殿阁被剥走的原因之一。青绿山水画原以接近原色的色彩填满,并隔邻使用有关的补色。因此当这种青绿山水画要转换为水墨画时,只能转化成墨色对比甚为强烈的水墨画,而中间色的中墨却容易被除去不用。高桐院山水图所见的浓墨与淡墨,及留下白底的余白所构成的极强烈的对照,便须从这方面加以了解。
小景画的意义,目前还不详。但是从传为赵令穰的作品也看不出画中有以相当平衡的近、中、远景的形式来表现自然的。因此当青绿山水再加小景画,两者配合套在一起所成立的山水画,究竟会变成什么样的似乎可以很清楚地预测出。至于其时期,可能是南未初,如果光以画院绘画来看,可能是在绍兴之间,而开其先路的可能就是李唐,对后世影响之大的也非李唐莫属。
从郭熙画之被撤出殿阁这一事实看来,徽宗指导画院的一大转捩点,当是宣和中无疑。正如嵨田君所说,徽宗的心情从以画学为中心转变为以画院为中心的时期,当在政和、宣和之间。因为在政和间,由古典画风所成的郭熙壁屏画仍俨然存在殿阁内,不管徽宗的心情如何,现实的作品对作家的影响当比任何其他事都要来得更强烈才是。
但在宣和间,要从殿阁剥去郭熙的绢画,然后再由徽宗亲自去将自己的绘画理念加以具体化,在时间上看来,留给徽宗的时日未免太短。宣和年号终于七年,在其末年,辽、金、宋间已开始血腥的战斗。因此最自然的推理是在徽宗在位期间,不可能充分的实现他自己的绘画理念。要在画院中将这种理念加以具体化,可能还需要二十年或三十年。而其具体的实现无疑的一定是由徽宗朝画院转入高宗画院的画家们所达成的。至其有力的推进者,我们不得不说是李唐。这是李唐之与刘松年、马远、夏珪同被称为南宋四大家的原因,同时他也是影响马、夏最大的画家。如果南宋画院曾在绍兴二十年代的某一个时期开设的话,那么李唐个人的画风之从松风图转变为高桐院,当然也可以认为是因其必然会发生而发生的。
当然我们不能只以上述两个因素来了解高桐院山水图。例如左幅右下方采用极快的速度描绘的树枝,它的描线可以想象必然是受到北宋末开始出现的墨戏的影响才能产生。苏轼的古木图那类画的影响便是其例之一。
从松风图到高桐院山水图的画风的变化正是李唐自五十岁前后的画风到八十岁左右时的画风的转移的结果。在这期间,各方面的价值观必然的都有不同的改变。这种改变在绘画观上也免不了发生。这是一个连攀仿的作品也会变质的时代。松风图与高桐院山水图两作品之间的画风与描法,乍见差异甚大,事实上却意外的小。何况一个画家的画风与描法既会随时间的转移而改变,那么我们应当可以认为此两幅画可以很妥善的依照时间转移先后插到同一画家的相称时期的变化之中。
作者:铃木敬【日】
译者:魏美月
据《国华》1047号第88编第6册。由干篇幅关系,原注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