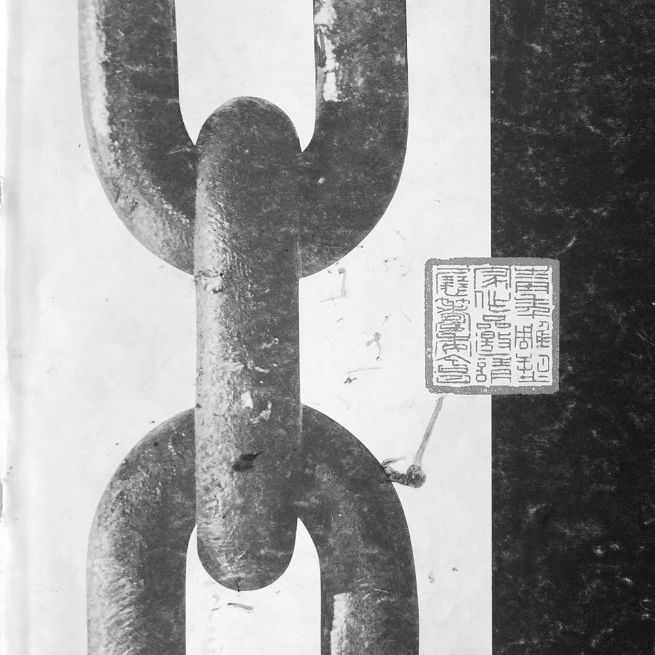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凡世界文明理无退化。独中国之画在今日,比二十年前退五十步,三百年前退五百步,五百年前退四百,七百年前千步,千年前八百步,民族之不振可慨也。夫何故而使画学如此其颓坏耶,曰惟守旧;曰惟失其学术独立之地位。画固艺也,而及于学。今吾东方画,无论其在二十世纪内,应有若何成绩,要之以视千年前先民不逮者,实为深耻大辱。然则吾之草此论,岂得己哉。
主旨与例
凡美之所以感动人心者,决不能离乎人之意想。意深者动深人,意浅者动浅人。以此为注脚,庶下之论断,为有根据。例如下:中国画山水,西人视之不美;西方金发碧眼之美人,中国老学究视之不美。刘洪升之歌谭迷深者不之美,王蒙倪迂等之画文人视之美,北碑怪拙吾人能得其美,上海月份牌浅人视之美。欧洲之名画,中国顽固人,意中以为照相,则不之奇,西方画有绝模糊者,吾人能解其美。凡寓意深远,艺复卓绝者,高等人类视之均美。吾今特以下列各例,充吾论之主脑。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
学之独立
夫画者,以笔色布纸,几微之物,而穷天地之象者也。造化之奥赜繁丽壮大纤微有迹象者,于画弥不收,故须以慧根人竭毕生之力研究之。中国画在美术上,有价值乎,曰有。有故足存在,与西方画同其价值乎,曰: 以物质之故略逊,然其趣异不必较。凡趣何存,存在历史。西方画乃西方之文明物,中国画乃东方之文明物,所可较者,惟艺与术。然艺术复须藉他种物质凭寄,西方之物质可尽术尽艺,中国之物质不能尽术尽艺,以此之故略逊。顾吾以此难施人力之物质,而欲穷造化之奥赜繁奇。人三年而艺成,我则须五年焉。人作一画五日可成,我则需八日,或十日焉。而所形容万物之情,无少异,则中国画尚为文人之末技,智者不深求焉其有足存之道哉。
改良之方法 学习 物质 破除派别
画之目的,曰( 维妙维肖) ,妙属于美,肖属于艺。故作物必须凭实写,乃能惟肖。待心手相应之时,或无须凭实写,而下笔未尝违背真实景象,易以浑和生动逸雅之神致,而构成造化。偶然一现之新景象,乃至惟妙。然肖或不妙,未有妙而不肖者也。( 前曾作美与艺可参阅之) 妙之不肖者,乃至肖者也。故妙之肖为尤难。故学画者,宜屏弃妙袭古人之恶习,( 非谓尽弃其法) 一一案现世已发明之术。则以规模真景物,形有不尽,色有不尽,态有不尽,趣有不尽,均深究之。中国画通常之凭籍物,曰生熟纸,曰生熟绢。而八百年来习惯,尤重生纸,顾生纸最难尽色,此为画术进步之大障碍。而熟纸绢则人以为易为力,复不之奇。又且以为绢寿祗八百,纸祗二百年,重为画惜。噫异矣,夫人习画,于生纸绢也成需六七年,且恐未必臻乎美善。熟者五年色与形已俱尽,徒矜凭物之难不计成绩之工拙,则戴臼而舞耳,焉用之。且斤斤于纸绢寿之长短尤愚可哂。不知物之不良,已无保存之价值。八百年后存在问题,又胡须早筹。此与鸦片烟鬼。偃起之求长生者同一陋见也。( 按中国绢纸,至今日均坏极,纸则蚕制者已无,绢亦粗脆光滑不可用笔,倭制甚精,故其画日进弥已也。) 笔与色尚足用。今笔不乏佳制,色则日渐粗矣。鄙意以为欲尽物形,设色宜力求活泼,中国画中凡用矿色处,其明暗常需以第二次分之,故觉平板无味,今后作画,暗处宜较明处为多,似可先写暗处,后以矿色敷明处较尽形也。人类于思想,虽无所不至,然亦各有其性之所述。故爱写山水者,作物多山水。爱人物花鸟者,即多人物花鸟。性高古者,则慕雄关峻岭长河大海。性淡逸者,则写幽岩曲径平村远山。性怪僻者,则好作鬼神奇鸟异兽丑石癞丐。既习写则必有独到。故吾性之何近者,辄近于何作之古人。多观摹其作物以资考助,固为进化不易之步骤,若忘自暴弃,甘屈屈陈人之下,名曰某派,则可耻熟甚。且物质未臻乎极善之时,其制作终未得底于大成,可永守之而不变。初制作之见难于物质者。物进步制作亦进步焉。思想亦然,巧思之人,必不能为简单之思想所系动。矧古人简约,必有囿于见闻者。今世文明大昌,反抉明塞聪而退从古人之后何哉,撷古人之长可也。一守古人之旧,且拘门户派别焉不可也。
今对各类尽应改良之点述之如次: 风景之改良,雪、树,平地,房屋。
( 馀论山石雪影)
天之美至诙奇者也。当夏秋之际奇峰起乎云中,此刹那间,奇美之景象,中国不能尽其状,此为最逊欧画处。云贵缥缈,而中国画反加以钩勒,去古不远,此真无谓,应改作烘染。中国画中,除松柳梧桐等数种树外,均不能确定指为何树。即有数家按树所立之法,如某点某点等,终不若直接取之于真树也。尤宜改节,因中国画中所作之树节,均凹癞者,无瘿凸者,树状全失,允期必改。其余如皮如枝,均当一以真者作法。中国画之地最不厚,以纸绢脆弱不堪载色也。古今写地最佳者,莫若沈南苹,南苹工写土石,小杂野花,且喜点苔,故觉醇厚有气味,盖彼固得力乎写生者也。宋人界画,本极工,但只有两面,若作斜面,则远近高低如一,去理太远。近人吴元和改正之,今已无守古法者,虽为可喜,实则今已无工界画者矣。
吾国古今专讲求山水,故于山石各家皆有独到处,但各家胸中邱壑逸气均太少耳。如李思训写北宗之山,必层峦叠嶂,直造纸末。王蒙亦如之。倪云林则淡淡数笔,远山近树而已。为邱壑者必叠床架屋,满纸邱壑,不分远近,气势蜿蜒,直到其顶。胸中直具邱壑为逸气者,日向水渚江边立,两眸直随帆影没。而无雄古之峰,郁拔之树。夫峰也树也,岂有碍逸气哉,直遁辞耳。( 倘登太山观论海,而从侧面作一图,舍山乎抑舍海乎,两不可舍为技不已穷乎) 吾国写山水者,恒喜写雪,不知雪中可游而乐,最不易宜写而观者也。若必欲逞逸兴,亦须点染得法,从物之平面上积雪,毋从不积雪处漫积之斯得矣。远山尤宜注意,中国画不写影,其趣遂与欧画大异。然终不可不加意,使室隅与庭前窗下无别也。( 参阅结论)
人物之改良
尝谓尽不必拘派,人物尤不必拘派。吴道子迷信,其想象所作之印度人,均太矮,身段尤无法度,于是画圣休矣。陈老莲以人物著者也,其作美人也,均广颔,或者彼视之美耳,吾人则不能苟同。其作老人则侏儒,非中国之侏儒也,乃日本之侏儒。其人所服则不论春夏秋冬,皆衣以生丝制成之衣。双目小而紧锁,面孔一边一样,鼻旁只加一笔,但彼固非立法者也。后人愿抛弃良智而死学之,与彼何与哉。
夫写人不准以法度,指少一节,臂腿如直筒,身不能转使,头不能抑面侧视,手不能向画面而伸。无论童子,一笑就老。无论少艾,赞眉却丑。半面可见眼角尖,跳舞强藏美人足。此尚不改正,不求进,尚成何学。既改正又求进,复何必云皈依何家何派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