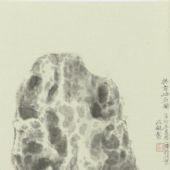在方政和心目中,花与鸟的气质是“矜持、优雅、娴美、文气”的,这本是他的个人气质,界定了他的眼光,也濡染了他的画笔。在他的创作中,宋元工笔花鸟画,尤其宋徽宗“宣和体”已经从被继承的传统变成被反复宣示和阐释的主题,他的《唐人诗意图》就采用了宋徽宗时期的宫廷绘画《五色鹦鹉图》、《瑞鹤图》、《祥龙石图》(这几件作品被许多专家认为原属于宋徽宗时的祥瑞画册《宣和睿览册》)图文并置的样式,文字布白和字体书风也与“宣和体”一致。《拂云岫石图》虽然采用立轴形式,但湖石造型又显然来自《祥龙石图》。《花鸟小品之一、之二》则取法于另外两件宋徽宗宫廷绘画《蜡梅双禽图》(四川省博物馆藏)。《宣和往事――犹当江南梦里看》采用充满现代感的双屏形制与丰富的用笔赋色技巧,但又以画题直接表达对上述传统的恒久敬意。
这让人揣测他的名字“政和”或许是有意为之,结果竟是巧合,当初父亲给他起名为“政和”,并未预见到他将会成为画家。那只能说是冥冥中的天数了――“政和”是宋徽宗的另一个年号(1111-1117),那时北宋的宫廷文艺包括绘画,正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在遗存至今的“宣和装”书画中,我们还能看到成套钤盖的“宣和七玺”,包括“政和”长方印和“政”、“和”连珠印,而后者正是方政和常用的名章,虽然大小字形与宋代玺印有些不同。他还用别署“方正禾”,“正禾”是“政和(龢)”的同音异体,同音异体正是古代文人习用的别署制造法。
与宣和体的繁华富丽相对照的是,他的画中罕用明艳的色彩,多是清冷苍灰,诗情画意中总是流露出淡淡的忧郁。草木的荣枯、禽鸟的生机,都成为生命感慨的寄托。这也许是因为他的艺术成长于南京――这座十朝古都,经历了十朝兴亡,王朝的生命就像草木荣枯一样轮回不已。方政和第一次到南京不久,就经历了长江边的冬天,寒风从不远的江面上肆意地冲进城里,直扑人面。在那令人绝望的彻骨寒冷中,他一定也体味到了这座城市空气中永远无法稀释的哀惋。他的新作《寂寞秋江上》只是画了平静空旷的水面上一片干枯的大荷叶和一只安静的绿头鸭,并题写了金末元初刘秉忠的散曲【南吕•干荷叶】,但是摘取曲中“寂寞秋江上”五字为画题,却更易令人联想到该句的文本原型——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名句“鱼龙寂寞秋江冷”,一句对王朝危局的感叹。然而曲家刘秉忠作为大元朝政治制度与元大都城市设计者的特殊身份,又把诗情画意从中古时代拉回眼前的北京,从亡拉到兴。画家行迹贯穿起来的历史感,就这样把一花一鸟的小小题材,扩大为捉摸不定的千古寂寥。
画家的人生经历和学画过程并不复杂。他1970年出生于闽南漳州云霄县,1991毕业于厦门集美师专,随后回到家乡担任中学美术教师。一晃十年过去,像微风吹过水面,在他的艺术生命中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不变的是对绘画执着的迷恋。他一直在画,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有很多话想说,却又手不应心,后来他笑谈当时的状态真像一个哑巴――技法水平上的局限,使他手不应心。他盼望找到一位能系统提升自己的好老师,而机会在多年以后才终于降临。2001年,他到南京艺术学院进修,师从工笔花鸟画名家江宏伟先生。多年以后,他深情地总结说:“南京是个特别能培养、涵养画家的好地方,是一个平静而自成良性循环的好系统,能让人从自我的蒙昧中清晰、豁然、顿开的好环境,能从0到1,这比从1到10的意义还要大。”
他是有慧根的,仅仅一年的进修,就像得到灌顶和点化,从第二年起,积蓄多年的能量爆发了,不断推出的新作屡获重要奖项:2002年获《2002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金奖,2003年获《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银奖和《2003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铜奖,2004年获《全国首届中国画电视大赛》银奖,2005年获《纪念蒲松龄诞辰365周年全国中国画提名展》金奖,2006年获《第六届全国工笔画大展》铜奖,2007年参加《同一个世界•中国画家彩绘联合国大家庭艺术大展》(与江宏伟先生合作),是年又获《全国第三届中国画展览》优秀奖……在此期间(2006-2009年),他又师从江宏伟先生攻读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来又进入北京画院成为专业画家,得以在这座北方都市怀抱里体会古代帝都、今日国际都会的别样风采。使他获得画坛认可的并不是奖项和文凭,而是立足传统、不断进取的治艺态度,是陆续问世的出色作品。十年来,他一步一个脚印,从一位籍籍无名的画坛新人,成长为全国工笔花鸟广为人知画家,个人风格也逐渐成形并走向成熟。
对当代画家来说,传统只是创新的原材料,无论画家本人对待传统的态度多么虔诚。在方政和更多的画里可以看到对传统的利用与改造。他的《画禽记》灵感显然来自被传为黄筌的《写生珍禽图》,原作中的不少禽兽被置换,造成一种穿越感,它们或似从其他宋画(如《山鹧棘雀图》、《禽兔图》)中翩飞而下,或似从方政和其他画中营造的世界中淡入。横宽的画面被置于中段,上下各接裱了同样大小的米黄色的纸,从《写生珍禽图》中精心临摹的四只鸟被等距离地排列在空白的背景之前,并构成大画面的中轴。这样,一幅古画就化身为具有装置意味的现代作品。
这一手法在《回望宋人――隔断千山》中变得更为大胆,中间部分是元人徐泽的《架上鹰图》复制品,鹰架华丽,鹰则姿态矫健。左右各配以大小形状相等的纸,各画了一只体型肥胖、引颈西望的家鹅。鹰的机警与鹅的悠闲形成对比,而它们引颈西望的姿态则构成呼应。猎鹰善于捕捉野鹅(大雁,也有天鹅,明代宫廷画家殷偕有《海青拿天鹅图》),将之与家鹅放在一起相安无事,也算小小幽默。而更直接的反差则来自形式的对比:《架上鹰图》本是绢本画,表面上矾,背后托粉,即使只是印刷品,物形仍不失厚重饱满,两侧的配图则画在生宣上,家鹅细腻中不乏清淡,而背景则用不匀的满涂造成浑茫与变化。
画在熟宣纸上的《咫尺之四》在湖石、鸭子、地面、墙面这四种深浅不等的灰调子包围下,利用银箔嵌入了两片明调子,地面、墙面和窗口(又像是墙上挂的画)交界的倒T字交角,被鸭子毛绒绒的身体挡个正着,写实与设计甚至装置感,也被轻松地揉和在一起。《千里万里心里梦里》则以四条天水空茫处的孤独飞鸟加一条深蓝之中的空无,传统的四条屏成了奇特的五条,也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装置,那种意境和画题一样,是画家自己内心深处的呐喊。
其实他内心有渴望渲泻的力量,想冲破伴随设计感的理性主义,只是他又觉得自己的个性更适合驾驭工笔画,强烈的表达欲求与形式上的明确指向,使他认识到细腻只是工笔画的表象,“重要的是要在细腻、精致中提炼、概括出生活的丰富性。意笔有豪迈、奔放的美和性格,奔放不是放纵,收放有度与只泛不收的泛滥只在一念之间”。因而他有意识地在工笔画中融入写意笔法,无论是勾描还是涂染,都试图表达出用笔的书写性。
这种尝试的极致,就是在生宣纸上画工笔画,这也成了他技法的特色与难度所在。他的很多画采用一种台湾生产的高档生宣,表面比较致密,但仍然对工笔技法提出了挑战,行笔赋色,来不得半点犹豫。笔与笔、墨色层次之间的衔接也颇费匠心。实际上,这种技术要求正与他追求的书写性不谋而合。他在工笔禽鸟与花果之旁经常配以小写意的枝干与湖石,背景大片空白中的涂染也不求平整,故意追求笔触造成的变化。他还屡屡学宋人作湖石,如《丑石》、《拂云岫石图》,宋画中多遍染就的弹窝痕,在他的生宣画中只能一遍画成,细看处用笔不乏流畅。《伯劳》以工笔画的飞鸟与湿染的石头并置,鸟在振翅的过程中仿佛静止并与静立的大石头融合为一体。
今天大而化之的“花鸟画”,实际上包括了宣和时代的花鸟、畜兽、龙鱼、蔬果、墨竹,以及在《芥子园画传》中列为小专科的草虫。方政和对于选择题材的看法是:前人画得太多的题材不好突破,人工干予太多的物种则缺乏天趣。相比于前人,他的眼光更多地从陆地、空中转向了水上和水下。他小时候在家乡农村当过放鸭童,对家禽的生活习性可谓体察入微。家鸭和家鹅都是他爱画的题材。这两种题材在宋人笔下也出现过(如宋代宫廷绘画《红蓼白鹅图》),在明清则多以小写意画法绘制,作为田园风俗或文人隐居题材的点缀(例如《羲之爱鹅图》),但用工笔精细入微地描绘它们,在数量、形制和主题上形成序列,却是方政和的特色。在水族题材中,他喜爱的不是宋元人喜画的鲤鱼,或近人开发的新题材金鱼,而是一些造型颇有古意的热带鱼。即使画这种新鲜的题材,也要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在《渌水双行》一画中,两条鱼优游并行,它们的背鳍、腹鳍、尾鳍都被极度夸张,大尾飘扬,有如古代高士手中的麈尾,吻部则化尖为圆,更接近传统的鲢鲤之类淡水鱼。
据说工笔画前辈名家于非厂先生画鸽子飞翔在天之状,一直只画其腹,不画背,有人问为何,他说人站在地上,仰观飞禽,只见其腹,不见其背。1959年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要画和平鸽,必须有多种角度和姿态,于是他被特别批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了三天飞鸽,哪个角度都看全了,才画得飞鸽生动多姿。前辈画家敬畏造化、体物入微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但今天画家借助科技手段和图像传播,已经长上了千里眼,上天入海,无所不能。《渌水双行》和《沉鱼传说》中,悠闲的游鱼(身旁还有湖石)似乎身处水族箱中,又似乎通过水下摄影镜头而进入我们的视界。它们的自得其乐与我们的濠梁知乐,成了同一件事物的正反两面。方政和有许多画暗示的观察方式与角度显然与日常生活中的肉眼观察有别,影像艺术对他的画自然有潜在的影响,《秋霜白》的主角――一只扭头梳羽的白鸭子,从青灰色的背景中浮现出来,浑身仿佛放射出圣洁的白光,这种光效对比就如同经过了镜头的处理和强化。
不过他要强调的不是技术化的照相写实,而是移情寓兴:“画上飞翔的姿态对我来说,是内心的结,也是内心的界,我总以为这算得上是与自然的另一种重逢,一种可期的相遇,高高的枝桠上安顿的其实是我们自己!”他在工笔的写实效果发挥到极致之时往往又施以相反方向的力,书写性和线条感除了使形式更为丰富,也是表达“间离效果”的手段,时时提醒观众这只是画,是摄影无法制作出来的手工作品。在《沉鱼传说》中,一条孔雀鱼轻灵地一头扎到水下,长尾拂处,在水面留下一朵浪花。水下是一片淡染无痕的青蓝,连湿染的湖石也用变化丰富的青蓝色代替了墨色,而这水面却是采用传统绘画中极具装饰意趣的鱼鳞纹大波浪,用线条一丝不苟地画出。一大片流动的、清丽的线,压住了水的幻觉。那个“沉鱼落雁”的美人,并不需要出现在画面上,但她的美就像这青蓝色,笼罩了一切。
线条比渍染能更鲜明地表达作者的个人意趣,又似乎是画与文字之间的中介。其实,方政和的文字也细腻动人,他这样享受着“工笔这种娓娓道来的赋彩方式”:“工笔画的绘制过程好似文火煮药,粗陶小炉,水汁浸没根茎和枝叶,木炭默默地燃烧,草本存储、凝结的精神重新被唤醒。一遍遍的渲染,植物的色彩调和清水,让草木花卉在它昔日的植物兄弟——宣纸上又一次生长开放。笔毫轻柔顺滑,点点和滴滴持续晕化成宣纸上一个个浓与淡的涟漪,圆圈缓缓扩散开来,甘美的品质重新被移栽——纸上这芬芳鲜艳的灵魂只配用这般柔软呵护、百转千回的方式来种植。”平生第一次,我感到一位画家的文字营造了与画境一般清雅优美的意境确实。有了这样细腻心思的人,才会以亲密的眼光去观察草木鸟兽,用温润的笔触去描绘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