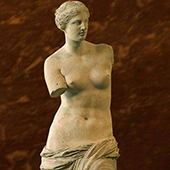在充满“革命现实主义”色彩的美术史叙事中,创作者的“艺术家”身份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他们往往首先是个“现实主义者”、“革命家”,而非是一个“艺术家”。比如,很少有人用看待“毕加索”的方式来看待王式廓。王式廓这一代艺术家身上的革命色彩、现实主义特征往往被强化和突出。这样的强化和突出既表现在对他们个人成就的评价文章中,也表现在以往所组织的大型展览对他的定位中。总体来讲,这些文章和展览基本上从宏观环境出发,把艺术家视为这一宏观环境的产物,当然,又和具体的地域相连接(比如延安、北京)。惯有的宏观叙事是否遮蔽了艺术家的更多特征呢——这些特征更多不是宏观的,而是微观的,更具有艺术家的个体特征的,因而更具有微观政治学的含义。相对宏观政治学而言,微观政治学主要研究政治主体个体的政治行为、政治活动以及与个体有关的政治现象及其各种有关因素。其注重对政治现象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研究,从而使政治学的研究进一步具体化、细致化。艺术家王式廓首先是一个“人”,才是一个革命者。而“人”这个角度,又和他的“艺术家”身份环环相扣。
王式廓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艺术家”身份的呢?由于各种原因,在以往的叙事中,王式廓往往把这个身份降低到次要位置。试想,用审视“纯粹艺术家”的眼光来分析王式廓,会在既往的艺术史分析之外,展现出这位艺术家的丰富之处。这一新的审视方式,应该是和王式廓的艺术创作中的核心问题相关联的——在既往的将王式廓的艺术道路视为追寻革命理想的维度之外,会发现他为艺术而殚精竭虑的一面。
其实,除了把自己视为一个革命者之外,王式廓是把自己的个人生命历程视为艺术创作历程的艺术家。王式廓早年一方面进行艺术技法的磨练,在国内几所著名的艺术院校都学习过;另一方面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后来他考入东京艺术大学,在考学之前,他就基本确定了后来给他带来巨大荣誉的素描技法的特点——“概括、传神,不陷入细节的琐碎处理中”。在聊城、武汉进行抗战绘画创作,王式廓始终在找寻这一艺术语言的和时代之间的对应关系。为了实现这个恰当的对应关系,他一方面继续进行着艺术技法上的锤炼,另一方面继续进行着现实环境的选择。
伦勃朗在《夜巡》之后,人生境遇出现了大的转折。在诸多解释中,有一种解释最为合理:伦勃朗这时的美术风格(可以具体化素描、油画技法)已经使他不再安于既往的偏向古典主义的画风,而这种新风格正是他周围的荷兰赞助人所难以接受的。伦勃朗的技法超越了时代,但他仍然执着于这样的表现方式,出现后来的厄运也就在所难免了。类似于伦勃朗,王式廓也在寻找他所擅长的美术技法和时代的关系。不同于伦勃朗的超越性,王式廓是想用自己所掌握的美术技法和时代形成真实的契合性。
抗日战争始发,王式廓在聊城、武汉进行创作,尽管规模宏大,周围的同志对他的绘画能力也倍加赞扬,但王式廓仍然觉得此时的创作和他真正要达到的表达仍然隔着一层“皮”。也就是说,他仍然找不到这一确切的和时代对应的关系,他也一直为此苦恼。
走向延安之前,王式廓由最初对绘画技法的沉迷以及对绘画技法价值的坚信,到对艺术精神的更深入挖掘,再发展到对现实社会的逐渐关注,这基本上是他早期求学、留学、参加木刻社、参与抗战等前期活动的三条主要线索。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王式廓何以会自动选择走向延安,因为延安是能让他的艺术才能得以展现,艺术理想得以实现,现实关注获得知音的地方。在以往的叙事中,王式廓走向延安主要是一个革命行为。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这次“走向延安”也是王式廓为自己的艺术技能找到合适的用武之地的艺术选择。尽管他在最初选择时可能是模糊的,但一股青春热情可能构成他“现实出走”以及“艺术选择”的共同源泉。
延安时期,王式廓早期的艺术追求和社会追寻最终被《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明确和完美表述。所以王式廓对《讲话》的选择不是服从式的,而是随着他的艺术思想的逐渐成熟,在恰当的时机与《讲话》的相逢。这个“相逢”左右了他一生的创作方向,成为支配他艺术创作的一根主线。当他进入到延安的特有环境之中时,他才在自己的艺术语言和时代之间找到了一种“恰当”的对应关系。
突出体现了这一“恰当”的对应关系的作品便是王式廓早期版画作品《改造二流子》。自徐悲鸿以来,对这件作品的赞誉已经诸多,在此不再锦上添花。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这件作品中,王式廓在人物表现、题材选择、版画语言等方面实现了高度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正是王式廓以往所苦苦寻找的。一方面,他为他的表现对象、他的主题选择找到合适的表现语言;另一方面,他的经过锤炼、延安之后几经变化的艺术语言,也找到了合适的表现题材。如果这样说有些抽象的话,可以想想米勒对巴黎郊区农民的选择,也就明了了。我们多从伦理角度去看米勒的选择,其实除此之外,米勒有没有技法上的考虑?以及他所追求画面风格和农民形象的暗合性?王式廓对农民有着自发、淳朴、深厚的感情,这在以往文献中多有提及。除了阶级感情之外,能不能从艺术家的风格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呢?王式廓一直追求的生动、概括的绘画风格与农民身上的淳朴、憨厚的性格特征,粗犷、沉重的外貌特征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呢?建国后王式廓的创作高峰为大型素描作品《血衣》。在《改造二流子》中,王式廓实现了西方绘画技法与延安革命氛围的链接,作品中洋溢着鲜活的生活气息,这件作品相对于其后的《血衣》来讲,还是一件“小品”。在《血衣》中,王式廓是期望实现一种史诗般的风格,并且已经达到。王式廓最为推崇的素描风格、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主题、他一直关注的农民……皆在这件作品中实现了高水平的融合,由于历史原因,这件作品最终没有变成油画。如果从艺术角度来看,这是不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呢?
毋庸置疑,王式廓是在延安进入了创作状态。王式廓曾多次动情地提到《讲话》对他的醍醐灌顶的提示。“鲁艺是根据革命艺术教育的特点,以及克服边区困难的自给经济的生产任务来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这就是艺术教育和劳动结合的方针。通过这个办法,顺利地解决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学与用的结合、艺术与政治、艺术与群众结合的问题,也解决了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以及提高与普及的矛盾和统一等等问题。” 此后的一生,王式廓是坚信这一创作方向的。这种“坚信”使他进入了一般艺术工作者所难以获得的深入状态,构成了王式廓的精神世界。换句话说,王式廓对《讲话》精神的坚持,构成了他创作的基点。他是位有所坚持的艺术家。时下对王式廓的评价,多和对《讲话》的评价纠缠在一起。能否将两个“评价”分开来看呢?艺术家相信什么,这个“什么”的价值高低,正确与否,往往和他最后的艺术成就无关。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小路也可以通罗马。问题是作为艺术家你能不能找到自己所适合、坚信的一条路。
作为艺术家的王式廓经常表现为作为“艺术家”的气质。此处仅举一例。就是他一直以来对于“画家之眼”的强调。
朱乃正曾这样记述王式廓所提到的“画家之眼”——“因为绘画本身是视觉艺术,是靠画面形象来说话的,所以艺术家要有一双深邃敏锐的眼睛是至关重要的。一切真的美的,需要通过眼睛去鉴别发掘,一切假的丑的,也需要通过眼睛去挑剔弃除。我一直很清楚地记得,王式廓先生在指导我们作画的时候,经常强调的一句话:‘你们不能以普通人的眼睛去看事物与对象,要时时刻刻用艺术家的眼睛去观察,这是个重要问题!’”
怎样的艺术家会拥有这样一双眼睛?在我看来,只有进入、并时刻处于创作状态的艺术家才可能有这样的一双“眼睛”。王式廓对他的“画家之眼”多是教学中的强调,我们可以与19世纪的罗斯金做一类比,在后者的理论体系中“纯真之眼”是一个核心问题。罗斯金的“纯真之眼”的源头是什么呢?如果说王式廓是基于《讲话》进入了艺术家的状态,罗斯金则是基于宗教进入了这一状态。
我们经常会惊异于罗斯金超常的、洞察细微之物的感受力,我们经常将他的这种感受力归功于他的艺术修养,但在罗斯金的思想中,难以将他的宗教观、艺术观区分开来,更难以确定这两者中谁是更基本的渊源:是狂热的宗教信仰激发了他的审美欲望?还是他的审美欲望强化了他的宗教信仰?这是难以回答的问题。有些理论家将罗斯金的艺术欣赏力归功于他的艺术知觉,比如文杜里,但同时他又认为这种能力源于“古老的宗教之根”。克罗齐发现罗斯金的遵循是“自然的和目的说和神秘的直觉说”,也认为罗斯金的超常感知能力是和他的宗教信仰相联系的。沃尔斯托夫也在《艺术与宗教》一书中批判了“艺术的存在是以审美沉思(aesthetic contemplation)为目的”的理论,认为艺术是以多种多样的渠道进入到人的行为结构中来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宗教。他强调自己写“这部著作试图明确阐释,作为一个基督教徒的我是如何看待现实中的艺术和审美领域的。”罗斯金认为这个世界有一个源头,就是上帝,他认为上帝与自然界、人类世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罗斯金将自然界视为上帝的“语言”,认为人类通过观察自然界可以发现上帝。
“画家之眼”只是王式廓表现出艺术家状态的一个具体方面,从多角度去理解20世纪的这位绘画大师,不仅是对他的个人状态理解的丰富,也是多角度看待20世纪中国革命美术史的一个契机,期待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文/刘礼宾
[1] 王式廓,“继承与发展革命美术教育传统“,《美术研究》,1958年第2期
[2]《美术研究》,1991年第1期,页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