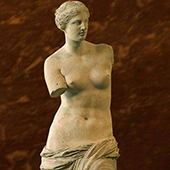在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中,“程蝶衣”(张国荣饰)曾两次唱昆曲《牡丹亭》。程蝶衣第一次唱《牡丹亭》是为了救“段小楼”((张丰毅饰)),他为日本军官“青木”唱堂会,唱的是《牡丹亭》第10出“惊梦”中的片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程蝶衣救出了段小楼,根本原因是日本军官青木“懂戏”。1945年以后,程蝶衣因曾为日本人唱“淫词艳曲”被捕。“袁四爷”(葛优饰)在法庭上慷慨激昂,他说程蝶衣所唱的《牡丹亭》并非“淫词艳曲”,而是国粹,因此赢得了满堂喝彩,但是“四爷”没能救出程蝶衣,原因是程蝶衣认为日本人懂戏,认为青木要是活着,戏早就传到日本国去了。程蝶衣之所以如此回答,一方面隐含着他对戏的痴爱,段小楼就骂他是“戏痴、戏疯子”,因为爱戏,所以他对“日本戏迷”的认同竟然超越了国界;另一方面,这里面隐含着程蝶衣对段小楼的痴情,他认为自己是为了段小楼才去参加堂会的,所以他不承认是自己是“被逼”的。最终救了程蝶衣的是一位军届要员,他也懂戏,程蝶衣第二次唱《牡丹亭》就是为了报答这位“要员”的救命之恩。段小楼获救是因为出现了一位懂戏的日本人,程蝶衣获救是因为遇到了一位懂戏的国民党军界要员。其实对于程蝶衣来讲,他最凄惨的日子是在建国后。在建国前,他无论遇到什么风险,他都可以凭借他的“戏”逢凶化吉。建国以后,他所痴爱的“戏”遭到了批判,他的“戏”没有了知音,只是反动文化的象征,真的成了“淫词艳曲”。遭到了红卫兵(吴大维饰红卫兵头目)的彻底打击。
我在本文中让“程蝶衣”、“青木”、“袁四爷”、“红卫兵”代表四个角色:昆曲、国际教科文组织、“昆曲戏迷”(比如白先勇)、没有接触过“昆曲”或难以进入“昆曲”所营造氛围的大部分中国观众。我把“程蝶衣”、“青木”、“四爷”“红卫兵”视为喻体,把“昆曲”、“国际教科文组织”、“昆曲戏迷”、“中国观众”视为本体。
(一)“程蝶衣”
程蝶衣的“成角”经历了艰苦过程,关于这方面。陈凯歌在电影的上半部分进行了大量渲染:程蝶衣是婊子养的,所以连当“戏子”的机会也没有。他的母亲想了个惨烈的办法让他进了戏班子。后来他逃出大院,自己又回来了,开始对“戏”有了认同感。再后来他实现了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认同,经历了彻底的蜕变,羽化成蝶——“程蝶衣”出世,他成了“角”。程蝶衣在建国前盛名一时,但到了文革时期。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故事为题材的京剧遭到了批判,程蝶衣对京剧“原味”的坚持成了反动,他那隐晦、凄惨的身世也成了打击的对象。在“旧”文化中,京剧有其存在的土壤,连程蝶衣此类的身世也可以在那样一种文化中被 “藏污纳垢”,但是“新中国的天是明亮的天”,那里容得程蝶衣的存在?就在“新时期”开始的时候,程蝶衣选择了自杀,其实文革结束并没有使程蝶衣看到什么希望。程蝶衣为什么选择死?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要“从一而终”,他要为他对朱小楼的爱情而死;二是他所痴迷的“戏”已被摧残,这在电影最后并没有指出。但是通观整部电影,不难看出程蝶衣在这方面的失意。
昆曲又称昆(山)腔,元末明初昆山人顾坚始创。明嘉靖年间(1552年—1566年)魏良辅改革,形成了 “水磨腔”。 这种新腔的特点是清柔婉转,成为集南北曲之大成的新声,但这时的昆曲仍是清唱,尚未能形诸舞台。昆曲由清唱搬上舞台,成为戏剧,则是由梁辰鱼的《浣纱记》开始,梁辰鱼的一方面为昆曲奠定了文学基础。另外在伴奏方面,除弦索之外,梁辰鱼又为昆曲加上了笙、箫、管、笛等乐器,形成管弦并举,令人耳目一新,于是很快流传开来。至明万历年初,昆曲扩展到江、浙各地,成为压倒其他南戏声腔的剧种。随之由士大夫带入北京,与弋阳腔并为宫中大戏,当时称为“官腔”,从此成为剧坛盟主。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一时风靡天下,昆剧达到鼎盛时期。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昆曲的辉煌与其特性有关,衰败也和它的特性有关。通过“注1”我们可以得知,昆曲的创始人顾坚是倪瓒(倪元镇)的朋友。昆曲的兴盛本来与当时文人的生活情趣、艺术趣味就是一脉相承的。文人的文化修养为昆曲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品位,他们的闲适生活和对空灵境界的追求赋予了昆曲超逸品格,使昆曲在音乐、唱腔上多表现出惆怅、缠绵情绪。1790年徽班进京,开始了“花雅之争”,以雅部昆曲的失败而告终,从此京剧大盛,而昆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其后昆曲曾有几次振兴:20世纪20年代苏州“昆曲传习所”培养出的40余名“传”字辈艺术家,被誉为是保留下昆曲拯亡断绝的星星火种;1956年一出昆剧《十五贯》轰动了全国,《人民日报》发表了“一部戏救活一个剧种”的评论文章,但是此后的昆曲仍不可救药地衰落了下去。2001年5月18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在巴黎隆重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昆曲名列榜首。这个时刻被称为昆曲的“第二个春天”。被发现的“春天”。
程蝶衣得到了日本人青木以及国民党军界要员的肯定,昆曲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肯定。
(二)“青木”
程蝶衣认为青木是懂戏的,否则青木怎么会放了朱小楼?国人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是懂昆曲的,否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怎么会把这样一个显贵的“头衔”给了昆曲?
艺术成就如此卓越的昆曲竟然需要“墙外开花墙内香”,国人应该为此喜悦,还是应该悲哀?自己的文化成果为什么需要借助外国人的眼睛“发现”?打个比方,一个村夫家里藏了一个破碗,有一天来了一个城里人,告诉他这是件宝贝,村夫高兴得不得了,满村大叫,“我有宝贝!我有宝贝!”兴奋过后,村民能做什么呢?或者藏起来等着升值?或者卖掉!因为他不会欣赏这个破碗!
程蝶衣对青木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青木欣赏昆曲,一方面它又是个侵略者。青木为什么喜欢昆曲,难以考证,可能是他在日本看惯了“能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怎样选择了昆曲,我不明了其中的细节,也不知道组织成员是以怎样的眼光选出了昆曲,对于认为“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国人来讲,过程好像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中标”了,于是举国欢庆,通过2001年、2002年网上的帖子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一点。其中北方昆曲剧院常务副院长刘宇宸的讲话最具有代表性:“联合国的这次命名,无疑在如此悲壮的时刻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它再次燃起了至今热爱着这门艺术的昆曲人心中的那团圣火。”“火”可以持续多久?这不得不让人想起了20世纪50年代的《十五贯》。
18、19世纪以来,欧洲的文化遗产政策所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转型:民族国家的价值取向,二十世纪初的普世价值的象征,再到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价值认同。在对“全球化”的解读中,许多卓见之士看到了隐藏在“全球化”名下的“西方化”、“美国化”、“欧洲化”。如果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选择后面发现“后殖民主义”的视角,那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身份是不是和青木就有点重合了呢?程蝶衣赞许青木的欣赏戏的能力,国人肯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选拔能力。国人是不是有点是非不明呢?艺术标准重要?还是爱国热情重要?还好,国人中的大多数没有发现 “欧洲价值的认同”问题,所以都在傻兮兮的笑着,就像程蝶衣救了朱小楼那样满心欢喜。但程蝶衣却被朱小楼扇了一记耳光。
“袁四爷”喜欢看戏,他是一个中国人,程蝶衣是他的宠物。
(三)“袁四爷”
“袁四爷”是谁?袁四爷是北京的梨园戏霸,他当然喜欢戏,并且喜欢得比较彻底,他喜欢上了程蝶衣。
袁四爷是旧社会的恶霸。旧社会的人能否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至少比现在的机会要多。抛开袁四爷对程蝶衣的痴迷,他是个戏迷。那时候当个戏迷相对容易,但是当个有品位的戏迷可不容易。暂且我们就算他是一个,毕竟他还和朱小楼为“西楚霸王”进营的“步数”争执过!白先勇也是一位戏迷,不同于“袁四爷”,白先勇是想为昆曲做点贡献,他称自己是“义工”,白先勇是一个很有品位的戏迷,他来大陆巡演《牡丹亭》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年轻戏迷。现在当个戏迷可不容易,你需要静下心来!跟着昆剧演员的轻歌曼舞轻吟低唱,而不是跟着街舞尽情摇摆,年轻人能习惯嘛?况且年轻人的心中还暗藏着两个黑洞:传统文化与“落后”的等价、时下环境与西方文化的天然亲近。
袁四爷是不倒树,其实袁四爷后面靠的是一棵更大的树:戏迷以及戏迷生成的环境。没有了戏迷,袁四爷也要完蛋!后来袁四爷作为“恶霸”被处决,其实和戏无关。但是我们却发现新中国的环境好象把“戏”存在的环境也清除掉了。程蝶衣的遭遇可以明证50年代到文革结束“戏”的环境恶劣,80年代到现在“戏”的环境也没有改善。“戏”的存在不可能是偶然现象,其实白先勇看到了这一点,白先勇在接受《深圳商报》的采访时说到:“经过几次社会大变革之后,中国人其实丧失了很多文雅,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快点把昆曲弄回来的缘由。中国人需要很多的精致文化陶冶,我们失去了这一部分,甚至有一阵子,人们把这些东西当作封建与落后对待。类似昆曲这种东西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最精致的一部分。”所以他不惜对《牡丹亭》进行改造,推出了“青春版”《牡丹亭》。
培养一部份戏迷也不是件太难的事情,其实最难得是培养青年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昆曲”的衰亡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京剧、书法、国画等等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艺术瑰宝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传统”自然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但是作为中国人好像又都知道有那么一样东西存在着。说“袁四爷”促进了京剧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大便里面发现营养物质”,说白先勇就可以,但是白先勇没有袁四爷的“好时候”——南京大学的一些网友的帖子指出了这个问题:“首先,不得不承认,昆曲因为她阳春白雪式的高雅,曲高和寡,在今天这个娱乐多样化,个人价值取向发生重大变化的社会中,面临着困境。大概当年的‘花雅之争’中昆曲逐渐衰落,不敌一些地方戏,就已显示了这个问题。昆曲实在太清高了,所以也就不能‘取悦’普通人,只能为精英所把玩。也许某一些戏局部地能引发什么热,但是就全局来讲,情况是不容乐观的。传统戏的流失,令人满意的新剧本又难以出现,观众越来越少,愿意一辈子从事昆曲事业的人也越来越少。”
袁四爷的戏迷没有经历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的洗礼。白先勇面对着更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向这些中国人讲述自己的过去。白先勇说:“所谓的全球化也就是西方强势文化的领导,他们加了科技的优势,把他们的文化推广成全球化。我想,的确,在商业、科技方面他们的确有优势,但是我们的更传统,我们的古典的传统,我们民族独创的,我们的书法、昆曲是别的民族没有的,我想,他们也是佩服的,而且西方人非常尊敬我们的传统艺术。”这里好像有程蝶衣“重视日本人”的影子,但是白先勇的苦心是值得敬佩的,他谈到“没有过去,怎么有将来?我们对传统有误解、偏见与误导,要恢复民族自信,有了自信,我们才能重建我们的美学。”
程蝶衣遇到了他能成“角”的“好”环境,正如他的师傅喊出的一句:“你们遇上了好时候了”。但是好时候很快就没了,于是后面就有了程蝶衣的更为凄惨的命运。袁四爷所代表的戏迷同志们后来也被改造了,还好现在跑出了一位没有受到“革命洗礼”的白先勇出来挖掘戏迷,据说他在大陆不乏知音,比如余秋雨。 但是谁来搭建当代和古代的桥梁呢?
(四)“红卫兵”
红卫兵最感兴趣的是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要“辩证地”分清“优秀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区别,于是他不但要在艺术上消灭“才子佳人”,还要在人体上消灭一切“封资修”的代表。“戏”被划为封建行列,属于要被改造的艺术形式,程蝶衣、朱小楼变成了要被改造的个人。
红卫兵对艺术形式的改造相对容易,后来不就出现了“八大样板戏”吗?对人的改造相对难一些,那需要朱小楼再拿起青砖碰头,需要程蝶衣“坐飞机”,而且需要逼着朱小楼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程蝶衣的“鸭子”经历,作为回报,程蝶衣说出了朱小楼老婆(巩俐饰)的“妓女”本色。红卫兵干得很出色,成功地完成了“文化革命”的任务。程蝶衣、朱小楼、朱小楼老婆从旧社会的“下九流”的人变成了新社会的“鬼”——可能是吸血鬼吧,专门吸自己朋友的血。
可以想象,这些变成“鬼”的人怎么可以再演出《牡丹亭》。“游园惊梦”不就是讲了一个封建小姐的“艳遇”吗?阶级论的分析模式是红卫兵的拿手好戏。
文革结束了,红卫兵成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但是这种社会决定论的分析模式真的结束了吗?那种辩证地肢解文化的趋势消失了吗?好像没有。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化进化论”,百年来形成的拒外、媚外、恐外的文化心理依然在发挥作用,现代与古代、中国与西方的“鸿沟”潜藏在大多数的中国人心中,现代与古代的鸿沟似乎是造成“昆曲危机”最重要原因,所以在中国有“昆曲危机”,在西方就没有“歌剧危机”。
(五)结束语
中国古代的“大隐”是隐于市的!在我们所处的所谓的“后现代”社会里,或许艺术是唯一让我们倾听心声、剔出物欲杂念的一种方式了。我们可以借艺术保持个人心灵的原始性、敏感性。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这是人的真实“存在”,用老子的话来讲这是“赤子之心”。或许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面我所谈及“鸿沟”,面对昆曲,其实少的是一份平常心,多的是成见造成的“堡垒”,这个堡垒潜藏在国人的心里。
程蝶衣自杀了,青木被打跑了,袁四爷被枪毙了,红卫兵在正常的生活。死的死了吗?跑的回来了吗?活着的在怎样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