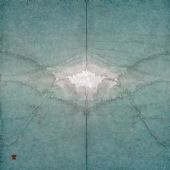对于任何一个艺术评论家而言,谈论“新国画”“新中国画”“新水墨”“新工笔”等概念都是令人头疼的话题,但偏偏近几年“新水墨”“新工笔”又成为艺术界的一个热点,至少是传媒意义上的热点。
所谓“新水墨”,自然对应着的是“旧水墨”。“旧水墨”所指与“传统水墨”基本一致。而“传统水墨”的核心又多指传统“文人画”。这种“旧”,实际上在清末就已经被打破。康有为提出了中国画之衰败,继而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导者极力提倡“美术革命”,革“王画”的命,力图用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来改造传统中国画。因此,如果论水墨之“新”,从历史来看,从此时起就应该算起。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画”和“国画的改造”成为美术界的重点议题,国画被融入到写实绘画和写生的西式学院体系中,最终形成了“蒋徐体系”(蒋兆和、徐悲鸿)。改革开放以后,国画领域形成了两种主要潮流,一为重新复归传统,一为借西方现代主义开创水墨新方式。
近几年,“新水墨”之热,一方面说明艺术界对水墨创新的期待与渴望,另一方面也部分的说明水墨自身发展的突破。然而,在被称为“新水墨”的展览、画家、作品中,我们往往看到的不是统一的艺术观念和艺术风格,恰恰是其差异性。如果说新时期的“新水墨”有一种共同点,那么就是排除了前述传统文人画和新中国以来“蒋徐体系”的写实中国画。除此以外,新学院派、新文人画、波普艺术、卡通一代、抽象艺术、观念艺术等只要以水墨为主要材料的类型和形式都被囊括其中。因此,将之作为一种泛化的艺术现象来看,比将其作为一个艺术潮流或一种风格来看,更为恰当。但这并不说明它们没有价值,也不说明它们缺乏作为历史和现实被梳理与讨论的可能性。
在传统文人画和写实主义中国画之外,实际上还存在一条融合西方现代艺术或借用西方现代艺术改造中国画的脉络。民国时期,林风眠、刘海粟等前辈画家已经在此脉络上有所突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兴起,谷文达、任戬、李山等艺术家也试图通过类似的方式去改造中国画,并将中国文化自身的特性融入其中。90年代初期和中期,水墨的发展得到突破,形成了以张羽、刘子建、王川等为代表的“实验水墨”和以李津、李孝萱等为代表的“新文人画”两种新的类型。但水墨并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材料和语言方式,同时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尽管该时期的新水墨在图像和风格上有所推进,但依然受其制约,难以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独立的现代艺术类别,因此,以吴冠中为代表的“笔墨等于零”和以张仃为代表的“守住笔墨的底线”这样的争论引发广泛的反响便不难理解。
1998年开始,“深圳水墨双年展”创办,2005年开始,“上海新水墨大展”(年度展)创办,力图通过展览的方式梳理历史、发现新的水墨画家、总结和把握新的发展趋势,并且收到了一定效果。纳入新水墨范围讨论的,不仅有“实验水墨”和“新文人画”,还包括徐冰、邱振中等人的文字水墨,黄岩、戴光郁等人的水墨行为,王南溟、彭薇等人的水墨装置;刘庆和、田黎明等创新的学院水墨。甚至有时,徐累等被称为“新工笔”的艺术,也是新水墨关注的对象——尽管就传统而言,“水墨”和“工笔”是中国画的两大门类——但在今天,它们之间的区别已经让位于创新的共识。更年轻的批评家和策展人所关注的“新水墨”则是由青年的水墨画家群体所创作的,如曾健勇、魏青吉、涂少辉、杭春晖、黄丹、杨珺、祝铮鸣。新水墨的倡导者之一杭春晓认为“新水墨”并非“风格概念”,而是水墨的一种“状态”。
相较于与传统文人画和写实主义水墨相对应的新水墨而言,这个意义上的新水墨是狭义的新水墨,具有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但很难形成一种学派式的艺术运动或潮流。因为,其内部的差异性太大,无法从学术上予以定位。不过,艺术市场对定义新水墨的愿望却非常强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今天新水墨作为艺术热点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拜艺术市场所赐。2012年,嘉德拍卖和保利拍卖两个国内最大的拍卖公司分别推出数个以新水墨为主的拍卖专场,由年轻水墨画家创作的新形态水墨作品成为关注的焦点。国内其他拍卖公司相继跟进,推出新水墨拍卖专场。这股新水墨市场的新潮流在在2013年初,由于国际性大拍卖公司佳士得、苏富比开启新水墨专场而被推向高潮,在该年内,其热度持续走高。但是,为什么艺术市场会集中发力推动新水墨?在传统的艺术市场中,当代水墨一直是不太受到重视且成交额也并不高的一个相对冷门的领域。
在2008年全球性经融危机以后,整个艺术市场萎缩,但艺术市场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青年艺术板块由于价格门槛低、投资风险较小、远期增幅大而受追捧。随着近几年当代艺术持续下挫、国画市场率先复苏,由青年艺术家创作的新水墨、新工笔则被认为是有前途的市场领域。一方面,在国内,水墨具有广泛的收藏基础,传统水墨藏家转型收藏新水墨作品的宽容度相对较高;另一方面,由于当代艺术市场的收藏信心减弱,新水墨因其既具有国画的基本形态、又具有当代艺术的某些特征而同样能够被当代艺术藏家所接受。从实际情况来看,新水墨专场拍卖尽管成交总额都不是特别大,但成交额一直保持较高比例,这进一步拉升了拍卖公司、画廊、藏家、画家及相关产业从业者的信心,新水墨因而迅速升温,形成热点。在此意义上,新水墨热,是艺术市场愿意看到的结果。但是,他们也对此怀有疑虑,希望学术界能对新水墨做出理论上的反应和长期的价值判断,以保持该领域的可持续性发展。
但艺术市场所谓新水墨中,其类型过于丰富,无比多元,有时甚至一些现代大家、知名油画家或当代艺术家的墨戏亦名列其中,难于进行理论总结。不过,学术界也一直没有放弃对新形态水墨的关注和研究,尽管这种声音一直不是主流,而且对新形态水墨的理论总结和命名也一直存在分歧。同样从2012年开始,“水墨纵横——2012上海新水墨艺术大展”、“再水墨:2000—2012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水墨新维度:2013批评家提名展”、“青年墨语:第八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及相关学术研讨会相继举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2月11日,“水墨艺术:古代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礼物”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开幕,展览策展人何慕文(Maxwell K. Hearn)特别提到,展览作品不涉及遵循国画传统规则及国画结合苏俄写实主义的派别,也不涉及一味地跟随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往下走的派别。“文字”、“新山水”、“抽象”及“非架上”四个主题囊括了35位画家的70余件作品。这些作品基本包括了上述各类新形态的水墨,但同样无法用“新水墨”一词定位其类型、内涵和价值。芝加哥大学美术史教授巫鸿在展览研究文章中认为,展出作品可以定位于“由国画形式演变而来”“以革新媒介阐述中国内涵”的当代艺术作品。
在水墨领域,如何从根本上摆脱千年来形成的既有文化范式,突破画种的界限从而参与进当代艺术的进程,并对整个艺术产生影响和贡献?这是90年代以来从事水墨实验的艺术家们的“终极”追问。现在,这似乎即将成为事实。正如巫鸿所言,他所关注的,究其根本不是“水墨”,而是“当代艺术”。而且,在更早些时候,这种可能业已出现。2003年,由栗宪庭策划的“念珠与笔触”和由高名潞策划的“极多主义”两个展览举办,尽管这是两个不同的展览,但其中均包含了大量“重复性书写”的水墨艺术家,张羽、梁筌、李华生、刘旭光等画家是其代表。这种“重复性书写”的新水墨多是抽象艺术形态,但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抽象艺术,因为他们普遍注重绘画过程、程序和对时间的占有,由于艺术形式被降到最低,因此,批评家们更关注的是其“无意义”艺术行为及其理论价值。在这里,这些水墨艺术实际上已经脱离开传统的范式,尽管依然在使用着传统的材料,但对其意义的讨论,却已经进入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理论层面。
前述狭义范围的新水墨相对便于总结,以年轻艺术家为主体在近两年内兴起的这种现象大多不再纠结于形式问题和本体问题,无论是2000年以前被视为争论焦点的抽象形式、表现张力,还是笔墨中心,都被淡化和回避,是水墨还是工笔这样的讨论也变得毫无意义。除对中国画本体的无兴趣外,它们大多是写实性的绘画或者带有较强的写实因素,一般或浓或淡赋彩设色,在主题和题材上多与日常生活细节相关,较少介入艺术哲学和社会现实诸问题。广义的“新水墨”则是一个多方参与构建和定义的概念,不同人或不同群体所谓“新水墨”,甚至有着很大的分歧和矛盾。对于艺术市场而言,自然希望新水墨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能够拓宽其拍品、市场和受众。但对于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而言,则希望缩小其范围,找到一种统摄性的因素来对新艺术进行描述、定位和价值判断。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顾丞峰在一篇论文中认为,新水墨“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的描述”,或许正是此意。在对其边界缺乏共识,对时间节点不预设的前提下,“新水墨”只能是一个临时性的方案。但是,在艺术市场固守新传统水墨物质形态基础上求“新”之时,另一种水墨参与进入当代艺术的可能性已经开启并正在形成——新水墨之新,不应是题材之新、手法之新、图像之新,而应是观念之新、哲学之新。
盛葳 《美术》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