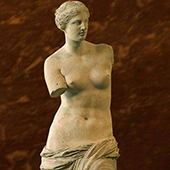“证伪”是一种质疑的精神。鼓励人们大胆地提出假说和猜测,不断修正,不断推进,乃至将最初假说全盘否定。无论是对于已奉为经典的科学理论,还是对于备受推崇的各种政治哲学,作为“证伪”倡导者的波普尔借助理性批判精神,都把它们推到了被重新评判,必须接受质疑的审判台上。这使得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各种科学理论,必须去除其作为“终极真理”的尊贵身份,成为面向未来的、过程中的阶段性真理;使得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各种政治哲学,其推崇者必须反思这些理论潜藏的历史主义内核,及其和集权主义、霸权主义的一脉相承,或和整体主义、集体主义及其时下各种变体的深层关联。
作为哲学家的波普尔对“证伪”的推崇,必然会导致对开放场域的倡导,对封闭场域的批判。历史主义认为历史进程依照普遍法则进展,最后推进到确定的终点,而终点就是一个闭合点,也就是“最好的假说”(“终极真理”的代名词)的目的点。而“最好的假说”便是封闭体系的理论核心,整个封闭体系基于它的合理性而构建。任何否认“闭合点”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都会被其所排斥和否定。因此,对封闭体系的质疑是证伪主义的重要使命,从而不停地开启开放的场域。“开放社会”题中之意的“民主和自由”正是民主社会的主要特征。
“证伪”是波普尔一生的使命。而他所批判的“整体主义”社会正是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的重要特征。由此看来,他的使命在中国仍然没有完成。作为哲学家的波普尔基于他的理性主义批判,解构西方的科学史、思想史。而作为具有反思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需要对整体主义的各种时下变体保持高度的警觉。20世纪80年代艺术界的理想主义,90年代的前卫主义,时下流行的艺术经济,都在经由整体主义的惯有脉络畅行无阻。没有发生改变的是社会运转模式、惯有思维方式,欠缺的仍然是对这种整体主义的反思与反抗。“证伪”除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质疑精神。对时下来讲,“证伪”是保持自我反思的一种立场。
我始终认为,艺术家的反思状态和哲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等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其呈现的方式却大相径庭。尽管处于同样的世界,具有同样的质疑对象,但是艺术家不同于哲学家:哲学家通过理论阐释来发言,艺术家则必须借助自己的作品来发言。这就要求艺术家必须对艺术本体进行坚持,对艺术语言进行锤炼。对艺术本体的坚持和对艺术语言的锤炼是艺术家有效进入“问题”的必经途径,否则就变成了不合格的哲学家、社会学家、革命者。而成功的“绘画”则是把“证伪”过程及其结果视觉化了,画家的思考则隐遁到了画面背后。
本次参展艺术家均是“整体社会”中的个体,如果他们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发言者和反思者,他们就必须具备证伪的独立意识以及反思能力。尽管应届毕业生的身份注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经历相对单一,即一直处于受教育的阶段,但这不构成他们涉世未深的充足理由。相反,在所选出的这些艺术家中,尽管他们处理的题材各异,画面风格倾向也不尽相同,但至少能看到一些独立思考的火花在闪烁,同时这些火花不仅表现为思考结果的直露表白,而是凝聚在画面中,让观者驻足欣赏并进入思索和自醒。
如果将这次参展年轻艺术家的个人成长过程以及所接收的美术教育作为证伪对象的话,那么可以把他们的创作历程视为证伪的过程,而这次展览的作品便是他们阶段性证伪的结果。年轻艺术家用视觉形式把被遮蔽、被塑造、被驯化的过程予以彰显:对“真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的困惑和质疑、对个人生活境遇以及私密呓语的暴露、对未被驯化的触觉的彰显、对逼仄以及尴尬空间的营造,是这次参展艺术家所较多运用的证伪方式。
一、遮蔽的彰显
历史总是以固定的样式向我们展现着“真实”,现实也被这一样式所同化和整合。长大意味着对童话世界的摒弃,但却经常坠入由各种话语构建起来的成人童话之中。遮蔽是意识形态构建起来的禁区,被遮蔽是自我与现实妥协(放弃反思)的结果。“黑色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遮蔽的彰显”要体现的是:黑色如何把我的眼睛涂黑,光明又如何将眼睛的黑色彰显?
陈皎、翟倞分别将被“遮蔽”的现实和历史予以照亮,并把“遮蔽”视觉化为自己的画面——“遮蔽”不但是他们画面的表现主题,并且内化为他们的技法以及画面风格。陈皎将日常生活中的“痕迹”肯定为画面的主角,“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而陈皎偏偏执拗地把雪泥鸿爪固定在画面上,去除光影,只剩下痕迹。翟倞对“盘若常在”的肯定必然导致对形式的质疑,因为任何形式都可能是过眼云烟,而他所说的“形式”中正潜藏着历史的悖论和荒诞。与两者不同,沈晶磊和殷俊敏则分别将童话和现实、现实与记忆进行了并置,在刻意营造的超现实中氛围中,指出现实的滑稽之处。
那危坚实的古典写实造型能力为他表现“真实”提供了便利,但在他刻意建造的真实之中,处处透露出他对现实的质疑。画面中惹人注意的“蓝色条纹”以及各种非常规的“马”使画面的“物”与“词”相背离,从而凸现出的“物”的质感,既引人入胜,又拒人于千里之外。鄢醒则将“人”与“物”彻底抽离出历史和现实语境,置入空茫的无时空的背景中。看似熟悉的他们,似近又远,统一在作者纯净的个人世界中,而这个世界总透出单薄、脆落的特质。
二、呓语的曝光
正常表述不时会滑入“话语”之中,而话语正是意识形态的显性外壳。做白日梦是人们拒绝无孔不入的控制、实现个人理想的虚幻方式,而视觉化的呓语则是白日梦的遗迹。呓语的被曝光如果出于被迫,是对呓语主体的羞辱;呓语的被曝光如果出于自愿,则是呓语主体对世界的挑衅。
吴霜和张小雨一个偏向内心世界的呈现,一个偏向个人经历的勾画,但同在讲述着个人成长经历中的思索与困惑。吴霜的魔幻世界中,人兽同处在鸿蒙未开的场景之中,色彩迷离的尘世中游走着的女性裸体与充满神话色彩以及欲望暗示的兔子交错穿刺。吴霜在塑造一个个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所有的非正常均可以以正常的面目出现。张小雨则借助图像学的方法,在《第一人称》中把个人成长史与宏观历史进行勾连,时间被画面所平面化,看似成立的历史逻辑被个人化的历史所质疑。而赵露则借“覆膜”的方式,把历史层层被书写、被篡改、被遮蔽的事实进行过程化的视觉呈现,从而质疑历史的可信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体生存的表面合理性。
沈芳正以游戏的心态,偷窥式的视角把成年人置入他的滑稽剧中,将成年人的尴尬进行讽刺性的呈现。开裆裤、超人标志、天线宝宝与历尽沧桑的脸庞以及成熟的身体并置,沈芳正是在成人世界中游走的“坏孩子”,但正是这样的“坏孩子”的眼光,使成年人的正襟危坐变得滑稽可笑。相对于沈芳正来讲,王杰的讽刺对象要宽泛的多,古今人物、市井百态、小狗小猫皆在他的视野之中,并在他的笔下呈现出狡诘、享乐、自由的天性。
三、触觉的物化
在图像泛滥的当下,视觉的疲惫与浮躁的心态有其潜在的相通之处,而对触觉的细心体会则有更多的内省特质。对抽象线面的迷恋,对涂鸦痕迹的肯定,对色彩笔触的专注,去除其和现代主义艺术的连接之后,正和中国当下语境中所需的沉静心态、反思状态相暗合。对触觉的物化是对自我沉静状态的肯定,同时是和外部世界交流的另类样式,这一种样式不同于视觉,后者充满了光影的导引和幻惑。
叶鲜艳对真实世界以及记忆的追问,使她着迷于图像世界的建构,图像层层叠加,到最后却消弭在图线的海洋中。叶鲜艳以涂鸦的方式制造属于自己的真实——可能是图像的真实,抑或是她所认为的现实世界的真实。与叶鲜艳类似,许浩琳期望通过绘画接近真实,并期望破除媒介的界限,使作品和背景融为一体。到最终,她所实现的画面充满了触觉的真实感。而叶惠玲的绘画则是童年视点上的乌托邦构建,尽欢她画面中的色彩与笔触敏感而脆落。
冷广敏、柳薇的绘画更加强调平面性,画面的纵深感被压迫到最小限度。在冷广敏的画面中,偶然所得的效果被放大,对无意识的强调正是对理性羁绊、惯常思维以及绘画积习的主动反叛。柳薇的绘画则与人生状态、社会主题相关联,画面凝重,色彩简练而高贵,体现着作者冷静的审视态度以及出色的画面控制能力。
四、逼仄的空间
对于个人来讲,空间可以分为生活于其中的物理空间、安身立命的社会空间、容纳心绪的心理空间。其中任何一个空间,都与个人生存息息相关,与社会整体构建模式存在同构性。对物理空间的追逐,必须以财富的获得为基础;对社会空间的获取,则以身份的提升为标志;对心理空间的获得,与前两者关系密切,同时又具有自我独立性。而大多数艺术家的创作均以个人心理空间为基础,发散出对各类社会空间以及生存空间的反思和批评。对逼仄空间的表现,也是从三个层面上展开。
黄一山、黄小宁、张霆更多地处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黄一山在通过瓷砖进行规则化处理的日常空间里面,制造出一幕幕看似荒诞,又引人深思的独幕剧。在场景、道具的置换过程中,把日常引入荒诞,同时把荒诞日常化。在高科技战争的今天,战争的物理空间已经不同,杀戮的威胁可能来自千里之外。黄小宁所描绘的冰冷的枪械暗示了这种潜在的威胁性,他所刻意营造的画面气氛明显与现代战争的特征相契合。张霆则用“并置”的创作方法,打破各类空间的封闭性,使它们在混杂中产生出歧义,从而使各类空间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
哈妮斯、邓玉婷、王苑更多地处理个人的心理空间。作为一位应届毕业生,哈尼斯表现出来的思想深度以及艺术成熟程度较为惊人。她以对个人心理空间的挖掘为基础,进入对生命、自由的思索,由此实现对当代社会的质疑。哈妮斯作品在图像弥漫、平涂技法流行的当代绘画领域好似一个异数,但其作品的确能够让人深思绘画在当代的尊严之所在!如果说哈妮斯的创作纬度是由内而外延展的,那么邓玉婷的创作则表现出更多的个体性。邓玉婷以巴尔蒂斯画面中的女主角为原型,将她们植入自己的遐想空间之中,让画面主角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而这个“自己”有着多重身份,恍惚在现实与梦境之见,历史、当下以及未来之间。正如其作品形制(圆轮)所显示,王苑把将个体化生存放置到大乘佛教所宣扬的教义之中来阐释,以一种看似超脱的姿态对待世界以及自我,但这种超脱是否又是一种无奈?另一种心理纬度的真实性也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