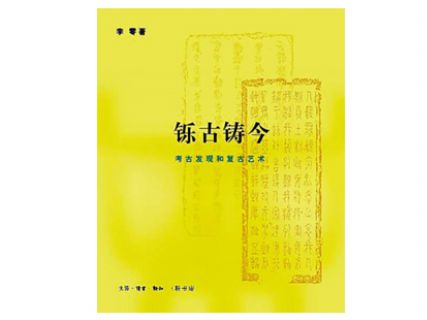
艺讯网:李老师,您好。今天您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做“山水”的讲座。那我想请教您几个与艺术、美术史相关的问题。
李:你怎么能请教我呢?我可不是美院的老师,我哪懂艺术呀。
艺:老师,您太谦逊了,您是在传统文化这一块有很深研究的大学者,而且我也知道近年来,您也对艺术、美术史这一块关注也比较多。我曾经读过您《花间一壶酒》这本书,我记得在序言中,您有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一直在逃,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从边缘逃向外面的世界”,那美术这一块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域呢?
李:对我来说,是外面的世界,但我现在更喜欢外面的世界。
艺:那您是怎样把注意力转移到美术这个外面世界的呢?
李:其实也没什么转移,一直以来,这就是一个业余爱好。从小时候开始就喜欢美术,但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阴错阳差,就是没有走到这个道上来,但还是有这个兴趣。
艺:您没有走到美术这个道,后来从事了考古工作,那我就请教您一个关于简帛的问题吧。传统史学基本是通过文献学范畴的材料构建起来的,而简帛呢,一般是考古发掘出来的,它的出土对这个学科都有些什么样的改变?比如说研究方法。
李:简帛本来就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书写材料,古代的书就是简帛,只不过后来变成纸的了,它们都是在传递古代的思想。我们研究晚一点的,比如宋元,我们能读一些纸本的文字材料;如果是早期一点,比如战国到汉代,就只能靠简帛这些材料。这些简帛的书都是从地下出土的,它填补了我们在这一块的空白。
艺:这种发掘出来的书跟传世留下来的书,在当时是处在一个文化系统下的吗?比如对于文化的记载。
李:传世的文献要看它记录的是什么内容,比如说《管子》、《老子》这些,它们还是从以前的简书上过录过来,再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它们是一样的,内容实质是一样的,但是在传写的时候会有很大差异。
艺:那简帛跟文献是同一层的文化载体吗?
李:不是同一个载体。早期是写在简帛上的,后来又传递给古书,把简帛上的东西转写成纸本的了,它们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
艺:那简帛的出土对这个学科有没有一种“打破”呢?就是说,这个学科在简帛出土以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构架,这个东西发掘出来对它有没有一种打破关系?
李: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书主要是宋以来的传世古书,无法从此了解比它早一点的古书面貌。早期一个题目的古书跟晚期同一个题目的古书,他们是完全一样的吗?并不是,它在传写的过程中不断的被改写,你要看到庐山真面貌,你还得看简帛上的古书。简帛的意义可能就在这层面上。
艺:那用这种关系来审视美术史这个学科,对美术史都有什么样的影响?
李:艺术里有古代的艺术品也有现代的艺术品,你要研究古代的艺术品,这个出土材料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博物馆,很多博物馆都不叫博物馆,而是美术馆。因为藏品都是从全世界各个地方搜集来的,也不知道原来出土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找到这些考古线索,你就能够重新解读他们收藏的这些艺术品,这些失去了考古线索的艺术品,是要靠这个考古发现去重新解读的。现在国外一些博物馆,在做收藏图录的时候要注明文物杂志上某个东西跟这个差不多,考古杂志上有某个东西跟这个差不多。这本身就是在依靠考古发现来重新解读以前发现的传世品。传世品跟出土品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在文献研究上简帛本跟传世本之间的关系。
艺:文献学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一些古文字的探究,然后还原一个历史真实。而美术史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做一个图像学的研究,但它们又都是属于史学,您觉得这两个史学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样的借鉴或是什么样的不同吗?
李:这个没有好好考虑过。文献学是一个文字写下来的东西,它虽然也是通过一种视觉,但看的是文字。而考古的东西跟艺术品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它们都是以实物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是通过研究这些实物从视觉上来认识它们。但这两个方面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文字的东西也有视觉的因素。
艺:您在艺术这一块主要都是关注哪些方面呢?
李:就像现在我也不是专门做考古的,我原来是学考古的,现在已经离开那个田野考古了,但是我觉得考古研究这个行当有自己的一套工作习惯,他就不会从艺术的这个角度去看它,它是讲究类型、年代这些东西。可是一个古物不是把它挖出来写一个报告就完了,这不是挖土豆。实际上,离开这个坑以后,你还要按另一个角度去考虑,那么艺术跟考古的关系就比较密切了。因为以前研究传世艺术品,研究传世古物的时候,其实主要的就是一个艺术史,之前我之所以跟你说那个博物馆,因为它不好从考古的角度来研究,就只能从艺术的角度。而且博物馆摆的都是一些比较漂亮的东西,那些长的比较丑的就算了,其实它研究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一些所谓精品,但考古发现不能以精品来衡量。拿出一个难看的陶罐、石斧都非常重要,角度是不一样。现在有很多博物馆是按照材质来划分的,比如玉器、青铜器、书画、瓷器,这个角度本身就是艺术的角度。而且考古和艺术在很多地方也是结合的,这个欧洲比较明显,美国的话,考古是属于人类学,但在欧洲考古和艺术是在一起的。现在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那个博物馆也是叫考古艺术博物馆,所以这两个方面还是可以结合起来的。
艺:我以前读过您《铄古铸今》那本书,看您关注的主要是一个复古的问题,您觉在中国艺术发展的几千年中这是一条主线,是一直存在的吗?
李:一直存在,其实国外也一样。比如说山水画,它里面有师造化,也有以古人为师,这在中国艺术中一直都存在。而且中国历史每一个朝代更替以后,制礼作乐往往是要以复古为号召,实际上是要做一个新的东西,所以新和古也并一定那么明确。
艺:这就有点像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打着复兴的旗号,而是一种创新。
李:是,是这样的。
艺:那这种复古在当下中国这种大的艺术环境下,这种情况是怎样的呢?
李:其实这也不光是艺术史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地方,按照政府的规划,要发展旅游,比如红色旅游、绿色旅游,还有一个古色旅游。古色旅游其实很多并不是古代的东西了,因为有一土城墙吧,觉得挺碍事的,也不好看,搬也搬不走,卖也卖不掉。他自己又去做好多新的,他借口当地原来有一个什么古迹,其实那个古迹已经拆了,他做一新的,这不就是一个复古艺术吗?咱们现在新的复古艺术是遍地开花,到处都是复古艺术。
艺:既然你这么强调这个复古……
李:不是强调,其实国外的艺术实践都很热心这个题目,我反而觉得国内的人关心不够,所以也试着做一点吧。
艺:那您是怎样看今和古这个问题的呢?
李:我觉得古曾经是今,今里面也有很多古的东西。现代的艺术也不完全是现代的,它是踏着古人的脚步走过来的。
艺:今天这个讲座是关于山水的,那谈一点您对于山水的认识吧。
李:我就是把去看太行山的一些感受跟大家聊一聊,交流一下,也是说一下对于山水之美的领悟吧。我觉得看得越多,越理解山水,可能不在于它表面的漂亮,不一定光是去表现秀丽之类的。如果你对山水理解的更多,可能觉得好像有些不那么漂亮的山水其实有它另外的一种美,比如说北方的山水,比如说太行山,北方山光秃秃的,没什么好看的,但是当你了解这些山水的意义,当然我主要是讲它历史地理,理解这些,多少会对山水的理解有所加深,其实也就是换一个角度看一看山水。也不知道对做艺术的有没有帮助?我自己觉得我做的这个东西是学科之外的。
艺:其实我觉得这个学科是没有多大界限的,就像考古和艺术。可能您看山水比一些艺术史专家看的要透彻,应该是这样的。刚说的是山水,那您对传世的山水画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认识?
李:中国的山水画,早期在墓葬壁画里就有了,它跟后来的文人画还不太一样,文人有文人自己的情趣。我想现在绝大多数画中国传统山水画的人还是会受到比较多的流派、自己师法的一些画家的影响,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但如果从艺术史的场合来看,早期的传统是什么样,工匠画的画是不是那么的不可取,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除了画家写生以一个艺术家身份去看山水,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人在看它,他们的角度有是怎样?那些角度对我们是不是也有帮助呢?比如古代帝王、老百姓、和尚道士、考古学家、地质学家。是不是多一些角度,对我们理解山水会更好一点呢?
艺:您刚才说墓室壁画里也有山水,那那种山水有是怎样的情境呢?
李:你们美院的郑岩教授写过文章,专门讨论墓室里面的山水壁画。它跟实际生活中一些山水画肯定是有关的,比如说画成屏风的形式。早期山水画的表现,跟后来的山水画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只是说从工匠画的画到文人画的画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也有很多联系,我看郑岩教授讲的时候是说,不要太强调文人画是如何跟工匠画的不一样,它们还是有关系的。
艺:那文人跟工匠所画的山水,它们的区别都在哪呢?刚你说它们之间是有变化的。
李:比如说,文人排斥工匠没文化,我书法好,我每一笔里面都有书法的韵味,我觉得这有文人的夸大。“书画同源”说好像说画都是从书法里出来的,其实是表现超越工匠的一种说辞。
艺:好,谢谢您跟我聊这么多。我想在听过您接下来的这个讲座后应该对您的观点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艺讯网记者:张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