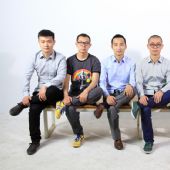王麟:无关小组是怎么什么情况下正式成立的?
陈志远:基本上是在11年吧。刚开始讨论的一个“行走计划”。有了那个第一个“行走计划”,那个就有点像集体创作了。我们抛出来一个关于游行的主题,就是用各种方式去游行,抛出来后,每个人去提方案,提了将近有二十来个方案。开始实施这些方案那会儿连小组名字也没有,就是只知道去做。第一次就是举着栏杆把自己围在栏杆里在798里面走。走完了以后,刚好艾未未出了问题,好多人说我们的行走是声援他。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事,跟艾未未的事件没有关系,后来我们就发表一个跟这个事件无关的声明。大概就是什么什么跟什么无关,很无厘头的一句话,比如跟花花草草无关,跟什么爱情无关,跟什么什么无关。有了这个声明,那我们才有了名字,开始叫做无关小组。后来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创作集体,我们的创作的方向脱离不开每一个人,但作品必须是一个集体,每一个人都参加进来的集体意识和创作状态。
王麟:作为艺术小组,你们大概多久开一次讨论会,成员叶楠在杭州,你们这些方案的讨论他是怎么参与的?你们最终怎么敲定一个方案?
郭立军:我们前期方案讨论是比较密集的,后来就没有那么多了。因为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讨论的方式是存在问题的,比如说一个人提出方案来说服大家,确定这个方案是可行,然后达成同意。这个过程相互之间都是在磨合开始的时候去考虑应该有一个差不多的大概方向,这样的讨论效率就能提高起来。叶楠因为不在北京,一些大的作品计划或者方案实施我们就在网络上或者电话上跟他沟通。方案的大概方向与作品的制作方向都是提前在电话里通知他,他也会自己考虑。最后我们集体讨论的时候,讨论作品的实施方案也会通过现场网络。
陈志远:其实我们这个小组做作品刚开始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每一组都要讨论,你想出一个方案大家有一组投票来通过不通过。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即使我们都在一个学校一个工作室毕业,大家的想法还是很不同。因为每次我们开会基本上都是在吵架,一个事情定下来要经过很漫长的过程。后来发现你想要做事情有的时候很民主不是很好的方法。
李良勇:大家相互提意见。你这块不好,否定掉。大家在一块就相互去改进,讨论就是这种情况。
王贵琳:有些时候想法和实际做的东西是需要分开的。因为这个想法他避免不了谈到一些比较个人感兴趣,有感觉的方案。这种东西没办法讨论。
王麟:你提到的行走项目是你们小组比较重要的项目,做过几期?这是一个持续性的活动吗?会自己定一个期限去做这个事情还是随机性的有方案就去做?
郭立军:以前是有一个期限的,那段时间好像是差不多一个月一次,并且有每个人负责。比方说一个人负责打吊瓶的方案,另一个人就负责扫地的方案,负责一个必须得跟进。然后做预算,告诉大家要花多少钱,大家来凑钱,然后是场地和材料,最后约好地点大家去实施。基本上是一个月为一个期限去实施。反正那会儿想了有二十多个关于行走的方案,现在还有好多没有实施。
陈志远:就是有合适的机遇可能就做。因为这个事情不可能放弃了,完全不做,完全的放弃了。
王麟:1980、1990年代那些小组,现在成为我们的前辈艺术家了。每个小组成立之初都有类似一个声明或者是宣言。你们的核心理念是什么?你们觉得现在小组的创作跟之前的他们小组创作有什么不同?
陈志远:我觉得不同点就在于,他们其实是有敌人的,他们敌人特别明显,他摆在那里,我们就灭掉他。他们都有革命的对象,其实我们现在没有。而且我觉得他们小组跟我们现在有点不同的是,他们以前组建小组呢还是各做各的。他们一起革命,但每个人都有手段。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是团结在一起,做一个动作。他们是每个人有一个动作,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郭立军:他们那个更像是思潮。
陈志远:其实那些小组都可以办一个群展,每一个小组可以办一个群展。我们这个小组只能办个展。
王麟:你们的创作方案的确定是以排除法进行的?
陈志远:我们没别的办法,只能是不做别人做的,我们找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情做,重复肯定没意义。现在,我们更关注自己,因为我们的假想敌不明晰,我们对当代艺术也有自己的看法。
郭立军:我觉得艺术家的东西,做作品的东西,太有限制了,太有局限性了。
陈志远:我觉得以前的小组有点像武林帮派,我要挑战少林寺,我们练这个招数就是要挑战少林寺。等到自己在武林中有一点地位了,或者说在武林当中已经有很高的地位了,那么他们就开始关注自身应该怎么发展了,就不再说我要挑战谁我要挑战谁。
王贵琳:在我看来这个东西可能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不可能说我这辈子就要怎么样,我就要把这个手机砸碎,我这辈子都干这个事儿。给我的感觉是那些宣言。某些时候你犯了一个病然后去吃一个药,但是一个宣言,而不是这辈子都在吃这个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一个集体性创作,其实也是遇到一些以前不曾有过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创作方式比较新,我们可能会集中力量在解决这些问题上面。
王麟:你们可以各自谈一下个人的创作方向以及个人的创作方向和小组创作的关系。
李良勇:最近想要去画画,先把油画这种技巧重新拾起来,油画就是差不多忘掉的东西。个人创作和小组创作,小组和大家都是一个人完成不了的事情,然后大家一块去完成,个人基本上就只能做一些其他的东西,从绘画入手。
陈志远:我自己现在在做木工。我倒不急着创作,我个人对现在当代艺术创作方式不太认同,但我又不反对。不认同是什么呢,太方案性,就是想一个方案,先在纸板上写出来,这是我的方案,这是我的作品,然后拿给别人去实施,或者是找工人找助手实施。这样实施出来的作品跟艺术家跟他本人关系其实没那么密切,其中的情感传递会丢失很多。现在正相反,作品质量反而是被工人把握,工人状态好他给你做好一点,今天不高兴就给你做差一点,这是很可悲的。我接下来的创作就是把木工当做自己的修炼,然后同时呢有一些创作,就是跟木头相关的,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是尽量往小组那边靠,因为小组是关于劳动的,那手艺其实也是关于劳动的,所以不相冲突。
郭立军:我其实一直在画画,画了可能有一年多了。我觉得大家现在创作方式确实是太偏向于设计方案了,就觉得我经常跟他聊我说,画画时候我觉得特别安静。我从小特别喜欢画画,可能让我天天去想方案往纸上弄的那种东西我不擅长,特别聪明技巧我不太擅长。关于小组,我觉得一个人的想法,很容易陷入到自己的情景当中。就觉得我个人想出的方案特别好,其实可能没那么好,反正就自己觉得特别好。小组就是能给你带来一种跟大家去讨论机会,大家都会想你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弄。
陈志远:小组就是一个容器,你丢一个东西进去,看有没有反应。咔就起反应了。
牛柯:我其实最近也在画画,从小时候就喜欢画画,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机会去学去画。一直到美院有专们绘画课,但主要精力也没有在绘画上,然后这个事就一直埋藏起来了。但其实我一直不想放弃,所以我现在自己画画也好,做版画也好其实跟小组的东西倒不是说差距大,这完全是两种概念两种思路,我蛮喜欢这种状态的。
王贵琳:我对艺术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狂热。只能说是某些情况下比较喜欢,可以说是感兴趣。跟我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喜欢东西比较多,会卷进各种各样事情里面。我现在做的事情不管是维持生计也好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做艺术也好,它可能是不同领域的不同一些事情各种各样都有,和我的生活也没有那么强的界限。开超市行,大家一起做披萨店也行。日常的讨论、创作也包括自己在家打游戏,包括帮别人做设计图,包括去云南做些旅游区的改造。这些事情都会成为自己的一种缘分。我觉得和小组创作没有什么截然的分界线,某些时候杂糅在一起。大家是一个整体但又比较独立。
王麟:信手超市,算不算小组的作品?
陈志远:肯定算。我觉得是小组未来比较核心,比较重要的东西。超市是比较新的创作状态,披萨店也是,他们都是真实在发生,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撇不开。我们经营超市经营披萨店,它是我们的生活同时也是我们的创造。我们也不想正儿八经的去开一个超市也不想正儿八经去开披萨店。那就变成了生意人。我们也不是生意人,我们是以艺术家的生活和方式来做这两件事情。
郭立军:其实也是生意人。
陈志远:对也是生意人。它其实是撇不开,没有那么截然的分开。超市就是我们的一个作品。
郭立军: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用你的带有创造性的思维去解决任何问题,比如装修也好比如说怎么去处理送披萨的和顾客的关系,我觉得这也需要创造力,这是一种最重要的东西。
王贵琳:在上学那会儿,大家还不知道怎么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关于定义什么东西是艺术品,最后有人定义无用之物就是艺术品。但是现在感觉起来并不是那么绝对。艺术品真的一点用处没有肯定不可能,它也可能跳出原来有用的范围。
陈志远:我觉得如果按整个长远艺术来看。我们这个时期的艺术是比较落后的,因为有才的人都没在搞艺术。
王贵琳:要不要得罪一圈人。
陈志远:我真的感觉,那些特别有才的人,做那些网络的包括拍电影,特别有才。当然电影也是艺术,只不过我自己一直感觉,艺术这个词跟我们生活的圈子有关系,因为我一听到艺术家,他要么是画画的要么做装置。当代艺术这一块,他把艺术给吃了,人家那些搞电影的,从来不自称是艺术家,反而是那些初来乍到的毕业生办了一个展览就说自己是艺术家这个我觉得好奇怪。你说你是个画家,我还勉强能接受,你要说你是个艺术家我就接受不了了。剪头发的都叫艺术,发艺、厨艺,都是艺术家。你非要把艺术定义成你们做装置的,甚至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创造性的去做某件事情他就是艺术家,我觉得只有把艺术这样泛泛下去,他的才会更丰富,搞团体搞精英化一定不行。这帮艺术家,你们不懂艺术,你们看不懂,不是我做的太高端,而是你们看不懂。
郭立军:很玄虚化,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圈子里,艺术家都很不好好说话。
陈志远:一点不真诚一点不朴实的那种。
李良勇:就像现在写的那种艺术评论那种。
陈志远:开超市也可以是艺术,为什么不可以是艺术。
王麟:去年无关在三亚获了一个大奖。你们自己内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奖金你们现在是怎么用的?
陈志远:奖金用在超市和开披萨店了。这是最好的用处了,我们要去腐败一下也可以,可是我们没那么做,我们基本上连请客都没请。
牛柯:欠了很多账。
陈志远:其实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
郭立军:我们觉得我们的东西确实不太像当代艺术,我们去做自己的事情,没想到能获奖。
王贵琳:最直接的感觉是有奖金就是最好的,比什么都实在。
牛柯:而且它也确实能帮我们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披萨店提前开业。
王麟:你们现在各自的主要经济来源?
郭立军:目前就主要投入到超市和披萨事业。
陈志远:存款都没了。
郭立军:对。存款都没了。
李良勇:基本上孤注一掷了就。之前一直就那种给人家工作,相当于是上班,然后拿一些工资。
郭立军: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美院的毕业生,解决不了你的生存问题,这就很失败。
郭立军:艺术家每次被包装成一个成功人士像明星一样。我觉得对学生绝对是一个误导。我特别瞧不起宋庄那边有些特别苦的艺术家,真的是一天吃两餐,生活质量特别差,很苦的做艺术,然后再禅修一个艺术境界,这不是纯属扯淡吗。
陈志远:你这话也会得罪一批人。如果以经济收入来判断,我们算是混的特别差的。就是包括生活水平也好生活质量也好,但我们追求的不是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够活就行了。我觉得我们不是为了赚钱,如果为了赚钱我们就不去搞这么费钱又费事的事情,还不一定赚钱。我们不是要赚钱,目的不是要开豪车,不是要穿名牌。
王贵琳:以后你买一辆豪车你会遭人把柄。
陈志远:我自己的生活经济来源是作木工。其实按道理我自己来说,我结合的比较好。一个方面练手艺一方面可以有一些收入,这个就是我喜欢的。
郭立军:理想职业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王麟: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认为的成功是什么?
陈志远:首先我不认为自己现在是艺术家,第二个我觉得成功不是别人给你的定义,是自己给自己的定义,就是你觉得你充分实现了你内心的想法,并且还在不断的实现我觉得这样。
牛柯:我觉得成功不是针对某一个结局,也不是段落的事情,它完全是一种心态的反应,一种心态,哪怕你做了一个很屌丝的事情,如果你觉得完全实现你的理想化的那种状态下你还能通过手工劳动,通过庆幸去做这些事之前想不到的东西他超出来的那种心态是成功的。
王贵琳:咱们也不需要成功,就是某种特别固定的东西,人活着他妈的不需要这种玩意儿存在他也可以好好活着。我要感兴趣这么做你管我成不成功,我天天乐在其中。
牛柯:许多的成功人士其实并不幸福。
郭立军:成功就是满足欲望。只要你满足某些事情你就成功,无非是你追求多和少的问题。我知道不同领域成功是不一样的。
王贵琳:这种东西我也不知道它和艺术家身份有什么关系。
郭立军:艺术作为一种可交流,只要你作品做出来了,对别人有影响我觉得就是成功的。
陈志远:你此刻成功,不代表你这个人成功。
郭立军:比如说你作为领导盖了几座大楼,这就体现你对这个社会留下了痕迹,比如说秦始皇的长城,那是他活着时候建的,死了还留在这个社会上。
陈志远:我不认为秦始皇留下长城是他成功的标志。
李良勇:秦始皇就是出了个方案。
陈志远:他只是出了个方案,成功的是那些铸造长城的人,是他们留下的遗迹。跟秦始皇没关系,秦始皇他妈的就是出了个方案。
郭立军:但是你知道谁去修了长城,你记不住啊,你记住了秦始皇。
牛柯:秦始皇的成功是我们回头来看这个事情,如果没有他,那未必有长城出现。
郭立军:谁留的时间最长,时间最长的人最成功的。
王贵琳:我百度了下成功这个词。成功就是指达到或实现某种价值尺度的事情或实践。他这个价值尺度的事情就比较关键了。我们等于从某一个角度去定义某些事情他才有可能定义,当这个价值尺度不确定的时候这个事是没法确定的。成功就有价值尺度里面。
——内容来源:《复调II》纪录片访谈
无关小组简介:
无关小组从2011年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用一种“更无关”的态度去进行生活和创作的整合。每一次的无关行动总是会跟某些看起来是那么回事的事无关,于是我们成了关于无关的有关,关于有关的无关。
1当我们是无关小组时,我们便不是表演家,不是艺术家,不是建筑师,不是工人农民,不是知识分子,不是诗人,不是理论家,不是批评家,也不是达达、激浪、后感性,我们是他们之后的某种事物。我们同时是他们的集合,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成为各种我们可以扩展的身份。
2我们是研究者,是观察者,是访问者,我们更是行动者,劳动者,是现实深处和意识形态上的工作者,我们在田野,在民间,在办公室和画廊美术馆,在一切可以产生真实行动的地方工作。
3我们不是标新立异和离经叛道。那么我们是什么?我们谈话就是谈话,行动一定要见效。我们试着建构新的关切和真的关切,我们要重建、转化这些支离破碎的关系。
4我们不在他们给我们的美术史里面。
5我们集体行动我们单打独斗,我们是一些活动的分子,我们用量变产生质变,我们用单个的针尖刺入其他集体内部。
6我们有时书写,有时调查,有时讨论,有时插科打,有时在边界上行走。
7我正在进行着某种基础建设,他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并且不断转型。
未完待续
主要展览:
“行走计划”(北京,中国,2011——2012年)
“我们是无关委员会”(苗圃艺术区,北京,中国,2011年)
“我们为什么做那些没用的东西”,(唐人艺术中心,北京,中国,2012年)
“与行走无关”,(站台中国,北京,中国,2012年)
“重新发电——上海双年展”,(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中国,2012)
“三亚艺术季新锐展”,(三亚,中国,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