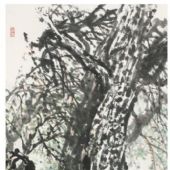离退休的时间越近,我心里对学生的牵挂就越强烈。因此,我决定在退休前夕,在美术学院展厅办一个展览,主要是为学生,再就是向教过我或长期关心着我的老师们做个汇报。
1974年3月,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到中央美院报到。我的老师很多都是徐悲鸿的学生,如韦启美、钱绍武、杜键、靳尚谊、刘勃舒等,还有是从延安“鲁艺”来的古元、伍必端、李琦,也有国统区资深的艺术家,如李苦禅、李桦、李可染、刘凌仓、田世光、梁树年等。在20世纪70年代“文革”中期,我们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受到了老师们的热情迎接和悉心呵护,他们像见到自己出生的婴孩宝贝一样地关爱我们,这其中也包括美院行政、后勤的工作人员。美院的电工、食堂的炊事员、专职的模特、门卫、教具室的人,跟我们都很熟悉,一起打篮球,一起玩。这对我这个从小就梦想学画的年轻人来说,真是有一种一下子进了天堂的感觉。进校后,我们很快就到陕西省户县“开门办学”去了。在户县,我们师生分成了三个“点”。我们那个“点”在户县的秦镇,是当时著名农民画家刘志德所在的村镇。
我们这个“点”的老师是伍必端、刘勃舒、薄松年、苏高礼,还有美院食堂的李胡师傅(他除了做饭之外,还帮我们师生理发)。我是小地方—湖南湘潭一个工厂的工人,画画基础差,在我们班属于中下等水平。虽然很刻苦,但进步缓慢,心里干着急。有一次在户外上厕所,我带上艺用解剖书和速写本,边上厕所边临摹,恰被伍必端老师撞见。他批评了我,说:“拉屎就拉屎,不要一心二用。”接着耐心地告诉我:“到生活里来,就要去画活生生的人。”还给我画了一张速写像。那时,我们都住在一个小院子里,户县的房子都有一个小天井,太阳光上下午都能照进来。我经常看到伍必端老师站在太阳下,把裤带解开,露出半裸的上下身,去捉跳蚤。我们同学有时也去帮他捉,背后则偷偷地把他当笑话讲。
刘勃舒老师鼻隆、眼深、清瘦,有胡人像,说话短促快捷,观其貌,便知是天才、敏捷、乐观之人。我和他住在一个炕上,吃完饭,他就带着我们一帮学生外出画速写。他下笔神速,把我们都震住了。晚上还教我们画马。他很善于跟老乡和村干部打成一片,这对于我们生活、学习包括找模特,都顺畅了很多。
薄松年老师教我们简单的美术史。他身材高大,一口京腔之中略带关东口音,讲起课来如说顺口溜快板。我想,当年他要是从事相声表演,也许会和侯宝林齐名。
苏高礼老师是美院最后一批留学苏联的青年教师,当时大概只有三十四五岁,教我们画头像素描。那时,我们定的规矩是:请老乡当模特,师生围坐着画,谁画得像,谁就把自己的画送给老乡。苏老师画得体面鲜明结实,却不太像老乡本人,而我每次都画得最像。结果,辛辛苦苦画的素描像,几乎都贡献给了老乡。我心里琢磨,下次我也故意画得不像,但一面对老乡模特,一不留神,还是次次都画得像。这在绘画上可能叫“感觉好”吧?
古元老师曾代表美院领导专程到户县来看望我们师生。当时,众多的农民画家听说大画家古元来了,都要求他现场写生示范。古元老师无奈,拿着铅笔和速写本,对着一颗杨树看了许久,迟迟不动笔,大家心里都急盼大画家“下笔如神风雨急”,等到终于下第一笔了,却异常缓慢,笔如刀刻,慢慢点来,一颗杨树足足画了一小时,好像是数着杨树叶在点,一片树叶也不放过。此时,抱着很大兴致的农民画家和我们学生,早已走了一大半儿,剩下的几个人,估计也是顾着给古元老师的面子,而咬牙坚持到底的。同学们回到驻地议论道:看来古元大画家也是徒有虚名,真是不如我们的老师陈谋、王征骅和学生梁长林画得好⋯⋯
二十年后,我独自在山西河曲的白鹿泉写生,也是4月初,一场春雨过后,梨花洁白,杨树挺立,山川如洗。我面对此景,茫然不知所措,突然不会画了。只好静静观察,然后一点一点地将树叶、梨花、山川草木,慢慢地摹写下来。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古元老师是用“心”去画。古元先生是大家,是诚恳至极的天才大家。
在美院的四年学习中,我们去过工厂“开门办学”,学习油画,到过部队,学习版画。最后一年分专业,我被分在国画系。
回顾在美院学习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使我收获最大的老师,他们的共同点,是人格高尚纯粹,学术素养精深,手上功夫过硬。
毕业留校后,我给叶浅予先生当过几天秘书,他是我的书法启蒙老师。李苦禅先生虽然只见过数面,但他的率真与豪放,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令我永远敬重他。
毕业后,我还在民间拜过“古文”老师。我家乡湘潭的万智康老师,他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琴棋书画皆能。他逐字逐句地教我《古文观止》,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能初通文言,这是他的功劳。关于万智康老师,有一件事令我终身难忘。那时,我学习古文之后,还想学诗。他说:“我不善诗词,我带你去拜访湘潭诗词名宿田翠竹先生。”约好的一天傍晚,他带着我,我跟着他,他躬着如同大虾背的瘦弱身躯,走三步,停一步,手扶着沿街的电线杆,气喘咳嗽不已。走到半路时,我对万智康老师说:“您身体不好,下次再去吧。”万老师停下咳嗽,喘着气说:“下次不知能否带你去了。”这句话,顿使我心酸不已。最后到了田翠竹先生楼下,爬上六层楼,用了十分钟。不长的三里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在田翠竹先生家里只坐了五分钟,问了些什么,学了些什么,我全然不记得了,但那晚艰难、漫长的路程,我永远记得。半年后,万智康老师辞世了。
毕业十年后,我还在日本拜过老师。他叫盐出英雄,是我国著名画家傅抱石在日本留学的同窗好友。1989年,我任美院附中副校长期间,携几名同学去日本东洋美术学校交流考察,通过该校田中明德教授,认识了他的恩师、日本美术院代理事长、武藏野大学名誉教授盐出英雄先生。第一次见面,相约在一个干净而简朴的饭店,他的另一个学生狄原延元教授抱着一本书,早早地等候在那里。我问他看的是什么书,狄原先生说是中国古代画论。他补充说,盐出英雄老师要求他的学生都要认真读中国画论。接着,满头银发的盐出英雄先生到了,慈祥厚道的面容有古圣贤者的遗风。席前,盐出英雄说:“日本文化的根在中国。日本的一切,许多都来自中国。”傅抱石的女儿傅益瑶80年代留学日本时,盐出英雄是其监护人。他对傅益瑶说:“你来日本学日本画不是目的,而应学习伟大的中国传统在你的国家失传的,或长期不使用的那部分东西。那些珍贵的东西,在日本都完好地保存着。”他还介绍他的东洋美术史老师高楠顺次郎博士为他写的一幅中国清代画家恽寿平《瓯香馆画跋》中的一句话:“意贵乎远,不静不远;境贵乎深,不曲不深。”这幅作品被他长期挂在家中作为座右铭。后来的几年中,盐出英雄给我写过数封长信,大意是:“期望我在美院附中任要职期间,要提醒和要求学生热爱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坚信中国文化艺术将来一定会有伟大的复兴。”作为一个邻国的画家,他对中国文化如数家珍,实在令人敬佩,实在令我辈汗颜惭愧。他还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对佛学的密宗有精深的研究和贡献。他写的与中国有关的诗歌比吟咏日本的诗歌还要多。盐出英雄,1912年生于广岛福山市,2001年逝世,享年89岁,今年是他100岁的祭日。我会永远记住他—我的日本老师盐出英雄。
2001年4月我得知盐出英雄辞世的消息后,画了一幅画,写了一首诗,以寄托心中的哀悼之情。
英雄本是扶桑人,佛门华夏植其根。吾言邻国遇恩师,岂分疆域贤者同。
吾师心境宁如水,泣血悬堂告天魂。衣钵可怜辜负了,名山事业误匆匆。
我在大学四年中接受的教育,主要是专业技能上的。而在学识、修养、人生、社会这一课,则是在漫长的工作和社会实践的岁月中补上的。在美院附中任教后,由学生转换成了老师的身份,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成了不适应的主要矛盾。这期间,杜键老师、高亚光老师、王德娟老师对我耐心地帮助与呵护,简直是救了我的命。所以我感慨,学生不仅需要耐心教育,青年教师也需要好好培养。
毕业后,我在国画系打杂一年之后,附中丁井文老校长调我去恢复筹建附中。当时附中已停办了十多年。丁校长从美院、电影学院等地方抽调了精兵强将,他们是杜键、高亚光、王德娟、赵允安、王应芳、赵友慈、张智新、孙为民、江大海及封楚方等。我们在老教师的带领下,夜以继日地准备着招收新生的工作。我们除在北京设考场外,还在全国设了几个考场。我和王应芳老师去杭州招生。考生中有个很白净漂亮的小女孩,把试卷带回北京总评后,这小女孩居然考上了。她叫藤菲,现在是中央美院设计系的教授。1980年附中第二届招生,我和张智新老师去了东北沈阳考点。在考场上,有个黑黑的精瘦小男孩,画了一半就晕倒了,我们把考卷带回北京进行总评,并重点介绍了这个考生投入考试的情况,把没画完的色彩试卷做认真的比较分析,认为这个考生虽然没完成试卷,但其色彩感觉很好,应打破常规予以录取。经过张智新老师和我共同争取,该生终于进了附中,他便是现在美院油画系的刘小东。
教师招生选拔学生,就是教学的开始,是“选种育苗”的重要工作。过去徐悲鸿先生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好的老师,应有爱才之心。
从我25岁到附中工作至今,已三十多年,附中的学生一届一届地进进出出,他们有些成了著名导演、设计家、作家、雕塑家,多数在院校的都是教授了,或是研究生、博士生的导师了,但我仍是一名附中的普通教员。人生的路是自己选择的,我没有丝毫的怨言。我为自己的学生所取得的成绩而高兴、自豪。有诗为证:
春来花开君最先,寥落篱下两三枝。待到满园花烂漫,她甘寂寞泥土知。
附中教学的特点也成就了我,那就是一专多能。我刚去附中工作时,中国画教学只有我一个人,因此,山水、花鸟、人物、工笔、写意、书法我都要教。上大学时,我主要学人物。为了给学生上好课,我便恶补山水、花鸟及工笔画。丁校长很好,他带我去溥松窗老先生家学过传统山水画。我还反复系统地研习过中国山水画史、花鸟画史、书法史,又对西方文艺复兴后的素描作过多年的学习,对美学、佛学也用过功。现在想来,认真教学一定会取得“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
我是青年教员时,面对学生,我是他们的兄长,除了教学外,我对他们的生活、心情是很关心的。第一届有个学生叫张嘎,怪异而有才气,经常有些出格的举动。经了解,他父亲是“右派”,家庭不和谐。我虽难于进入他的内心,但我宽容以待。他曾鼓起勇气跟我借过钱,我不加思索地如数借给他,不知他今日在何方。
我是老教员时,面对学生,我则是他们的叔、伯、父辈。自90年代后,我已进入“老夫”的年龄,对学生更多的体会他们都是独生子女,我更关心他们的生活。首先要吃好饭,注意身心健康,尤其是同学之间的和谐关系。平时,常会有些学生到我的画室来聊天。有两个叫寇奕和徐皓峰的学生,平日沉默寡言,也很守规距,但课堂作业一概不按教学要求做,画的都是塞尚的立体分析大直线,若要评分很难及格,但他们又都是很认真的学习态度。我对他们采取的是肯定、鼓励为主,建议为辅的引导方法,收到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1992年秋,我刚辞去副校长职务,由附中教员申胜秋、阎明魁带队,我则作为普通教员带学生到山西河曲县的黄河边上写生实习。在实习快结束时,我们随去的一名校医李大夫,她嫌弃乡干部不讲卫生,与当地乡干部发生了严重的纠纷。同时李大夫也与带队老师阎明魁发生争执。在这不稳定的时侯,我突然接到附中领导发来的电报,要我火速赶回学校评定副教授职称。一边是几十个学生在外面临混乱的不利局面,一边是自身的利益,孰轻孰重?我与阎明魁等老师商量,决定不回京评职称。此时李大夫根本不相信我会放弃职称评定,跟我打赌说:“你真不回去的话,我一切听你的,不再与他人纠缠了。”经过我的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最重要的是学生安全地返回北京,圆满地完成了实习的任务。虽然返校后美院给了我补考职称的机会,最终也评上了副教授,但在工作事业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一贯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个人利益。
在附中工作的这许多年中,我的同事一批批、一个个地先后调离了附中,先后有孙为民、封楚方、江大海等,后又有刘小东、陈平,再有高天雄、孙逊、贺羽、龙力游等。其实,我的机会比他们不会少。90年代初国画系山水画室曾想调我去,我画完人民大会堂《万里长城》之后,清华美院也想调我去,中国艺术研究院也有意要我去,但我都一一婉言谢绝了。人过了四十,老夫、老朽了,从一而终地在附中很好,很安静,可以在教学之余无声无息地修炼和学习。再者附中也需要有老教员在教学上多操点心。因此,我会在附中工作、教学直到退休。这条人生之路也是自己心甘情愿选择的,所以,无怨无悔。
凡事将心比心,在我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中,会遇到不少的老师和同事。好的老师能影响甚至改变你的人生,好的同事和领导也可以感染你的人生。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诸多的好老师恩泽于我,我理应将这些师友美好的人格、精深的学问、过硬的功夫,修炼到手并承传下去。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大多是这样代代相承而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的高尚品格也是由人来一代代相传递而得以延续的。故,我要做一个好老师。这次临退休之前的展览,取名为“许仁龙教学创作观摩展”,其初衷是给美院和附中的学生们看看,给曾教过我的老师们看看。只可惜韦启美、李琦、卢沉等老师已经离世。我深深地怀念他们。
2012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