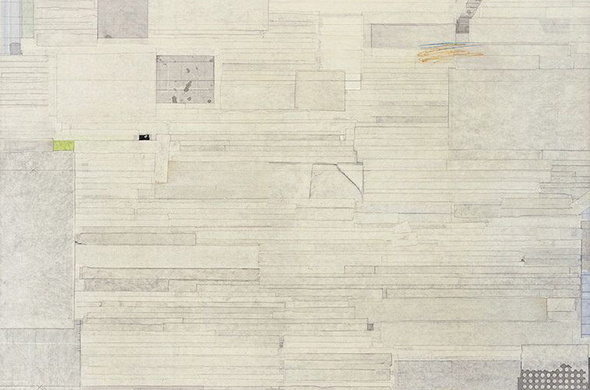
昨天晚上梦见了一座宫殿。梦境的形象光辉灿烂,梦中的朝阳(也可能是夕阳,这要视情况而定)耀眼夺目。我走进了石碑林立的大殿内。浮想连翩之中,已经有什么东西浮上心头、涌向嘴边,只差一步就要脱口而出了,可是我却始终无法将它说出来。这种情况就好像伊凡•参卡尔在《梦幻集•自序》中曾经说过的这样一句话:
然而,他走在人们中间,打算把自己目睹的一切告诉人们的时候,他的舌头受到了约束,那些话不愿意从他的口中迸出……。
根据荣格的说法,大殿代表了人类两百万岁的自我、也就是融合了自身意识和祖先积累的集体无意识的居所,而石碑则代表源远流长的祖先。
荣格在《自传》(也可能是其他的某部著作)中说过,他感受到一个家庭似乎都会存在一个没有人格的业(karma),从父辈向下传给子辈。人类的心理和灵魂充满了对于祖先的回忆,或者就是这种回忆本身。然而我不能理解的是,我对于我的祖先,回忆却非常单薄。我连我曾祖父的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有见过曾祖父,就是说,我的家族回忆仅限于我的祖父为止,连我祖父的两个兄弟(其中一位刚刚去世),面目都是模糊的。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感觉不到自己家族的那种存在感呢?至于我父亲的曾祖父,根据我父亲的回忆,他好像做过几任行将灭亡的大清国的地方官,政绩平平。他没有参加康梁的变法,但是也没有反对新政;没有开仓济民泣血上奏,但是也没有搜刮民脂民膏。任期到了就下台,没有给当地的人民(甚至包括他直系子嗣的我)留下任何印象。
似乎他在任的时候积攒了若干财富,置办了很多田产。不过很可惜,和那些田产一起进入他(乃至于他的子孙后代)的命运的还有对于鸦片的嗜好。这就决定了那些田产再怎么喧赫,最终也是他人耕种。在最辉煌的时候,我父亲的曾祖父——我该叫他什么?——似乎曾经拥有很多家财和田产,以供给我们这些子孙后代在凭空想象中向人吹嘘。但是很快就随着阿芙蓉在阴天上午并不强烈的光线中的那袅袅的若有所思的蓝色烟雾而飘零得烟消云散了。
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可圈可点的经历吧。抽鸦片败光了万贯家财,——而事实上很有可能没有那么多,——也总算是给那些将他遗忘的不肖子孙们提供了一点点茶余饭后的谈资,好让他们在某些自欺欺人的可笑想象中玩味一下那种并不实际存在的悲壮感。
上午阴沉的时光在飞逝,我看向空气中飘散的蓝色烟雾,——它们可能来自于花园里的草木,也可能来自河堤下的水面。——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父亲曾祖父的事情,就仿佛这蓝色的雾气就是当时从他嘴中吐出的烟味,一种强烈的家族回忆感涌上心头,但是我不能言说,只能心念飞动。而且很快我就发现那并不是回忆,而是一种……认同。很可惜,它们就只是一种不切实际感受而已了。
祖先就是我们自己。
好吧,那就让我模仿那个爱吃皮蛋的苏珊•桑塔格在《中国旅行计划》中的思维方式,试着推测一下他(我父亲的曾祖父)的种种情况罢。
1:他的个子一定很瘦高,中年发福以后身材也会很匀称。我的祖父和我的两个叔叔都很高,可是我父亲却很矮。他的眼睛不大,也谈不上有什么神采,眼神随时都很飘忽,仅从目光来看就知道不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的头发和体毛都很稀疏,花白的辫子短短细细。这是我们家族一贯的遗传。我祖父、父亲乃至我自己头发都很稀少。他蓄着长长的指甲,指甲缝隙里毫无污垢,手保养得很好,看上去又抚琴鼓瑟的气质,非常儒雅。他可能真的会一两件乐器,例如萧或者筝,如果是三弦则稍显俗气。
颧骨高,我差点忘记了,这是我们家族的又一遗传,在清瘦的时候颧骨会很高,不过发福以后(例如我父亲和我)就被掩盖了。这也是广东人的一种基本的特征,广东人在人种上是属于南方古猿纤细种的后裔。
2:他应该读过一些书,但是不会太过渊博。功名方面,至少应该具有贡生乃至举人的资格,这是大清国涉足官场的必要准备。不过这一点并不稀奇,因为在大清想要取得这种读书人的身份,途经并不单纯,可以说难度不大。例如《王韬日记》里面说,1859年上海一个富绅一次向中央捐银二十万,中央就奖励上海县永远增加生员名额十九名,松江府十名。此外,毋须考试直接获得生员资格的“捐监”制度也是由来已久,依靠捐输获取的生员资格叫“监生”,虽然与正式生员称呼不同,但是享受的待遇都是一样的。在明朝时期,捐监的费用还比较高,捐监现象还并不普遍,至于清朝费用就大大降低,尤其是到了太平天国以后,一次捐监的费用降低到了十几两,即便是一般的中下人家也能够轻易承受。
3:他会写一点诗,尤其是在心情好的时候,譬如过足了阿芙蓉瘾、欣赏了一次令他满意的湖光山色、或者参加了某次觥筹交错并有艺伎相陪而令人心情愉快的同僚雅集,往往是在这样的场合。他的作品应该是不完整或者说不规范的同光体,能用一些典故,但是语句堆叠得比较生硬。总而言之,大都泛泛之作,总体水品不高,格调高古、有品位的作品不多。阻止他成为大诗人的另外一个硬伤是,他的作品中的押韵很有可能会出问题,因为当时没有普通话的概念,我们知道用广东话咬的很多字写出来用官话读会完全不押韵。例如当我们在朗朗上口地背诵东坡的《赤壁怀古》的时候很多广东士子就会感到怅然若失,因为他们念不出“樯橹灰飞烟灭”这句话。
4:他的书法很娟秀,可能兼学碑帖。学贴的目的是科考,因为当时科举制度的规定字体是馆阁体,粗劣的书法可能会导致某个糊涂考生的卷子被忿怒的主考官所拒绝批改,所以读书人的书法一定是在某个标准之上的。学碑的目的则应该是自娱,出于纯粹的书法艺术的考虑,因为清朝末年碑学非常发达,这是一个时代潮流。他还可能临过米芾、赵子昂或者圣教序,总之所进行的都是非常实用的训练,艺术价值不高。他在高兴的时候可能会写几幅对联分赠给他的同僚或者属下,馆阁体的,隶书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因为隶书在明清两季的读书人中间非常流行。但是都没有流传下来,说得直接一点,都没有流传下来的价值。
5:他对于诸子百家的涉猎仅限于孔孟和老庄,此外还爱读史记,唐宋八大家;他可能出于读书人的必要礼节,也读过一些朱熹或陆九渊,但是对于王阳明、陈献章、湛若水和李贽等则完全没有兴趣。这就是说,尊重一般的史实,但是对于过于思辨的、精神的历史则敬而远之。他虽然惭愧地身为一个古人(我们姑且这么认为),阅读量也并没有超过现代某些有良知的、对于历史有崇敬之心的士子很多。
6:从第五点发散开来看,他的哲学观也是那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二元模式,就好像冯友兰在著作中说的,中国人进可以儒,退可以道。中国读书人对于儒学的孜孜不倦是出于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是作为一个身处瘴气繁盛、汉夷杂处的偏远地区的下级官吏,他不可能有这样的远大抱负,所以根据我的推测,他在感情上还是更加接近老庄思想的。对于道家的清静无为有一种天生的、懒惰而闲适的亲近感。本着这样的基本情况,他对于《世说新语》、《菜根谭》也非常具有好感,认为《世说新语》里面毕卓说的那句关于食蟹饮酒的话是读书人人生的最高境界,任诞第二十三中的这句名言是这么说的: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无独有偶,张季鹰也曾经说过:“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那么对于大多数挣扎在平庸线上的中国人来说,与其追求那本来就高山仰止的身后名,更加不如即时一杯酒了。
7:我们继续这个思路。他的酒量不会很宏,广东人都不怎么会喝酒,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九江双蒸严格说来也不过是日本清酒级别的一种消暑饮料而已。不能不说这是给他在对于毕茂世、张季鹰心有灵犀的同时带来的一个不小的遗憾,不过很快他就惊喜地发现,对于阿芙蓉的尝试和习惯弥补了这一遗憾,甚至发挥得更加出色。在中国人意识到鸦片是那种白皮肤的野蛮人对于他们帝政和文明垂涎不已时所设计出来的、一种居心叵测的卑鄙阴谋之前,他们一直觉得那的确是一种好东西。通过阿芙蓉那令人飘飘欲仙的美妙蓝色烟雾,魏晋风度好像又一次从历史的坟场中借尸还魂。我们来看李伯元《南亭笔记》中的这么一段话:
“……(任立凡)阿芙蓉癖甚深。值窘乡则攒其眉而入小烟室,僵卧败榻破席间,涕泗横流,乞主任赊取紫霞膏以制瘾。主人不允。于此有人焉,先密商于主人,俟其至,当其穷蹙,乃谓主人曰:‘余有数百钱,权为任先生作东道,并无他求,扇一页,或纸一桢,便愿代请一挥何如?……呼吸既毕,即假笔砚,就榻间,攒蔟渲染,顷刻而成。视之,真佳构也。转售于人,立致重价。故得其画者,十九从小烟室中来也。……”
有了“魏晋风度”四个字,人们似乎能够原谅一个知识分子的一切荒唐不经的举动。这可以说也是中国文化史中一个相当值得关注的课题。晋人之风的提法似乎能够在所有领域中为离经叛道之举进行开脱。
8:在中国读书人看来,气节虽然可以说是比天还大的事情,但是有幸遇到乱世有机会留取丹心照汉青的毕竟不多,所以在一般人看来英雄距离他们都很遥远。也没有任何史实证明我父亲的曾祖父有这一方面的壮举,虽然他身处乱世,但是可能是因为他管理的行政区域在战略地位上实在太次要了,他没有机会一展自己的操守和气节。
父亲的曾祖父并没有过殉节的壮举,这是不是说明他是一个没有气节的人?在很多世界观简单的人看来就是如此。但实际上,大多数的中国士人在大节的问题上缺乏的并非品格、也不是价值观、甚至不是勇气,他们缺乏的只是一个机会。
我旅居的城市最东北面郊区的海边深山里埋葬着南宋的最后一位皇帝。他死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陵墓的选址应该是在他的遗体被海浪冲上岸的地点,这么认为的根据是赵氏族谱记载:“后遗骸漂至赤湾,有群鸟飞遮其上。山下古寺老僧偶往海边巡视,忽见海中遗骸漂荡,上有群鸟遮居,设法拯上,面色如生,服式不似常人,知是帝骸,乃礼葬于本山麓之阳。”这位才十岁的小皇帝在被身边的大臣背负着投海死节的时候不知道心里作何感想,他们从花团锦簇的中原一路逃难到这里的天涯海角,大地已经到了尽头。敌军追兵已经不远,鼓角峥鸣之声可闻。然而这最终纵身一跃只对于个人而言比较壮烈而已。后世大多数人甚至念不出这位小皇帝那个拗口的姓名,他们忽视这血淋淋的事实,只把它看作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儿童为了他以往雍容华贵的生活所理应作出的一种姿态。
呜呼。宋少帝陵破旧不堪,杂草丛生。民国的一次修葺让它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水泥怪物,但是很快又一次荒废了。站在这里,路到了尽头,已经不能再向南走。滚滚的道德压力如洪水猛兽,甚于忽必烈的大军,它将一切碾碎在这个终级的、惊涛拍岸的冰冷滩涂上。这里的海岸没有碧水、甚至没有沙滩,没有一点柔和的信息。纷乱的碎石和惊心动魄的海浪就映衬着人们心中的绝望,道德露出了它本来的狰狞面目,就好像这丑陋的海滩,纷乱的碎石犬牙交错,它根本不欢迎儿童的奔跑、情侣的追逐、老人的漫步,它蔑视生命而崇拜死亡,只想把一切淹没。
9:道德的伟岸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但是道德的适宜却和每个人息息相关。那么,怎样才算是一个有道德的读书人?虽然老庄诗词、《永州八记》都被认为是读书人所垄断的精神享受,但是事实上还是有很大出入,就好像我的一位老师范景中教授在文章中说的那样,附庸风雅在最初的时候被看成是一种感时髦的故作姿态,久而久之也会产生真正的精神的愉悦。
中国读书人的雅集是一种完美而高雅的娱乐方式,从王右军曲水流觞一直到民国为止,文人的雅集为中国清流的故事编写了一个又一个完美的神话。魏晋时期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在集会形式上可能还没有区分开来,到了宋代以后,精神方面的雅集与前面说过庞大而豪华的宴会走到了两个极端,雅集必须是不沾染一丝俗气的。有一部《宁波府志》中的这样一句话描述得非常形象和引人入胜:
“每良时美景,辄飣野菽园蔬为会,素衣藜杖,散步逍遥,人望之如神仙也。”
发展到明末时期,因为政府对于文人的思想言论干涉较少,雅集的组织和活动已经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社会炙手可热的一种流行风潮。这一类的雅集在明朝开始,也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叫“社”。明朝有个叫吴麟的人,他在一篇题为《家诫要言》的文章中说,“秀才不入社,做官不入党,便有一半身分”,认为只有参加了雅集活动,文化人的生活才算完整。吴麟的这种说法虽然不无夸大其词,但是在当时的文人思想中非常有市场。因为综观晚明文人的言论,有很多知识分子和吴麟有着同样的想法。比如说还有个叫方九叙的文人,他在《西湖八社诗帖序》一文中,也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夫士必有所聚,穷则聚于学,达则聚于朝,及其退也,又聚于社,以托其幽闲之迹,而忘乎阒寂之怀。是盖士之无事而乐焉者也。古之为社者,必合道艺之志,择山水之胜,感景光之迈,寄琴爵之乐,爰寓诸篇而诗作焉。”
方九叙在这里一口气列举出了雅集的四方面的要素,即“合道艺之志,择山水之胜,感景光之迈,寄琴爵之乐”,这可以说也是雅集活动的一种固定模式。
是真的风雅还是附庸风雅,是一个难以判定的问题,这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这就好比南齐孔稚珪《北山移文》里所描写的那个人那样,你很难判断一个隐士是真正的隐逸还是在走终南捷径。——商山四皓就中断了隐居的生活出来辅佐汉家的天下,而把自己搞得好象梁伯鸾那样娶丑女过穷日子好象也不完全对,有的事情并没有一个可以作为标准的标准。
是否具有真正的隐逸精神要看一个人的素质和隐逸思想,我觉得父亲的曾祖父那样的小官吏不太可能是那样的人。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的序文中对于隐士有加以类型的区分,归纳起来,范晔认为隐士一共分为以下六种类型:
①:隐居以求其志;
②:曲避以全其道;
③:静己以镇其躁;
④:去危以图其安;
⑤:垢俗以动其概;
⑥:疵物以激其清。
虽然范晔自己没有具体指出这六种类型的实例,但是根据唐代颜师古在注解《后汉书》的时候则为之列举了一些名士高隐,为这六种类型一一对号入座。颜师古认为姜尚属于第一种类型、薛方为第二种类型、介之推为第三种类型、商山四皓为第四种类型、申徒狄为第五种类型、严光和梁鸿则为第六种类型。
梁代的阮孝绪是继范晔以后对于隐士文化更进一步、更专门研究的后起之秀。阮孝绪综合了范晔的意见,他在《高隐传》这篇文章中进一步发展了范晔的隐士类型说,而且分类根据更加实际可考。他认为隐逸生活一共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分别是:
①:言行高逸,名氏弗备;
②:始终不耗,姓名可录;
③:挂冠人世,栖心尘表。
看得出阮孝绪和范晔分类法的平分秋色不同,他的这种划分方式是具有一定层层推进的倾向性的。虽然他并没有说这三者孰高孰低,但是根据道家学派的思想,从“无名”到“有名”,还是能看出其中的等级结构。至少我们从他的这种区分中可以看出一点毫无疑问的是,不管隐者与尘世的关系亲疏程度如何,他们都必须要作出一种刻意远离俗世、与社会保持距离的姿态,并且随时准备好绝尘而去。
相比之下,宋代程伊川的隐士分类方法多少就有些拾人牙秽,他在《程氏周易传》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说:
“士之高尚,亦非一道,有怀把道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有知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良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
这种刻意的孤立和边缘化,可以说是维护自身精神优越性的一种风范、或是一种生活态度。中国隐士与社会主流的不协调性千百年来一直被看作是隐士阶层的荣耀之所在。
《东坡志林》里有一则题为《贺下不贺上》的短文中有这样几句话说:
“贺下不贺上,此天下通语。士人历官一任,得外无官谤,中无所愧于心,释肩而去,如大热远行,虽未到家,得清凉馆舍,一解衣漱濯,已足乐矣。况于致仕而归,脱冠佩,访林泉,顾平生一无可恨者,其乐岂可胜言哉!”
隐逸是一种性格,要甘于寂寞,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做到。就算孔子也说过“人不知而不愠”但是他自己就做不到。
可见阮孝绪的标准本身就是一种悖论。一个你所不知道他存在与否的人,你又如何将他在品格上判定为隐逸与否呢?古往今来载驰载趋,活过的人不知多少,大多数人不为人知,又如何判断他们之间有多少人是隐是逸、还是隐而不逸?阮孝绪的这种推论可能来自于《荷蓧丈人》这篇文章。但是综观其全文,那位老人真正所说的只有一句话,就是指责孔子五谷不分。如果不是孔子自己的演绎和发挥的话,联系上下文关系,将那句话理解为一个疲于生计的老人受到打扰时絮絮叨叨的抱怨,倒也并无不妥。
既然谈到了“名氏弗备”这个份上,我想我再也没有什么话题来对于父亲的曾祖父说长道短了。父亲的曾祖父出生于广东香山的惠明村,他似乎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五岭以南的那一箭之地,这一点恰好对比于我,我至今没有回到过那个我只能勉强念出它拗口名称的、祖先的故乡。这故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天涯海角的、而且事不关己的存在,就好像父亲的曾祖父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基本陌生的古人一样。在直观想象的印象之中,祖先的故乡可能是几块黑黄的房顶,几乎凐没于芭蕉和榕树还有那种岭南特有的牛屎菊所拥挤出来的、踊跃的绿色世界里。那个地方的地气蓊郁,植物掌控着那里的一切。
虽然我是对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作纯粹的推测,但是实际情况不可能相差太远。翻越了五岭的烟云,你所能看到的都是这样一个接连一个的小村庄,火车前进半日,景色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时间久了,你会感觉你丝毫没有任何地前进。你会感觉世界除了这些东倒西歪的小村庄以外,没有高原、也没有大海,没有任何除了这一望无际的灌木丛之外的其他内容。村头枝条虬结的荔枝树是相似的,甚至树上晾晒着的补丁累累的衣裤彼此之间也毫无任何区别,坟墓造成房屋的形状,但是很快就都荒芜了。时空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仿佛我们在不断进入同一个小乡村,郁郁葱葱、奔腾起伏的灌木丛仿佛一个均匀的罩子,将我们此时的一切封闭在这些过去的回忆之中。在这里强调生命的所有格并没有意义,个人的生命太过渺小,甚至只是一种错觉。
走进任何一个这样野草般的村镇,房屋的门窗,就好像一个个深不见底的洞穴,不知道里面吞咽了多少代人的回忆。在这些房屋里或者它们之间,时间几乎是胶状地凝聚着。一个从出生到出嫁到生子到垂老都没有离开过深山中一箭之地小山村的老太婆步履蹒跚地从这门里走出来,她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她家里的门槛应该有五十公分高,甚至更高。——这一幕就仿佛是卡了壳的留声机,在几千年的时光流转之中不知道被重复了多少次。所不同的只是一些无关痛痒的细节而已。
祖先,或者说故乡就是这样的整体。正如我津津乐道地猜想我从来没有去过的那个叫广东香山惠明村的地方——在半睡半醒的谵妄中它似乎与我有了一点关系——而丝丝入扣那样,我想象父亲的曾祖父、他的生活、他的人生,一切都全无根据,但是一切都和事实不会相差太远。因为祖先就是这事实,我们自己就是事实。
每一位祖先都是一枚蓝色的、微不足道的精子,在游荡中与水母般漂浮着的卵子相遇。他们的人生也几乎全都“名氏弗备”。也许他们之间有哲人、有异人、甚至有人被雷电击打以后无端地能说出一口流利的德语,可是全都不得而知了。事实上在历史中,大多数的祖先都是名氏弗备。这些“名氏弗备”的祖先们在历史的视野之中,看上去就好象只有一个个模糊的影子,没有人会去问他们是谁,因为影子彼此之间都很相似,——而事实上他们的人生也确实非常相似。在这种相似与相似之间,我猜想了父亲的曾祖父的学识、修养、嗜好、生活、工作和人生态度,这里涉及的,几乎是人生问题的全部。
夜晚的星辰将会一颗不剩,
夜晚本身也即将无影无踪。
我要离开这纷繁人世,
那整个令人无法忍受的世界将会与我同行。
我要抹掉金字塔和勋章、
还有大地的脸孔。
我还要抹掉过去的积淀,
使历史从此灰飞烟灭、尘埃落定。
我看着最后的落日、
我听到最后的鸟鸣。
而我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后人。
这是博尔赫斯的一首诗。
不阴不晴的暮色挤进窗棂,从那之中看不出任何时光的飞逝,就很像自古以来一直如此。毫无根据的空想差不多花掉了我一整天的时间。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不阴不晴的天气占据了我们的大部分人生,因此可以推算出这种天气也同样占据了几十万年岁月的大部分时光。我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想象着我的一位素不相识的祖先的零零总总。这位平庸的祖先已经回归灵魂的大海,但是我、作为他的同样平庸的后代的我,却还要继续这样百无聊赖地生活下去。我望向阴霾的暮色,邻居家若有若无的广播音乐声音飘浮在空气中,我突然感到一种滚滚而来的、无边的寂寞。愿荣耀归属于不朽者,父亲的曾祖父已经回归灵魂的大海。在历史之中的大部分人似乎从来都不需要存在,他们就好象是模糊的影子。没有人会去问他们是谁,因为影子彼此之间都很相似。我望向阴霾的暮色,突然感到一种无边的寂寞,风起风息,我们都在不断地被人遗忘。我的种种猜想,可以看作是一个时代的平庸的人的缩影。愿荣耀归属于不朽者,被遗忘者只是为了维系因果关系和结构的构成而存在。
2007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