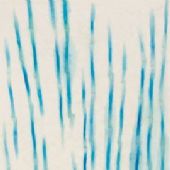在我的朋友中,卢辅圣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说特殊,一是他对中国美术史有自成体统的独到见解,大凡读过其《天人论》、对他提出的“象限论”略有所知的同道,都会有同感。说这些见解“自成体统”,并非空泛的赞词。《天人论》谈的是绘画,所涉及的问题却具有历史学和哲学的意义。他用一种不同于数十年流行的发展论的新方法论探讨艺术史,这探讨是学术方式、有思想深度的,而与集体无意识式、运动式的反叛和批判不同。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思考,在他担任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辑的这些年里,先后组织与主持了以“四王画派”、董其昌、赵孟頫为题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主编了《中国书画全书》、《黄宾虹文集》、《朵云》、《书法》等颇有影响的丛书和杂志,编辑出版了大量有学术份量的著作和画册,对书画出版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辅圣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是以画家身份进入美术史论界和出版业,但其逻辑思辨能力、史论素养与相应成就,让我们这些学艺术史论“出身”的人都感佩不已。这样的才能,不是很有些特殊吗?
二是他有比较深厚的古文化修养。卢辅圣生于1949年,是在新中国初期开始读书的,但他同时又接受了传统的私塾式家教:读古文,颂古诗,写书法,因此其传统文化的功力,比一般同代人高出许多。只要读一读他的文字(如《中国书画全书序》),看看他写的诗文书法,就能明显感觉出这种差距。他对于画史画论的思考,对于传统类图书的编辑策划,以及在书画创作中传达的传统文化信息,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对于同样生长于革命年代、传统文化底子薄弱的人群来说,这种“厚”也就显得特殊了。
三是他一直从事出版工作,编书著述,人们都已把他视为史论家和出版家,但他始终坚持作画,屡屡参加国内外重要展览,作品面貌也独具一格。作为一家著名专业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在开会、策划、运筹、审稿、联络、应酬之余,还能挤出时间转换角色,平心静气地画出诸多构思缜密、描绘精致的作品,这样的本事,当然也算得上特殊。
1990年,香港城市画廊出版《卢辅圣人物画集》,他为画集写的自序中,称自己远酒近茶,偏爱月色而疏于日光。他说,茶“与酒之不同,正在于迷而不乱,嗜而有敬,使人在清醒中应对世事,在沉静中反思现实,在安祥静谧的冲淡心境中把自己引向生活的彼岸。”而月色“是虚灵超旷的,空明混茫的,似真似幻的,置身其间,必然产生梦境一般的幽邃深远的冥想,直至冰雪其心,肌骨俱爽,物我恍惚融为澄澈透明的一体。”“在我的画上,很难看到奇恣纵肆、狂傲不羁的激情与力量,也很难看到恢诡谲怪、徘谐怒张的侠骨和幽默,弥漫于笔墨形象之间的,大多是轻淡、纯净、舒缓、宁静、平和、澄明、悠远,以及蕴藉含蓄、欲说还休等等意味的静逸之趣。”这个自述,清晰地勾画出其作品的风格倾向以及产生这种倾向的个性心理和趣味根源。熟悉卢辅圣的人都知道,他虽然身居生活节奏日益紧张化、快速化的上海,但处理纷纭复杂的人事艺事,从来都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在淡然中化解紧张,于平和里消融激烈。而这种化解与消融,总是伴随着清醒的理性,同时又不乏出人意料的想象。我们常说“画如其人”,但在艺术品急剧商业化的当今,许多画家失去了真诚和创造,迷失于摹仿和风格化套式的复制里,“画如其人”也变得混沌模糊了。卢辅圣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个性与趣味,保持着那份自然和真诚,他的作品,是他的个性生命的延伸,这种延伸就像他对茶和月的描述,是情感化、充满浪漫诗意的,是他在精神上的一种逍遥,尽管这种逍遥大多以发古之幽思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令人感到过于空寂和虚无。
卢辅圣擅长人物,多画古圣贤者、文人雅士、仕女儿童,都是前人或同时代人画过的题材。但对他来说,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达什么以及如何表达。譬如,同是以陶渊明那首著名的《饮酒》诗为题,他没有像一般作品那样描绘诗人采菊,而是画了一个鬓角插花、皱眉思考的头像——塑造的不是隐逸文人而是“欲辨已忘言”的晋代名士。这表达了画家对历史人物的独特理解。其它如《宅心》、《大风起兮》、《白露》、《日乌》和近期巨幅代表作《丽人行》、《兰亭雅集》、《大司命》,也都具有这样的特色。这类作品,与其说是对古人形神的再现,莫如说表达了画家对某种古代精神的体认和形象表述。不必说,这种形象表述是困难的,其古拙的变形,充满哲理意味的题跋,题跋中大量古文字、异体字的使用,更为这表述增加了一些高深莫测的味道。也许画家要有意拉开与当下流行的大众趣味的距离,因而追求“文”与“雅”、追求“另类”的表现,也许是觉得非如此不能传其情达其意。这让人想起一百年前用石鼓大篆题画的吴昌硕和出奇制胜、不拘一格的海派传统。
卢辅圣的基本画法是工笔:细勾,淡渲,富于装饰性,即便大面积泼墨或没骨设色,也加以归纳,赋予画面单纯与工致的特色。就是题跋,也只用略带汉简意味的秀丽古隶。但从整体看,作品结构的空灵简洁,笔致的松静散淡,色调的单纯简逸,特别是精神的虚旷淡远,又具有浓郁的写意性。不妨说,这是一种写意性工笔或工笔性写意。画家所使用的手段精而巧,所创造的形象秀而拙,所呈现的风格幽而奇,所指向的境界迷远而深冥。这倾向富于古意,也相当现代,它与画家的南方气质、清醒理性与浪漫情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与当代中国知识层的文化追求,尤其是与正在兴起的重视以传统精神丰富与重造自己人格形象的知识层文化追求有着深刻的关联。
2006年1月25日于北顾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