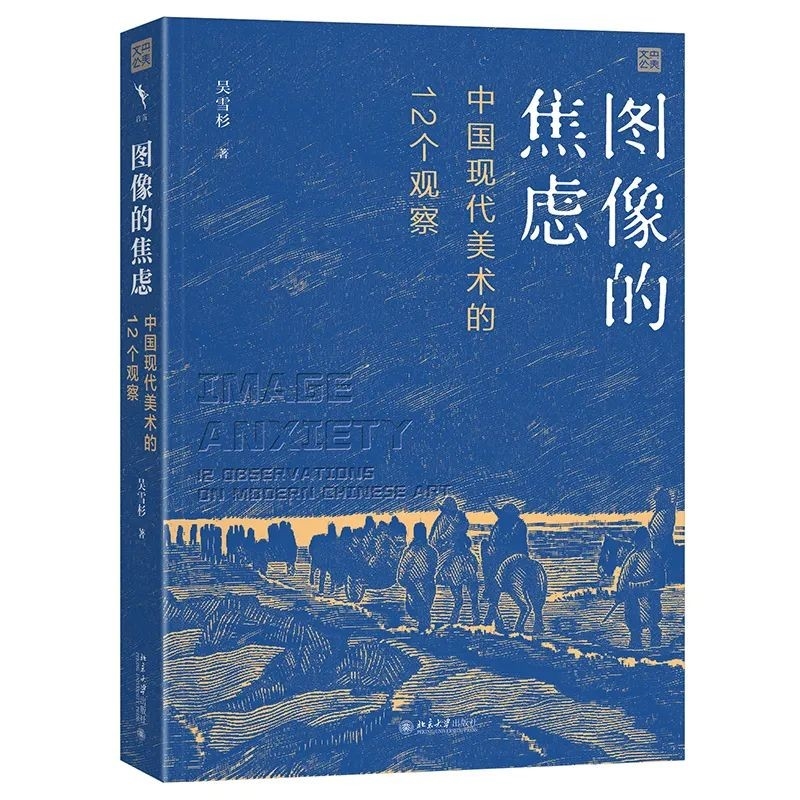按:2018年10月,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国内首次劳特累克主题展“经典•劳特累克作品展”。此次展览共展出90余幅作品,涵盖了绘画、素描、石版画和海报,其中珍贵的纸本版画更是每隔两年展出一次。本次展览展出的版画作品都毫无修饰地记录了夜巴黎中红磨坊中的奢靡,风月场中的私密和剧场文化的风靡。无论是台前红极一时的歌舞明星还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夜场女子,劳特累克均一视同仁地将她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勾勒下來。我们可通过他寥寥几笔之下的曼妙身姿一窥19世纪末光鲜亮丽的夜巴黎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人间百态。
亨利•德•图卢兹•劳特累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是法国19世纪末一位天才型艺术家。13岁坠马及父母贵族通婚隐患造成的残疾,使其从贵族继承人的身份变成上帝的弃儿。他的创作风格受德加等印象主义与日本浮世绘的影响,往往选择以巴黎娱乐场所中的底层女性为描绘对象,在他短暂的37年生命中,创作了大量油画、石版画、海报、素描与速写插图等艺术形式。红磨坊艳丽的舞女,背景里西装革履的绅士,喝着苦艾酒的艺术家们……他画笔下的人物融进世纪末夜晚巴黎的黑色之中,充满了华丽又颓废的魅惑色彩。
劳特累克并未计较每幅作品将会换取多少报酬,也从未在意绘画是否会带给自己何种名誉,甚至他对致力成为后人敬仰的艺术大师的那种雄心勃勃的诉求也显得意兴阑珊——尽管他临终不久前被告知作品被收进法国最伟大的艺术博物馆卢浮宫,也没有阻止他放弃自暴自弃式的酗酒行为。但恰是因为他心底苦楚只能以手中画笔为诉求途径,从而成就了他的艺术之名。
现代性的描绘——“浪荡子”
19 世纪是法国艺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时期。毫无疑问,劳特累克的艺术受到了印象派的影响,尤其是德加——劳特累克甚至将其在蒙马特的住所搬到了德加的隔壁,以便近距离的向这位优秀的大师学习。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皆以现代都市为描绘对象,不去表现重大历史题材,而是从自身融入的日常生活里汲取灵感,这种创作方式改变的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波尔莱尔的“现代性”概念的提出。波德莱尔认为,艺术家需要描绘的是19世纪的现代生活特征。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他指出“现代性”即“过渡、短暂、偶然”,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在他看来,美不是唯一和绝对的,美是双重的,一面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面是“相对的、暂时的”,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因此艺术创作中那些当下的、特殊的新奇之美仍是艺术家需要关注的对象,尽管它们可能并不优美、也不高雅,甚至丑恶或肮脏,但那也是现代生活中不容忽视的成分。19世纪法国贵族开始失去往昔的社会地位,但他们仍保持着涵养、精神及自我的优越感。巴黎街头出现那么一批人,他们出身高贵,教育良好,富有才华,常常置身于人群,漫无目的的闲逛,从瞥见的日常为对象,就像吟诗作画的“浪荡子”。波德莱尔将其称为“浪荡子(Le Dandy)”,这一词“包含着这个世界的道德机制所具有的性格精髓和微妙智力”,“浪荡子”对固有的权利模式感到厌倦,渴望用全部的激情去观察、体验生活。从此层面上,劳特累克的形象同样具备了波德莱尔所言的“浪荡子”属性。
但是劳特累克并不仅限于此。与同时期的艺术家对比,劳特累克虽然也是以现实生活为描绘对象,但他并不把焦点聚焦于都市中那些随心所欲、悠然自适的社交生活。劳特累克充满着一种明显的矛盾,在他那里我们看到了两种对立的需求,就像波德莱尔所言的每个人身上的两种需求,一种趋向上帝,一种向往撒旦,“对上帝的祈求或是对灵性的祈求是向上的愿望,对撒旦的祈求或是对兽行的祈求是堕落的快乐。”
世纪末的颓废——“享乐与虚无”
劳特累克出生的时代,正逢法国乃至欧洲艺术变革的历史阶段。艺术家的创作从重视造型、严谨的古典主义审美转向了自我情感的抒发阶段。这时期,工业革命的发展导致社会进步了转型期,许多手工业被机器所取代,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大众观念的急速转变使得社会步入了一种世纪末的焦虑、恐慌情境。虚无与没落笼罩了法国社会,大众寄托于空幻的精神世纪,巴黎的娱乐业大量兴起,“动荡与压迫摧毁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制度与世俗的冲突更挑战了人们内心的情绪底线。一时间,无处倾诉的痛楚在艺术中得到安慰。”
从劳特累克自身经历来看,其早年跟随过画家普兰斯托(Princeteau)学画,他擅长画马,捕捉那些在运动瞬间的马的姿势,展现了精湛的绘画天赋,此后他也尝试过一段时间的古典主义题材的创作。因为身材的缘故,劳特累克受到来自朋友和部分亲人的异样眼光甚至嘲讽,对内心自我情绪的迫切纾解,促使劳特累克不断寻求一种更加直接、更加激烈、更加纯粹的艺术方式去倾诉这种原始需求。
19世纪的蒙马特,浪漫、颓废、享乐,各色娱乐业风生水起,风流场所弥漫着情欲的味道,红磨坊的舞女,纸醉金迷的夜色……时运不济的艺术家和落魄流浪者在此扎根,其中不乏许多在当代享有盛名的艺术大师,如梵高、高更、塞尚、米罗等。劳特累克在这里寻找到了属于自己心灵上的片刻安宁,热闹喧哗的室内环境使其充满了安全感,他喜欢将自己隐藏在灯红酒绿的影子下,以第三视角去观察、描绘对象,他还会将自己变装成武士、小丑,或是穿着康康舞的服装。在这里,他迎来了自己艺术创作生涯中最多产的时期。爱德蒙•德•龚古尔曾说:“这个侏儒将自身的缺陷投射到他的作品当中,并达到了其艺术的巅峰。”自此,绘画成为他寻求心灵慰藉的一道途径。
丑恶中的美感——“情欲与女人”
劳特雷克往往以人物尤其是女人作为其绘画创作的主体对象。他用敏锐的画笔捕捉那些在下层生活圈里活得卑微又用力的女性,妓院、酒吧、歌舞场等,劳特累克对这些场合里的妓女和舞女的描绘使其声名鹊起,但也被贴上了“低俗”、“不雅”的标签。劳特累克的父亲认为他令家族名誉蒙羞,禁止他在画作上签上劳特累克家族的名字,指责其作品“只是黄色的劣作,是在妓院和舞厅放纵、沉溺于玩乐的借口”,这些抗议的声音让劳特累克显得更为孤独。
我们可看到,劳特累克并不塑造那些令人愉悦的美感给予观者高雅享受,也不一昧追求大胆裸露的画面给人以感官刺激,他有意识的避开了一切传统意义上的美,即便描绘对象是风姿卓越的女演员:《坐着的小丑——査尤可小姐》、《红磨坊的査尤可》中的女演员穿着夸张又滑稽的演出服,査尤可仪态粗俗随意,体态发福臃肿,看似漫不经心的态度却带着小丑演员强颜欢笑的无奈心酸;作品《拉•古吕走进红磨坊》里,红磨坊中的舞会女王在旁人陪同下摇曳进入,表情傲慢不屑;《在红磨坊》近景右边的舞女拥有黄色的头发,鲜红的唇,以及艺术家有意为之涂上的那抹骇人的绿。劳特累克画中的各种女子姿态各异,忧郁、放荡、滑稽、心酸、凄凉、张扬……他利用变形夸张的手法将这些形象进行“丑化”处理,以至于歌星吉贝儿曾写信央求“请千万拜托不要把我画得那样丑陋”。
劳特累克认为,“丑陋总是有它美丽的一面,发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是令人激动的。”1986年劳特累克将他一系列的石版画创作集结成册,取名《她们》,画册内容为那些风尘女子的日常生活,包括10幅彩色画、卷首和封面。在卷首,劳特累克描绘了一个女性的背影,她正在梳头发。为了暗示她的职业,在近景处画了一顶男士的帽子。这一细节足以点名风尘女子们的世界,但又不会沦为庸俗的色情艺术。有人将劳特累克描绘舞女的兴趣完全归因于他对社会底层人士的关心与同情,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劳特累克这种复杂情感里包含了同情,也包含了自我怜悯。那些压在生活最底层的哀怨,那些为生活、为尊严所承受的麻木,那些看似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就像劳特累克心灵的一面镜子,映射了艺术家难以言喻的心境——
“他在画她们,也是在画他自己”。
文/林佳斌
图/北京画院美术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