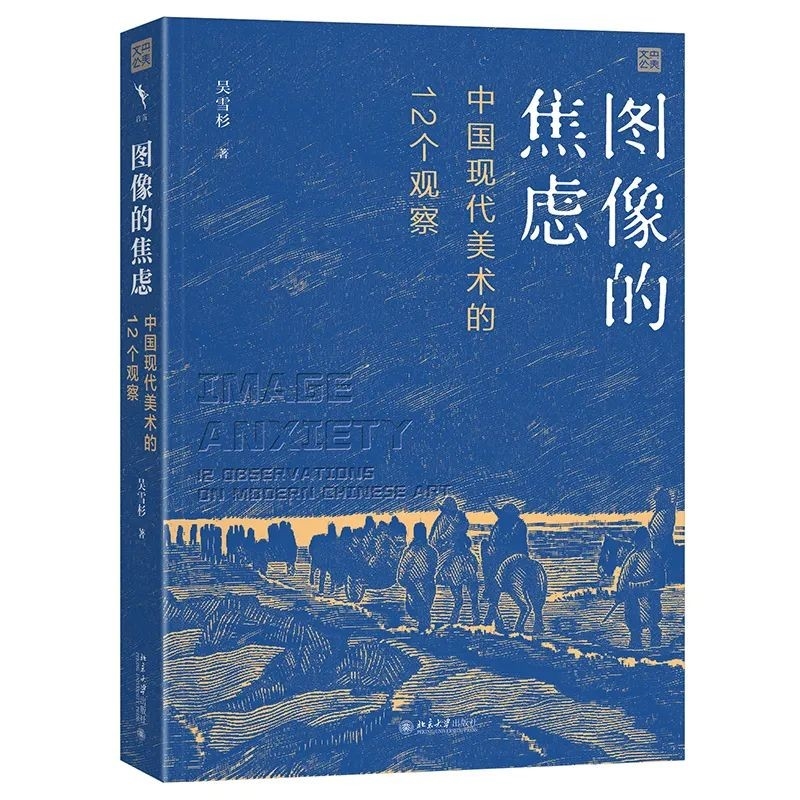2014年6月12日19点,中央美术学院空白诗社联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在中央美院北区礼堂举办了一场名为“寻找孙佩苍——一段终见天日的传奇”的主题沙龙,对谈嘉宾为陈丹青与孙元。陈丹青是中国著名艺术家、评论家,孙元为孙佩苍先生之孙。
在对谈开始前,陈丹青对孙佩苍先生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孙佩苍先生是辽宁辽阳人,曾任驻法公使、东北大学教授、中法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等职,被聘为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陈丹青提到,在20世纪50至80年代,中央美院陈列室陈列过一批欧洲十九世纪的珍贵画作,包括库尔贝、德拉克洛瓦、列宾等人的原作,这些都是孙佩苍先生的收藏。《寻找孙佩苍》是孙元历时两年,走访不同的国家与档案馆,搜寻整理关于孙佩苍先生的文献资料后所作,揭露了一段鲜有人知却极为重要的历史。
陈丹青:孙元,你是怎么找寻你祖父的?
孙元:我祖父曾是国民党的参政员,所以我先去了台湾的国史馆,后来又去台中南投国史馆的文献馆翻阅当时的报纸。内地主要去了国图和北大图书馆,还包括成都与东北的省图书馆和省档案馆。国外我去了东京的国立图书馆和京都图书馆。再利用网络大海捞针似地寻找,最后找到这些资料完成写作。实际上这本小书中还存在很多空白,但值得庆幸的是,读者之后又给我提供了颇具价值的信息,比如中信图书馆的沈明先生等。
有一位读者说寻找孙佩苍,不仅是还给历史一个真相,更是还给我们每人一个尊严。因为每一个人都不该这样不明不白的生活在无声的沉默里。这些读者的支持以及今天诸位的到来,都鼓舞我去继续寻找祖父的足迹。
陈丹青:我刚才提到的在陈列馆的这批收藏,其实是属于孙先生的家族,因为政治运动的原因才交给美院托管。你可以把这个过程讲一讲。
孙元:1969年,林彪副主席号令许多内地的企业和院校都迁到三线备战。当时我叔叔在北大进行核物理研究,家里的四间房堆满了画,但是房子并不能保留,而且当时文艺界的多数人被迫害致死,三婶非常害怕,觉得这个画不能留。后来美院的吴作人先生把所有的东西,包括画和爷爷的笔记都拉到了中央美院。几天以后,中央美院陈列室给了奶奶一份清单,但是这份清单所记载的作品并不齐全。文革结束后,1986年5月12日,美院把这些画按照清单还给我们,不过其中大概有20幅遗漏了。祖父丢的另一批画是在成都办画展时。这批画的具体数量我不清楚,只知道包括张大千、谢稚柳的作品。
祖父健在的时候本想建一个陈列馆,但到我们手中时并不打算捐献,因为当初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当时的那些画和现在留下的画相比,其艺术价值大概已经丢失了70%-90%。至于边界条件,就是指现在的人文环境。
陈丹青:能具体解释下边界条件吗?
孙元:捐献也要看这个社会环境和你的心情是否一致,这就是边界条件。
陈丹青:我绝对不主张你们捐献,我从孙佩苍先生的收藏里读到很多讯息。第一,他是在二三十年代收藏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西方经典的唯一收藏家。除此之外,蔡元培先生小规模收藏过法国早期立体主义的作品17件。这是我所知在民国期间收藏过西方原作的两个人,但是孙先生收藏的是油画,这其中有很大的区别。第二,我发现他的祖父跟张道帆、徐悲鸿,以及几位留法的前辈,都是老哥们,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徐先生手上也收藏了不少名画,可是里面没有西洋油画。第三,国家买不起藏品,不能像美国、俄罗斯等国,靠皇家、大财团的力量收藏欧洲的作品。百年以来中国往现代化转型,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份自己的世界美术史收藏。日本的民间美术馆有数百座,其中二十多座有非常完整的西方艺术收藏,古希腊、古罗马、埃及、两河流域、玛雅文化、东亚文化都包含其中。今天中国崛起了,但是中国没有一家美术馆收藏一张法国十九世纪的经典。在这一个层面上我们输给了日本。此外我也好奇,你的祖父不是生意人,那么他的钱哪里来?他怎么买到这些画?
孙元:我祖父虽然是随着179人去勤工俭学,但是他的身份是教育调查员,所以他有一定地位。
陈丹青:他的地位拿到今天来说,也就是东北地区一个教育局的年轻干部。他有钱买原作,这件事无法想象。
孙元:他在1926年的东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叫《法兰西教育现状》,主要讲到他调查法国的美术和音乐。我想他对于绘画的收藏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他考察了各国将近100个美术馆。我祖父曾经收藏了西洋美术品的印刷品,从伦勃朗到印象派都有,并且都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进行收藏。第二个阶段是他去中法大学当校长的时候,鲁迅先生当时是教授。那时候他的收入比一般公务员多得多。
陈丹青:鲁迅主要收藏版画,但是版画无所谓原作,他买了不少德国的版画,油画可不是那么便宜的。
孙元:其实有很多作品,比如德拉克洛瓦、杜尚的,他买的是画稿,也不是原作。
陈丹青:画稿也是原作,有时候画稿比原作还好。
孙元:他当了大学校长以后生活可能比较宽裕。此外,二十年代他在法国期间,可能已经加入了国民党,受到了国民党的资助,当然这些都是我的推断。并且他第二次在中法大学期间,他还在联合国的教育委员会任职,代表中国政府。我不知道这其中是不是也有酬劳。
陈丹青:你解释了半天,他的收入全部是工资。一个人靠工资能够买国外十九世纪的油画原作,我还是不太明白。
孙元:您能告诉我当时那些原作大概多少钱?
陈丹青:跟今天的市价不能比,但是跟当时的工资也不能比。如果他能买得起,徐悲鸿一定买得起,徐悲鸿的收藏里面我不记得有任何记录是西画,几乎全是国画。
孙元:这个大概是需要继续寻找的话题。
陈丹青:我希望做美术史的学生留心,也许哪天研究时会碰到这个问题。在二三十年代,法国市面上的售价大约是多少。
孙元:我们打算今年在中国油画院举办一次“孙佩苍藏画纪念展”,如果如期,也希望各位能够来看这个画展。
陈丹青:中国现在学油画的人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看的都是印刷品,只能支离破碎地观赏一些原作。中国自己没有脉络清晰、全面的收藏。这个困境会影响学画者的判断,中国几代人都没有摆脱这种命运。孙佩苍以他个人的财力,即便不遭受后来的厄运,也有他的局限,他不可能收藏那么多东西。这件事应该由好几十位,甚至上百位收藏家,几代人共同努力,使它变成一个大景观。
孙元:如果你看了这个画展可能会比较失望,因为剩的东西不多。祖父的收藏本身也不全面,但是丢失的是比较主要的。这次画展主要是一个纪念。我比你们稍微年长,以我个人经验,我认为应该多了解历史,我们需要恢复历史记忆。有一个学者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总之我会继续追寻,同时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谢谢。
文/张高珊
图/全晶
编/张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