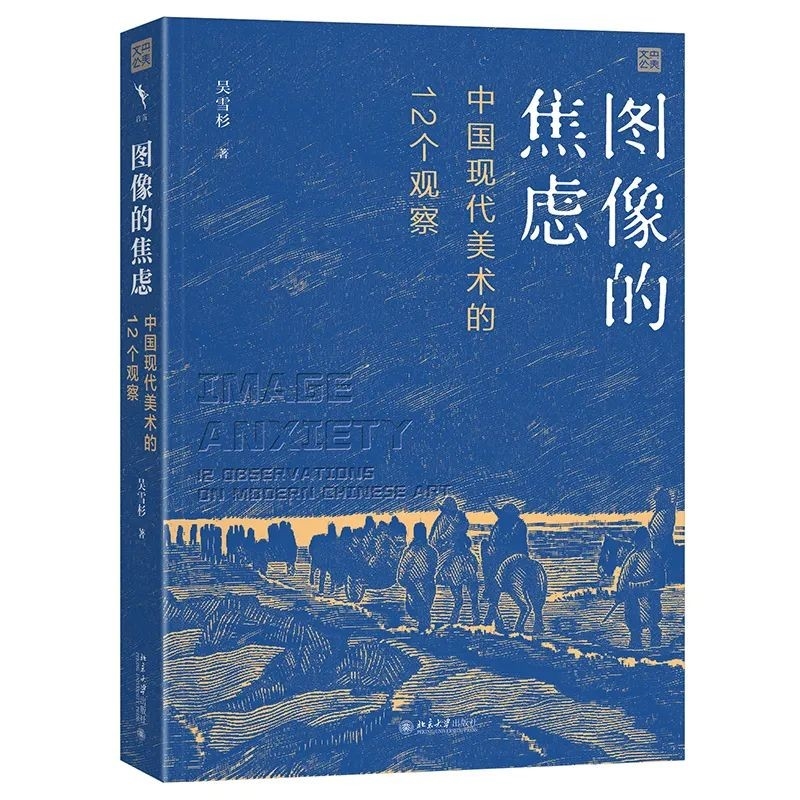“这条神秘之路是通往内心的。只有在这里,在我们心中,才存在着永恒的世界——过去与未来。”
——诺瓦利斯(Novalis)
从北京飞抵银川再到达内蒙古额济纳旗,还需要在高山和荒漠间乘坐一架小飞机,辗转数次大巴,或不舍昼夜驾车穿越绵延不绝的戈壁无人区,无论何种方式,对初次到访的旅人都是极大的考验。然而艺术家刘商英却多次深入这片广袤的荒漠,连续三年、独自一人在黄沙漫天与满目孤绝中进行着大尺幅绘画写生。2017年10月21日,刘商英在额济纳旗汉代关隘遗址“红城”举办个展“生命场”,展出其三年间以额济纳死去千年却不腐不朽的胡杨林为创作对象的31幅大型油画作品。在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几乎烧毁了全部作品的大火后,这个史无前例的野外展览的举办对于艺术家个人来说真正带有“灰烬中重生”的意味。
早在2011年,刘商英就开始多次深入西藏阿里进行写生创作。对于典型学院派出身的青年艺术家,写生是十分重要的创作方式之一,而很早以前刘商英就明白了图像时代“写生”另外的意义——重要的不是描绘,而是能够跃然纸上的抽象感受。远离都市,将惯性和琐碎削减到最低,进入洪荒自然,是为了“离自己更近”。他享受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未知的神秘力量指引。
全景自然:作为一种展览形式的实验性探索
场地的选择仍然是本次展览最值得探讨的部分。当这个几乎没有先例的展览真正拉开大幕,带给观者异常强烈和复杂的感受,超越“宏大”。地处中国北疆的额济纳人迹罕至,古称居延,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土尔扈特蒙古语所称的“先祖之地”,在历史研究中常被作为北匈奴最早的首都,虽坐拥11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常住人口仅3万有余,境内多为无人居住的沙漠区域。
作为首个利用与现世隔绝的异域场景作为展览现场的艺术家,距今2000年历史的汉代红城遗址在为期15天的展期内,成为这批创作24小时不间断展出的空间场域。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源自刘商英一次画作拍摄的偶然经历,当已完成的作品摆到在这个沙漠里兀自屹立的残破城墙前,历史、现实、自然、文明的瞬间交汇所产生的能量极大地激发了艺术家的想象力与决心——“好似生长在一起了”。
对于千里迢迢赶来的人们,仍有被吞噬之感。古老的城墙遗存与无垠的戈壁大漠,无不让人感到怅然。时间在如此广阔的空间中似乎静止了,人之渺小形如蝼蚁。尽管是如此强有力的画作,伫立在这远古荒原中仍觉吃力,好似刘商英作画途中被风暴不由分说地裹挟——艺术家把创作现场强烈的情感激荡和失真的体验同样带给了来到展览现场的观众,“笔触行动的痕迹似乎与流淌的额济纳大地具有同构的关系。”自我、画布、颜料,就是这广袤宇宙中微尘一般的存在。它们从自然中生发,最终回归自然。
这个遗世而独立的户外场域,偶然出现的“人”已不是最重要的观者。天地、日月、星辰从黑夜到黎明的守望与阅读,风沙、霜露的肆虐与纠缠,与作品构成了最重要的互动关系。刘商英将自己对“生命场”的理解通过此种绘画方式与展览方式表达出来,他舍弃了传统美术馆展览空间会带来的公共性探讨,承担着作品随时可能被摧毁的风险,虔诚地将作品献给天地,以完成一场与自然的真正对话。从这一层面来看,无论从绘画行动的出发点还是绘画观看的完成度,艺术家刘商英都属于极为纯粹和理想主义的代表。
尽管这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刘商英和他的工作团队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让这次展览得以实现。他们不断寻找在巨大风沙下更有效的固定方式,并尽最大努力掌握好作品在这个自然空间的节奏——作品与城墙之间的关系,作品与宽广荒漠之间的关系,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人在作品间穿行的路线与进出城墙的感知,画面的朝向、顺序、内容与时空文明的交流……他们运用等比例缩小的模型尝试各种作品摆放的方案,像一个作曲家演奏音乐,在辽阔大地和古城墙边创作出或短促跳跃或深远长鸣的音符。
从仰望天空到俯视大地:近年来的创作脉络
从西藏阿里无人之境到内蒙古额济纳旗荒漠,不断深入极端自然环境让刘商英的脸越发黝黑,神情亦难掩艰辛。近三年来,刘商英以每年一次个展的密度高强度工作,2015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空故纳万境”,2016年于常熟美术馆举办“青山半入城”,2017年在内蒙额济纳红城举办“生命场”。马路教授认为,“商英的画,一直都有一个很强的‘生命’的线索。”
西藏部分的画被学者认为是“相对经典传统的写生”,尽管2011年阿里写生的经历是他近年来创作转折的起点。这批作品呈现出抽象表现主义的风格,我们仍能依稀找到天际线、远山、湖泊、蓝天这些具体的物象。第一次面对广袤洪荒,刘商英感到绘画彻底失语。深入其境,他不得不放弃掉传统的绘画经验,不再拘泥于绘画语言形态或风格样式的考究,而投身于身体力行的“朴素劳动”之中,平静下来的过程让他“感到踏实”。这是他与自然对话的开始,亦成为绘画生涯的转折。
常熟系列是刘商英创作中的一个形同“疗伤”的插曲。一次噩梦般的经历,使得常熟之行之展成为他重新出发的过渡期。2016年春天,应常熟美术馆馆长吴文雄之邀,刘商英来到江南常熟进行写生创作。创作进行到一半,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电路导致的一场大火将工作室的所有存画烧毁殆尽,包括所有西藏时期作品、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写生以及常熟已完成的作品。作为大火的亲历者深知现场之惨烈与触目惊心,刘商英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经历一段时间的消沉与低落,他终于艰难地重拾画笔。虽是江南小景,但刘商英在常熟的创作却融入自己对地域历史、文化、生活的感知,呈现出一个偏离大众视觉经验的深邃厚重的江南。
如果说刘商英在西藏阿里是仰望天空,来到内蒙额济纳则是俯视大地。策展人奥利维耶·卡佩兰(Olivier Kaeppelin)谈到刘商英这批绘画的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他受到中国传统绘画、诗歌及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理想,人在宇宙自然中的渺小;第二层面是类似于行动绘画的实验,不同于印象派的户外作画追求光线与物象本身,行动绘画所强调的是身体介入在绘画表达中的拓展。相对于画面留下的痕迹,观看的感受、身体力行的体验以及自然变化在绘画过程中的参与更为重要;第三个层面是艺术与自然的交织,“艺术创造属于它本身的自然,即拥有独立领地、空间与法则的‘第二自然’“,而由绘画或雕塑行为所创造的属于生命的场域,正是刘商英本次展览的核心。
神秘之路通往内心:刘商英的绘画观
作为最古老也是当代艺术中最难走出新路的艺术形式,绘画的发展及可能性是数字时代全球文化语境共同面临的难题。刘商英关于绘画的思考及其创作方式的探索,不仅在个人实践层面具有突破性意义,更是对当代绘画问题的一种有效回应。
在原始混沌的生态,刘商英找到一种新的风景画创作方式。他强调“在现场”却不是为了“画现场”。不论是高原还是荒漠,克服体力上的巨大困难进行现场大尺幅创作,并不为了去描绘风景本身,而是通过绘画感知自然、进入自然,继而走向内心、寻到自我。与自然的博弈能够将他的感受放大,从而更专注于直觉,在可控与不可控的边缘,人与画便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所有行为都是自然形成的,相互融合,所有的体验都令人激动,近乎完美。”
“自然与艺术,究竟谁更有生命力?”奥利维耶·卡佩兰向自己发问,更向艺术家发问。他认为艺术作品是人类心灵对自然的一种投射,能让“死亡”永生,因而艺术比自然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而刘商英认为,艺术的生命力更多是精神层面的,具有某种对未来的启示;而自然的生命力在于它永远在那里,始终如一。它们都带有某种神秘和神圣,悄悄隐藏在客观现象之后生生不息。
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在大自然中看到了“世界精神”,但他也在人类心灵中看到同样的“世界精神”,自然与精神事实上都是同一事物的显现。故而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道破玄机:“神秘之路通往内心。”意为,整个大自然都存在于人的心中,如果人能进入自己的心中,将可以接近世界的神秘。
文/朱莉
图/吴松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