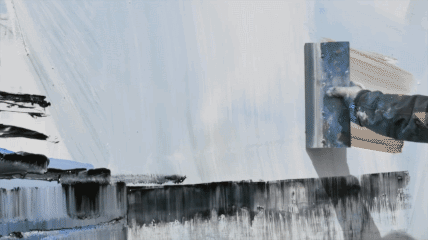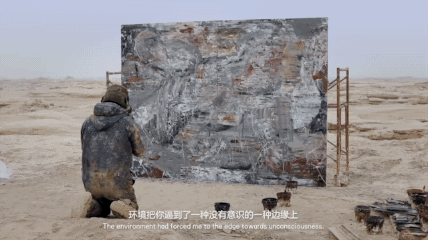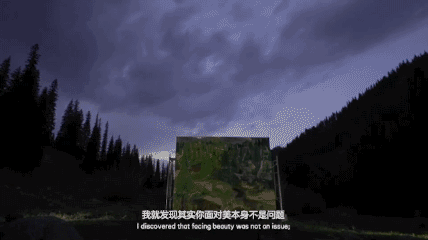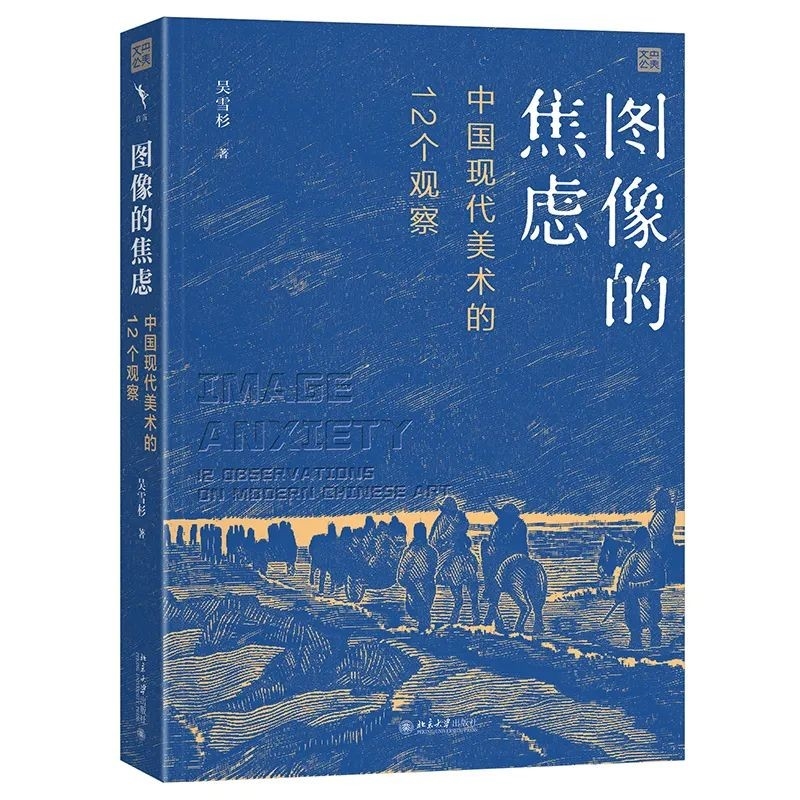2011年,刘商英首次踏上了西藏阿里之旅
面对自然与万物
风景画仍是一个绘画者本能而惯性地选择
但这一次
刘商英只从这些小幅风景画感受到了沮丧
他意识到,传统意义的“描绘”风景
无法与如此广袤的自然取得联系
这种无法沟通、无法关联的状态
令他感到无比无力
“一切需要重新开始”
刘商英明确而坚定地说到
艺术上的转折从来不会一蹴而就
投身变化莫测的自然
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奇妙的外部契机
2013年,在玛旁雍错
突变的天气使过往创作中的
一切惯性和平稳都被打破
刘商英第一次舍弃了调色盘
长时间的凝视与瞬间的绘画反应
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创作路径
又或是艺术家与自然间的一种
崭新的交流方式
那是不可名状的具身体验
是摇晃着的不安定间的决断
自此,刘商英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行走计划”
走过西藏阿里、内蒙古额济纳旗
新疆罗布泊、阿尔金山、东天山北麓……
每至一处,体验不同
过往的创作经验被抛下又重新找寻
“行走”成为了创作不可割裂的部分
甚至演变为了创作本身
于刘商英而言
在各地的行走经验之中
他与自然的交流
常常指向生命的本质和无限
没有目的、没有结果
“绘画成为一种朴素的劳动,
一种耕种,让我觉得踏实”
 刘商英在“洞见ART”采访现场
刘商英在“洞见ART”采访现场
本期“洞见ART”将带来
艺术家刘商英的行走与自述
“绘画”何以成为人与自然间的交流方式?
刘商英将分享十余年间的创作与思考
01 西藏·阿里 2013-2014
我必须跳开自己熟悉的环境,绘画的舒适圈就像是柏拉图的洞穴,只有逃离惯性你才会追问自己为什么而活,为什么画画?因为自然并不需要被描绘。
2013年,在玛旁雍错,砸下的冰雹打乱了绘画中的平稳和秩序,我第一次舍弃了调色盘,也第一次体验到我不是在画一张风景。那里的神圣之光,让我获得了一种奇幻的神秘体验,也获得了一种渴望新生的内在动力。

 《玛旁雍错4号》,布面油画,135cmx200cm,2013
《玛旁雍错4号》,布面油画,135cmx200cm,2013 《玛旁雍错19号》,布面油画,160×240cm,2014
《玛旁雍错19号》,布面油画,160×240cm,2014在变化莫测的光影下,我选择了长时间的注视和之后瞬间的绘画反应。此时,绘画是一种在光的不安定中的决断,一种指向内心的拓展,不可言说也无法确切把握。
我体验到了真实的存在绝不是眼中所见的客观景象,而是通过身体感知与其建立的联系,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我在注视自然的同时,自然也在注视着我。
02 内蒙古·额尔纳旗 2015-2017
额济纳旗和阿里在地貌上的巨大反差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它让我在2015年有理由再次重新出发。在阿里,我的视线在远处,是一种散视,在额济纳,我的目光不由得向下俯瞰。我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扔掉了西藏绘画中的经验,转向一种密集式的,聚焦式的,对某一生命现象的关注。
那些干涸的胡杨散落在沙中,与它们的相遇构成了在我内心巨大的矛盾和冲突,而自然却以它的方式化解了这一切。我惊讶于眼前的死亡之美,也感知到生与死在无限的瞬间中没有任何分别。


我不设定具象、抽象,也不设定主体、客体,主观、客观。我将颜色的选择很有节制地控制在一个很小范围,有时只有两三种,这使我在绘画时更遵从内心而不太受视觉的控制。
2017年项目结束后,在额济纳旗汉代红城遗址的首次户外展览,让我打开了另一扇与自然交流的大门,所有完成于现场的绘画作品,与日月星辰和风沙共同相处了十五个日夜。自然成为了绘画,而绘画也成为了自然本身,观看绘画以及自然的边界都被打破。自然接纳了我,更接纳了一种平等的交流关系。
03 新疆·罗布珀 2019
2019年,我把绘画放进了一个我更加无法掌控的限定里,或者说是一个自然的绝境。因为罗布泊的能量非常强大,始终掌控着一切。



那里的地景把我指向了一种虚空,那种单调的极限,逼出了绘画面临的所有问题和挑战,为什么来这儿画画?画的又是什么呢?所有的艺术问题指向的是一种虚空的极限。
单调,这种巨大场域会随时把你吞噬,罗布泊是一个无边的真空地带。在极端恶劣的气候下,除了感受到身体的艰难之外,艺术更是变成了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当时把那张画画完。
环境把你逼到了一种无意识边缘,那种无意识实际上是极度挣扎的状态,是完全被迫的。在那种情况下,绘画跟以往比是一个决裂的状态,是出于一种本能的自救。
在无数次的冲撞与撕扯后,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最终的和解依旧来自于身体的本能,用手沾上颜色触摸大地后,我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
04 新疆·阿尔金山 2021
阿尔金山是真正意义上的“无蔽之地”。星空在那里并不是诗和远方,而是一种恶无限,天堂和地狱在那里拥有同一扇门。
2021年,我第一次在荒原中看见如此多的野生动物。
我想当然地决定在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沙山上跟随野牦牛的足迹平行行走,狂妄险些付出代价。走过之后,我用画布涂上白色油画颜料,将我们其中的一段脚印以严苛的取证方式拓印下来。骑虎难下的行走困境让我体验到本能与身体感知的错位。
尊严往往以最孤独的写照呈现出它的形式。站在荒原上,我凝视散落在其中的野牦牛与野驴的尸骨,也强烈感受到生命的尊严,它们被荒野接纳,一种最原初的敞开,一种没有遮蔽的自由。而我能做的就是以最虔诚的绘画方式向它们致敬。

阿尔金山彩虹的绚丽,以它不可接近的真相打动着我。在山体的岩石上,我随机选择了二十个点,并用二十块画布和二十种颜色分别对这些点进行采集,之后在两山间划了一条可以接近的“彩虹”。阿尔金山用它的“无蔽”最终认领了我。
05 新疆·东天山北麓 2022
2022年,我走入天山,那里的美很不真实,我曾想过放弃。但是,当发现在美的秩序中夹杂着奇妙的无序时,我最终选择了面对这种美。天山留住了哈萨克人,因为他们愿意遵循与自然共处的原始方式生活,这就是天山的动人之处。
熟悉的画布和颜料,会再次变得陌生。真正的进入需要一切都慢下来,我必须再次清零。这看起来有点像狗熊掰棒子,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真正的启示是一些微小的东西。我会把随处可见的松针、羊毛、羊粪和马粪置入在画中,试图让它们说话,这时我发现一切都对了。
天山对于哈萨克人来说是独特的,也是唯一的。我在体验这些的同时,也慢慢知道了天山与哈萨克人之间并无差别。于是,明快的色彩重新回到我的画面之上。


06 尾声
回想这十几年在自然中的绘画,每个地方的行走经历都不可复制,因为它们是动态的,不会固定在某个地方,它们带给我很多经验不曾把握的动向,是一个需要用肉身慢慢体验,自然而然去意义和经验化的过程。
我和自然交流,而不是描绘它,这种交流常常指向生命的本质和无限,所以没有结果。因此,在不设定结果的时候,交流才具备了真正的条件,绘画作为交流的方式才得以存在。
那时,绘画成为一种朴素的劳动,一种耕种,让我觉得踏实。
文|刘商英
编辑|周纬萌
图片|艺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