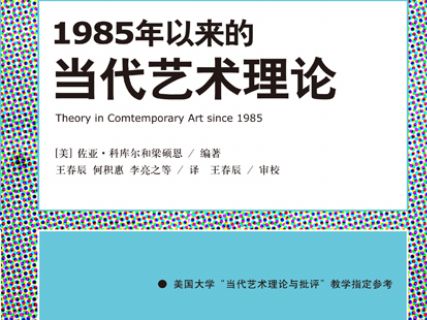
中国的艺术界近几年很是热闹,社会媒体对星罗棋布的艺术区、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大大小小的画廊、风风火火的拍卖会、形形色色的展览作了较为密集的关注和报道。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少新的艺术杂志和报纸。海量的媒体信息,很多都涉及到对当代艺术的争议与讨论,一个又一个有关当代艺术的话题被挑起,人们对此时而同意,时而反对。
“当代艺术”一词经过这么广泛、频繁的使用、利用之后,似乎变得更无所指,更让人们抓不住什么是当代艺术,或如何去看所谓的“当代艺术”。当代艺术一词的理解,在这几年的国内使用和理解上,差异很大、矛盾重重,似乎使用的越多,就越不清晰;关于它的争论连篇累牍,相应的研讨会也频频举办。
那么,作为国际背景中产生的“当代艺术”概念,究竟如何从其源头看待,就成为我们的期望和好奇。也许人们历来对于“误读”都不介意,都认为它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所谓言路不通、信息不对称,必然会导致误读;误导也会产生误读的结果,即便“正读”也不见得比误读更理解原意,或更能够被接受,所以误读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着,视为认识知识、认识异样的文化、观念的方法。好在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代艺术”作为一种文化事件已经发生,至于如何廓清、梳理它,大概也不必急于一时,相反从长计议,随着事物的展开和内在矛盾的呈示,未来历史会给以它一种历史框架的描述,甚至说是否“当代艺术”不在于贴标签,而在于艺术本身、在于不同地域看待艺术的态度。接受一种艺术观念的认识与从这种观念认识的重负下释放出来,都需要勇气和知识。
所以,经过近几年的艺术发展和变化,人们大概更需要回头去思索何谓艺术、何谓当代艺术,话题永不会终结,只能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无论正读、反读或误读,他山之石总是我们需要的,今天的中国艺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空中楼阁建起,一定是吸收了不同素养的文化知识和艺术(包括理论),才长出来的成果。
那么,读这本《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可以使得我们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来检视一下我们的艺术,也有助于反思一下我们今天的艺术。首先,当代艺术在海外的发生,有一个自身的文化逻辑,这就是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而随着宏大叙事的结束,开始了一种“当代艺术”的文化现象。这是社会自身与文化关系的结果,从时间性和艺术的内涵来讲,当代艺术是一种当下性的艺术。至于什么属于当下性,则因为文化要素构成的差异以及社会政治态度的不同,对其内涵的界定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艺术在今天已经脱离了现代主义的那种形式革命,从自身的功能追求、价值判断、形式语言上都力求超越为形式而论形式的形式主义,进入到以“理论”为立足点的创作与批评上。没有当代的这些理论框架,就无法创作、阐释这些艺术及其作品。也就是说,随着艺术和社会、和政治意识的结合,它已经变得不再是视觉判断的直观问题,而是理论阐述与解析的对象;理论进入到艺术认识与艺术创作的内核结构中,成为其存在的一份子,甚至说这时候的艺术已经不是艺术的问题,而是理论的问题。对当代艺术的认识基础,越来越不是从美术本身说起,更不是从视觉性或架上绘画训练出来的视觉敏感出发来谈论当代艺术;从知识准备的背景上看,美术与当代艺术是两回事,是关于艺术体系的不同范畴。或者说,作为观念与方式的当代艺术已经与传统艺术(重技术)、现代艺术(重媒介)拉开了距离,变成了重态度的一种方式。
在这部文选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当代艺术涉及的领域和问题是如此广泛,也是如此复杂,在经典的艺术观点看来,这些都不应该是艺术,也不是艺术力所能及的事情。但问题的发生恰恰是因为这些问题需要以一种视觉形式去表达,以一种视觉的直接性来呈示其背后的问题,这就是海外当代艺术存在的前提和理由。如身份问题、族裔问题、性别问题等,都是社会性的复杂问题,与某一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有密切联系,既受制于后者,也受惠于后者的矛盾存在。没有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则不会有这些艺术表达方式的必要。比如宗教与身份问题,如果没有强烈的当下冲突性和现实性,那么美国艺术家塞拉诺和梅普尔索普的作品就不会引起轩然大波,牵动了社会各种宗教力量和政治势力的神经(见本书第9、28章)。如果不是美国社会的族裔问题,那么洛杉矶街头一段业余拍摄的录像,就不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不会在传统艺术概念的前提下成为“当代”艺术(见本书第15、16章对罗德尼•金事件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当下性”与艺术史的发展有关,更与艺术介入社会、关注社会、表达社会有关,其相关层面的阐述皆依赖于理论,诚如书中所言,“艺术中的所有知识形式在本质上都具有‘理论性’”、“艺术从来不会摆脱对其意义的理论化,声称意义的透明性的主张与其说是具有意识形态、具有‘理论性’,还不如说就是‘理论’本身”(见导论)。这也正是美术史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变化,多种知识系统进入到艺术的阐释、研究中,回避或忽略这一趋势都无法廓清今天的艺术现象,知识的更新更加“紧迫、必要和令人激动”,“理论是艺术教育中要去占据的新领地之一”。
第二,当代艺术的广度已非个体的单一行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行为。它的创作模式是基于社会知识场域的一种行为,而且它始终是凝视、反思、批判社会体制、或者被艺术世界给以景观化、媒介化、甚至商业化(本书第1章)。它在多元主义的方向下,仍然具有强烈的反思历史、社会以及政治的维度,独立的批评声音仍然贯穿了当代艺术。在此时,展览制度、美术馆以及学校都成为当代艺术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美术教育从19世纪以来已经跨过了三道门槛:1)建立在技艺基础上的传统学院派模式;2)与包豪斯相联系的现代模式,其宗旨在于特定媒介的创新;3)充满了批评理论并由美术馆、艺术学校等艺术机构产生的当代模式,它的主要属性就是“态度”(本书第2章)。如果要展开当代艺术的实践、创作与批评,都离不开这些艺术世界体制的关联;单纯一个方面的描述都无法揭示当代艺术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美术体制在我国远没有全面、有效地建立起来,社会对艺术的认识与接受处在矛盾之中,这方面的建设对于促进积极的当代艺术发展是实属必要和不可缺少的。
第三,当代艺术作为在社会体制中的一种有选择的艺术,迄今中国语境中的体制对它的各种样态仍然是排斥的,在文化语境和知识积累上也还是排斥的。可以说,我们是在不断排斥的态度之下来理解当代艺术,然后将自我认同的艺术视为“当代”艺术。但另一方面是,我们现今在国内看到的很多所谓的“当代艺术”恰恰是不够当代的,是疏离了社会性、政治性与历史价值维度的,仅仅作为商业化的一种运作,而非强烈反思社会、批评社会、对话社会的艺术。甚至大量的东西涉及到的话题和问题泥陷在几个筐子里:文革、毛泽东、天安门、大头大脸、卡通漫画造型、拼贴等,给人的偏差印象以为这些是“当代”艺术。大谬不然。常识上讲,艺术分为不同的取向,或者个人愉悦,做色彩与线条的逍遥游,或者歌颂赞美,做满幅欢声笑语的大合唱,或者为生存计,做通俗浅显的行货儿为生活;也有视艺术为独立之生命,追求艺术本体意义的突围,也有信奉艺术为形式之唯美,孜孜于形式章法的追求而不悔。但对于当代艺术,则另有规则,决定了“当代艺术”超越于这一切而成为知识场域中的一种表达。我们所缺乏的是那种以艺术为媒介来吁请、反思社会公正的作品和标竿艺术家,艺术家的身份已非个体的自吟自唱,而是社会关系与社会问题揭橥于视觉的行动者、思考者(见本书第22章对里希特的分析)。如果说,中国有当代艺术,应是有一种社会意识的觉醒,这样的当代艺术是一种有社会公义、公正、有使命感的艺术,而其艺术家作为社会活动家、社会参与者,不期然尽了一点历史责任、表达了应有的社会良知和公义。这是社会转型对一部分当代艺术的要求,而不属于这一类诉求的艺术,可不必苛求自身属于“当代艺术”。
固然,我们有我们的艺术历史传统,也有我们新历史中的艺术传统,但面对今天的现实,“当代”艺术的发展不尽人意,其片面性、其投机性、甚至将当代艺术局限在市场化的狭隘取向上,都无助于艺术的开放、无功于艺术的价值实现,艺术在今天是一种多元、宽容与民主观诉求的表达,有时候它不见容于时间-地点的观念差异,但也不是被框进一统的规范中。在面对历史的现状时,我们承认历史的局限性,也客观承认我们对历史不具有超越性,但它并不妨碍我们在观念上超越自己,或者更全面地扩大我们的认识。
中国的当代艺术获得国际瞩目,它既需要国际语境下的理论批评,也更需要中国语境下的理论批评,而且来自于中国语境中的研究者、批评者的声音更应该具有话语活力和创造性,但实际上关于这方面的阐释与研究,还需亟待跟上来,系统的课题研究、学院的硕博士论文写作都存有顾忌,若干杂志上时或发表一些时论,严肃的专著零星出现,与中国如此广泛的艺术相比,仍然不够、不全面。
在此,当我们阅读这部书结束之际,我们应该有所收获:“当代艺术”没有定义,在这部书里通篇没有关于它的定义和限定,相反,它展示了一个广阔的场域,让我们思考艺术的当代转换和置身于问题域中的功能体现,它们是否契合我国、是否带来我们的反思,则是开卷有益的,也是正逢其时的,而启发我们去做深一步的探讨也是当仁不让的。顺便提及,这本书也是美国大学美术史系“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教学使用的一本参考书。
(《美术研究》2009年第4期)
(《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