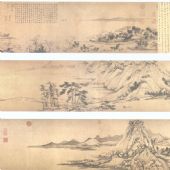【内容提要】:本文以朱乃正(1935-2013)的油画代表作为对象,以“视角”为着眼点,具体讨论中西古典艺术中的观看与观念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为朱乃正所认识和选择并经由他的“视角”呈现出来。于其中,本文尤为注意揭示的是,朱乃正在油画的中西融合探索方面——具体而言即其逐渐触及的油画“造境”实践方面——来源有自的思考与探索步履,包括他所遭遇而未解的困局。
从一般视觉经验来说,人类肉眼对外部世界的观看不出平视、俯视、仰视三种视角,平视能见物形、俯视能察物貌、仰视能得物势。
从普通照相原理来说,在这三种视角之下所观看到的景观详略取决于焦距长短,短焦视野大,取景横阔,可见整体;长焦视野小,取景纵深,可盯个体。
若基于上述视觉经验和普通原理,浏览朱乃正从艺六十年来的油画创作,我们能够发现和讨论什么问题呢?
一、仰视视角:从工具到风格
朱乃正自1953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从事美术创作与研究以来,矻矻于油画艺术六十载,创作作品不计其数,而尤以如下几件为同仁所熟悉:
《金色季节》,161×152cm,1962-1963年,油画。
《第一次出诊》(亦名《新曼巴》),1972年,120×150cm,水粉画。
《春华秋实》,180×350cm,1979年,油画三联画。
《青海长云》,178×145cm,1980年,油画。
《国魂-屈原颂》,190×190cm,1984年,油画。
这几件作品中,《金色季节》、《青海长云》、《国魂-屈原颂》更是在全国画坛享有盛誉,以致于大家在提及朱乃正时,会不约而同地在大脑映射出扬青稞的少女、蘑菇状的长云以及茕茕孑立的屈原大夫的形象甚至色调。朱乃正的这几件广为人知的作品主要完成于上世纪60到80年代,并且是画坛中人都懂得的“主旋律”、“主题性”创作的类型。浏览一过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朱乃正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在观看视角和呈现上具有一致且稳定的倾向,即:
仰视——以大于45°甚至是逼近90°的视角观看和呈现对象;
长焦——以纵深透视取景而又突出主体的观看方式锁定和呈现对象;
顶光——以来自顶部的光源通过明暗交界关系塑造形象主体。
这里要问的是,朱乃正这种稳定的仰视、长焦、顶光“三位一体”的视角表达方式是怎样形成的?或者可以进一步问,朱乃正为什么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形成这样一种稳定的艺术表达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朱乃正上世纪50年代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接受的造型基础教育的内容和特点说起。
在上世纪50年代,处于由普及转向提高的“正规化”发展的中央美术美术学院,在造型基础教育的内容上,特别以石膏、静物和人物的素描、色彩写生练习为主。其中,无论中国画(时称彩墨画)、油画、版画、雕塑,各系各专业均依据“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一“原则”,在室内外安排大量课时,用以素描写生并渐至色彩写生训练。这里我们姑且不谈这一时期俄罗斯“契斯恰可夫教学法”在政府“一边倒”的国际外交方针下被引进和推广所产生的问题和影响,也不谈各系教师对“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一“原则”的不同态度和反应,以及最终通过“反右”运动粗暴处理学术论争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这是可以另外讨论却暂时无关本文宏旨的两个问题,本文所关心的是一个更朴素的视觉观看问题,即美术学院在教学中是如何训练学生“观察”对象的?这方面,上世纪50、60年代的一些教学老照片可以给我们非常直观的解释。
50年代初徐悲鸿和王式廓在室内进行人物写生,可以看到模特儿坐得多高,徐、王二人坐得多低。
1959年雕塑系五年级人体泥塑课堂写生,男模特被安排在一米多高的木台上,很有气势地站在那里,俯瞰着学生忙碌。
1960年油画系素描教学会议,师生围坐在身形高大的石膏像《被缚的奴隶》边上研讨解剖,站得看都得仰脖儿,何况是坐着。
1961年国画系人物写生课,面对叶浅予请来的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5名学生中有3名蹲坐在地上画速写,20分钟后他们有可能站起来画另外一张。
1961年油画系二年级外光写生作业,面对全副武装为红军战士的男模特儿,所有学生都坐在小板凳上,在阳光下观察着对象,寻找着外光下的色彩关系。
1962年王式廓在油画系第二工作室面对高坐的模特儿辅导学生写生。
由这些老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即除了某些石膏因身形巨大,客观上必须仰视外,对于那些不存在这种视觉客观性的对象,美院师生也常常选择高于其视平线的仰角去观察和描写。为此,他们常常故意坐得很低且保持不动,同时希望高处的模特儿也保持不动地坚持十来二十分钟,以确保观察和描写的稳定性。而且,不仅在室内教学如此,在室外教学同样也如此。同样如此的这一视觉行为,其关键所在即定点、仰视、长焦。由此,带给学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技术考量,即对透视学常识的理解和掌握。因为,不如此就不可能在画面中呈现这种仰角的视觉行为。这样,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注意透视比例,注意近大远小,即成为教师对学生不厌其烦、强调再三的基本要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50、60年代教学老照片全部出自《中央美术学院1918-2008》(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这本校史图集,而其中所刊同时期其它教学老照片,亦无一例外地不出以上分析,虽然本文不能就此断定当时的写生教学采用的视角只此一种,但却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这一视角训练在当时的写生教学中绝对是主流。毋庸置疑,在经过这种经年累月的练习后,受训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种视角下的造型透视思维逻辑并形成惯性,认为这样或者只有这样去观察和表现对象时才“好看”,至于为什么如此,绝大数受训者只是习惯使然,心中并不见得真正自觉和了然。本文在此姑且暂不解释为什么这样才“好看”的来龙去脉,因为这并不影响本文即刻所得出的如下判断,即肉眼观看对象的视角虽有三种,但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术学院教育中,通过老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仰视”——具体来说是仰视的焦点透视观看——被视为是认识对象的上选“工具”,也就是说,“仰视”在当时美术学院的教育中,不是一个普通的视角,而是一个让受训者学会观看和表现对象的工具性视角。受训者正是通过这一“工具”,逐渐进入如何“艺术地”观看和表现对象的门槛。
就此,来看看朱乃正当年在校就读期间完成的两幅比较重要的素描作业:
《维纳斯》,36×27.3cm,1955年,纸本炭笔。
《站立的北方农民》,74×53cm,1956年,纸本铅笔。
从中可见无论石膏还是人物,作业皆取仰视,造型与透视、明暗交界与空间关系的处理,都已达到当时比较突出的水平,显示出作者对仰视这一工具性视角的要求和特点非常熟谙。尤为重要的是,朱乃正由此起步,踏上一个由量变而质变的视角发展过程,其关键的一步即在60年代初的《金色的季节》里,比较早地实现了仰视视角由工具性向叙事性的转化,他也因此而一举成名。
《金色的季节》在视角选择上与朱乃正就读美院完成的作业一脉相承,但之所以说从这件作品开始实现了他仰视视角由工具向叙事的转变,主要不是强调他“怎么看”的方式,而是强调他善于用“这么看”的方式对对象进行置换与组织,从而使“这么看”富有了另外的情节与意义。如果我们将《维纳斯》雕像、《胜利女神》雕像、朱乃正绘《维纳斯》素描以及《金色的季节》并置一起,即会对这一解释有所了然。可以看到,朱乃正正是通过维纳斯雕像素描掌握了“怎么看”的视角,又在这种视角下将引导他掌握这种视角的维纳斯,置换为他“这么看”之后所愿意和希望看见的劳动人民的形象——扬青稞的藏族妇女,通过对双人物在仰视视角下的长焦、顶光的组织和塑造,逐渐形成他《金色的季节》的基本形象。显然,这样的视角塑造使普通劳动妇女产生了一种像希腊女神一样的伟岸与婀娜的风姿,成为统驭画面的巨人;同时也使得仰视工具视角下对象高大的视觉感受,自然而然地开始向仰视叙事视角下形象高拔的艺术风格转变;主题叙事与高拔风格由此在仰视视角中开始被建构和统一。由此可以说明的是,仰视在朱乃正艺术创作的第一步中,已不仅是一个工具视角,而是一个叙事视角,同时还是一个风格视角。
至此,我们可以暂时部分地回答仰视视角为什么被认为“好看”的些许原因。从一般的视觉经验来说,对象在仰视中会有一种平视和俯视中所没有的高大感,但这并不足以说明仰视的视觉经验就一定“好看”于——优越于——平视和俯视,因为,平视和俯视同样具有仰视所不能见的好看的视觉经验。因此,好看或者不好看的选择与认定显然不是由视角本身所决断的,而主要取决于视角之外的力量。如果将朱乃正的创作还原到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文艺创作的历史空间中,不难看到,干预这种选择的力量来自一套观念以及对其实践不断倡导的一整套文化行政行为,即党中央对艺术为人民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二为”方针的强调,并因之而建立一整套机制、动用一切工具对这一方针下的探索性创作实践给予切实鼓舞。那么,什么样的情感最适合也最能够满足这种“服务”的要求呢?是崇仰的那种讴歌!“歌颂”随之成为艺术工作者进行政治叙事的不二之选。歌颂领袖的英明、歌颂党的伟大、歌颂工农兵的翻身当家作主,歌颂新中国能够被歌颂的一切。在这样的“歌颂”基调里,仰视的视角特性与道德属意——仰之弥高——较之平视和俯视显然更符合这种政治叙事不二之选的表达,它因之而被认为“好看”并在艺术实践中被一而再、再二三地运用。在朱乃正的大学时代,他的老师们的创作——从罗工柳《地道战》(1951)到詹健俊《狼牙山五壮士》(1959)——所给与他的也正是这种逐渐成型的仰视歌颂的叙事范型的启发。可以这么说,正是这种力量决定了朱乃正从工具性视角向叙事性甚至是风格化的视角逐渐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相当程度上,这也可以被视为朱乃正为什么在创作中逐渐形成这样一种稳定的视角倾向的一种解释吧。
《金色的季节》之后,作为叙事视角的仰视在朱乃正创作于70年代的《出诊》、《春华秋实》中日益风格化,或者与其说仰视在这里是一种叙事视角,还不如说它是一种更为风格化的叙事视角——风格视角——要准确。《出诊》、《春华秋实》在仰视视角下对更多的人物与脚力进行的长焦捕捉、顶光造型、空间处理,较之《金色的季节》要驾轻就熟。比较难能可贵的是,朱乃正在这一风格视角中不遗余力地开拓政治叙事的多种表现可能性,尽可能地在风格形式方面与常规化表达拉开距离,体现出他对观念先行的风格程式努力自拔的探索。比如,很明显的是,“文革”期间创作的《出诊》在色调上的清新亮丽显然有别于当时泛滥的“红光亮”套路。进入新时期创作的《春华秋实》则不满足仰视视角下单一的聚焦观看,试图尝试用三联画格式开辟多窗口、多途径的观看和叙事。这也就是朱乃正的仰视视角虽然日益风格化但却没有僵化,而是继续有所发展和深入并能引人瞩目的原因。
1980年代初的《青海长云》和《国魂-屈原颂》,是朱乃正仰视视角风格化的重要里程碑。之所以这样说,当然主要不是指朱乃正在艺术技巧方面又达到一个新的高点,虽然随着画幅增大,大仰角、超长焦、大纵深的空间处理和形象处理给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要求,使他在艺术技巧方面又有新的发展,但相对更重要的是,随着“文艺春天”的到来,画家朱乃正作为知识分子的那种矗立天地、诘问苍穹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开始在久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鼓荡起来,并率先通过他特别擅长的风格视角在作品中呈现出来,在画坛上反映出来。我们看到,此时的画家已不再满足于已有的艺术叙事——艺术家在既定且越来越左的文艺方针限定内,绞尽脑汁地去挖掘和营造一个符合政策要求的歌颂性的情节瞬间——而是在既有的仰视的风格化视角上,尽力拆除庸俗化、教条化的条框束缚,任由壮怀激越的天问——一种富有其个人恢弘气度的精神觉醒——借升腾的长云、孤愤的屈原而抒发,托物言志地传达他作为被贬谪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持久的精神压抑后获得释放和希冀求索的思想心迹和心力,实现了他风格化视角中的叙事转换,说明确一些就是,由党国要求的“政治”叙事转向知识分子的“精神”叙事。也就是在这种转换和调整中,已经风格化的仰视视角因之而呈现出新的视角魅力,从而使朱乃正和他这一辈以仰为主的画家拉开不小的距离。
二、中西之间:从仰视到俯瞰
迄今为止,朱乃正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主题创作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对“仰视”的迷恋和建构,还未见诸于任何批评与研究提及。更重要的是,本文注意到,这种对“仰视”的迷恋和建构,并不仅仅表现在朱乃正等个别画家的创作中,而是表现在同一时代一大批画家的知名主题创作上。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建国后三十年主题创作发展史,基本上就是一部“仰视”美术史。其影响深远,直至2009年“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依旧不衰。因此,从这个视角所做的研究和讨论,其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朱乃正。由此,我们进一步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被用为“工具”与“风格”的视角的美术史源流在哪里?
在美术史上,仰视作为一种观看和认识客观对象的“工具”并且逐渐在教学中体制化,是欧洲文艺复兴中诞生的美术学院贡献于人类文明的一项视觉艺术成果。这一判断可从如下有关16-20世纪初欧洲学院与画室教学场景的一些图像资料中获得佐证。
N.多里尼根据17世纪意大利画家卡尔罗·马拉蒂的作品所作的版画《绘画学院》,大英博物馆藏。
M.F.Quadal1750年作油画,描绘维也纳美术学院的人体写生素描课。
C.N.CochintheYounger1763年作铜版画,描绘18世纪法国美术教学,图中人物分三组,左为素描临摹,中为石膏像素描写生,右为人体素描写生。
约1900年都灵美术学院写生教室。
巴黎私立朱利安美术学校雕塑工作室学员为站在可以转动的模特台上的女模特摆姿势。
在文艺复兴及其以后的二、三百年间,欧洲学院与画室对仰视的这种教学建构与完善和人文主义思想兴起密切相关。针对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束缚和宗教禁欲,新兴的人文主义者推崇人性反对神性,鼓吹人权蔑视神权,要求个性自由反对人身依附。具体影响和反映到艺术家这里,就是他们开始把世俗社会中的人当作神祗、英雄一般的偶像加以敬慕和研究,以体形健美的男子作为观察和描绘的范本,置其于中心高点,环坐其左右,以在科学助益下建立的解剖学与透视学知识辅助观看和表现,建立了一套视觉上以仰视为行为特点、以透视为理论依据的古典主义观察和表现方法。并且,久而久之,在这套方法成规之下,即使作为模特儿的男子体格不够英武、气魄不够豪迈,也要将其想象并描绘成符合这种人文需要和观看原则的美少年或圣斗士。然而,随着18、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对孕育和承载人文主义思想和古典主义文化的社会关系与制度的冲击和影响,这种也近乎于宗教崇拜的、学究式的对人的崇仰观看,首先在学院之外慢慢受到销蚀。尤其是在19世纪后半叶法国印象派画家那里,开始将女性从女神崇拜的神坛拉到凌乱的画室,拉到阳光草地、酒馆咖啡馆以及妓院中,由此所看见的就不再是裸体女神而是裸体女人,于是,画家与女模特儿之间便悄然建构起一种更为日常随意的姿势和观看视角,这些更为日常随意的姿势往往在平、俯视的视角之内即可获观,并不需要刻意仰望,但画家与对象之间成焦点透视的看与被看的关系却始终没有改变。这些,我们从以下的一些图像资料中可以捕捉到这种由由仰视到俯视、由崇仰到随意的视角与意义改变是如何在静悄悄的发生。
作者不详的《樱桃酒-1843》描绘了在凌乱的天窗画室里,面对斜卧床榻的女模特,画家和朋友即兴讨论攀谈的情景。
摄影师ManRay俯拍镜头下的法国女模特Kiki,约20世纪20年代。
印象派画家在室外草地上画女模特儿。
法国雕塑家罗丹平对着模特儿雕刻。
法国野兽派画家马蒂斯对着模特儿画速写。
欧洲美术学院之外的这种视角改变在20世纪30、40年代也或多或少地反馈和影响到学院自身,这在当年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所完成的油画人体中既有反映。有意思的是,欧洲美术学院内外在三百年间形成的这种视角衍变,在20世纪初被留学生整体移植到中国的专门美育建设中。若以如下私立上海美专——该校曾因模特儿事件而享誉民国画坛——遗存教学老照片为例,可以看到这所学校的写生视角既有欧洲古典主义的仰视视角,也有现代主义的平、俯视视角,多样并存,并行不悖,并未将其中一种定于一尊。
1918年龙华写生。
素描人体写生课堂。
油画人体写生课堂。
私立上海美专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多视角事实,代表了同期民国公私立美术学校引入西学的一般情况,显然这与1949年之后大陆美术学院以仰视为正宗的教学状况有很大的不同。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中国大陆美术学院写生视角集中于仰视,与本文在前面提及的文艺方针以及该方针下日趋严重的“左倾”认识、日趋矫情的偶像崇拜和工农兵表现有关。在讴歌和美化这一面,欧洲古典主义的仰视视角为歌颂现实主义提供了足可衔接的视觉资源和历史经验,更对应和满足歌颂现实主义讴歌领袖英明、人民伟大的实践需要,因而得以在美术教学和创作中不断发扬和光大,逐渐演化出“文革”特有的高大全的视觉表现模式,而印象主义及其之后的平、俯视视角——也可以说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视角——则在意识形态的高强度消毒处理中日趋边缘甚至灭绝。我们看到,遗存至今的50、60年代大陆美术学院的课堂写生作业里,已绝少见女裸体写生,更遑论横倒竖卧、四仰八叉、更为随意日常可被俯观的女裸体写生了。
言及诸多,无非是想说明一点,朱乃正上世纪50年代在中央美术学院接受的这种仰视视角训练,以及他在这一视角下于60-8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叙事实践和风格探索,从美术史而言,渊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推动发展的古典主义文脉,并且这种渊源联系离不开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艺先锋拥抱和学习西方、图谋民族文艺复兴的文化抱负,更离不开1949年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有的政治情境和文艺政策。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看,这实非画家独立的艺术探索使然。然而无论怎样,这种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且被新中国美术工作者高歌猛进予以弘扬发展的视角——以定点、仰视、长焦为视觉行为,以空间透视为理论解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方艺术视角。而随着这一结论的形成和给出,也就逼迫我们更深入地追问、反思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中国古有的艺术文脉中不存在这样一种视角与实践吗?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把西方科学以及以此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科学方法论作为解决中国社会各方面危机、以求救亡图存的知识学引进和实践成为主流,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以西方透视学理论赏鉴和套解中国艺术文脉的“经营位置”问题渐成美术界研究“中国画学”的主流,制造了诸如“散点透视”、“动点透视”等牵强附会的所谓“中国画透视理论”,以至于被各种美术教材视为科学常识而大加普及。然而,暂不说相对偏重笔墨的元明清绘画,仅就相对偏重丘壑的宋代绘画而言,西方透视学理论的解释其实也是文不对题。这是因为在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建立的透视学理论与11世纪在大宋王朝出现的“三远”、“以大观小”等经营位置认识,由于不同的哲学观基础——西方重视“我”对“物”的掌控驾驭(艺术中所谓“解剖透视”即是)、中国重视“我”与“物”的相知相生(丹青中所谓“饱游沃看”、“目识心记”即是),彼此之间很难做深刻地对等解释。例如:
范宽《溪山行旅图》
主峰呈现出的高拔耸立之势,并非仰视的长焦透视经验所能解释,因为画面主峰形象显然是偏于俯瞰的呈现,而主峰这种在俯瞰下的高拔视觉效果也并非什么“散点透视”能够解释,因为画面景观明显反映的是一种整一观照下对“脑之所知”的表达,而非分段观察下对“目之所见”的拼装。显然,在视角背后,中西方各有其不同的观与看的理解逻辑。有学者这样认为:
西方古典绘画以焦点透视为预设前提,以视网膜成像之“看”为根基,其“观点的观”是“片面的静止固定的结构”。“观点的观”有时而穷,受到诸多限制而不能进入主体创造自由的境界。中国古典绘画之“观”是是事物自然存在呈现的境界,没有预设前提,是“观的观点”。观是综合经验的直觉体验,是记忆、想象的创造,而不选择单一再现视网膜成像的路径。观的世界,是诗化的世界,是审美的世界,是超越有限生成无限的人的精神世界。故而能自由地展现一个包含一切的整体的动态的创造过程。
由此,我们不妨看一些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画作: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苏东坡《枯木竹石图》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董其昌《秋兴八景图》(之一)
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局部)
八大《河上花图卷》(局部)
这些经典画作的美术史联结所展现的“文人画”演进历程对于美术史研究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即自宋苏东坡倡士夫之画,经元赵孟頫、元四家以及董其昌、四王、四僧等明清诸家之理论跟进与笔墨实践,渐成在中国画坛占据绝对话语权的文人画之笔墨图式与精神。虽然宋元明清文人绘画的演进在笔墨图式与精神方面各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并非亘古不变,但若细读一过之后,则可以看到在这个演进过程中一直比较稳定地存在着一种“画之为画”的艺术理解和视角呈现,其奥秘早在11世纪即被沈括《梦溪笔谈》以“以大观小”一语道破,其谓:
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溪谷间事。又如屋舍,亦不应见其中庭及后巷中事。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境。似此如何成画?……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
由此而言,丹青水墨中的“经营位置”关系并非固定视点下对所见景物关系在画面中的成比例缩小,而是在饱游沃看的运动体会中形成的对景观整一性的观照和记忆,在画面上按照物与物、物与我的比例关系的展开和推移,正如“人观假山耳”,它要求或者希望,即能看到山峦叠嶂重重,又能看到溪谷茅屋簇簇;既能见街衢外熙攘之人流,又能见商铺内营生之人家,讲究的是对景观“全貌”——而非目之所见一隅——“折高折远”的把握和理解,在实际生活中,相对比较接近这种要求和希望能够窥其全貌的视角只有俯瞰。我们看到,上述经典画作在视角上莫不暗合于此。不过这里需要特别加以强调指出的是,丹青图画中呈现的这种俯瞰并非是有真实的高于视平线视点的目击经验的反映,而主要是在饱游沃看、目识心记的游观后对全貌做到心知肚明的直觉体验的反映,因为只有在这样“心眼”的俯瞰中,而不是在那种视平线之下的“视眼”的俯瞰中,才会再现(造就)山峰巍峨、重峦叠嶂的体验。这,正是它区别于实际生活中的“俯瞰”的独特之处。由此而言,丹青水墨中的“俯瞰”是中国作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理解性视角,是一个“画之为画”的中国古有的文化视角,并非纯粹生理学视网膜成像意义上的或者图谋平面再现视觉幻真意义上的视知觉视角。故而,以西学透视中焦点比例之方法,论丹青水墨中经营位置之文思,纯属牛头不对马嘴、斧木皆损的世纪谬误、百年扯淡。
朱乃正虽以专工油画在业界知名,但他也是同辈西画家中少有的称得上是书法家的擅书者。他少年即临池学书,以后入读中央美院乃至被远谪到条件艰苦的青海高原工作的二十年间,也始终没有中断对书法的研习。他的书法起步于颜真卿,后由宋四家入手,上溯晋唐、下逮明清,渐悟书道之要、运笔之理、点画使转之意。这一历练至关重要,是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自觉临习明清诸家绘画、悟通中国画学“经营位置”之要义不可或缺的前提和经验,也是他的艺术探索较之同辈不少画家更有品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对八大、恽格等明清花鸟画诸家作品的临摹,朱乃正开始由书至画揣摩和理解中国画学陶写性灵之妙谛,文人先贤“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形成的视觉心理图式——俯瞰造境视角——开始主导着他这一时期的水墨实践,进而也非常明显地影响到他这一时期对油画创作的思考。这一自修过程中出现的那种常被大家熟视无睹但却具有内在关联性的有趣变化,在以下图像资料中可以获观一二。
1974年朱乃正在青海写生留影。
1978年朱乃正临摹八大山人花鸟画。
朱乃正水墨画步骤图。
《大漠》,120×120cm,1982-83年,油画。
《长河》,120×120cm,1982-83年,油画。
从中,我们发现这种有趣的变化关乎具有内在联系性的“身体”和“视角”两方面。朱乃正的油画写生、创作和所有的油画家一样,其身体姿态主要表现为“举头面对”,而他在水墨创作时的身体姿态则基本表现为“埋头伏案”,这种身体行为的不同即中西之间观与看的差别所致。油画家作画时之所以要“举头面对”,主要是双眼既离不开画面又离不开实物(或参照物),这样适于二目在“画”和“物”之间头部移动的“面对”行为成为常态。而水墨家作画之所以“埋头伏案”,主要是目识心记的结果,因为物象已了然在胸,二目只关注“画”本身,无需旁视,故而有埋头作画之说。我们看到,朱乃正一“埋头作画”就和属于记忆系统而非知觉系统的中国画学俯瞰图式亲密起来,进而对他既有的仰视油画创作图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差不多与《青海长云》、《国魂-屈原颂》同时期,在他的艺术实践中同步出现了一种疏远仰视作风而偏于俯瞰把握的新探索,其中的先声即表现在《大漠》和《长河》这两幅油画风景画上面,这两件作品分别以俯瞰式的构图呈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境意象,反映出作者由“写境”走向“造境”的自觉意识和实践诉求。为此,他在完成《大漠》和《长河》后这样写到:
来自于欧洲传统的写实油画,其长处且不在此表述,而其基本规律是表现客体之真实时空形态。正因如此,西画中也颇多意境引人的杰作,但却仍然囿止于“写境”的范畴。而中国绘画艺术高妙之优异处,全在于艺术家吞吐自然造化之涵量,绝非以纯客体的如实描写为计衡。这就大大开拓了真正的主观创造的无边疆土,而任自驰骋。一获此识,我在油画创作实践上开始明确地以“造境”之说为本。面对一块空白画布时,力求摆脱对象写生之缚,绝不参用摄影照片、惟凭脑中的储存、胸中之块垒,以双眼为尺度,信手画去,东涂西抹,以期自家之境在画布上显现,创造一个自己的视觉世界。诚然,“境”由“心”造,更意味着“心”与“境”二字中包容的全部意义:“境”自“心”出,但非一蹴即可就,一触即可发的,而是主体与客体水乳交融为一体的长期修炼磨砺过程,若无客体现实存在之源,则主体无所依;而失去主体的自由能动,客体本身不能变成更不可代替艺术创造之完成。至于运用油画艺术语言如何“造境”,更非朝夕之易事。这是一个归依到我们自己母体文化根脉的问题,也将是需要我们许多人甚至几代有此共识之士,以充满自信之全部心力,去探讨并付诸实践的重大课题。
作为一个艺术实践家,朱乃正对于“境”与“心”的主客体理论解读其实并没有什么超越先贤之处,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若不结合朱乃正在上世纪80年代文化处境中的创作实践,实难显现清楚。在本文看来,上述解释之于朱乃正或者与之同辈或晚辈画家而言都太像“美学概论”的名词解释了,并未击中朱乃正经由个人实践所倡“因心造境”之于20世纪中国美术如何发展所进行的朴素反思。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初,朱乃正对“心”-“境”思考的价值不在于对主客体的理解,而在于对“因”什么“心”的觉悟,这才是他思考的意义所在,其中所涉及的正是西潮汹涌之际中国现代艺术前行应该依托怎样的文化态度、源流予以突破发展的问题,正是从这里我们才能了然朱乃正油画创作实践回归文化母体、求取自由表达的内在意义。显然,相对于热切拥抱西方现代艺术、希望走出文化封闭的新潮艺术青年的“离家出走”来说,同样希望解放的朱乃正选择的是“回家探亲”。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批油画画作所反映的正是他这方面实践的基本步履:
《归巢》,140×140cm,1986年,油画。
《临春》,100×100cm,1986年,油画。
《西部大风》,190×180cm,1993年,油画。
《雨雪松云》,200×200cm,1998年,油画。
《执薄·悟深》,80×80cm,2008年,油画。
《雪色》,55×55cm,2009年,油画。
《第一场雪》,50×60cm,2012年,油画。
由上可见,自上世纪80年代迄今,朱乃正的油画创作由过去以人物为主转而以风景为大宗,在意识形态对文艺创作的压制逐渐转向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底线的放开后,更易陶写性灵和便于对接发挥中国画学造境经验的油画风景创作,成为朱乃正油画艺术探索的主要载体,其基本特点表现为:1、俯瞰视角居多;2、弱光、纯色,形象单纯且人格化,象征性进一步增强;3、对于长焦纵深空间的兴趣远大于对短焦横阔空间的兴趣。显然,这些特点相对于朱乃正此前油画创作的视角图式而言有显著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呈现视角上仰视退隐、俯瞰上位,视角的这种升沉起伏显然和朱乃正这一时期着力于油画语言的“造境”、与中国画学“造境”观念和经验接驳有关。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朱乃正毕竟是在长于“写境”的油画语言的尺度范围内讨论和实践“造境”的可能性,毕竟不能纯然以中国画学的“造境”观念和经验画油画风景,因此,朱乃正也遭遇到所有试图寻觅中西融合之通途、使油画语言富有民族气度而又不失其语言价值本色的画家都必须面对的困局。
三、两难之下:造境的困局
自20世纪初以来,希望通过融合中西以求中国文艺复兴的策略选择,一直是百年中国美术思潮的主流之一,其间不乏各路精英先贤的摇旗呐喊的鼓吹倡导和筚路蓝缕的实践探索,自然也不乏不苟同此道的批评和警训。不过随着一百年来的融合摸索,试图在中西之间找到契合点的画家们越来越感到中西艺术各有其极则的规定,面临着难解的困局。这在朱乃正的油画造境探索中也有深刻的反映。
就本题来说,朱乃正因醉心于油画语言的“造境”探索,旁参中国画学游观-造境所积淀的俯瞰图式与经验,进而影响到他油画风景创作的视角选择与呈现也开始逐步偏移到俯瞰视角。不过,无论怎样,他油画风景中的俯瞰依旧难以摆脱西画焦点透视原则的束缚,这是因为,虽然他从理论上已经明白并且希望自己也能做到“面对一块空白画布时,力求摆脱对象写生之缚,绝不参用摄影照片、惟凭脑中的储存、胸中之块垒,以双眼为尺度,信手画去,东涂西抹,以期自家之境在画布上显现,创造一个自己的视觉世界”,但是由于他的油画风景写生是建立在空间透视关系中的对景写生,而非目识心记的整一性的文化观照和审美理解,因此他脑中所存储的其实是对特定空间关系中的自然物象的记忆,而不是先验图式在外师造化后中得心源的激活,这使得他在创作时无论是仰视还是俯瞰,其实始终无法改变的是那种西画固有的长焦纵深空间对画面、对他自己的主导,在这样相对保持着视网膜成像特征的空间里,无论作者做出怎样的疏浚,与中国画学“画之为画”的经验沟通,都无法更改其境之实的束缚,所谓“造境”之想其实只是对“实境”写生的加工改良而已。这是他油画“造境”探索源于西学本身所面临的一难。朱乃正对此似乎也有所直觉,在2008年之后的个别油画风景作品比如《执薄·悟深》中,可以看到他并不是十分自觉而是凭着一种直觉尝试性地嫁接和转换宋人大山堂堂的山水图式,试图能够脱离物象实体转而依凭图式经验而有所“造境”,但是一来他好像并未对此尝试抱有画一批的决心,这使得《执薄·悟深》在他后期的油画风景创作中显得有些形单影只;二来这样相对比较直白的嫁接先入为主的程式化图式,对于实践家造自家境、注自家思当然也有莫大的局限。这是他油画“造境”探索援引中国画学图式所面临的又一难。在此二难之下,朱乃正对油画“造境”的探索,距离他心中梦想要造的那个“境”当然并非一步之遥。然而,遗憾的是,上天没有再给朱乃正时间和机会去进行一次更富挑战性的困局突围——2013年7月25日,朱乃正因病去世——他只能走到这一步并在这一步上招引着后人。诚如朱乃正自己所言,“运用油画艺术语言如何‘造境’,更非朝夕之易事。这是一个归依到我们自己母体文化根脉的问题,也将是需要我们许多人甚至几代有此共识之士,以充满自信之全部心力,去探讨并付诸实践的重大课题。”
2013年8月14日初稿于养誉堂